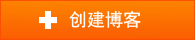目录:4.1 狭谷关战役;4.2 女娲向家人辞行; 4.3 瑶池圣火;4.4 自由恋爱;4.4-7 巫毒学院;4.5 武二郎病了;4.6 女娲为二郎神诊病;4.7 模拟升天仪式;4.8 宝莲灯 4.4 自由恋爱 本文是由女娲和尧皇(如图4.4-1)设计的,尧皇给二郎神(如图2)下蛊(如图3,4)的过程。尧皇也因为此次做法的成功而获得了 “自由恋爱” 的美誉。与本文类似的案例还有9.5.2 《阪泉之战》,描述了舜王给大禹(即黄帝)的下蛊过程。7.3 《相亲 》描述了刘健君给作者我的下蛊过程。 当武二郎(即二郎神,如图...
海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