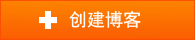目录: 4.6 女娲为武二郎诊病;4.7 模拟升天仪式;4.8 宝莲灯 4.6 女娲为武二郎诊病 目录: 1. 治疗诅咒的方法;2. 琢磨武二郎的天眼;3. 赠送宝莲灯;4. 寻找丢失的记忆;5 女娲的治疗措施 1. 治疗诅咒的方法 武二郎(如图4.6-39)到达夏国位于杭州的皇宫后,女娲(如图38)直接接见了他。她听了武二郎的讲述又看了跟踪观察报告后回答:“二哥!你是被巫毒女妖给诅咒了!我能够治疗你,让你痊愈!一般我们治疗诅咒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发现她是如何诅咒你的。如果发现了,对你进行有针对性地驱魔,那很快你就能痊愈。...
海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