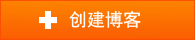1、《孙存周击倒王芗斋神话的破产》 ——兼答几个流氓文痞对我的碰瓷行为 近日,有关“孙存周先生击倒王芗斋”的旧闻再次见诸媒体。该文名为:《孙禄堂父子称雄武林,孙存周击倒王芗斋是否真有此事》。 网址可见:https://www.sohu.com/a/683727919_121709105 该文中详述了孙存周不仅身怀“不闻不见”之神功,更在多次比试中挫败各路名家,甚至包括意拳创始人王芗斋。 该文声称:“武术界最扑朔迷离的,也是最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孙存周击倒过王芗斋。孙存周和王芗斋年龄相差不...
海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