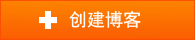《造假造神陳粉大師岳南微信現形被捉記》 京都静源教授、文學博士 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来,我在我个人的学术演讲录频道的第31讲、第89讲、第90讲、第91讲、第92讲、第94讲、第95讲、第96讲、第97讲、第107讲、第108讲,已经讲了十几次。今天的第146讲是再一次揭露陈寅恪和陈粉的造假造神运动。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陈寅恪研究学术专著和我的这些学术演讲在大陆读者群和知识界的传播。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寻找主公和塑造大神的基层信仰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人的DNA中。(我将其统称为找爹现象。社会的爹和精神的爹) 作...
海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