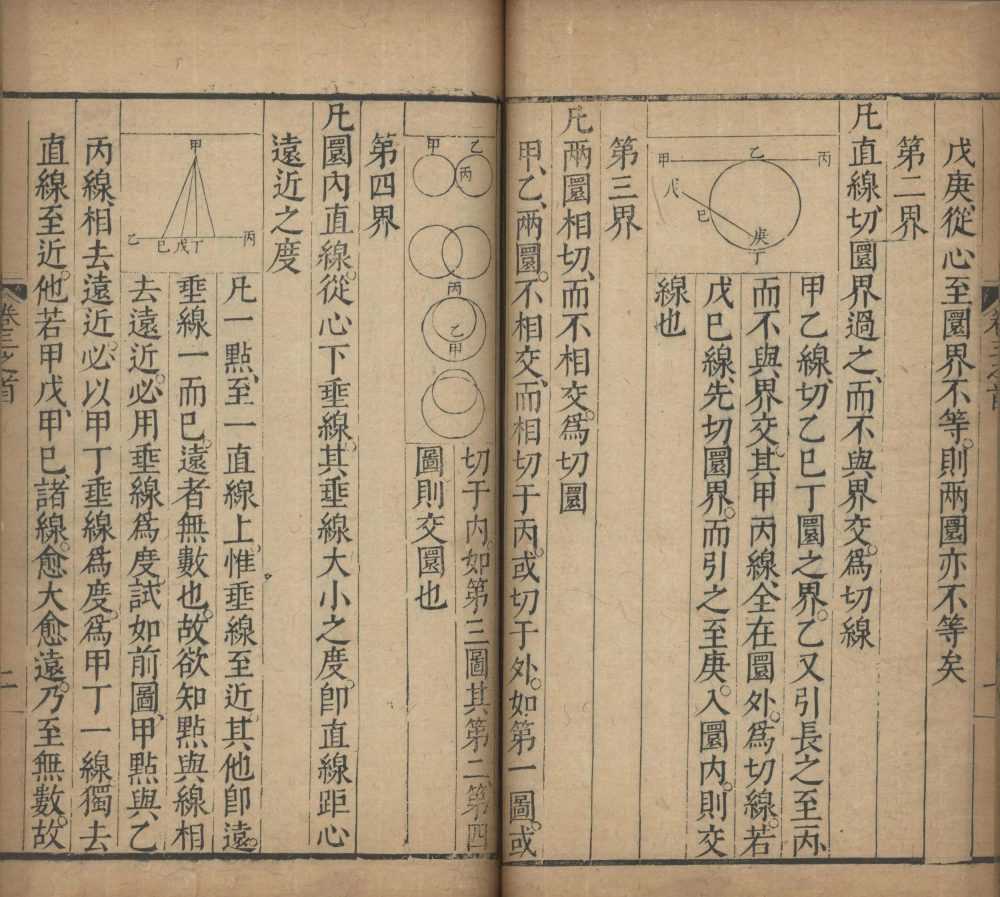俞频
无知亦无得

笔者近期发表了《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一文之后,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的热议,其中有不乏宝贵意见和观点实属难得和恳切。在诸多讨论中似乎对“封建”这个词认识不一,概念不统一就很难规范意见观点之异同。以下笔者以“封建”的词义和中国近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经过作进一步解释,作为《再议《唐宋变革论》及意义》一文的后记。
1927年国民党“清共”国共分裂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为确定现时中国革命性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意见,1928年蔡和森先生发表了“半资产阶级半封建社会”一说,陈独秀先生在1929年公开批评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陈先生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其实陈是回归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三民主义十六讲》中的“封建观”。这一争论有党内延伸到党外引发全社会学界的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主要课题是关于“封建”的理解,“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认定,多位曾经留学海外的青年社会学家参于了讨论,其中包括“新思潮派”,脱党的陈独秀的“动力派”,和国民党官方的“新生命派”,还有自称“第三种人”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
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情形复杂且与政治斗争和党派分歧密切连接,这里不扩展叙述。论战形成了两个大流派,以陶希圣先生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和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泛化封建论”。1929年5月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其中提出了“古典封建论”,即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秦朝已经解体。陶在《中国社会之史分析》中说,西周曾有过“分邦建国”制度,到秦统一六国后实施的是“废封建置郡县”。陶认为,秦汉以后中国已经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力量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士大夫阶级。秦以后至民国,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应当指出,陶先生提出的“封建”论未将限定在政治概念而力求兼从经济制度加以解说,他又无力完成对“封建”的经济义和政治义的整合。
“泛化封建论”的登场对后世社会影响巨深,这一派的学者都是以中共和共产国际为背景在上海有影响的《新思潮》杂志上笔战,他们援引的理论来自苏俄学界关于中世纪社会特征的概括,认为封建社会的普遍特性是,生产者主体已经摆脱奴隶身份而成为保有不同程度人身依附的独立生产者,其次经济方面是货币流通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土地所有者对独立生产者即农民实行经济剥削榨取剩余价值,这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雏形。郭沫若先生有“以农业为基础的是封建制,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奴隶制”论述,从而把“以农业为基础”的春秋至近代中国认定为封建社会,因为有上述关于“封建制度”的界定,使“封建”这一词被泛化,郭沫若先生五四后从事文艺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他期间以撰稿方式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他认同日本对译fendalism的新名“封建”,从指称欧洲中世纪和日本中世与近代的“封建社会”获得启示,将中国的古代时期至明清也冠以“封建社会”。郭在192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开始了关于古史性质及古史分期的探讨,郭氏的“封建社会”定义,既全然摆脱了“封建”本义即“分邦建国”,也同日本所相对西方学界对“封建”的“封土封臣”大相径庭,尤其是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等内容,本来恰恰是“非封建”的,却统统纳入“封建”,从语义学角度说,这种作法的过程,在不加论证情况下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扬弃,而根据所论时段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这种关键词内涵的异动使以后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产生深远的剧变。1945年郭发表了《十批判书》中又认为殷代奴隶社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史稿》提出影响深远的“战国封建说”,中国义务教育教科书至今还沿用这个观点。“战国封建说”确立了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封建经济和政治开始逐渐解体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所以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1949年前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今天厘清“封建”概念,进而为中国“封建社会”定位已是一项关乎中国史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
首先中国古汉语就有“封建”一词,《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汉代学者郑玄也有“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自王绾与李斯在秦廷展开“封建—郡县”孰优孰劣之辩,到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郡县论》,再至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竞相以“封建”比拟“地方自治”,古今论者探讨“封建”之短长,其价值判断可以划然有别,但对“封建”内涵的把握却是一致的,并未发生歧义,日本明治维新先于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学说,于是将本国江户末期到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看成是解除封建制的举措,可以断定作为西方史观为背景的日本历史诠释“封建”一词和中国自古的“封建”大致接近。
其次,郭沫若提出泛化的“封建”概念并不是其学术发明,它的鼻祖是俄国的列宁,他在 1912 年撰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该文在批评孙中山的民粹主义倾向时,把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列宁此说与他将俄国及亚洲中古历史与西欧中世纪相类比有关(而马克思是反对这种类比的),在此不细论。20 世纪 20 年代初,沿袭列宁泛化封建说的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当时中国。随后在上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左翼理论家遵从共产国际论说,此后,以斯大林观点为依据的《联共(布)简明历史教材》将“五种生产方式”单线递进说提升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将西欧历史的发展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普世规则,中国历史也无出其外。斯大林推崇的历史单线递进说是古典进化论的产物,它试图将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世界各地的多种社会形态,如亚细亚形态、斯拉夫形态、日耳曼形态、古典形态等塞进一种单线模式,这显然与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相悖,马克思在其所著《资本论》描述资本主义形成时说,“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注意五个“不同”。
“泛封建”说不仅扬弃了其本来的词义,更严重的是模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真实内容。如果对种种“泛封建”短语加以辨析,即可发现,这些熟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词汇,所含概念多存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基本症结在于:将“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为一谈。比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两词即互相矛盾: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怎能加上前置词“封建”?“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又如“封建帝王”:既然是中央集权的“帝王”,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建”?“封建”义为“封土。又如“封建皇权”与前例同类,存在将不相兼容的“封建”与“皇权”拼接在一起的问题。又如“封建官僚”亦然,既然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官僚”又怎能加上定语“封建”?在泛化封建观的长期濡染之下,国人早已对有关封建的短语习以为常,反复使用以致“封建”成了代人受过的、表明“落后”“不时髦”专用词,上世纪八十年前,国人还习惯用“封建糟粕”与“民主精华”对立起来看,殊不知“民主精华”相对的是“专制糟粕”。
总之,以“五种社会形态”递进序列表述中国历史正如天文学上曾经的“地心说”一样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考之中国古史实际,经历漫长的“氏族社会”之后,殷商、西周形成“宗法封建社会”的全盛,春秋战国成为“宗法封建社会”的解体。秦汉以降,中国长期延续的社会性质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官僚政治综合而成的“皇权宗族社会”。至于近代的划分点,笔者还是推荐朱维铮教授所提倡的“明代利玛窦来华传教”,开启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结点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详细叙述请参考笔者所著的《重修中国近代史之必要性和概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