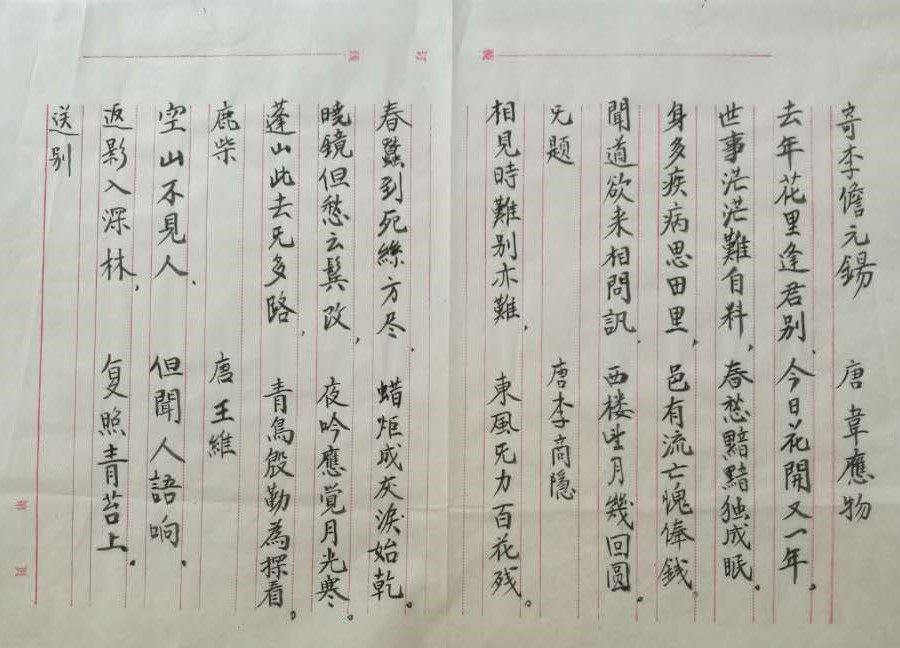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二)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的晚年
母亲的命运也在1979年被改变。根据当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18],政府给她摘掉了戴了21年的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革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全面的摘帽行动,实际上取消了建国后所划分的地主、富农阶级成份。连[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一)管制分子的生活(6),文革后期的母亲
母亲一人呆在成都,但时常给我们写信,定期寄钱,关心我们的生活,提醒我们注意身体。母亲还特别关注我们在农村的劳动,她的一封信甚至直接影响了我在农村的知青生涯。记得是在1970年的夏天,母亲来信说,同院子的彭姆姆(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当母亲被赶到天回镇农村时,施以援手,让[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管制分子的生活(5),文革前期的母亲
很快,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国大地,狂飙骤起,华夏震动,举国狂热。1966年6月,成都的中学就停課了,我当时正在成都五中读高中一年级。哥哥64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四川省财政学校,此时也停课闹革命。
成都街头最初很热闹,到处都在“破四旧”。所谓“四[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九)管制分子的生活(4),被驱赶回原籍
到1963年时,成都的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当时的领导者吸取前几年头脑发热带来的教训,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出现了集市贸易,农民重新有了自留地,农村开始实行生产队核算体制。邓子恢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12]。邓小平提[
阅读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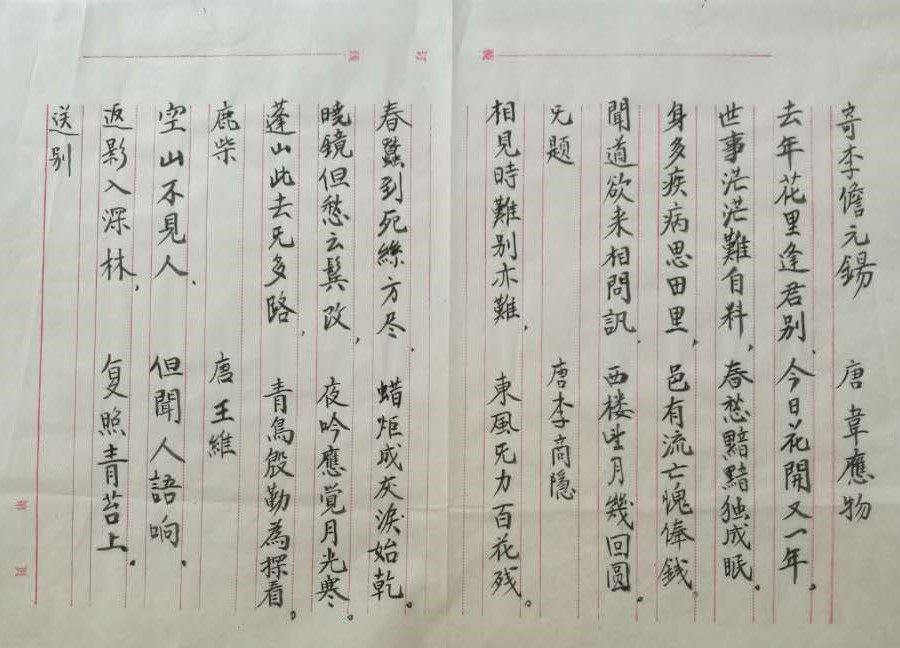
我的母亲孙清芸
(八)管制分子的生活(3),重回成都
母亲在1962年春天被允许回到成都原居住地,结束了她两年多的农村放逐生活。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成都市的决策者们决定对我母亲这样的五类分子开恩?是上面的指示?还是成都地区的额外雨露?也许,这和1962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有点关联。七千人大会开后在全国引发出了一系列的反[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七)饥饿年代中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
不久,到了1960年夏天,街道上也热火朝天办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中。街道上到处有震天的口号和夸张的壁画;有全街道的人上房吆喝,敲盆子摇竹竿消灭麻雀的壮举;有建起土炉子大炼钢铁的热火朝天;有形形色色的街道工厂的建立。
梓潼街属于当时的鼓楼人[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六)管制分子的生活(2),被驱赶到农村
1959年下半年,母亲病好了,可以正常劳动和做家务了,但不久后,成都市当局开始驱赶五类分子到农村,母亲也在驱赶之列。其中原委,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来厘清其来历,此处只能作一点推测。据“当代成都简史”载:“1958年冬,全市农业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10[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五)管制分子的生活(1),以泪洗面
过后的日子是母亲经常以泪洗面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时晚上醒来,看见母亲坐在我们的床头,含着眼泪看着我们,床头浸湿一片。我们问她,她不说话,只是含泪笑笑,给我们掖紧被子,叫我们好好睡。母亲后来说,她当时想死,但一看见我们三弟兄幼小的样子,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我放[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四)重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到了1958年,这一年是母亲一生之中除1951年外最难受的一年。先是母亲发现她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关节肿大,疼痛难忍。此病是人类疾病中至今搞得不很清楚的免疫系统疾病,发病后的母亲睡眠不稳,身体消瘦,肌肉无力,还浑身发红斑,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能沾冷水,洗衣服成了问题。当时,在梓潼街30号内废[
阅读全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三)最初的平和生活
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于灌县(现在叫都江堰市),那是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母亲的内心忧伤我还体会不到,但她的辛劳我却有深刻的记忆。时值1952年,父亲由于设计施工任务紧张,长驻白沙,不能回家,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去白沙看望父亲,顺便给父亲捎点衣物和食物。母亲抱着弟弟,而我和哥哥随母亲走路,由于年龄幼小,走[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