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我的博客复制一份至《海外博客》
由于数据量较大,请您耐心等待复制完成
复制

正文
沈乔生|朱大可印象
(2022-07-05 12:35:37)
下一个
朱大可是一个富有诗性和个性魅力的人。这是我最初的直觉,也是我读了他一系列文章后的结论。我们都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是七八级的,他是七九级。那是个可以彪炳历史的时代,像所有的狗都要叫一样,大家都在努力发声。在那些热闹的声浪中,我读到了大可的文字,记得他的文字是孤傲有力量的,有着鲜明的质感。离开学校后我们有些交往,不算多,却生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会在下面讲。
今天,我之所以写大可的印象,源于一个发现,他儿童、少年时生活的环境,竟然和我少年时活动的一个主要场合重合,这有意思!那地方在上海西区,是一个富有上海特色的高档区,西边是太原路,北边是永康路,被人称作“外国弄堂”。我一直以为那些房子是法式建筑,看了大可的文章,才知道它们是西班牙建筑。当我成年后回想上海时,那个地区就会像蒙太奇一样跳出来,外国弄堂住的人,是一些特别的上海人,其中不少是蜇伏不出的人,你能看见他们的面孔,但看不透面孔后面的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各自复杂的历史,不可能轻易读懂他们的内心。平时他们安静地生活着,他们的面孔隐藏在丁香树后的窗子里,在动乱中才被启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地区隐藏着大魔都所有的最深刻、复杂的魔幻因子。
而大可就是在这里生活、成长的。他是这样描述他的居住环境的:
“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总统黎雹洪的长子等等。我家是个例外。”“到了文哥后期,那楼住进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我家离朱大可住的外国弄堂有两条马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我一直在这里玩耍,一放学就跑来,我有几个同学就住外国弄堂里,我们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撑背跳、打弹子,抽贱骨头、刮香烟牌子,玩到天黑也不愿意回家。我对这里的有磨灭不了的印象,宽敞如梦的弄堂、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混杂着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焕发出一种经久不息的阴柔的美。
我想,这个环境给朱大可打上的烙印必定是深邃、混合的。虽然我和他的人生轨迹有很大的不同,却感到一种神秘的精神契合。为了弄清大可后来的思想裂变,我们必须从最初开始,先看他和一个女孩的故事吧: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读这段文字,谁的心弦能够不被拨动?这是一段摇人心旌的描述,在有限的文字内把两个孩子的交往写得悱恻动人,充满诗性的迷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检点孩提往事,大概都会有类似的发现,小男孩小女孩,老大可!老俞头!她像妹妹一样亲我,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香气,不可避免地想起结婚。这种儿童的梦境喜悦,甚至是人类最高幸福之一。然而,它夭折得那么突然,大可还没有来得及把借她的书还给她,她就从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他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大可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
悲婉色彩蒙上大可的童年,编写了他的性格密码,日后真正的力量就从这里开始。
他和“外国弄堂”的人曾经一起经受苦难和磨砺,关于邻居、关于空房子和游戏,关于看书,和好友在上海马路上近似于梦游的游荡,都有不俗的描写,这里我不一一细述了。
在那最后的时光里,我几乎每天都跟父亲在一起,我躺在他身边,陪他说话,跟他肌肤相触,希望时间能静止这个时刻。我们谈论文学、历史和音乐。他一直勉励我好好写作。假如你想当一个作家,那你就要变得更加勤奋。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在广州的岁月,以及他跟母亲相识的日子。后来我才懂得,他在向我拷贝他的记忆,以便在他辞世之后,这些记忆能被子代传承下去。
读到我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颤抖起来,这是一段温馨、有深度的文字,又是一幅多么绚烂、迷人的图画。我注意到“肌肤相触”四个字,大可的父亲是幸运的,任何一位父亲,如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他的独生儿子终日相伴,和他“肌肤相触”,都是幸福的,这种父子感情能够疗伤,能够医治不公世界带给他的任何创伤!同时,我们的大可先生也是幸福的,这时候,父亲的病榻就是课堂,他们在仅剩的时间里讨论文学、历史和音乐,这时上苍怜悯的眼光也落到这对父子身上,他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恬静的好氛围的课堂。在娓娓细语之中,儿子获得的不仅是知识,他不仅了解到父亲坎坷的人生,了解到他和母亲的相识,至关重要的,是在交谈中折射出一种人性光芒,就像春天里幼苗破土而出一样,纯粹、纤弱的人性就在这时颤巍巍滋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以为,这是富有意义的传承,大可后来思想的裂变、诗性的抒发一定和这病榻上的讨论有关,这里是出发点!同时,这幅图画又是高度浓缩的,它是大可从少年到青年的概括,读懂这图画,你就读懂了他的生命历程。
父亲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啊,多么热烈的观察,一个父亲给儿子这样的评价,是十分难得的,很可能父亲通过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必须给儿子最大最热烈的鼓励!我相信,这将给年轻的大可增添无比的自信。
我以为,自信是成功的一大要素。由此,往后的思想裂变和才华爆发,变得不可遏止。在我看来,这里蕴藏着朱大可之所以成长为朱大可的全部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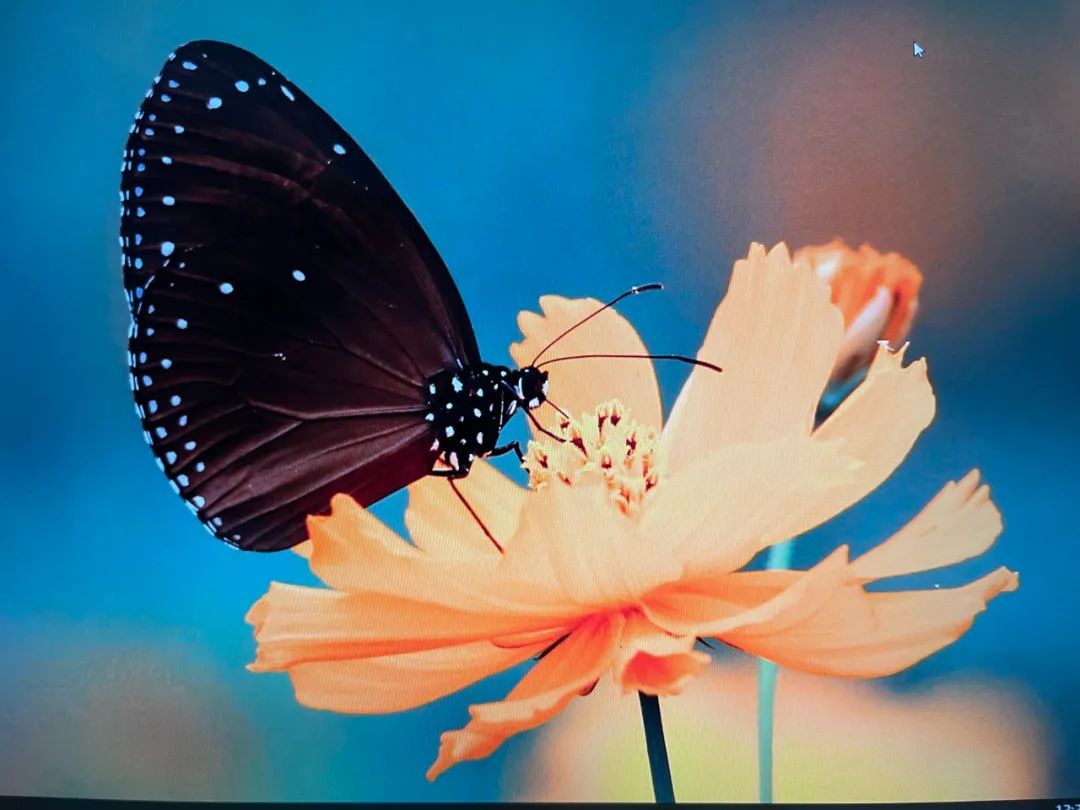
大可的主要理论著作是《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他做学问,充满了奇思妙想,与大学里的大多数人做学问不同,他把学问做得像诗一样。他打破了学问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建立自己的构架,在他的园地中,诗和学问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下面那段话,浓缩地表达了他对“人民”这名词的见解:
人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正是它构成了潮流的主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温顺可爱的绵羊,但却在某些非常时期突然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转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气。这种反叛激情是与参与者的人数成正比的。人民在这个限度内改造着历史,企图把它引向世界正义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人类记忆中最明亮的书页。
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他们写作是一只眼睛瞄着殿堂,瞄着晋升的仕途,想着在官方文学史上留名,想着多得俸禄,这些是他们的动力,也果然取得了成功。这样的作家我们没有少见。而另有少数作家,他们所有的追求和努力,不在上所之希冀,而是为了思想本身的价值,为了文学本身的纯粹。他们活跃在民间,潜伏在民间,也矢志在民间,朱大可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我以为,大可文章就可贵在有思想主导,表述独特的见地。如果没有思想主导,任你什么样的才华,都无法写出那般文字,而惟有犀利、独特的思想,又辅之以朝霞般的才气,才可能写出大可的绚烂文章!
这种时间算术几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的遗产感到恐惧。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毁灭之上。正是这种“项羽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建筑的彻底覆没。在某种意义上,被拆毁就是中国建筑的命运。而我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种叙事逻辑的统治。
我觉得,除了思想之外,大可的行文有一种特殊的句式,字与字、词与词的搭配有他自己的特点,很容易辨出,这是文字老到的体现。可以举书法的例子,你拿一些古帖给我看,蒙上作者的名字,我一眼就能认出,是王羲之、颜真卿、怀素、黄山谷、米芾写的,还是欧阳询、柳公权、张旭、王铎、傅山、董其昌写的。我相信许多熟稔书法的人都能做到。说实话,我觉得大可的文字组合有独具匠心的创造,很好辨认,不会混淆于他人。请看下面对上海外滩独特的“情欲”描写:
我已经说过,上海的旧式情欲带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滩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它的在情欲地理学上的显著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和黄浦江的亲昵关系。文革时期,它的长达一公里的丑陋的水泥栏杆边,曾经站满了上千队喃喃对语的情侣。他们彼此摩肩擦踵,犹如一个漫长的爱情链索,整齐地排列在发臭的黄浦江水岸,从外滩公园一直延伸到气象信号台。
1968年,民兵组织“文攻武卫”经常在上海外滩围剿谈情说爱者。他们成批地逮捕恋人们,用卡车带往革命委员会总部。执法者挥动军用皮带对他们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待“黄色下流”的“罪行”。情侣们的惨叫和外滩的东方红钟声遥相呼应,俨然是对后者的一种神经性回声。
大可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大概属于大气晚成。就是说,他在思想裂变和艺术爆发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成长期,这与我心有戚戚焉。这怎么说呢?实话讲,我从1969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以来,到我退休时为止,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总觉得写写而已,不足为训。然而,等我到了64岁,突然醒悟,仿佛一觉醒来,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主要是思想价值),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定了一个十年的写作计划,内容庞杂,现在已完成大半。虽然其中小说的发表不尽如人意,但文字是留下了。我敢肯定,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还在干应该年轻人干的事情,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景象吧。
《东观汉记·明德马皇后》中说:“穰岁之后,惟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而大可和我都不安静,无法悠闲地含饴弄孙。虽然我也在享天伦之乐,但我们都有孽债在身,都被命运和性格中的某些因子鞭策。我想,大可和他父亲肌肤相触时的真挚交流,和那个叫“老俞头”的女孩儿的梦幻往事,都是因子,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们还要折腾一阵子!
大概是1992年,我们是在大可的陕西路上的家见面的。他父亲过世后,母亲为了离开使她无比伤心的旧居,费了很大功夫,换了房子。关于这个新家,他有一段文字,我摘录于下:
一座独立的三层洋房,殖民地新古典主义风格,拥有罗马式的外立柱和旋转式楼梯。新家位于二楼东侧,主体为一个大间,约22平米,加上8平米的朝南室内阳台,一个储藏室改的5平米饭厅,一个4平米卫生间,总共39平方米,房租25元,比原先的还贵了一块钱。但母亲必须为此支付高昂的租金,她的退休金仅有70元,在付掉25元之后,只剩下45元。
清清楚楚,一笔不苟。我很少这么做,我的老家主卧多少平方,客厅多少平方,我住的房间多少平方,我从来不甚清楚,也没有记下来,记的是大概数。这反映了大可的一部分性格。
我记得这新房,内墙很高,很气派,在上海属于好房子。就在这房子里,他把新书送给我,我把近期发表的七八个中篇小说交给他。那次见面挺简单。二个月后,他寄来文章,是对我中篇小说的评论。那时没用电脑,是纸质的。我带着欣喜的心情,急迫地读完,一时心情十分复杂,怎么说呢?他的不少见解都很独特,发人之所未发,但是,也尖锐,尤其是说到我的几篇小说中都有一个情结:乱伦;虽然有时并没有确定的行为描写,但这种乱伦更多是潜意识,在字里行间弥漫。我不免有些尴尬,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别的批评家也没有这么说过。那么,我的创作潜意识中,是不是有乱伦意识呢?我无法回答。
我沉默了几天,想过来了,我的小说发表出来,就是交给批评家和读者了,怎么解读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解读,必定带着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我手中的稿子就是大可的解读,是他带创造性的解读,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写信对大可表示感谢,随即把稿子寄给一家评论杂志社的一个编辑。
那是经济大潮起来的年代,社会在急速地转型,那个编辑粗粗地看了,觉得不适合他们刊物,他自己也在匆匆转型。他说寄还我了,可我始终没有收到,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在写我小说的众多评论中,这是唯一一篇没有付梓的文章。
岁月荏苒,一直到2019年,忽然收到大可的微信,传的是照片,拍的是八张格子纸,用蓝水钢笔写的字,字体峻峭洒脱,我眼前一亮,哦,原来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底稿。大可说,他收拾陈年杂物,居然发现这个了!就拍照给我。我猛然醒悟,就像树上悬挂着青苹果一样,他心里还一直悬挂着此事呢。我又读了多遍,尘封多年,此刻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恍然意识到,大可说的情结其实存在,当时就他说破了。
我把底稿打成电子稿,交给南京大学的教授丁帆先生,丁先生成人之美,在他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

朱大可,文化学者、文化批评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专著《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文集《燃烧的迷津》《孤独的大多数》,小说《古事记》《六异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