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王妃第二天就跟随多尔衮离开了扬州,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回到扬州。多尔衮视察南方结束后,王妃和多尔衮一起回到了京城,住在京城皇宫旁边的一座王府里。
知府自从知道王妃喜欢吃小饼屋的点心后,第二年到京城觐见朝廷时,特意从小饼屋买了一大盒烤好的点心带去。知府亲自把点心盒送到王府,自己在门房等着,想看看王妃有什么吩咐没有。知府在门房坐了没多久,里面的侍卫就传出话来,让知府去里面的大殿觐见王妃。
知府进到大殿里去,看见王妃坐在大殿中央的硬木椅子上,就赶紧跪下来给王妃磕了一个头请安。王妃微笑着给知府赐座,要知府讲讲扬州城的情况给她听。聊一会儿天之后,王妃询问起小饼屋的近况。知府欠身说,托王妃的福,那个瞎子的小饼屋越开越好了,客人越来越多,在扬州城越来越有名了。王妃听知府这么说就笑了,笑得很开心。王妃让侍女把知府带来的点心盒打开,当着知府的面,拿出一块小点心咬了一口,赞着说好吃,要知府再多讲讲小饼屋的故事。知府见王妃很关心小饼屋,就搜肠刮肚地把自己知道的小饼屋的情况都给王妃讲述一遍,又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下在他的亲自关照下,那个瞎子的小饼屋的生意怎样怎样地好。王妃听得很聚精会神。知府讲完之后,王妃问知府说,他有没有娶个扬州的姑娘。知府摇头叹息说,那个瞎子,就是一根筋。知府说,瞎子是一个很怪的人,自从小饼屋生意好了,瞎子赚了不少钱之后,上门来提亲的不少,知府太太还曾给他介绍过一个远房的亲戚,但都被那个瞎子婉言拒绝了。知府说,看样子瞎子是铁了心要一辈子自己单身了。王妃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在知府临走的时候,王妃厚厚的赏赐了知府,嘱咐知府,要知府在扬州帮他找个好女人。王妃还让知府以后到了京城就来聊聊。知府正巴不得有个机会巴结多尔衮这样的王公贵族,连声答应着高高兴兴地走了,心里盘算着以后每次进京时,都要带几盒点心来给王妃。
知府走了之后,王妃屏退了侍女,自己一个人在大殿里坐着,从点心盒里拿出点心来,慢慢地在嘴里咀嚼着,品尝着。王妃的眼光迷茫着,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王妃知道,她不能再回扬州。王妃知道,她跟他走不到一起。只要她在他心里,他永远也不会幸福起来。她能给他的最大帮助,就是让他见不到她,好让他放弃自己,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只是王妃不知道,两年之后的一天傍晚,她也会是这样,打开知府供奉给她的点心盒,从里面挑出一块她最喜欢吃的,放在嘴里咬着。只是那一次,她会觉出味道的不同。那一次,她会把点心又咬一口,仔细在嘴里品尝一下。她会觉出,还是味道不对,跟过去吃到的不同。难道他改了配方了吗?她会心里产生一种纳闷。她会把知府叫过来仔细询问,她会从知府的口里听说,点心是店里的伙计做的,不是他做的。她会问知府,他怎么了,为什么不自己亲手做了?知府会告诉王妃,他得了一场重病,被庸医误诊,开错了药,吃了药之后没多久就咽气了。知府会说,他临死之前在昏迷弥留之际,失去了知觉,什么都听不见了,什么都不会说了,谁跟他说话他也不答应,连他的女儿叫他,他都听不见了。他只能张着嘴像鱼一样的倒气,但是他的嘴里一直叫着一个人的名字。知府会告诉她,谁也不知道他叫的是谁,谁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连他的女儿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整个扬州城里都没有一个人叫这么名字。
她不知道,两年之后的那个傍晚,她会把嘴里含着的点心哇的一口吐在地上。侍女们会匆忙地跑过来扶住她,她会大口大口的吐着,吐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只有她知道,他叫得是她的小名。她知道在陪着母亲住院的时候,母亲一直叫她的小名。他是从医院里知道她的小名的。他临死前惦记的是他,千百遍呼唤的是她的小名。那时她会后悔穿越,后悔把他带到这个乱世来,后悔她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没有像她答应的那样去做小饼屋的老板娘。她会觉得自己害了一个人,她会觉得这个人无怨无悔的陪着她,离开了北京,跟她去了小城,跟她在一个单位里,跟她一起去穿越去寻找她爱的人。经历了战火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至死都没有忘记她,都在惦念她,都在小饼屋里等着他,都在心里呼唤着她。她会觉得是自己的错,让他死在了扬州城,让他孤独无助,让他就像是一叶枯黄的树叶突然一夜之间被风刮落,她即使泪如雨下的悔恨也无法补救自己的过失了。她会终于知道,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走了,走得这样匆忙,都没能来得及跟她告别一下。她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离开人世,他过去一直在她身边陪着她,她以为他会一直陪着她老去,在她死后才会死去。
她不知道,两年之后的那个夜晚会是她生命里最黑暗的夜晚。那天晚上,大殿里的朱红蜡烛会映照着王妃的美丽的脸庞,她的眼里会滴下泪来,就像是一滴滴的烛泪,凝固在面前的碟子里,打湿了碟子里的咬了一口的小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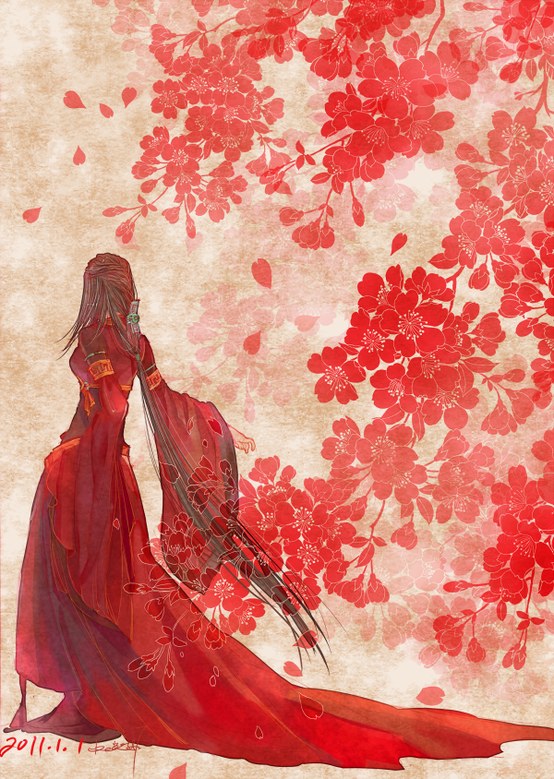
王妃离开扬州城之后的那个秋天,是个潮湿的秋天。雨水好像不想停一样地隔三差五地下着,落叶也比往年落得早,小饼屋前的水杉树和泡桐的叶子早早的就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扎进稀疏的星空里。屋角的被雨水侵泡的落叶过早地失去了颜色,和黑色的泥土混在了一起,小饼屋前的黄土官道变成了一条不堪车轮重负的泥泞不堪的坑洼之路。他过去一直喜欢南方的湿雨天,觉得那样很有湿意。只有在绵绵细雨带来的潮湿和黑暗渗透了他的全身之后,他才开始想念北京的秋天,那种天高云淡的晴朗的秋天。过去总是想离开的北京,如今却遥远得再也回不去了。
他依然在小饼屋,带着有些残疾的女儿做蛋糕和小点心。就像知府说的那样,自从王妃来过之后,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说他的点心和蛋糕做得好。扬州城里的官宦人家,有生日和喜庆日子时,都来找他订制蛋糕和点心。他的饼屋的生意越来越忙,越来越好了。赚了一些钱后,他把小饼屋请人翻修了,翻修后的小饼屋比以前大了很多,也装饰得好多了。他自己忙不过来,就雇了几个伙计。
他每天忙碌着,几乎没有时间想什么。他每天疲劳不堪,觉得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好像有什么大病在潜伏着,等待着有一天发作。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着四周笼罩的灰暗,他依然会想起她来,想起来过小饼屋一次的她。他想起她来的时候,眼前的黑暗就逐渐消失了,一片柔和的光会笼罩住房间。他不怪她离去,他不怪她没有再来,他知道她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她不可能来小饼屋做老板娘。但是他没有后悔穿越,没有后悔跟着她到这个乱世来,没有怪她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没有怪她没有像当初说好的那样,找不到千年之前的爱人就来小饼屋做老板娘。他一直无怨无悔的陪着她,等着她。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么多年,在扬州城等她等到眼睛都瞎了之后,他还是终于见到了她,跟她在小饼屋重逢了。而且,他还去亲手给她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一个最精美的翻糖蛋糕。虽然蛋糕还是有些泻脚,但是他相信她一定会喜欢这个蛋糕的。
有时在半夜里醒来,他会想起在北京的家,想起大学时回到家里就有很多好吃的饭菜热在桌上等着他;想起那些什么都不用管,只要好好念书的日子;想起母亲,想起家里的亲人。有时他会想起雨夜里离开北京的那辆火车,想起火车响着尖利的汽笛声在瓢泼大雨里穿过原野和城镇,想起火车钻进黑漆漆的隧道又穿出来,想起餐桌上的带着油腻的白桌布,想起他躺在铺上夜不能眠,想起她躺在对面的铺上,身体在睡梦里匀称地呼吸着,想起火车靠站时积着雨水的月台。回忆过去让他很伤感,特别是那些美好的过去。他尽力不去想北京,不去想过去。回想过去,只能让他感到更加难受,让他感到她和他之间的迈不过去的鸿沟在不断扩大。他早已经不抱幻想了,不再幻想有一天她会来做小饼屋的老板娘,但是他依然在爱着她。他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她在离开小饼屋时,看了他最后一眼,放下了轿帘。他不知道,她在放下轿帘的一刹那,脸上会不会挂着泪珠。没有道别的道别,没有分手的分手,轿子从视野里离去的那几分钟,对他来说,却是非常的漫长和艰难。他看着远去的轿子,心情沉重,知道她可能再也不会来了。没有了她,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但是他还得继续活下去,还得继续繁忙下去,因为他需要把女儿养大,让女儿有个幸福的生活。
他想,他的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了。没有她的日子里,他只能以后好好开小饼屋,照顾好女儿,将来给女儿找个好婆家。只要女儿能够过个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也就知足了。过去的一切,他都不再想了。
他以为自己也就这样了,会在小饼屋里忙碌终生,有一天悄无声息的离开人世。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的小饼屋的后院里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让他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是刚过了春节不久的一个夜晚。那年春节,扬州城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扬州城的冬天,很少下雪,即使有雪,也大多是零散的雪花在空中飘,落到地上就融化成雪水。只有那一年,一连好几天都是阴云密布,云层在空中越积越厚,厚得像是要压下来。天空低得很压抑,像是抬头就会撞上一样。乌鸦在低空飞行,拍打着翅膀从人们的头上掠过,像是尖利的爪子随时会把人们头上戴的帽子抢走。人们都有些害怕,特别是看到乌鸦的黑色的眼睛从眼前闪过,乌鸦的羽毛像是黑色的火焰一样在空中飘落。小饼屋里的客人们纷纷议论着,天气很怪异反常,像是一种朝代更换的不祥之兆。雪终于在一天早上开始落下来,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雪片大得像是泡桐的叶子,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山色在雪中迷蒙,空气在雪中凝固,喧嚣的人声和车马声在雪中沉寂。大雪一直下了七天七夜之后,又下了一场冰雨。冰雨把扬州城凝结成一座雪白的宫殿。冰雨终于停了的时候,扬州城的城墙上,寺庙顶上的琉璃瓦和飞檐上,水杉树和泡桐的褐色树枝上,以及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被玲珑剔透的冰覆盖住,变成一片白皑皑的冰雪世界,连一直被秋雨淋得泥泞的官道,也变成了一条一望无际的笔直晶莹的溜冰道。
那天晚上,他在睡梦之中被一阵晃动和响动惊醒,觉得房屋像是地震了一样在颤抖,随后听见后院发出了一阵轰隆的响声。他爬起来披上衣服,看见睡在另一房间里的女儿也被惊醒了,正在惊慌地迈出房门查看。他拿起了靠在门口的一个木棍,让女儿到小饼屋前门去打开插销,如果是坏人来抢劫,就赶紧从前门跑出去叫人。他提着棍子走到与后院相接的后门去听,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踩着冰雪走动,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向着小饼屋走来。随后,他听见有人在拍打着后门,向里面急促地喊着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虽然他也记不起来了,到底是在哪里听见过这个声音。不管怎样,他觉得是一个友好的熟悉的声音。他打开了后门。他看不见外面的人,但是在灰与黑的色彩之中,他看见有一束明亮的光柱在面前闪耀,就像是手电筒的光。
终于找到你了,那个人张口说。我是工程师啊,当初帮着你们穿越的,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这次终于找对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真是那个曾经帮着她和他穿越的工程师自己穿越过来找他们来了吗?
我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他放下手里的木棍说。但是能听出你的声音。请屋里坐吧。
他把女儿叫来,让女儿去把小饼屋的蜡烛点上,再给客人泡一杯热茶。女儿把蜡烛找出来点上,随后很听话地去烧热水了。他引着工程师来到小饼屋,请工程师坐在椅子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他好奇地问工程师说。为什么要来找我?
说来话长,工程师搓着手说。都怪我当初把时间计算错了,本来应该把你们送入宋朝,没想到把你们送入了明末清初的时代。自那之后一直觉得很内疚,但是那时时光机器还没有完善,只能单向穿越,不能回来,所以想来找你们也不敢,怕自己回不去了。直到最近,我才在时光机上有了突破,可以双向穿越,既能回到过去,也能穿越到未来,才敢来找你们。知道你眼睛瞎了,我就觉得更难受了,因为要不是我把你们送错了年代,你可能就不会这样悲惨了。所以才几次回来找你,想把你找到。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呢?
在你和她一起穿越之前,听见你们说,要是穿越丢了,就到扬州城的小饼屋见面。我穿越来了几次,不是来早了几年小饼屋还没有建造,就是穿越晚了几年,你已经不在了。
我不在了?他疑惑地问。几年后我就不在了?
你两年之后就死了。我是从你店里的伙计的嘴里得知的。两年之后的秋天,你得了一场重病,没能治好,就离开人世了。他们说你去世之前一直在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谁?
你该知道是谁,工程师说。就是跟你一起穿越的那个女孩的小名。
她?
她。
她后来怎么样了?他有些焦虑地问工程师说。你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工程师点头说。你女儿告诉我的。显然你在临去世前把王妃的故事告诉了女儿,你女儿把故事讲给我听,我就去了京城,在多尔衮的王府里找到了她。她认出了我,她说她知道了你去世的消息。她说是知府告诉她的。她说她从来没有想到你会离开。她说她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快就离开。她说她没能去参加你的葬礼,她说她来不及,也无法去。
你有没有问她想不想回去,回到现代社会里去?
我问过她,想不想穿越回去,工程师用手擦了一下眼镜说。我知道你一直爱她,我看得出来,在你们最早穿越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你是陪她穿越去的。说心里话,我想把她带回去,再来把你带回去,让你们重新回到现代社会去,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也许经过这些年的经历,她会改变一些,会跟你在一起也未可知呢。
她怎么说?他一把抓住工程师的胳膊问。她想不想回去?
她不想回去,工程师叹息了一声说。她不想回去。她说已经习惯了做王妃,过这种人上人的日子。她说,她有三个孩子,为了孩子,她也不能回去。她不愿意让孩子们放弃王子和公主的地位,回去做一个普通百姓。她说,可惜你已经死了,不然让我把你找到,把你带回去就好了。
女儿端着刚沏好的茶走了过来,给工程师端上一杯冒着香气的清茶后,自己站在柜台边上等着。工程师打量着女儿,看着女儿走路一瘸一拐的腿,问他说:
腿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吗?
可能是,他说。现在医院有办法能治吗?
有矫形手术,工程师说。到底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也许经过矫形手术后看不出来,也许两条腿还会有些粗细不同,走路有些不稳当,但是应该比这个样子好多了。
你们在讲什么啊?女儿打断他们的话说,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工程师喝了一口茶,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既然两年之后你就会死去,再也见不到她了,而她不愿回去。那么,你想带着女儿离开这里,跟我回去呢,还是想继续在这里?如果你跟我回去,你就不会死在这里了,你还可以在现代社会过一个好日子。
等我问问女儿,他看了女儿一眼说。
他把女儿叫过来,问女儿想不想去一个未来世界。他告诉女儿说,他就是从那里来的。他说,那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虽然还不是很完美的世界,但是已经很完美了。他说,那里有很好的医院,有很先进的医疗技术,也许能把女儿的腿给治好,让女儿有个健康的身体。他说,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带着女儿一起到那个未来世界去。他说,如果女儿愿意,就一起去。如果女儿不愿意,就一起在这里。他说,女儿要是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随便问。
女儿只问了一个问题:爹,那里能治眼睛吗?
他们在阴郁的雪夜里走出小饼屋,来到后院里。空气很凉爽潮湿,雪地里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也没有响动,只听见脚踩在厚厚的冰雪上的咯吱声。工程师打着手电在前面引路,手电形成的光柱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女儿走在他的身边,有些恐惧地拽着他的胳膊。他的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一直没有尽头的灰色。他知道,那是雪落在后院和四周形成的灰色。女儿跟他说着话,好像怕他一下就失踪了一样地说着话。工程师走到小巧的时光机前,让他们坐上去。女儿有些害怕,站在时光机前不敢上,问坐上去会不会掉下来。工程师说不会,只是会有些头晕想吐。他让女儿回屋,去拿花瓶来。他说如果晕了想吐的话好吐在花瓶里,免得吐在时光机上。女儿很快就抱着三个花瓶来了,说三个人一人一个。他们抱着花瓶,坐在冰凉的时光机上,像是坐上了游乐园的一辆过山车一样。工程师帮他们系好了安全带,问他们说,准备好了吗?女儿说好了。他也说好了。
那我们走了,工程师把手放在时光机的按钮上说。别害怕,一会儿我们就穿越回去了。
这回不会穿越错了吧?他有些担心地问工程师说。
不会,工程师很自信地说。现在比过去先进多了,放心好了,误差不会超过几年的。
时光机启动了。就像是起了一阵飓风一样,周围的雪一下子向着他们的身上扑来,硬硬地打在他们脸上。他们像是在雪雾里穿行,在密密麻麻的颗粒状的雪雾里穿行。女儿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像是怕丢了一样地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十几年前他和她一起穿越时,她的那双伸向他的手和渐渐远去的身影。他的眼前出现了她的有些恐惧的面孔,看到他们之间的距离在越拉越大。他看到他伸出手去,但是他抓不到她。他看见她把手也向着他的方向伸出来,看见她张着嘴像是在呼喊着他,他看见他把两手在嘴边卷成一个话筒喊着:我在扬州等着你。在时光隧道里,他的眼前时而黑暗,时而闪烁着耀眼的白光。一条条白光像是流星雨一样地穿过他的身体,向着身后闪过,又像是冒着夜雨前行的火车窗户上洒过的一条条雨滴。
北京,他心里默默地想着,难道真的又能回到北京了吗?难道真的又会见到母亲和家人,回到熟悉的龙潭湖,回到熟悉的光明楼,回到熟悉的幸福大街,坐上熟悉的八路车了吗?
十七年了,自从离开北京到南方小城,到现在已经足足有十七年了。他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北京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他一定已经认不出北京了。但是,他一定会认出自己的家,认出家里的人和幼时的伙伴,认出过去的同学的。只是可惜她不想回来了,他想。可惜她不想回来了。





谢仙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