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的博客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选载作者论著章节和新论新译莎士比亚隐秘的灿烂
《莎士比亚的诗歌纪念碑》导论(节选之三)
傅正明
二、莎士比亚的作品之谜
要破解莎氏作品之谜,像欣赏任何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首先需要美学的钥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好奇心,给我们带来观赏的愉悦,是因为画中有一种说不清的美。华兹华斯在<别小看商籁体>一诗中写道:用十四行诗这把钥匙,「莎士比亚打开了他的心房」。可是罗伯特·勃朗宁在<房舍>一诗中对此提出了质疑:「真如此,他就不那么莎士比亚!」换言之,作者的内心的深邃、神秘是不可能完全打开或深入的,莎氏作品有一种说不清的美。用托马斯·哈代的<三百年后致莎士比亚>一诗中一个矛盾说法来说,莎氏打开的是「明亮的朦胧灵魂」。言筌所捕获的美,需要我们去意味,同样不可全得。反讽的是,批评家的使命就是做这种「理还乱」的工作。

莎氏十四行诗的美,乍看之下,首先是其形式的美,韵律的美。但是,深入一层,我们就能发现其内容的美。在他那里,像在任何伟大作家那里一样,美与真和善密切相连。诗人在第105首写道:「真善美是我全部主题,/真善美不断变换辞采/转化中发挥创造技艺,/三位一体,奇妙天地任我骋怀。」这里依照中文习惯译为「真善美」的原词是「Fair, Kind, and True」,这三者虽然融为一体,但其先后秩序是否有轻重之分,换言之,在一切美的事物中,是否「善」更重于「真」?在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中,「美即真,真即美」。但是,莎氏首先强调的是,「善即美」(Virtueis beauty),拙译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同样说得通:「美是嘉行却中毒,内魔擅织浮华衫」(《第十二夜》第三幕第四场)。作为伦理概念的「善」,应当是人的内在本性,同时体现于外在形式或行动中。可是,外在「浮华」,并非真美。在莎氏那里,内美始终重于外美,借重外美而相得益彰,如第55首诗人在赞扬他所爱的「美男子」时所写到的那样:「冷看大理石,睥睨镀金碑,/王公墓铭锈,难与铿锵诗韵比寿。/君有内美载文笔,日益增辉」。
除了美学的钥匙之外,我要强调的另一把破解莎氏作品之谜的钥匙,是政治的钥匙。莎氏全部作品,均以「王公贵胄」为英雄或主角。作者或赞美讴歌,或抨击揭露,皆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Bloom)在《莎士比亚的政治学》中指出:「几乎在他所有的戏剧中,莎士比亚都在以一种大关怀致力于设立政治背景,他描写的最大英雄都是统治者,他们在操练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才能操练的各种能力。谁忽视这一点,就是被偏颇的聪明弄瞎了眼睛。」⑨当然,这并不是说,莎剧有现代民主思想,因为莎氏写作的时代,民众还没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⑩作为时代的产儿,莎氏同样带着时代的烙印。由此可见,没有政治这把钥匙,不可能打开其堂奥之门。
美国诗人惠特曼在<十一月树枝>(Nowember Boughs,1888)一文中认为,莎氏的真实身分可能是「如狼的伯爵」(wolfishearls)中的一位,即牛津伯爵。这一形容词所包含的比喻意义,充分表现了古代专制社会王公贵族的野蛮和残暴,但是,莎氏笔下的「如狼的伯爵」,或带着狼性的贵族统治者的精英,往往有收敛的倾向,经常在自我驯化。假如他们不能自我驯化,那么,推翻暴政的起义就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历史剧《恺撒大帝》、悲剧《麦克白》、《哈姆雷特》和传奇剧《暴风雨》等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
在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中,诗人肯定了推翻暴政的合法性,用领导起义的勃鲁图斯(L.J.Brutus)的话来说:「正义的武装才能扫清骯脏的街巷!」在《恺撒大帝》中,组织并参与刺杀独裁者恺撒的悲剧英雄勃鲁图斯(M.J.Brutus)说:「当他勇敢无畏,我敬重他,当他野心膨胀,我杀了他。」勃鲁图斯把他刺杀独裁者的唯一动机解释为「为了罗马之大善」(第三幕第二场),并且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自杀。由此可见,莎氏对暴力的思考和艺术表现不是简单的,而是深入人性的,并且借以提升了人的尊严、善德和高贵。《麦克白》中率军讨伐暴君的苏格兰王子马尔康的一断台词,像警钟一样警示以暴易暴可能带来的危险。当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革命和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以议会的胜利告终,英国终于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圈子,此时,莎氏早已谢世,但他的艺术作品对推动历史的思想启迪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莎剧《哈姆雷特》(KeanCollection - Staff/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在丰富多彩的莎剧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哈姆雷特》。从《哈姆雷特》的批评史来看,浪漫主义时期更强调王子的政治性叛逆。如苏姗·伍福德(SusanneL. Wofford)所指出的,十九世纪的哈姆雷特日益带有一种反叛政治法律制度,与堕落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浪漫派性格。甚至哈姆雷特的「延宕」和「疯癫」或装疯,都应当给予政治的诠释。?莎学家福克斯(R. A.Foakes)的《哈姆雷特对李尔王:莎士比亚艺术中的文化政治》一书,是从政治角度透视莎剧的重要著作。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把这两部作品称为「青年和老年的原型悲剧」?,这就暗示了他所说的「文化政治」,是过去的和未来一切可能的悲剧难以抹去的浓厚色彩。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道理,一千个时代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属于我们时代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所反映的古代专制社会与现代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之间的极大可比性。
首先,古代专制和现代极权都建立在杀戮的基础上。《哈姆雷特》的情节,围绕在丹麦前代国王弟弟克劳提斯为了篡权而弑兄娶嫂的故事而展开。相比之下,现代极权社会的独裁者杀戮的规模比古代社会要大得多。除了统治者内部的谋杀或变相谋杀之外,屠刀往往针对一切异己、知识分子和平民。
其次,古代专制和现代极权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克劳提斯弒君后散布的谎言是:他是在花园里被蛇咬死的。有所不同的是,极权统治者在谋杀政敌和异己前后,编织的罪名要精巧得多。西方和东方同样流行的谎言是,君主就是上帝之光的显象,就是「天子」。因此,他们窃取了独占了一个辉煌意象,即光照生命的太阳。在《哈姆雷特》中,当国王克劳提斯问哈姆雷特:「怎么阴云仍然笼罩在你头上?」王子答道:「不,陛下,我太多地沐浴在这太阳之下」(第一幕第二场)。此处蕴含的反讽意味不易觉察。因为,太阳(sun)与儿子(son)谐音,只听音,也可以理解为「我太多地作了儿臣」。因此,阿提克(RichardD. Altick)在<哈姆雷特和凡人的味道>一文中指出:「往往被忽略的是,太阳是腐败强而有力的动因」。?《哈姆雷特》的悲剧即将结束时,王子对国王克劳提斯的盖棺论定是:「你这乱伦嗜杀十恶不赦的丹麦奸王!」这出悲剧表明,这个「奸王」是丹麦的宫廷和社会罪恶的总根源。那种认为在极权社会的浩劫中每个人都有罪的论点,容易掩盖大罪,应当从莎剧中学一点伦理和逻辑。
因此,在聚光灯下看看《哈姆雷特》反映的权力腐败、社会腐败和各种顽症,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借镜。女学者斯珀津(CarolineSpurgeon) 在《莎士比亚的比喻》一书中发现:《哈姆雷特》剧中最显著的隐喻同死亡和腐烂有关,这绝不仅仅关系到哈姆雷特个人,而是象征着整个丹麦身患疾病、正在腐烂的国情。其中的主要比喻是毒瘤或溃疡。?
「毒瘤」是哈姆雷特用来形容克劳提斯的比喻之一:「假如让我们人性的这个毒瘤进一步恶化,难道不会招致天罚吗?」(第五幕第二场)「毒瘤」(canker)一词,在当时多指口疮或溃疡,后来用为癌症的同义语。哈姆雷特劝告母亲时说:「不要在您灵魂的伤口外敷膏药,/误以为不是你自己的罪,而是我的疯狂,/那只能在溃疡的表层层结一层薄膜,/而社会的腐烂在内里啃噬人心,/暗地里扩散」(第三幕第四场)。
莎学家伯纳(Miguel A. Bernad)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神学的维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剧中反映的社会腐败,甚至连王子和他所爱的奥菲利亚也不能幸免污染。因此,王子的困境在于,他不能像外科医生一样动手术,因为手术刀会触动他自己的伤口。这种腐败只有通过王子的受难来清除,换言之,他自己必须成为牺牲品。?
哈姆雷特同样染病,但他是一个寻求健康,有心改善社会制度的的人,尽管在他心目中并不那么清楚,什么社会制度才是健全。同样反讽的是,哈姆雷特既是牺牲品,又是疗救剂。当代医学家在人类母乳中发现一种能够杀死癌细胞的物质,命名为「哈姆雷特」。这一命名的深意,是耐人寻绎的。
除此以外,《哈姆雷特》所反映的古代专制社会,与现代极权社会还有许多可比性。莎剧仍然能给我们的时代照一面镜子,那是因为其书写的是一种共同人性及其作者对这种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艺术把握。哈姆雷特性格的复杂性就是人性的复杂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英国批评家哈兹利特(WilliamHazlitt)早就说过:「我们都是哈姆雷特。」?诗人拜伦也说过:「我们爱哈姆雷特,甚至像爱我们自己一样。」但是,诗人拜伦尖锐地批评王子对奥菲利亚爱情的背叛,指责他的「无情」甚至「没有心肝」,把他称为「最难于自立的无能的英雄」。?
精神分析为探讨共同人性提供了一把奇妙的钥匙,它同时是解读莎氏著作的一把钥匙。佛洛伊德提出的「俄狄甫斯情结」,即男孩潜意识中的反父恋母倾向,有三大文学支撑,除了希腊悲剧《俄狄甫斯王》之外,便是《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具有强烈反叛专制家长倾向的儿童,成人之后,推广到社会,往往会踏上反叛专制暴君的道路。
佛洛伊德看重人的童年对日后精神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照英国诗人吉普龄的理解,莎翁同样看重这一点。吉普龄在<艺人>一诗中虚构了几个小故事,说的是在当时诗人聚会的伦敦美人鱼酒店,莎翁一次酒醉后如何对他的朋友谈论自己的创作体验,即他剧中的几个女性人物如何由他自身的见闻转化而来。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泰晤士河畔一个孩子想溺死小猫,却退缩着不敢下手,「他的姐姐----刚满七岁的麦克白夫人」猛冲过来,脸一沉笑她的弟弟没用。吉普龄借以探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同时捕捉到莎翁对人性的理解:从婴幼时代起,人性就有相对的善恶之分,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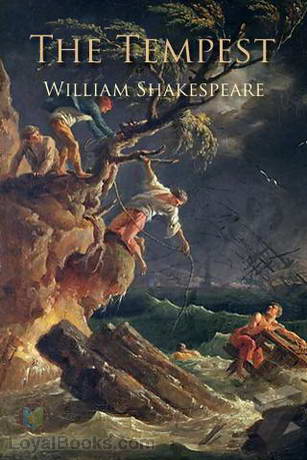
莎剧《暴风雨》
有「莎氏的诗的遗嘱」之誉的《暴风雨》,涉及上述政治和人性问题的各个方面,笔者在<《暴风雨》的鱼人梦>一文中作了浅释。简言之,那个荒岛上的土著,看起来像「半鱼半人」的凯列班,他的梦既是政治梦也是性幻想。他对侵入荒岛的落难贵族普洛斯彼罗有一个颠覆他的权力甚至谋杀他的梦想,即使在他对美丽的米兰达的「邪念」或性幻想中,也掺杂着政治梦的因素:假如一个野蛮人与文明人结合,其后裔的政治和社会立场,就有可能站在土著一边,或多或少重塑人性,逐步改变这个世界。普洛斯彼罗的权力梦最后消散了,领悟到「我们短暂的人生/环绕在睡梦之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