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27岁,我目睹了一个国家失控的全过程
焦翔,一个山东小伙,因主修阿拉伯语专业,27岁时,被人民日报派往中东。按原计划,他的驻外理想生活是边旅行,边写稿,不料刚到埃及,就碰上政坛大震动,“被迫”成了一名战地记者,一做就是3年。

叙利亚战时,不知所措的小朋友

在叙利亚,因要躲避狙击手的视线,必须跑步快速通过
3年里,他辗转在炮火的最前线,每天与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擦身而过,他用相机拍下了变幻莫测的政治动荡,也记录下战火中平民的日常。这些见闻在2021年集结成新书《坚守战地1200天》出版。
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今天,一条连线对话焦翔,听他讲述这1200天的战争与和平。
讲述 焦翔 编辑 陈星 责编 倪楚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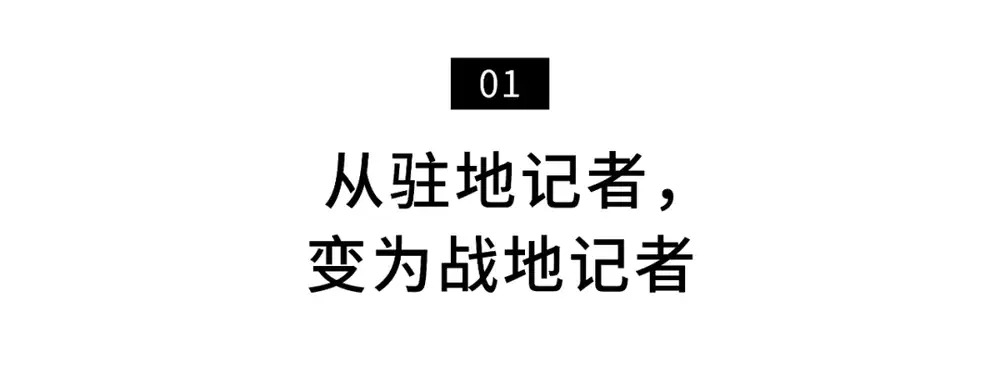
 焦翔采访士兵
焦翔采访士兵
2011年,我27岁,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开始了在中东的生活。
第一站是埃及开罗。我非常期待,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空闲的话还能逛逛博物馆。
开罗也确实没让我失望,它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飞机落地的第二天,因为安全局势失控,开罗机场关闭了。一大批中国人焦急等待在候机楼不肯走,盼着航班恢复,迫切地想回国。就在前一天,埃及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抗议,民众要求总统穆巴拉克引咎辞职。
当时在埃及的中国人有几十万,他们觉得埃及的局势不明朗,着急回国。

埃及的城市里没有一个红绿灯,路况非常拥堵
去驻地办公室的路上,尘沙漫天飞,路上散落着垃圾,远处的金字塔与城市连成一体。我有点发懵,内心也很有紧迫感,我该拍些什么?怎么拍?我想了一路……
我抵达的第二天,晚上就宵禁了。
上百万人聚集到解放广场,他们喊着口号,声嘶力竭,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坦克组成的钢铁屏障,也任由人群穿过,浓烟一直笼罩在尼罗河上。

百姓聚集得越来越多,很快就失控了,披萨饼店、快餐店、商铺的玻璃都被砸碎,只有用木板钉死门帘的店户免遭一劫。
解放广场上一栋大楼被点燃了,玻璃和金属因为高温燃烧,带着飞火流星从高空掉下来,很多平民都在发出尖叫。
真的可以拿“腥风血雨”来形容这个场面。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这种场面的亲历者。我不断跑上街头,想要尽可能多地捕捉一些画面。

当时报社里鼓励做新媒体,我算是第一波配了摄影机的人。在解放广场的大楼前,我做了第一次的出镜拍摄。
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全程目击了埃及从开始示威游行,到武装部队上街,到战斗机低空掠过城市,到趋于失控的整个过程。
接下来整个国家进入一种漫长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每天都在试错。


穆巴拉克下台当天,士兵和示威者便不再对峙了。
版面编辑让我把“示威者帐篷已清除”的主题拍摄出来。我觉得有点为难,帐篷都没了,怎么展示?

我又去了解放广场,行走期间,一幅长约50米,由几百人拉着的巨幅埃及国旗出现在我眼前。我冲到人群最前面,举着相机,所有人都对着我欢呼雀跃。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表达。
在开罗,我一共待了8个月。

之后的三年,巴以冲突,突尼斯发展停滞,利比亚社会解构,也门支离破碎,叙利亚炮火连天……整个阿拉伯地区就像在暴力的怪圈中迷失了一样。我也跟着转战了很多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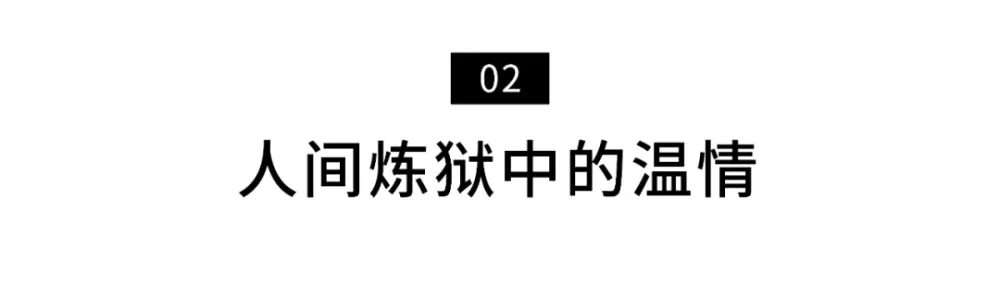

战争状态下,国家的整个运转是无效的。
每天都在发生各种恶性事件。你会感觉到非常煎熬,没有法律在保护你,唯一的保护就是你对别人的判断,以及别人内心的道德和行为底线。

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2·21大爆炸,方圆400米的车辆、楼房无一幸免

当平民谈论起战争的时候,每个人的情绪都很激烈,一谈起对敌对势力的仇恨,就怒目三分,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措辞、声调,因为没有安全感,而变得不可控。

但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虽然草木皆兵,但他们依然努力维持着生活。
比如我在利比亚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来自浙江的家庭。整个城市只有他们还在做中餐,还在做外卖。
我当时点了一份炒米线和红烧牛尾。我没想到送外卖的时候来了三个人,一个看着像妈妈,应该就是饭店老板娘,带着两个十几岁左右的孩子,她说:“我带着他们俩是怕出意外,好有人相伴。你们注意安全,如果要走了,给我来个电话。”
虽然就是短短的一两分钟的交流,但在异乡见到同胞,还是很温暖的。

我还见证过一场炼狱中的婚礼,那是2012年,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老城。
整个城市都空了,很多人都逃走了。出门能不能活命,全靠运气。每天掉进城里的迫击炮弹少则十几枚,多则上百枚。
有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我经过一个漆黑的巷子,发现里面是人挤人的状态。走进才发现,这里在举办一场婚礼。

在场的宾客有近百人,大家都穿着晚礼服,在拥挤的餐桌间跳舞。新郎和新娘在一周前,被落在停车场的一枚迫击炮炸伤,身体还没有恢复,也拖着受伤的身体在跳舞。
婚礼上播的是赞美祖国的歌曲,在祝福新婚夫妇的同时,他们也祈福叙利亚能在战争中挺过来。

过去,他们的婚礼都要去郊区办,至少八百甚至上千人参加,不热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不会结束。现在这场婚礼只能算是迷你版了,而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必须在夜里12点钟左右结束。
婚礼上我跟一位叫卢比的姑娘聊天。她说她有一个未婚夫,因为躲避兵役,出逃黎巴嫩了,但她却坚持留守叙利亚。战争阴云下,生离死别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在大马士革,我感觉“空袭”就像“下雨”一样,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气候,人们活在死亡的游戏中,大概只有淡忘死亡才能找到一丝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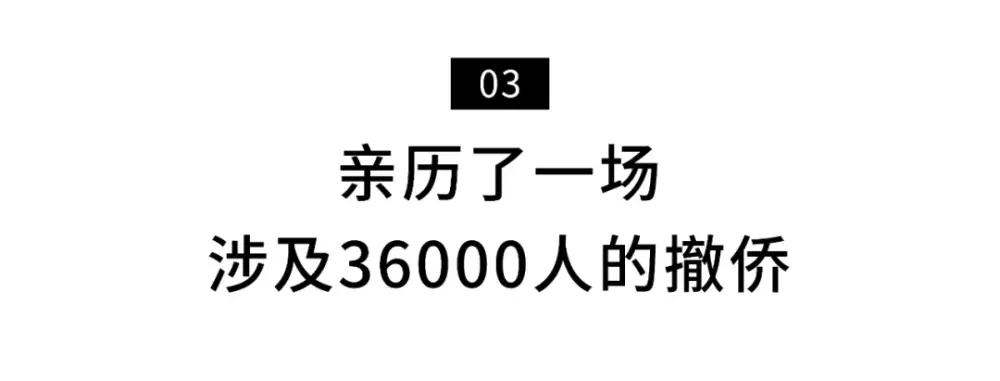

“撤侨”这两个字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都挺熟悉的,只要国外有战乱冲突,一定第一时间会安排撤侨。
2011年,我当时正在埃及。因为利比亚内乱,有大批民众从利比亚涌向埃及,其中就包括了3万6千名中国人。
我接到报道任务后,就坐车去利比亚和埃及的国界。

车子沿着山路一路开,不时就会看到一辆辆小皮卡经过,车顶上捆满被褥与行李,应该就是逃难的难民。
路边布满铁丝网,能看到联合国各个机构的旗帜和成片的帐篷。惊魂未定的人们在张望,衣衫褴褛的男人还企图拦下我们的车。

中国大使馆的人比我们更早抵达边境。在一个小旅馆里,给中国公民办手续,那一批中国人大概有300人。
他们因为是劳务派遣,逃难时护照都不在身上,和黑户没什么区别。使馆人员与利比亚海关交涉,以确保他们能在“黑户”的状态下顺利通关。
中国影响力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中国公民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但其他国家的难民,无法获准入关。

中国租用的大巴停在边境上,凌晨1点的时候,当工人们走出关口,看到中国国旗和车辆,很多人都泣不成声了。
25辆大巴上,每个座位都搁着矿泉水和饼干。凌晨2点,所有撤出人员都已上车就位,连夜驶向繁华的开罗。汽车开动时,所有中国人都自发地鼓掌。
抵达开罗,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他们被安排在了金字塔下的一座五星级酒店。第三天,他们坐上包机返回中国。
一个多月后,当所有中国人逃脱噩梦时,我再次驱车到口岸采访,发现仍有1.2万人滞留边境。

许多来自非洲的难民,除了随身衣物和被褥外一无所有,他们用被子在地上打地铺,很多人在口岸已经等待了很多天。
有些人知道了我记者的身份后,开始跟我一字一句地诉说他们的经历。

其中一个扎红围巾的男人,他原本在利比亚东部的城市班加西做服装生意,为了躲避战乱,一路向东来到埃及。许多人跟他一样,身无分文来到口岸,哪里也去不了,完全依仗国际组织和埃及政府的救助,已经在口岸呆了25天了。
另一个名叫阿里的埃及难民,他一家老少费尽周折,走路、找私营的巴士、找公交车,花了比平时多四倍的时间,才到了口岸。

路上还有一大群胆大的人发国难财,一天开车几次进出生死线运送人员,当然价格也高得离谱。当然,这钱是靠命换的,在战乱的时候,最好用的就是钱。
现场提供医疗的医生告诉我,医生免费开的药他们都不舍得吃,而是藏在身上换钱用。
我看着他们的遭遇,想到3万名中国人可能已经与家人团聚了。当你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同胞们的一声“祖国派我们过来”,都会让心倍感踏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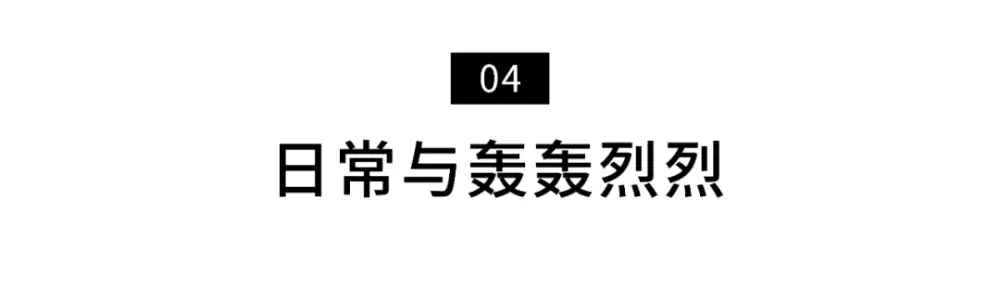

这三年的驻外经历,对我来说很宝贵。我的生活就是在日常和轰轰烈烈中不停切换。
日常的时候,就跟普通人去一个新城市生活是一样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重新开始。
每天上午接国内的约稿,然后是采访、写稿。工作完就进入一个自由的时间,可以找当地的朋友,吃饭聊天逛街。

轰轰烈烈的时候,就自然是在炮火里。
每天轰炸空袭,睡觉也要保持警醒,不能睡得太沉。有一次在黎波里的酒店,夜里1点的时候,我被一阵接一阵的轰鸣声惊醒了。
当时,落地窗在冲击波的冲击下,发出“咣咣”的响声。我赶紧爬起来,躲到房门处。

我按照酒店的逃生线路图,爬到楼顶,发现已经有记者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衣,架好机器等待拍摄下一次轰炸了。这里每天对着城区的轰炸有20-30次。
我回到房间,把房间的窗户贴成像蜘蛛网一样,以防玻璃碎裂的飞溅伤害。为了更加安全,我还放弃了床,睡在床和墙夹缝的地毯上,以床做屏障。

我很后怕的,是一次抢劫的经历。那是在利比亚,当时我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走过来,把我的钱包和相机都抢走了。我跑步冲上去,想抢回来。他停下来,示意要掏手枪了。
当时我脑子里根本想不到害怕,满脑都是这几天的所有照片。僵持当中,他用力一把将我推倒,大步流星地逃走了。
我卧在地上,才发现腿已经吓得抖个不停,一时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后来在路人的帮助下,我才回到酒店。

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人的身体和精神会有些异样的变化。比如睡觉会减少,精力异常旺盛,情绪波动增加,容易大笑大哭。
更不好的是身体的零部件会出现奇怪的问题,比如有一天我吃早餐,不小心咬到钢叉,结果门牙被碰掉了一个角。

这些生活的细碎太多了,但都不重要。怎么样更好地完成我的报道,怎么样尽快把真相向国内读者,向全世界的读者去展示,这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坚守战地1200天,我对世界有了新的领悟。在战争里,我遇到过许多手无寸铁、命运飘摇的人,我想我把他们报道出来,总能激发世人更多的悲悯之心,一同努力让战争远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