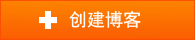目录:4.1 狭谷关战役;4.2 女娲向家人辞行; 4.3 瑶池圣火;4.4 自由恋爱;4.4-7 巫毒学院;4.5 武二郎病了;4.6 女娲为二郎神诊病;4.7 模拟升天仪式;4.8 宝莲灯 4.1 狭谷关战役 公元前1626年,武二郎(号二郎神,如图4-2)是华国湖北战区的主将。他率领三万铁骑沿着四川盆地东部的川谷地带向南,进攻到了龙国(亦作云海国,如地图4.5-4)首都重庆的巫山地区。龙国的国王熬达派大元帅蒲劳领军十万去抵御武二郎。同时,他认命云海三公主熬忖(号尧帝,如图1)为此次战役的监军。 蒲劳在政治上主张由太子熬钦来继承龙国的王...
海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