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文章
文章分类
归档
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2015 (497)
2016 (457)
2017 (603)
2018 (637)
2019 (816)
2020 (700)
2021 (539)
2022 (880)
2023 (542)
2024 (159)

正文
面对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要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方法去“看”?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从鲁迅的一篇“奇文”讲起——《论“他妈的!”》通过考据“国骂”的来历,挖掘其背后深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中国无时不在的等级制度。
导读 《论“他妈的!”》
钱理群 文
鲁迅说,要“睁了眼看”,是需要“勇气”的,却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鲁迅还提醒说,光有勇气也不行,要有“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准风月谈·夜颂》)。这就需要智慧。
这里就有一篇体现了鲁迅式的大智慧的“奇文”。每当人们问我,读鲁迅,从哪里读起?我总是说,读《论“他妈的!”》。
“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谁都会骂;就连我这样的“大教授”,尽管不会在公开场合骂,私下遇到烦心人、烦心事,也会骂一句“他妈的”。但谁也不会想到要“论”,而且真的正儿八经地作“考证”文章:“他妈的”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骂人从来就有,中国自古就有,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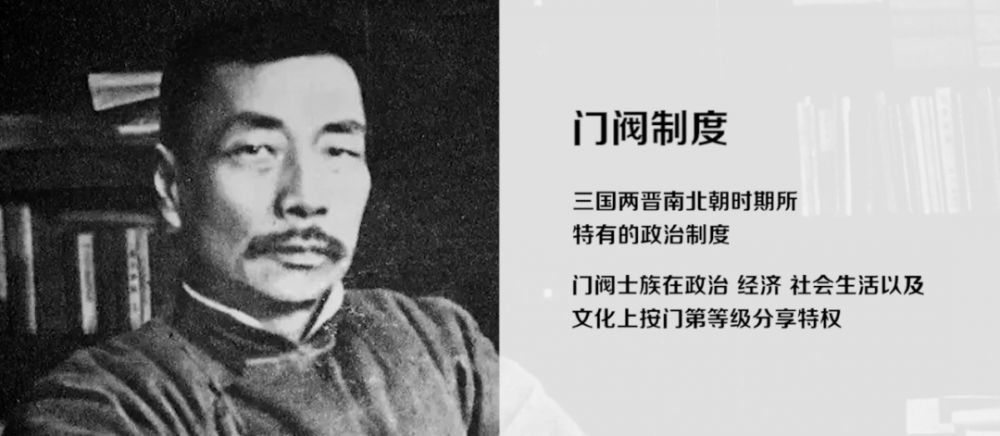
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什么都有;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仅凭出身就耀武扬威的大家族子弟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你神气活现,不就是有个好妈吗?那我就骂“×你妈的”,这就出了一口气,心里也似乎好受一点。这或许可以说是“迂回胜利”吧,但在鲁迅看来,这是“卑劣的反抗”,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样,鲁迅就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中国无时不在的等级制度。由此更引出惊心动魄的追问:今天还有没有“等级制度”?有什么新表现、新特点?我们不也是既不满又不敢说,只有暗地里骂“他妈的”?
这就是鲁迅式的“看”的智慧:他总是从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看起,却往深处看,大处看,仔细看,就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一眼看出隐藏很深的内情,揭示出国民性、社会的“大问题”,最后逼得你把自己也放进去,并和你一起反思,反思社会,更反思自己的人性。
《论“他妈的!”》
《坟》1927年3月,未名社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