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讲述 / 陈玉梅 撰稿 / 然然 编辑 / 丑丑
我从小就重度残疾,医生说,我会在床上躺一辈子。我23岁的时候,一位健康、英俊的男子朝我走来。他对我说,我的腿脚,就是你的腿脚,往后的路我带你走。
又30多年过去了,此刻,我坐在轮椅上,和您讲述我的爱情故事。

我生在青岛,长在青岛。23岁之前,我没离开过青岛。我每走一步,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青岛棉纺厂的宿舍是连在一起的一排排低矮平房,家家户户在门口建一个厨房,围成个小院,院门挨着院门。
我坐在小院子里晒太阳,抬头望着一块小小的碧蓝天空。平房没什么隐私,各种与我相关的闲言碎语,翻墙越户,扑面而来。
“我家孩子不听话,真恼人!”
“你就知足吧,你看看陈书记家养了个什么东西,你孩子健健康康的还不乐意。”
邻居们声音大,距离近,想不听都不行。这些话像一把把尖刀,插进我心里。
我9个月时不幸得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疾病导致我双腿瘫痪,不能站立行走。我的骨骼变形,肌肉萎缩,身体只有三分之一是健康的。侧弯的脊柱,压迫着心肺,我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按照医生的说法,我会在床上躺一辈子。医生还预言,我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
可我不甘心就这样活过一生。我要摆脱这个宿命。
6岁时,我用双臂拖着瘫软的身体,将自己从炕上摔到地上,练习爬行。我用膝盖和双手往前爬,手掌磨破了,皮肉往外翻。膝盖在地上摩擦,身后拖出长长的血迹。
日复一日地练习,我的手掌结出厚厚的茧子。练习到后面,我学会了蹲行:蹲着用手搬动脚往前移动。蹲行时,我上身是笔直的,腰也是直的,我眼睛能够直视前方,头也能扬起来。我喜欢这样可以直视他人的姿势,这让我觉得还有尊严。

虽然学会了蹲行,但身体还是被禁锢着。我每天坐在家中,靠着字典学会了认字,开始学着看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迫切地渴望上学。
考虑到我一个人在学校无人照料,父母让我晚一年入学,同妹妹一道念书,每天由妹妹背我上学。
上学后,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
我想,我的身体已经这样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能在学习上强一些就尽量强一些,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9岁那年,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搬了凳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小人书。阳光温暖和熙,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享受着这个美好的周末。最近一次语文考试,我考得很好。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上朗读。
老师说:“这是陈玉梅同学写出的金句,你们好好学习。”
同学羡慕的目光和老师赞赏的话语,如同这暖暖的阳光,照得我的心温暖、明亮。
没高兴多久,一些话语伴随着哗哗的水声飘进了我耳朵。
“陈家的学习就是好哈,一考就是第一,我家孩子还比不上个残疾。”
邻居们聚集在公共水龙头旁洗衣服,她们又说到我了,我竖着耳朵听。
“学习好有什么用?养了一个残疾这么重的孩子,将来肯定没人要,愁死了。”
“她爸妈不在了,我看她也难活下去,不知道是个什么下场呢。”
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住我。半分钟之前,我还是一个天真浪漫、对未来抱着朦胧憧憬的小女孩;半分钟之后,未来的美好面纱已经被撕得粉碎。
我以后没人要吗?如果爸爸妈妈走了,我还怎么活?
我心中一阵恶寒,眼泪奔涌而出。我对着太阳痛哭,拼命压抑着喉间的声响。
妈妈回来了,看我哭得如此伤心,吓坏了。她把我抱回卧室,关上门,问清缘由。
妈妈眼泪也下来了。她忍不住哀叹起来:“那些邻居虽然嘴坏,说的也不全是假的,我现在能养着你,我死了你怎么办?给你根打狗棍,你也讨不回饭来。”
我大哭着说:“你和爸爸死了我会饿死的话,我死你们前面好了。”妈妈紧紧地搂住我,我们哭成一团。
哭了一会儿,我们渐渐平复了情绪。妈妈打来一盆水,帮我洗了脸,然后给我梳小辫。
她打量着干干净净的我,说:“小模样挺招人喜欢,小脑瓜也聪明,未必没人要呢。”
她又想了想,说:“没人要也没关系,妈妈会想办法,给你存一大笔钱。就算爸爸妈妈不在了,你也能活下去。”
父母都在青岛第九棉纺织厂工作,爸爸是党委书记,妈妈是食堂会计。他们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一些,我们总共姐弟三人,孩子算少的。
自从妈妈有了为我存钱的想法,我们家就开始省吃俭用。

食堂采购的大葱,会剥掉外面几层老皮,丢进大垃圾筐里。妈妈下了班不急着走,在办公室里等着。食堂师傅每天会把大垃圾筐拖出来,把垃圾倾倒在地上,收垃圾的会来收走。
待食堂师傅离开,妈妈看看周围没人,就快步走向倒在地上的垃圾堆,把还能吃的大葱皮捡起来,拿回家。
晚上8、9点钟,公用水龙头旁没人了。妈妈偷偷拿着大葱皮去洗干净。回到厨房,妈妈把大葱剁碎,掺上苞米面搅拌,加上猪油,做成团子吃。
家里很少吃白面,做馒头时会用白面掺上更便宜的玉米面、地瓜面。玉米面、地瓜面揉作馒头芯,再在外面裹上一层白面。馒头热腾腾出锅,看着都是大白馒头。
邻居看到会笑着说:“陈书记馒头出锅了,这大白馒头。”
爸爸妈妈会打个哈哈,只有我们知道,大白馒头的里面是什么。
爸爸是党委书记,他有一份作为干部的自尊。爸爸的大白馒头,是我们在局促的生活里竭力维持的小小体面。
吃的还好瞒过去,穿的就太明显了。我和弟弟妹妹基本上没有新衣服,大的穿了给小的,裤腿子短了接上一块儿,屁股那块磨碎了打补丁。
弟弟妹妹也不抱怨,对于家里为我存钱也很支持,吃不好虽然有时候不高兴,却从不说什么。
每个月,妈妈都会拿存折给我看。存折上每月都有十几块、二十块的款项存入。妈妈握着我的手说:“这是给你存的钱。你有钱,以后可以活下去的。”
我扑在妈妈的怀里,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小孩,虽然身体残疾,可家人的关爱,一点都没少。
曾经有人对妈妈说:“你把她扔了就是了。”
妈妈坚定地说:“那怎么舍得扔,那是我的孩子,再怎么不济,都是我生下来的。”
妈妈为我买了日记本。我开始写日记,念给家人听。每次我念日记,家里都很有仪式感,吃过晚饭的夜晚,大家全部坐定,不要有声音。我开始朗读日记,过程中他们从不打断。念完后,家人举手提意见,讨论日记内容。
我很庆幸生长在这个家庭,即使我有残疾,依然有家为我的依托。在家里,我深深体会到一种用钱买不到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是我心灵健全、自强不息的力量之源。
我读书到高中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的成绩可以念一所好大学,我也非常想读中文专业。遗憾当年政策规定,身体有残疾,不能参加高考,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没有办法读大学,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也是好的。有健康的双手和聪明的大脑,我估摸着找一份会计或企业宣传的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没想到,艰难人生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81年7月,我高中毕业。9月,同学们该读大学的读大学,该就业的就业,都开始了新的人生轨迹。10月,我开始找工作。
爸爸将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我软塌塌的双腿像面条一样耷拉着。爸爸载着我一家家求职。
我找的第一家企业是生产纸盒的福利工厂,他们的纸盒是用一种黏性很强的胶水手工糊出来的。我说,我可以做会计和宣传工作,糊纸盒,我也可以做。
对方委婉地说:“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出来干活,在家可以领取救济。小姑娘别想太多,回家去吧。”
碰了一鼻子灰。但我觉得找工作是双向选择,被拒绝是正常的。我继续找下一家。
找的第二家企业是生产草编制品的,用玉米皮做篮子和工艺品,产品主要对外出口。
我还没开口,对方就直接和我讲:“我们公司是外贸下属福利企业,经常有外国人来厂里参观,你残疾这么严重,怕外国人看了会嘲笑我们国家,怎么这么重的残疾还要干活。”我听了心里一片冰凉。
我继续找工作。从10月开始到12月,一直没找到愿意接收我的企业。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我下肢循环很差,出门在外奔走,腿脚发寒,长了冻疮。
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12月。一年快过完了,下一年要来了,我希望在新年的开头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是一家制造业工厂的小车间,我可以做计件记录的工作。家里辗转托关系,才和那里接上了头。
去车间的头一天,我专门洗了头洗了澡,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我早早穿上棉衣棉鞋,套上妈妈的宝石蓝呢子外套——这是家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渐渐地升起了自信。妈妈过来,为我系上了一条白围巾,我怀着饱满的信心出门了。
爸爸自行车载着我到了工厂大门。门卫问了我们情况后,让我们进去。前方又出现了一道灰色的铁门,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铁门前,朝我们这儿看。待他看清我耷拉着的双腿,闪身到灰色的铁门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
爸爸推着我到了铁门前,敲了半天门,铁门关得紧紧的。爸爸继续敲,里面终于传出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别敲了!没人!不在!”
爸爸载着我返回到门卫处,跟门卫讲:“我们是老郭介绍来的,是来找工作的,约好了是今天这个时间。”
门卫也不知道情况。
来来回回我们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想找的人。只好回家。
爸爸去找介绍工作的中间人老郭,老郭也没说什么。其实,老郭也不用说什么了,我们明白,自然是因为我的情况了,他们不愿意见我。
这是无数次拒绝的最后一次,也是一次很彻底的拒绝。那扇灰色大铁门无情地关上的那个瞬间,我的心门也黯然关闭。我再也没有找工作的念想了。算了。
求职失败,对我打击很大。
从小,我生活上有家人,读书时有老师同学,他们对我都很友善,很关心我。我求学顺利,成绩也好。我自信地觉得,自己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找一份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命运已经给了我足够的苦难和功课,我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应该可以过关了。
可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坠入了更深的深渊。从那时开始,我自卑心理越来越重。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我。我变得压抑、内向,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见人。
爸爸妈妈不再跟我说找工作的事。他们把图书馆的图书,厂里订的报纸成捆地借回家,对我说:“你喜欢看书写东西,这些书你都看一看,想写的时候就写一写。不找工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也挺好的。”
我投入地读书看报,慢慢地从伤痛中恢复。

读书看报,时间长了,有了投稿的念头。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哦,春天》,描写的是自己真实的心境:在黑暗的冬天里,盼望着春天的到来。我将文章投给《青岛日报》,竟然过稿了!
我很激动。我想赶到太平路的青岛日报社去,见一眼编辑袁一平老师,亲口向他说声谢谢。但去报社有30里路,坐车要倒好几班车。家里人都很忙。
我把这个想法压了下去。我给袁一平老师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袁老师回信说:“你不用来了,等文章发表了,我来看你。”
不久,袁老师真的来看望我了,还带来了一摞印着“青岛日报”字样的稿纸。我非常珍惜这摞稿纸,仔细地存好。
我背后塞着枕头,在爸爸给我搭的木板上写作。我通常先在其他稿纸上写底稿,再在“青岛日报”稿纸上誊写。每次誊写前,我都清洗双手,然后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书写,非常虔诚。

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夏天,很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通过报社中转给我写信,都说我不容易。10月,一位叫赵保乐的通讯员来家里采访了我,写了篇人物通讯《在她的心中有一条小路》,发在青岛日报上。我一下子成了所谓的“名人”。
有一位叫陈道真的残疾人长辈,看了这篇文章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我。
陈叔说:“你发表文章要跟我讲,我也好去看看,我们残疾人团体出人才了。”
我爽快答应:“行,发表了文章,我会告诉您。”
陈叔经常在一位小友面前提起我,给他看我写的文章。
有一天,那位小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刚写了一篇散文,请你给我指点一下。我们交流写作,以文会友。”
没过几天,小友又来了封信:“你近来身体如何?有需要我来做的,请不要客气。不要老不出门,憋久了会影响思路和心情。请把我当朋友,想出门知会我一声,我一定赶到你面前。”
天气暖和时,小友来信向我发出邀请:“我过去找你可以吗?咱们出门看看栈桥,大海,崂山。”
我开始每天盼着邮递员来。邮递员骑着墨绿色的自行车,自行车后座挂着两个墨绿色的袋子,上面写着黄色的两个字——邮政。
每天上午九点半,邮递员会准时经过我的家,如果有我的信,他会按响车铃铛。我特别盼望铃铛声响起,那意味着小友来信了。
我蹲行到门口,躲在铁门后,听到邮递员上楼,我知道我的信到了,我伸长手,拉开铁门门栓。
看到突然在门后出现的我,邮递员会惊讶地说:“啊,你早在这儿啊?”
我笑着回答:“对啊,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接到邮递员递过来的信,我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展信阅读。
小友在信里说:“我一个人背着你去登山,看风景。你不能去的地方,我都要带你去到。我能做一顿饭给你吃,虽然做得不好吃,但是熟的,热的。”
我非常感动,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他发出的邀请很热烈。那也是我想做的事。但我不敢说行,我还困在“没人要”的闲话里,眼前这一切好像太虚幻了,不真实。

我总是含糊地客气一番。“你寄来的文章我看了,根据稿子我写了一些看法和修改意见……”在回信的末尾,我署上名字,日期。我从不表露自己,虽然内心激动,但回信冷漠。
我和小友一周通一封信,如果这周他给我多写了一封信,我会觉得很幸福,是一种特别的甜蜜。
有一次,他回信迟了两天。在这两天里,我情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往下跌落,直至陷入绝望。他信里所写的一切都只是随便说说的吗?我整天胡思乱想,忧虑焦躁,提不起精神。
两天后我收到了他的信。我又活了过来,飘上了云端。
最后,小友写信说:“我要来和你见一面。”
我们往来了两封信,确定了见面时间,7月6日。这是在1988年。
他来的那天,阳光很好,我把两扇玻璃窗擦得干干净净。我蹲在地上,把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家里清清爽爽的。
我洗了头,用电夹子把刘海夹弯。我洗了澡,穿上新买的白底淡黄小碎花短袖上衣,衣服上小花疏落清新,我希望自己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如同这小花,是清新美好的。
下午3点,敲门声响,陈叔和他的小友一道来了。
我和妹妹住在小北间,床和窗台之间搁着一块木板,排列着我的书,那也是我写字的地方。我坐在木板前的椅子上,假装在看书,假装很专心,假装没听见。
陈叔坐在客厅和我父母聊天。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抬起头来,愣了一下。
眼前这个男子,是与我通信了两个月的,刘华保。
在见他之前,有人说,他肯定长得很不好看,找不到老婆才来找你。我想象中他应该也比较丑。
眼前的男子,穿着藏青色裤子,蓝红色格子衬衣,浓眉大眼,健康帅气,皮肤略微带些古铜色,我甚至觉得他长得像明星。
他看着我,也没说话,脸上挂着笑。眼前的他和写信的他是同一个人吗?
他一直在笑,但我感觉到了他的紧张。他缓了一会儿,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24岁了。嗯,比我还小一岁,是个弟弟。
他说,他在包装制品厂做质检工作,家里有父母,兄弟四人。有些信息,之前给我的信中有写到。我确定写信的就是他。
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偶尔翻一下,听他说话。他不是很会说话。讲了一阵儿,没话说了,他挂着笑走了过来,问:“我看看你都有什么好书,可以吗?”
我点点头,说,你看吧。
他拿了一本《写作技巧》在手中翻弄,问我:“这本书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感想?”
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我真的要好好学写作技巧,不然达不到你的要求。”
他音色是洪亮的,但压低了说。
陈叔和父母在客厅,我们都不敢大声。我们低着头,偶尔瞟对方一眼,也不敢看得太实,就匆忙收回了目光。
那天我们心里都太激动了,话都说不好,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装模做样地看《写作技巧》,似乎很认真,但我清楚他实际什么都没看进去,因为那本《写作技巧》被他拿倒了。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爸妈招呼我们去吃饺子。大家看出我们对彼此有意。这顿饭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

第二次他上我家来,吃过晚饭,爸爸把他单独约出去,在周围公园找了一处僻静的亭子。
爸爸存了考验他的心思,把话往重了说:“我女儿的身体,严重残疾,不能走路,要人照顾,能不能生孩子不敢说。你年纪轻轻的,找一个正常人结婚、过正常生活都是你要考虑的,你好好想想,我们家是不是不适合你。”
他回答得轻描淡写:“这是我的选择,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不觉得身体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跟玉梅谈得来,感觉也很好,我不会放弃。”
爸爸说:“婚姻大事,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你要把情况跟父母讲清楚,征得他们同意。”
他说:“我会和家里好好说的。”
爸爸回到家里,对我说:“小伙子要考验,看他是否真的能扛下来。他之前不是说要带你出去玩吗?让他带你去。”
第三次见面,刘华保买了《兵临城下》的电影票,带我去楼山剧院看电影。他推着我爸爸的自行车,把我放在后座上,出了门。他骑车习惯了右腿打到后面上车,载着我,腿要从前面上,他不习惯,就没骑,一路推着走。

刘华保推车带我出门
走着走着,他突然扭头对我说:“我这辈子就给你推车。”
我沉默着,什么也没说。
夏夜晚上,路灯明亮,刘华保穿着白色短袖,配了一条黑裤子。他适合这样简单的搭配,显得洋气、高大。
经过好几对恋爱的情侣,他们勾肩搭背地并排走着。我不禁叹道:“能这样走在一起多好,可是我不能,没有办法。”
他乐呵呵地说:“他们那样太千篇一律了,像咱们这样的,整条马路没有第二对。”
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差不多20分钟后,到了楼山剧院。剧院在半山坡,有很多级台阶,进了剧院还有楼梯。我们的影厅在3楼。

刘华保停下自行车,要背我上去。第一次让年轻男性背我,我觉得害羞。另外,我也不想给他增添这么重的负担。我纠结地说:“算了,我不上去了,我们不看了吧,咱们就在马路上走走。”
他不干,说:“来就是为了看电影,无论如何,我要背你上去。”
我趴上他的背。他用手托了我的腿,开始爬楼。我很紧张,努力钩住他的肩膀,生怕掉下来出洋相。
我有80多斤重,背着往上走还是很吃力的。爬了两层楼,我跟他说:“你停一停,把我放在扶手上,你休息一下。”
他说不用了,一口气爬到影厅门口。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他微笑的侧脸,他说:“没事,我愿意。”
他背着我走进影厅,来到座位前。为了防止椅子一下子弹回去,他用一只手绷平座椅,另一只手托着我坐到椅子上。
他老担心椅子不牢靠,一直用手扶着。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坐稳了。”
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我可以用手拉着你的手,这样我就不会担心你。你也给了我安全感。”我同意了,把手递给了他。
电影开始了,我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电影上。我手又软又小,蜷曲在他的手心里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潮润。是出汗了。
过了一会儿,他捏捏我的手,看我的手还在不在。我侧脸看他,发现他也没心思看电影,时不时地侧脸看我。看到我在看他,他笑了。
电影看完,除了电影的名字,其他什么内容都没记住。
晚上回到家,我一夜未眠。我反反复复地想着今天约会的每一个细节,从他带我出门,到他背着我,拉我的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缘分太美妙了,要是我能一直抓住就好了。不要松开,不要丢掉,我在夜里默默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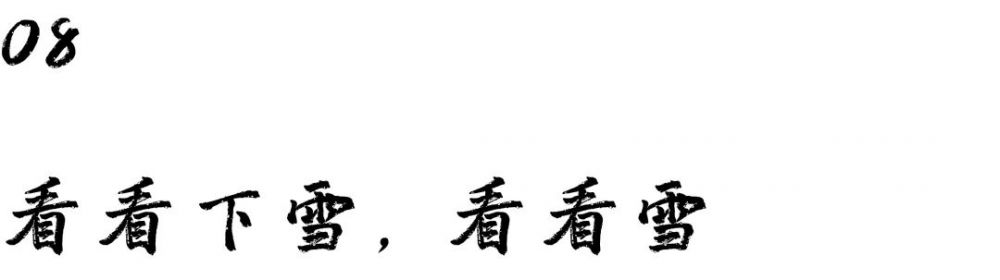
我喜欢海,喜欢大海纯净的蓝色。家人带我去海边,都在不太冷的季节。我想看冬天落雪的大海,我想,雪花飘落在海上,一定很美很不一样。
我跟刘华保说了这个想法,他自告奋勇要带我去。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刘华保把自行车后座用棉被垫了,将我放上去,推着车上路了。
骑车到了海边,再往里就不好走了,沙子很软,轮子没法转动。他把自行车放在沙滩外面,抱着我往沙滩里面走,沙子太软,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
雪不大,零星飘洒,他一边费力前行,一边用力托举起我:“看看下雪,看看雪。”我心里很热,嘴里却说不出什么。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仰着头问我。我们两个都开心得哈哈大笑。
他抱着我走到了离海很近的地方,把棉被铺在沙滩上,我们坐在上面看雪。他觉着沙滩太冷,让我坐到他腿上,这样能暖和一些。我顺从地照做了。他解开粗呢外套将我裹进去,他身上很热。
雪时而小,像天空撒遍碎盐,时而大,像飘絮。雪花落在沙滩上,慢慢融化。可落在海里,是无声无息的。

他看看海面,看看我。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想写一篇下雪天看海的文章。”
我笑着问:“构思好了吗,说出来我听一听?”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这一片落雪的海面。很干净,很安静,心头所有的不愉快都没有了。
我们在那儿坐了两个多小时。一直都这样就好了。

冬天,一天比一天冷。我身体循环不好,浑身都是凉的,肢体麻木,从腰到髋关节,膝关节都疼痛难忍。
通常上半夜都冷得睡不着,后半夜,身体才在被窝里缓过来。休息不好。
刘华保知道了这个情况。他来找我,我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他直接说:“你身体这么冷,一个人在床上缓不过来,我体温高,身体热得快,可以暖你的腿脚,现在没结婚,不大方便,结婚了就顺理成章了。”
他把我的两只脚抓在手里,抱着,说:“这样就很好,是不是?”
我通红着脸,拼命往外抽脚,说:“这是臭脚丫子,不行啊!”
“没事。”他撩开贴身的衣服,把我的双脚按在胸口上。我想用力挣脱,但他都不松手。
真的很暖和。我感动得想落泪。“我愿意这样。”他说。
我努力坐了起来。
“怎么坐起来了?躺下吧……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关于结婚的话么?当然听进去了。我含泪点点头。我很高兴,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我无法做跳的动作,我最多只是坐起来。
这么好的人,真的会跟我在一起吗?我不敢相信。

23岁的我,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
吃过晚饭,他跟我爸爸妈妈提出要娶我。
爸爸妈妈很高兴。爸爸说:“我们这边没问题,该说的话说了,该讲的也讲了,你那边不知道怎么样。”
他说:“明天我就回去跟家人说结婚的事。”
刘华保回去了,然而就此消失,不见人来,没有任何音讯。
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日夜盼他的消息,食不知味,晚上失眠,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刘华保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我文章也写不下去,整天胡思乱想,落笔错字连篇。我的心思全在大门上,时刻听着门栓有没有响。门栓响了,可能就是他来了。
他怎么还不来找我?我与他就这样断了,结束了?我的心沉沉地坠下去。
一个星期后,下午,一位熟人敲门进来,说有话对我们讲。爸爸妈妈招呼他在客厅坐下。他喝了口水,低声说:“刘家人也认识我,他们委托我,给你们传个话。”
我躺在房间里的床上,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我听见那人说:“你们两家的婚事,刘家坚决不同意,坚决反对,你们不用再想了。”
爸爸叹了口气,说:“都料到了,我们能接受。”
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哭了。我躺着,泪水不停地流。我和刘华保的感情结束了,对我来说,这件事比残疾更让我害怕,让我绝望。
我流了一整夜的泪,无声地哭泣,印着牡丹花的红枕巾被泪水浸透。同他恋爱后,我开始穿大红衣服,铺粉红格子床单,用大红底牡丹花枕巾。我还指望着这些红色能为我们的恋爱带来好运。
我的手指摸着湿漉漉的红枕巾,害怕,绝望,无助的情绪挤压着心脏,一阵阵生疼,连呼吸都会疼。刘华保是这么好的人,我再也遇不到了。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爱我的人了。
天边泛白,我的眼泪渐渐停了,我感觉体内所有的水分已流尽。我双眼肿得像烂桃。心中支撑我的是对刘华保的最后一点念想:我希望他来,当面跟我说清楚。
哪怕是在绝望地哭泣时,我都时刻听着门响,听他是不是来了。
一天过去了,他没有来。第二天,门栓被人拨动,我侧耳倾听。
门栓被拨动,停顿一下,再被拉开,是刘华保!这是他专属的开门动作,他来了!我猛然从床上坐起。
这么多天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突然起身,头晕,脑胀。刘华保垂头丧气地走到我面前,看起来很狼狈。
他身上还是上次跟我分别那天穿的外套,整个人脏兮兮的,胡子拉碴,头发打结。他面容憔悴,明显瘦了。他看我坐着,有气无力地问我:“你怎么不躺着?”
我看着他,想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忍住了。让他自己说吧。他回避着我的目光,拿出烟吸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枯坐着,沉默地挨到中午。简单地吃了点面条,他开口说话了。
他回去和父母讲了要和我结婚的事。父母坚决反对,还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出门。他妈妈哭了好几天,他爸爸还打他、踢他。
不让他出去,他就在家里绝食,整整四天,他水都不沾一滴。父母怕他饿坏了,打开了门,哄他吃了点饭。他身体略微好点,就来找我了。
“家里很反对,没有半分商量余地。难度很大,我怎么办?”他烟抽得很凶,眼睛红红的。
“你的想法是什么?”我问他。
他大声地说:“我是不会变的!”
“对呀,我怎么会变呢,那是不可能的,”他又喃喃自语道,“堂堂正正地爱一个人,又没做坏事,为什么要变?”
刘华保请求我爸爸妈妈去他们家一趟,跟他的父母谈一谈。
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他不变,我就有主心骨去面对一切。

我们的感情还有希望
我爸爸妈妈去了刘家。
他们比较客气。他爸爸说:“我们担心他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感情冲动下做决定,将来要后悔。”说到结婚,他们就是不同意,怎么说都不行。
爸爸说:“您不要把话说得太绝,您的儿子和我闺女真心相爱,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们被拆散。您没看到我们家的情况,看一看再定吧。”
他们同意过来看看。两天以后,刘华保的父母来了。
我很紧张,像过关大考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厅沙发上。他们进屋一眼就瞧见了我。他爸爸笑着说:“看不出来腿有毛病。”
在屋子转了一圈,他爸爸单刀直入问刘华保:“你确定就想和她过一辈子?你不怕吃苦受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可要想明白了。”
他妈妈说:“这是一个火坑啊,你们在一起,以后生活会很艰难的。”
他站在父母面前,坚决地说:“我和她分不开了!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如果跟玉梅不成,这辈子我不会结婚了!”
说完,他一下子坐到我身边,紧紧抱住我。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也紧紧地抱住他。
刘华保抱着我说:“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和她的关系决定了!”
我的爸爸妈妈过来安慰我们。刘华保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边不说话。看到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大家都偷偷地抹眼泪。
轮椅上的爱情(上篇)完结。刘华保和陈玉梅能终成眷属吗?他们又会遇到哪些磨难?请关注丑故事,周五(5月22日)上午7:30推出轮椅上的爱情(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