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95)
2007 (227)
2008 (147)
2012 (9)
2014 (1)
2017 (2)
2018 (1)
2021 (9)
2022 (29)

1.
说起崔健,我属于可以对他宽容再宽容的那一类歌迷。
有人说他老了,有人说他被西方摇滚撅折了,有人说他迷失自我了他江郎才尽了。
也都是爱之深责之切的评价,不无道理。
虽然《阳光下的梦》挺好听,可是我们怎么都会更喜欢《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就像Eagles,任凭这帮老鹰如何活到老唱到老,Hotel California肯定是他们终生无法超越的颠峰;我们爱听《蓝色骨头》和《混子》这没有错,可惜它们不可能像“花房姑娘”那样让我们泪流满面了;崔健一RAP,我们只好傻眼,挥着荧光棒敲敲节奏,那些抄写过的好歌好词,竟然有点像是从周董那吐字不清的嘴巴里面唱出来的。
确确实实崔健秃顶了眼袋也大了,他用音乐进行的思考跟从前不太一样了。可他还是中气十足,依然不愧为真唱先锋。他在中国摇滚界的地位,远远不止是一块基石而已。后来的所谓代表人物,不论是唐朝还是魔岩三杰,迄今未有能够望其项背者。至于现在的什么谢天笑,根本就是垃圾。
所以,那些振振有辞的所谓乐评,不也就是在演唱会的余音中才能勉强跳跃两下的么?到了下一场演唱会,失望了的评论家们还是会屁颠屁颠去听。不是去听老崔的自我超越,是去听老崔的二十年不变。
女儿阿小J问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看这个她不认识的叔叔唱歌。我说因为妈妈从上highschool就开始听他唱了,认识这位叔叔(那时候还是个哥哥)的时间,比认识她的时间,还要长好多好多。阿小J吃惊地望着我——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妈妈是那么的老,有着那么长的一段历史。
是啊,一个人能有几个二十年?在为数不多的二十年里,又有几首歌让我们肯拿出不变的激情去听?难道我们不该心满意足么?
2.
对于听众,我反倒就是做不到宽容。
在我们前边,有三对男女。
第一对如胶似漆,仿佛听的不是崔健,而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给了他们一个幽暗温柔的场地以便贴脸亲嘴咬耳朵。
第二对各人顾各人。先生怕吵,时常要把手指头捅进耳朵眼里隔音;女士翘着二郎腿吃零食,让我直想过去问她:do you care for some popcorns, Mam?
第三对西装革履,正襟危坐,面无表情。我们在后边使劲唱使劲叫使劲跳使劲打匪哨,他们顶多回头厌恶地看我们一眼,然后继续掉转头去坚持他们人大会议的姿势和表情。
我实在搞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花钱找罪受?因为住在附近,周末正好没什么安排,权当一项社区活动?
想起当年我们听不起现场演唱会,在寒风里等着散场好能见上老崔一面;也想起我的好多朋友要么不住湾区不能来听,要么孩子太小不能来听;也想起一路上看见的那些把孩子扛在肩膀上小跑着往演唱会赶的歌迷,我觉得,我前头坐那些个听众,或许更应该用这点钱去买一套柴可夫斯基,回自己家里听去,把崔健的歌声,留给真正热爱老崔的歌迷。
3.
有位网友在老崔现场看见我了。刚才收到他逗我开心的短信,特此贴出来,谢谢这位体贴的哥哥对无名的了解,呵呵。
你三次从我身边经过,第一次,你和珊瑚礁往后走,边走边打电话。第二次,端着啤酒往回走,第三次由于要拿票,只好把啤酒放在地上,我本想帮你拿啤酒,又怕你说我想骗你的啤酒喝,眨眼之间,你就健步如飞的消失了。
特改编崔健的花房歌以记之。
你三次经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
我不敢使劲看着你的,噢......脸庞。
我想问你去向何方,你冲着啤酒的方向,
我知道你想喝几杯,噢......真棒。
你端着啤酒回剧场,我想上去帮个忙,
检票的说你走错了,噢......方向。
你说要发现我在剧场,见了啤酒全都忘,
你不知不觉和啤酒,噢......一样
我就站在你身旁,你和看不见一样,
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
你回到司令的身旁,你已经坐在座位上,
我只好上前说一声,噢......姑娘!
你就要回到老地方,你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知道你爱喝啤酒!噢......姑娘!
4.
最后贴几张我在现场拍的照片吧。相机不好,只能看个大概。这一组是老崔第二次返场,在唱《红先生》。
这回老崔的演唱会,有两个小小的遗憾,一是竟然没唱《南泥湾》。二就是他《时代的晚上》演唱会,在工体的时候唱“花房姑娘”,歌词改成“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工体!”,已经够矫情的了;这回在湾区,竟然干脆改成“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湾区!”,我笑到差点把啤酒喷到坐我前头那俩人大代表的脑袋上。
有对《时代的晚上》这台演唱会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我早俩礼拜转贴过的一组关于北京工体《时代的晚上》的乐评文章:为崔健《时代的晚上》热热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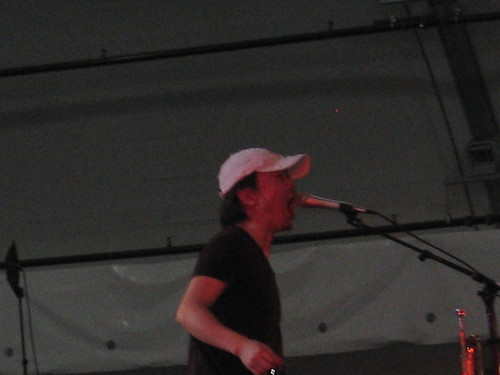










我不管你要向何方,我也会看着你方向。。。。
我要再举起酒杯,噢。。。崔健!!!!!!
今儿,写了一篇“和平鸽的思念”- 怀念帕瓦罗蒂 - 5(诗与歌),同时也是对崔健的致意。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05&postID=11623
中国摇滚不归路啊!
我虽不是老崔的粉丝, 本也打算去演唱会, 可还是错过了. 谢谢你的观感和评论. 希望以后能在这儿听到更多我爱的老歌!
这里有人说“后来人的针在后来的皮球面前都太钝了。”不会吧,80后的摇滚一样犀利,甚至凄厉。比如“伤的从来都是自己啊,飞啊飞,你手中的刀”,不谈政治,一样锋利。
南泥湾是著名的“红歌黄唱”,原词曲都是大牌。而且这首歌完全体现中共的抗战精髓。绝对经典。
我在第一排,还上台和他一起跳,唱,给了他一个big hug! 值!
我开始也想他唱南泥湾, 可是后来我明白了,他不喜欢软绵绵的歌!我喜欢南泥湾是因为我诧异一首歌曲然可以被演绎成那样阳刚!
崔健没变,中国摇滚有戏!
我猜崔健都有可能后悔曾经翻唱过“南泥湾”。在我的记忆中这好像是唯一的一首飞崔健创作的歌曲。我要是他我也不会去唱。
我更喜欢带有崔健鲜明特征的作品,像是“新鲜摇滚”之类的。
老崔的声音还是够劲的啊!!!顶!!!
你可真是幸福的一塌糊涂啊.
关于 “we can have dream and live boring life at the same time”
想起了另一位音乐家巴赫。他的一辈子都似乎在过着boring life. 但从他的音乐里可以听到最美的dream.
写得好!
赞同:我们“不配问”。
住在西北角:我确实在这方面不理智,这个没有办法,你看看我新的文章,可能在那儿说得稍微清楚一点儿。杨一我没听过,谢谢你推荐,回头找来听听。不过谢天笑确实是垃圾。
huntfox:你这篇写得真好,本来想转贴去杂谈,才发现你已经在那儿贴过了。
司令在她的崔健一文中写道:
“崔健真正的粉丝基础是理想主义的七十后,他应该继续忠实于他们,他们也才能继续忠实于崔健,即便他们都已经是一帮拉家带口三十奔四十的人了,也仍然需要发泄,需要理想。要知道理想即便被消磨殆尽,奄奄一息,也仍然有存在的需要,也时刻希望着被点燃。理想不灭!理想万岁。”
于是我们今天再次谈到理想,这是我们两人的对话:
她:we can have dream and live boring life at the same time
我:that's why we have dreams. or say, that's how we survive boring life, until one day, our dream is to live a boring life.
与君共勉。
****************************************************
凭谁问老崔老矣,尚能唱否?
老崔(崔健)来了湾区。去听演唱会之前,我在心中问过自己:老崔老矣,尚能唱否?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一次听到老崔的声音,是高一。其实那时候老崔已经出道3年了。从第一次听到老崔吼着“一无所有”,他就成了我年少时的偶像,夸张点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因为偶像在我狭义的理解中应该是属于F4,金城武的专有名词,而不应该加诸于塌鼻子,大眼袋,头发日渐稀疏的老崔。但只有老崔,这么多年,也只有老崔,会对着天空喊:我一无所有。只有老崔一直表现着他不妥协的性格。扪心问问我们自己吧,这些年,我们已经妥协了多少次?数的清吗?理由呢?为生活吗?为柴米油盐吗?
老崔的专辑从第一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听到第三张“红旗下的蛋”,始终喜欢。到了第四张“无能的力量”,我就已经听不动,也听不懂了。以至于第五张“给你一点颜色”,根本就没有去听。私下以为老崔后来的音乐已经走火入魔,痴迷于复杂到极点的配器中,却忽视了旋律的可听性。直到这次现场,我才明白了,原来老崔于我,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作为一个好听的歌手而存在的。我终于想通了这一点,在看完现场的第二天。因为老崔在现场的问话这两天一直盘旋在我脑海,挥也挥不去。老崔的问题很简单:“你们20年前的理想还在吗?”。如此简单的问题,让我整整想了两天,也许还要再想下去。
San Jose的会场,看到很多年纪比我大的人,头缠红布,在比我更狂热的向着老崔挥舞着拳头,和老崔一起唱。你可以说他们是追星,但谁又能否认他们更可能是在向着那遥远岁月中自己单薄的身影致敬?老崔的演唱会在返场中的“一无所有”中达到高潮,我看不清场中所有人的脸,但我相信会有许多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谁能追回自己的青葱岁月?那些年少轻狂,无惧无畏的岁月?
市侩的我替老崔算了算,San Jose这一场的票房总收入是12万5千美金,刨去场地租用费,旅费,住宿,老崔分不到多少。老崔来这里唱歌真的是为了这几个钱吗?我不知道,但我不愿相信。我宁愿相信老崔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他的理想他还活着”。那么我呢,我的理想知道我还活着吗?抑或是我已没有了理想?
也许老崔并不像我想像的这样,也许他只是年少的我在记忆中为自己树立的一个标榜。我不知道,可那又怎样?我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人在不屈不挠的为了一些也许是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在奋斗。对我,这就足够了。
凭谁问老崔老矣,尚能唱否?我现在不配问,不过我已经开始去想了:我的理想还在吗?你呢?
仅以此文纪念血性的老崔!
崔健的优与劣同样明显,出得早,得有利环境的宣扬加之早年国人的闭塞是他当年时不我与的命.可这些年是退化了.
他的确有江郎的味道了,我说今天杨一(知道他吗?一真正搞民谣的艺人,可惜没老崔的条件)的音乐就比他老崔"红先生"更有意义.
不能因为崇拜就全盘接收,不能因为资历低(我说的是谢天笑)就全盘否定,那不是理性的看法.谢的第一张"冷血动物"要搁早年也绝对是很棒的音乐,只是现在这第三张实话是真差了.
你那是追星,不是品音乐.
崔健之于八十年代,借用跟司令提起过的一个比喻,就像“把一根针扎进皮球里去”。他是我唯一佩服的大陆音乐人。
崔健那根针已经完成使命了。后来人的针在后来的皮球面前都太钝了。
--------------------
伊沙曾在某报撰文说崔健的唱片是“一蛋不如一蛋”,可巧的是,笔者的朋友们持上述看法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对崔健的歌词还是相当敬重的,他们不满意的是歌曲旋律的缺失和崔健对说唱乐的大量采用。笔者曾撰文推测崔健的用意是要大家换一套听觉神经,换一种思维模式,换一个活法儿,因此他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不久前笔者有幸去听了崔健在洛杉叽的演唱会,发现崔健的“变化快”其实还有更实际的理由。
演出于1999年8月4日晚8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Mayan俱乐部举行。这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俱乐部布置得像个神殿,周围墙上到处是各种妖魔鬼怪的雕塑,灯打在上面显得阴森森的。由于门开得早,7点半时俱乐部里就挤满了人,绝大部分是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其中女孩多得令人惊讶。我有个可能是错的感觉,即这里多数人没怎么听过摇滚乐演唱会。记得当演出中间崔健换吉它时我后面的人惊讶地对同伴说:“怎么弦又断了!”
崔健还是那么精瘦,似乎岁月没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上身披件花衬衫,下面是一条肥大的运动短裤再配上一双运动鞋。这身打扮足以把南加州的小青年们蒙得一愣一愣的。只是老崔的不加修饰的黑头发露了馅。这年头在美国的老中们要想在穿着上扮酷容易,可要让他们染发纹身穿鼻孔就立刻会现出革命不彻底的原形。相比之下,吉它手埃迪还是头发上包手绢的老样子,萨克斯手刘元则头戴鸭舌帽儿,身穿丝绸褂儿,再配一副圆眼镜,标准的打扮。就是这么三个很不般配的人,再加上贝司手张岭和鼓手贝贝(?),把全场的人彻底镇住了。
崔健一上来就是两首极为火爆的《飞了》和《混子》。想象一个这样的情形:当你一见到崔健那张熟悉的脸,那张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磁带的红封面上被你凝望了无数次的脸,当你正跟着脑子里的旋律卡拉OK着《一无所有》那揪心的歌词时,耳朵突然被一阵阵迎面扑来的巨大声浪震了个半聋,然后崔健象跟台下的谁过不去似的喊道:“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我的感觉已经晕了浑身没劲儿……”其实我这是在演绎呢,因为你根本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别以为你的英文已经好得让你忘了母语,崔健根本就不想让你听清楚。调音师完全按照美国一般摇滚乐队在俱乐部里演出的惯例把音响调到足以让你失聪半个月的水平,崔健、埃迪和贝贝又把他们手中的专出高音的乐器弹(敲)得山响,而崔健的嗓子又跟刘欢还有一段距离。几个因素加起来,你要是能听清他在唱什么那倒真奇了怪了。
可是,当最初几秒的震撼过去之后,台下开始有了反应。许多人(大多数是年轻的姑娘们)开始随着节奏扭了起来。如果你把那些戴眼镜穿白衬衫的三十岁男人去掉,这里跟迪厅没什么区别。又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崔健的音乐越来越感人,还是姑娘们的带头作用起得好,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跳了起来。虽然他们跳舞的样子就象他们在学生会迎新舞会上跳的那种迪斯科,但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去请那个漂亮女生跳舞会不会被拒绝,再也不用牵就学生会主席贡献出来的失真的建伍音响,再也不会因为没有舞伴而站在一旁欣赏“舞棍”们随着快三的鼓点儿丈量舞池了。他们就这么自顾自地跳着,这么旁若无人地跳着。他们兴高采烈地笑了。
当然,崔健还是给了每个人卡拉OK的机会。他唱了《花房姑娘》、《一块红布》、《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南泥湾》和《解决》等大家熟悉的歌曲。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他用放慢了很多的节奏唱了那首《一把刀子》,听起来更有一种“恶狠狠”的感觉。台下的听众对这些歌的反应很一致:当崔健唱起《新长征》里的歌时,人们就都一起跟着唱,同时还象拜里红痔似的左右摇晃着高举的双手;当崔健一唱从其它三个蛋里选出的歌时,人们就闭上嘴跳舞,象吃了摇头丸。
演唱会上最感人的是他唱那首专门献给留学生的歌曲《出走》时,台下人们都一字不落地跟着唱。那些在国内读完大学的,出国超过三年的人们,当你们听到“望着那野菊花,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哎呀!”这样的歌词时,你们能不想家吗?!
老崔那精瘦的身体里似乎藏着个正转的,连跳带吼了两个小时愣是没事儿。我跟着唱了几首歌嗓子就哑了,跳了一会儿舞小腿肚子就开始抽筋。不过累是累,那感觉可真是舒坦极了。
环顾四周,人们在黑暗的掩护下,在舞台音响强烈的刺激下疯狂地扭动着。我突然想到,这与我当初听崔健的情景有多大的不同!那时的我总是躲在蚊帐里,头戴耳机,手拿歌词本,象学毛选一样对崔健的歌字斟句酌,生怕漏掉点儿什么隐藏着的涵义,一直到唱老崔的歌不用看歌词,用嘴当伴奏连过门都不带错的地步,才算出了师。当初父辈们背诵老三篇也不过如此吧?
可十年之后的现在,我们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崔健的歌词却越来越长了,难怪姑娘们总是说崔健不实实在在。可听了老崔的演唱会我才突然发现,崔健其实早就不想让我们背歌词了,他想让我们尽情发泄,让我们在强烈的节奏下撒点儿野。
崔健变了。他已不再为蚊帐而写歌了,他开始为舞台写歌。说唱乐在蚊帐里听会显得嘈杂而不合时宜,可在舞台上它却是最有力量的。说起这一点,我发现所有的音乐都可以归纳成两类:适合现场表演的和适合家里听的。在唱片业还不发达的过去,音乐多半是前者。劳动人民要想听音乐要么自己会弹,否则多半会去戏园子或者小酒馆,或者就是在打谷场上围成一圈欣赏民间艺人的表演。这类音乐多半是娱乐性很强,而且很多都非常吵。当人们把唱机买回家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听音乐变得越来越容易,音乐也有机会从纯娱乐变成一种所谓“高雅”的精神享受。举例来说,你一个人在家听窦唯那张出色的《黑梦》专辑就很容易进入他刻意营造的黑暗而封闭的世界,可当窦唯站在红勘体育场中央唱着那些冥想似的歌曲时,我只是感到有些不伦不类。大德高僧的经文写得再好,你也不用买票去庙里听啊?没有唱片的话,象《黑梦》这类音乐形式就不会有存在的空间。这是唱片对音乐的一大贡献。
唱片的另一大贡献是传播新的音乐形式。近一百年来在世界各地诞生了无数种音乐形式,它们大都是由唱片为媒介开始在世界上流行的。这些音乐形式大都来自民间的表演音乐。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先有了黑人大批进入美国北方城市,黑人酒吧开始为这些城市黑人演奏适合他们听的音乐,才诞生了现代布鲁斯;是先有了黑白混居,互相模仿,才有了最初的摇滚乐;是先有许多贫穷的城市黑人青年在街头放着录音机,然后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跟着说,才有了现在十分流行的说唱乐。这些音乐的反对者们与其说是不喜欢音乐,不如说是讨厌它们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由白人传给我们的源自黑人的摇滚乐,但却仇恨同样来自黑人的说唱乐,而且还恨得咬牙切齿呢?
中国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民间娱乐活动被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现代流行音乐完全是由海外流进来的唱片所带动起来的,国内的民间基础(现场演出)则是后来慢慢形成的。这一民间基础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国内唱片工业的发展方向。如果你抱怨国内的港台歌太多,那么你得先去各地的演出场所转转,看看那些歌厅里都是什么人在“消费”。如果你抱怨国内的摇滚乐太差,那么我劝你先别忙着骂乐手,而是去国内的演出场所走走,数一数有多少歌手在唱港台模式的卡拉OK,有多少人是在摇滚?中国的民间摇滚乐手极少,演出机会更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能有几个不错的摇滚乐队真是很难得的。在这个人们都是通过听唱片来认识音乐的时代,听者自然会习惯性地去分析唱片的所谓“意义”,而忽视它们的娱乐性。
崔健的新唱片则换了一个思路。他用急速的说唱把国人听惯了唱片的耳朵同大脑之间的线路切断,让人们暂时忘记歌词背后的那许多深刻意义;他用长长的无旋律的歌词把耳朵同嘴巴之间的线路切断,让人们暂时忘记卡拉OK这一单一的娱乐方式;他又用强烈的节奏把耳朵同身体直接连在了一起,他要人们尝试另一种参与方式:随着音乐跳舞。崔健用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把音乐从蚊帐中拉进了音乐厅,他让我们象我们的祖先们常做的那样,直接欣赏那原汁原味的,没经过录音室加工过的音乐。
崔健成功了吗?我不敢说。但据我观察,那天晚上来听音乐会的人大多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去。我们不知道说唱乐是洋人的东西吗?我们知道;我们不爱国吗?这要看你对爱国的定义;我们认定说唱乐最适合中国人吗?未必。不过既然现在还没有那位音乐家能找到最适合我们的音乐,还是让老崔试一把吧!他毕竟还在说中国话。中国国内有很多音乐人都在作这个试验,别只盯着崔健一个人不放。我是学生物的,我有一个忠告:不能对一个人盯太久,否则你会出现诸如此人身后长了条“摇来摇去的尾巴”这类幻觉。那样可就会影响寿命了。
谢谢红豆豆为我讨大价钱。回头分你一半。:)
Thanks for sharing:)
刚才还是南泥湾,怎么就变了
每次听这首歌,我也是烂豆子一地阿,呵呵
啤酒弄洒了没关系,你已经把我往酒鬼路上带了,那微熏欲醉的感觉真让人忆起初恋那会儿。,,
老崔和那众多的老啥老啥,伴我们慢慢成长,逐渐老去,没有声息的溶合在我们的生命和内心,听着个某只歌回到某个场景,那个人,那件事,那段日子,那份心情,仿佛大树的年轮。新的老崔也许也仍然fuse进我们的生命,只是那是不一样的年轮了。
还有,不许你们再说我天真,那不是“傻B“的客气用语嘛,我至于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