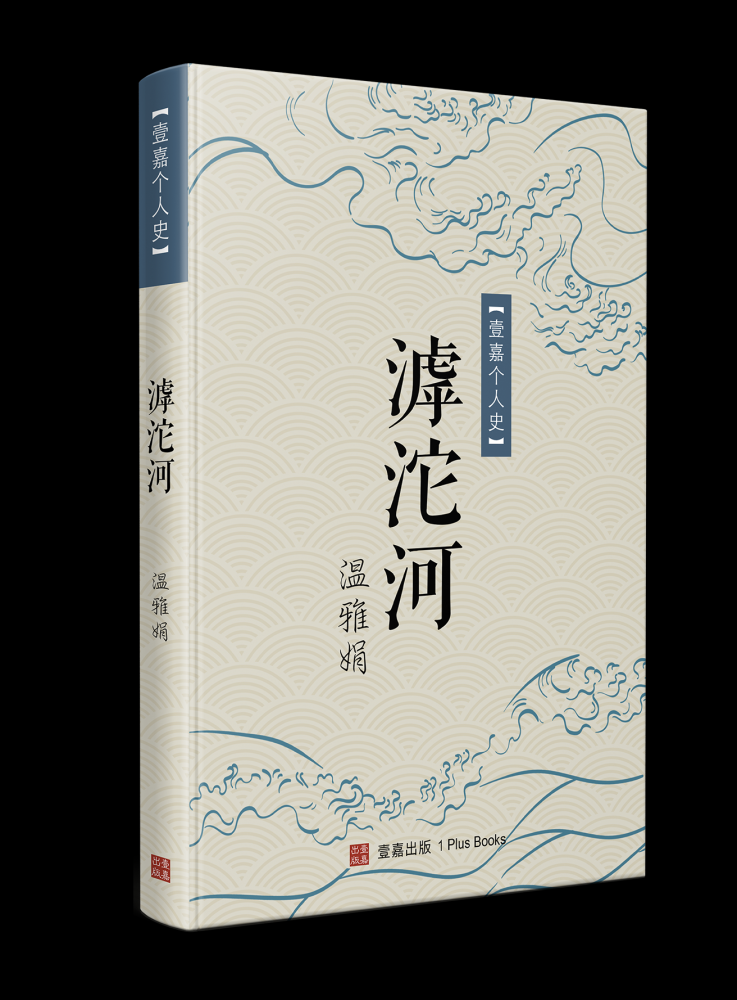大跃进时期,温象桓在包头机校担任教师。戴着右派帽子的他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却不料因为懂冶金技术,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真的练出了钢,成为一时红人。而他自己则“一直纠结于炼铁过程中巨大的浪费,也不知道自己炼出的钢到底碳含量是多少,能用做什么”……本文摘自壹嘉新书《滹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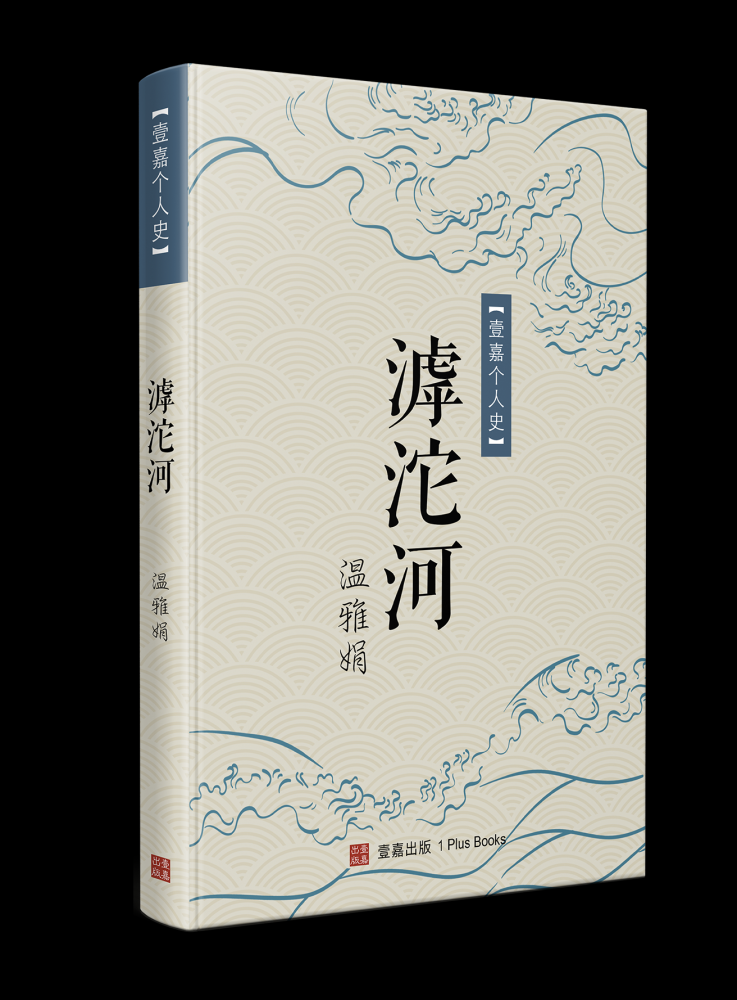
《滹沱河》 温雅娟著 壹嘉2022年6月版 点击购买
《滹沱河》记录温象桓,一位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人生。民国乡绅家庭,家道中落,烈士子弟,党的宠儿,红小鬼,大学生,右派,歧视、迫害中找到真爱,收获家的温暖……温象桓的一生,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也给那段历史提供了难得的注脚。
土法炼钢专家
白云鄂博是一座海拔1783米的圆型山,位于包头以北149公里处,地处阴山北麓敕勒之川的乌兰察布草原上,蒙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1927年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首次发现了它的铁矿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数次地质勘探和考察,国家决定利用这一矿产资源建立大型钢铁企业——包头钢铁公司,并成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包钢尚在建设中,还没有正式投产,白云鄂博的山头上则早已插满了红旗,开始了大跃进时期哄抢式的开发。与此同时,挖煤也在紧锣密鼓中大干快上。在包头南端,隔黄河与之相望的是地处毛乌素沙漠的鄂尔多斯。在这个蒙语为“众多的官帐”的沙漠腹地及黄河冲积平原上,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70%的地表下埋藏着乌金。8月17日,中央发出《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要求以后各部门、各地方将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其他一切工业“为钢元帅让步”。与此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铁炼钢。就在包头北部新城乡的前口子,在一块空旷的荒地上,几十万包头人在市委的统一组织和部署下,动用人海战术挖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巨型坑。那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场面着实让人震撼: 先是将一车一车来自鄂尔多斯的煤,有几百吨之多,倒进大坑里垫底;然后把一车一车来自白云鄂博的铁矿石,有几百吨之多,也倒了进去。来自大青山上刚刚砍来的泛着青的松树也被当做燃料扔进坑里。终于点火了,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势升腾起来,越烧越旺,红透了天空。人群沸腾了,市领导激动万分地颤抖着声音在大喇叭里广播:“我们点火了!我们炼铁了!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这个好消息!”这也叫炼铁?我简直要晕了。从古至今,自从有了铁的冶炼技术,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人类的文明才大大向前进了一步。但冶炼是一个技术活,铁的熔点要超过1500℃,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用煤炭木材去烧,永远也达不到这个温度。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耗费了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竟然如此没有章法、没有技术,令人汗颜。可是我什么都不能说,我的“界限”在哪里,我清楚。几天以后,我们眼见着温度不够的铁渣混合物软塌塌黏乎乎地扒在大坑里,在炉火褪尽后渐渐变成一堆黑乎乎的矿渣。这些矿渣不得不废弃,后来被堆放在去一电厂、二电厂的大路两旁,像山一样绵延起伏,没有尽头。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大炼钢铁热衷追捧。党委副书记于峰和主持教学的副校长童昊天都认为,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打乱,大炼钢铁这项政治任务可以在周末去做。他们实在是没有看清形势,低估了老人家对于钢铁的执着和痴迷。老人家不是一个工业专家,但他能轻而易举地背出每一个国家的钢产量。他的脑子里全是钢铁,超过英国就意味着超过它的钢产量。8月下旬才提出1070万吨的目标,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钢产量只完成了450万吨,不全民炼钢,1070怎么能实现?这是国家大计,谁敢质疑?市委机关报《包头日报》对包头机校的冷淡予以点名批评。文章说,在全市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包头机校领导不够重视,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与全市和全国极不协调。市委对此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改正。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批评,校领导显然是慌了。那么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学校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大炼钢铁冶炼办公室,进行全面领导和协调调度。陈烈学的是热加工,我学过冶金,我们俩被任命为冶炼办公室正、副总指挥,负责从小高炉建设到炼铁炼钢的一切事宜。学生马上停课,大队人员马上开往白云鄂博去采矿;还有一部分人专门留在实习工厂,把运回来的大块矿石用小榔头敲碎。小高炉要马上垒起来,火要马上点起来,刻不容缓。而此时,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小高炉已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尽管我学过冶金,但对土法冶炼却没有一点把握,我提出要去兄弟单位参观学习,领导立刻批准,给我和另一位同事开了介绍信。我们选择了几家在报纸上连篇累牍介绍经验的单位,实地看过才知道那不过是骗人的谎言,没有谁能炼出真正的铁,更不要说钢了。我和陈烈这对黄金搭档开启了我们俩一生中最默契、也是最完美的合作,我们决心用土洋结合的方法,用最科学、正规的方法搞一个小高炉,我设计炉体,他设计管道和线路。上面催得急迫,我们只能通宵达旦地工作,一个晚上就把设计图纸完成了。学校工作的重心全部围着小高炉转,我们需要什么,领导马上批,马上办,一路绿灯。不出几天,我们的小高炉就平地而起,屹立在后来统称为“小高炉”的那块荒地上。这个小高炉外部是用砖砌的,内部是耐火材料涂层。我们特意聘请了一个河北省的泥瓦匠来砌炉,他的活干得整齐漂亮;高炉所需的鼓风机和电机是直接从学校实习工厂的机床上拆下来的;校领导还动用了社会关系,从二机厂借来吊车用于往高炉中投料,并从他们的炼钢高炉处拉来一车焦炭。在我们看来,焦炭提供的高热值是炼铁能否成功的关键。机校的小高炉终于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喜庆气氛中,在众多的掌声和注视中点火了。对于校领导来说,点火的意义非同寻常,与其说它是一个“起点”,不如说它是一种姿态。在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形势下,如果没有这种姿态,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将功补过、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关键时刻,我心里充满了“好好表现”的决心和动力。时间已是秋后,天气越来越冷,学生们轮流上岗,我和陈烈几乎白天黑夜守在那里。这一天下来,不炼出红红的铁水,不完成当日指标,我们是不能回去睡觉的。高炉中焦炭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源源不断地释放着巨大的热能;鼓风机呼呼地吹个不停,仿佛电光火石轰鸣作响,使人忘却饥饿和寒冷,长时间保持一种莫名的亢奋。所谓炼铁,就是把金属铁从铁矿石中提炼出来,它是一个还原过程,即把铁矿石中的氧化铁还原成铁碳合金。在实际生产中,纯粹的铁是不存在的,炼铁得到的是铁碳合金。当炉腔的温度达到1300℃~1400℃时,铁矿石在熔剂的作用下逐渐发生熔解,矿渣等杂质的比重轻,漂浮在铁水上部。所以高炉炼铁首先要排掉炉渣,然后才能得到铁水。我带头用铁锹捅开用耐火材料封堵的出渣口,液体的渣像一条小河一样流了出来。待炉渣流净后,再打开位置稍低的出铁口,红红的铁水也像小河一样流了出来。我们把它浇在模子里,铸成铁锭。这些极高危险的高温作业,都是我和陈烈带领学生用极其简陋的手工工具完成的,我们把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溶化到了血液中。党委副书记于峰经常来我们的工地给我们加油鼓劲。他穿一件黄绿色的军大衣,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有一天晚上,他叫住挥汗如雨的我,说:“小温,来歇一会儿,”并顺手递给我一支烟。我赶紧双手接过这支烟,犹豫了一下没有点燃,就听到他开口说话了:“小温啊,我就不明白你是怎么打成右派的。我看到你这么踏实、这么肯干,你是怎么打成右派的?啊?”他一连问了好几遍,也不听我回答,就连珠炮一样又问了起来:“你们单位是怎么搞的?怎么把一个这么好的青年,一个烈士子弟打成了右派?”这是我来到包头一年多以来第一次由党组织跟我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是非官方的谈话,用这样质疑的语气。他一下就戳痛了我的泪点,这一年多以来,我像一个鬼一样封闭在自己幽暗的心灵世界里,如今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投入大炼钢铁,不就是为了让党看到吗?我终于按捺不住,任眼泪决堤,无声地滑落。他吸了一口烟,盯着炉火,眼光似乎凝固在他的回忆中:“你刚来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你的档案,看了你打成右派的材料。我认为一个革命烈士后代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单位简直是胡闹。”“他们说我忘本了”,我忍住啜泣小声咕哝着,我的冤屈终于有人理解了。我感激地望向他,任眼泪一泻千里。“在你的工作安排上,党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虽然没有权利给你平反,但我们可以安排你上讲台,发挥你的专长。事实证明,你是一个好教师,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顿了顿,接着说: “为了不影响你好好工作,我们当时就决定为你保密,不让学生和教工知道。”让我费尽心力猜测的真相原来是这样。虽然我的秘密通过别的渠道泄露出去不胫而走,但党委却从来没有因此歧视过我,他们对我的保护难以置信得像一个美好的童话。终究是因为我的父亲啊,他的在天之灵一直在默默看护着我。我突然觉得我不再是个孤儿了。于书记看着我笑了,他拉着我的手用力握住,说: “你放心!好好干,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对你的问题进行甄别。千万不要背包袱。”他放开那只温暖有力的手,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我望着他离去的方向,久违的欢喜和安全感将我包围。虽然天气寒冷,虽然极度疲劳,但我下定决心,要用更踏实、更拼命的干劲来回报于书记和党委为我所做的一切。怎样把铁进一步炼成钢,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现代科学的“洋”办法施展不开了,周围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怎么办?我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研读,终于从老祖宗——明朝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找到灵感。俗话说百炼成钢,炒钢是老祖宗让我脑洞大开的好办法。在高温高压下,生铁再次熔解成糊状金属,利用罗茨鼓风机吹风,经反复搅拌,令生铁中所含硅、磷、碳等杂质氧化,从而把碳含量降低到钢的成份范围。在冶炼过程中要不断搅拌好像炒菜一样,“炒钢”因而得名。我凭着一腔热血和激情再次设计炉体,把炒钢这件事变成了现实。炼钢的过程纯手工操作,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设备,仅凭经验和估计判断,我们把含碳量高于2.3%的生铁硬是铸成了钢。看着那红红的一大块在铁砧板上被学生们抡起斧头千锤百炼,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包头机校不仅炼出了铁,而且炼出了钢,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远,让我一夜之间成为星光熠熠的名人,一个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还有创新技能的土法炼钢专家,在大跃进中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哪个单位炼铁炼钢出了技术问题,就会派领导的专车接我去做技术指导,单位领导往往以最高的礼遇招待我吃一顿食堂的小炒。我这个右派就这样红了起来。这个过程持续到12月初,冬日的严寒让遍地开花的小高炉不得不偃旗息鼓。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宣布: “一年之间钢产量翻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 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我心里一直纠结于炼铁过程中巨大的浪费,也不知道自己炼出的钢到底碳含量是多少,能用做什么。既然1070万吨已经实现了,那么我所纠结的东西也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滹沱河》的作者温雅娟,现居加拿大温哥华,是一位注册审计师,为了替父亲完成他记录自己一生的心愿,她辞去工作,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本出色的处女作。娴熟、优美的文笔之外,作者以女儿的身份,成功地进入父亲的角色,将作为上一辈人的父亲的所历、所感、所思、所悟表达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同时,她也成功地将时代、地域等环境因素嵌入到书写之中,为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氛围。点击这里阅读《滹沱河》节选《执子之手》。
作为一位初次写作者,温雅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她是怎样起了为父亲写传的念头,又是怎样搜集资料,怎样采访,怎样取舍?为什么采用第一人称,而且做得如此成功?欢迎带着你的问题,来参加11月5日壹嘉出版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的《滹沱河》新书发布活动,与温雅娟通过 zoom 直接交流。(请扫描下面海报中的二维码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