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喝茶,聊天,会友 - 壹嘉出版网上会客厅
美国独立中英文出版机构壹嘉出版网上会客厅,以发表壹嘉书摘、人文资讯为主“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 --李慎之
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国著名的体制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便参与组织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毕业后加入新华日报,后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多次作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外交出访活动。1957年,他因为倡导"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改革开放后,他先后陪同邓?平、赵紫阳访美,并受命创办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学生运动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务,开始提笔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纪念,原因不仅仅是他几起几伏的为官经历,更重要的是他离职之后奋笔疾书写出的几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极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李慎之厚积薄发,提笔作枪,为自由正名、为民主摇旗、为启蒙呐喊,书写了他一生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
本文节选自壹嘉新书《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档案中的自传、检讨,以及他?根据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写的文章和书信,或者源自他人对李慎之采访的文字记录。因此,本书可以说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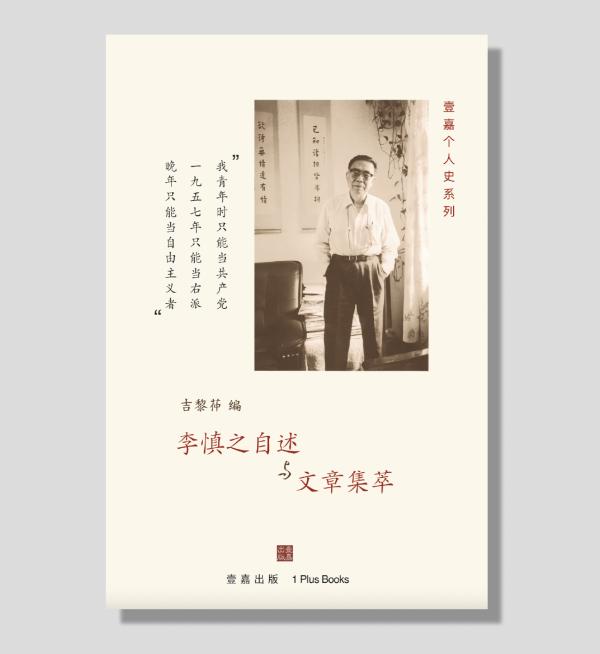
一,我编“内参”
后来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五十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从二十大开始,我自己下的命令,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三十二页,中午版二十四页,晚上版二十四页(有时三十二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晚上七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实际上送到我的桌子倒是真的,我不了解中央同志们,两点钟根本没人看,要到晚上才看。这样“一日三参”,八十块十六开的版面,尽管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有十几万字,数量是很大的。我当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
那时新华社还有一个任务很忙,到五一节就赶快打电话、打电报给莫斯科,“挂像怎么挂?斯大林还有没有?”反映过来,“有,很少。主要是列宁的”。这些毛都非常注意。这个不上《大参考》,上《内参》。

1945年李慎之燕京大学毕业照
我还有任务,要搜罗全国、全世界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要求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或者党报或者中央的正式意见反映,就是《批判斯大林文集》。外交部有个会,张闻天主持,就外交部几个司长以及我们新华社跟广播电台,我是每礼拜都去,姚溱1也挤进去。他知道有这个任务,就去跟陆定一请缨,由他和我合编,因为材料都在我那儿。合编可以得到一点稿费,我认为这几千块钱稿费是大家翻译的,我不过编一编,我有什么资格拿这个钱呢。而且编的条例都是毛主席规定的。所以我以我同姚溱的名义请了两桌谭家菜,那个很贵,最高标准280元,请吴冷西等人吃了一顿,我生平第一次吃谭家菜,唯一的一次。剩余的还有2000多块钱,全部交给参编部的小金库。陈适五就讲:“你们今天都是吃的斯大林。”
吴冷西差不多每天要去毛主席那儿开会。他进宫以前总要找我问一问,了解最新情况。我也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权利,他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当时我被认为是消息特别灵通的人士,不是一般人呐,乔冠华见我面,[都]问我:“老李,有什么消息?”
【1】姚溱(1921年3月20日~1966年7月23日),曾用名姚静,化名姚澄波,江苏南通人。曾任新华社华中二分社社长、华中总分社副编辑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科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处长、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文革开始不久,遭到诬陷和迫害,含冤去世。
二,波匈事件后
在一九五六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王飞和我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林克本人自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时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十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按: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开八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一定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
整个一九五六年,是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高饶事件与先是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后来又扩大为肃反的运动都随着一九五五年过去了;也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这一年开头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私营工商改造完成的喜报,然后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了。三月份的苏共二十大推倒了斯大林,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去除了不少思想上的压力。接着就是四月份毛主席发表有很多新思想的《论十大关系》。五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更多的人心情舒畅、思想活泼,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
三,会错意、表错情:“大民主”的提出
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至于毛主席引用王凤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是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我还因此而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
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要搞“不断革命”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时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却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促使我这样想的原因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他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至少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王飞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吴冷西没有任何反应。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得最多。“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这样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古来未有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
四,钦定“右派”
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因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绝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会整人的领袖。另外,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
不过林克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话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家就住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还是并不在意。
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去了。后来总理跟陈毅访问十六国好像常有人提,其实这两个价值至少相等,甚至于前者更大。总理跟贺龙访问十一国。我们还是老班子。从越南开始,然后柬埔寨,然后缅甸,然后印度,等等。

1950年周恩来的外交班子合影,后排右四为李慎之
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尤其是毛主席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头上要长犄角”,“要敢唱对台戏”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以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五,“最后一次跟党一致”
凡是右派都是背后先做结论,当面,头一天这样开始,说:“我们最近发现李慎之有些言论很不寻常,我们大家来给他辩论辩论。”
总理我不敢找,但我敢找吴冷西。他跟我讲:“你当年争取民主,是向国民党争,现在你怎么向共产党争取民主。”当时我真是眼泪往下滚。一般他还能听我说,我说完了他就说:现在我要去中央开会,你有什么问题找穆之谈。朱穆之跟我的交情不够,我找吴冷西也可以说是百无聊赖,满腔冤屈无处申诉。还有一条:恐惧,怕是怕得不得了。我这一辈子可以算是红干部了吧,一有特别的任务就是李慎之,这一下子掉到十八层地狱。

李慎之1957年的日记本
我在划右派以前,干了一件事情。南斯拉夫有德热拉斯,写了一本书叫《新阶级》,受这本书教育的青年非常多,但他们看的是后来新华社的译本。台湾的中央社在反右前期全文翻译出来,一大厚本。我下的命令在《参考资料》全文发表。这是我最后一次作这种决定,幸好没人提到,要提到的话,这是向党示威,反党行动。发完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李慎之你上场吧!我简直无脸见父母,父母不在北京无所谓,老婆、子女,前面后面的院子。我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关着灯,到十点过了以后,我才敢回家。
我无法交待清楚我的错误言行。忽然发现王飞的抽屉,锁上留着钥匙,连忙偷偷拿出来,拿到我的办公桌上,因为在人家的办公桌如果被人发现怎么办?在我的办公桌上打开灯一看,原来都是揭发我的材料。王飞后来老年痴呆症,我没法跟他核对了。可能他有心救我一下。这下我得其所哉,明天要揭发斗我,先说两句不着边际的话,慢慢再对上号。“瞧,李慎之态度好的。”本来没法态度好。王飞那时是国际部主任,是斗争我的小组成员之一。他真尴尬极了,他跟我思想根本一样,但他要揭发我,我对他是绝对原谅。
王飞请求,甚至可能会说:“我也有点不干净,还是请邓岗主持”。所以由邓岗来主持批斗我,邓岗跟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也无交情。他还可以,前后斗了一个月。
到给我做结论那天,也就是开除我党籍那天了,专门有人跟我讲,“你一定要自己举手!”理由很简单:“你要最后一次表示跟党一致。”我也知道这逻辑有荒谬性,但是表示一种忠诚吧。
王飞还是领导小组成员时跟我谈话,没别人在场,“老实承认错误,你的态度,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再过一次、两次运动,立功表现(好),还可以入党嘛。”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多少人怀着重新入党的希望”。
有一点,就是想绝不带害一个人。第一个受我带害的王飞,文革中造反派找我写揭发他的材料,我极力地帮他说话,后来等我平反了以后,我交给王飞看过,那时候他还没得老年痴呆症。他说“你很不容易的。”第二个典型就是乔冠华,说乔冠华跟你差不多,你应该好好揭发他来立功。动员我的是我们党委书记,因为外交部来要材料。当时我就说我这个人有点骄傲自大,我只记陶里亚蒂、南尼这些人的这些话,就算把他搪塞过去。其实乔冠华有些话比我还厉害,硬是讲到两党制。他说两党制也有根据,可能是我告诉乔冠华的,内部参考登了一条消息,苏联有两个院士主张搞两党制,结果被苏共开除党籍。毛主席看到这个了,就在常委会议上讲,吴冷西回来传达的,说“苏联为什么把他们开除呢?要是我啊,我就要专门向他们请教,你这个两党制怎么搞法?”我把这个话告诉乔冠华了,乔冠华可能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跟我吹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所以我没多说,他倒说了。就这样传来传去。要问我他到底说了没有,我也不知道。
批判李慎之以前先进行一个练兵运动,叫做反对温情主义。出墙报,说:“有些人认为李慎之业务不错,不能这样看,剥开皮来看是一条毒蛇。”国际部有两个人,号称李慎之的金童玉女,是我的重点培养对象。金童你们不知道,玉女就是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起来批判说:“李慎之是反动,他怎么怎么瞎说。”李慎之忽然身份改了,说“李慎之业务上是强的,政治上不行的。”本来我高明就是政治上,凡是像我那种经历的都是政治上强的,一变成右派就政治上不行了。
我是要极力用感情压制自己的理智。我现在只能够接受,说我是背叛了党的原则,这一棍子打下来,打死了。我的办公桌上有个日历,中干才有,上面我写“一错百错,直滚下坡;一切维党,诸法无我。”没有我说话的余地。我觉得是舍身饲虎,用一切荒谬理论自我解脱。这就是我的实际过程。我后来对佛经下过点工夫,这过程其实也不长,顶多两年。我真正内心深处是不服,但上面我不断地加一层一层地涂料,一个字,要“服”。叫做缴械投降。我有什么“械”呢?“械”就是你要坦白。好不容易王飞救了我一把,否则我坦白不出来。人家说“李慎之你不要不老实,现在请谁谁谁来揭发。”开头叫辩论。我还想辩。我有一个冲动,李慎之还有足够的聪明,当时我记得很多,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说的什么,后来一想,我要一说这个,完蛋!那就更逃不了了,人家就说“你污蔑”。这一点我没做。第一不揭毛主席。我是学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但是我全忘了,自信归命正宗共产主义了,到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冒起来了,冒起来又要往下压,完全用忠君、忠孝的思想来置换民主思想。专制主义确实厉害,“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我也一再念的。我经常这样问“毛主席能错吗?”只有李慎之错了,哪能毛主席错呢?第二“是我领会毛主席的话领会错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他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的结果。
毛选第五卷,毛有的话是留了两面性的。冷西跟我讲的时候也都讲到了,但是我只记得对我有利的。极力说服我自己,毛主席不是像我这样想的。前两年把毛选第五卷仔细看了,他里头还有句永不忘记的话,“毒草可以肥田。”我就是毒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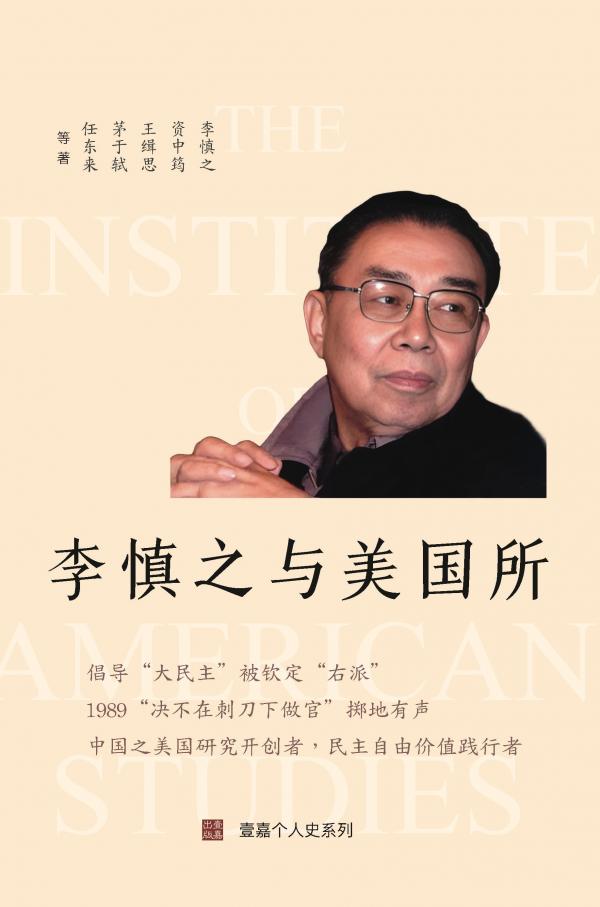
《李慎之与美国所》 不明白播客丁学良教授推荐

资中筠先生最新自选集《夕照漫笔》上下卷持续热卖中,各国亚马逊及其他网络书店有售





的制约不可或缺。
说到底还是“人之初是心本恶,还是心本善”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