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857)
2023 (2384)
2024 (1325)

艾伦·麦克法兰、赵鼎新对谈:重拾现代生活的精神地图
10月19日,英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与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赵鼎新做客北京万圣书园优盛阅读空间,共同进行了一场名为“重拾现代生活的精神地图”的漫谈。
 “重拾现代生活的精神地图”《宇宙观与现代世界》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重拾现代生活的精神地图”《宇宙观与现代世界》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1
将“不可见的”宇宙观变得“可见”
什么是宇宙观?它如何塑造文明?艾伦·麦克法兰在《宇宙观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探讨了西方尤其是英语文化圈的世界观变迁,借助人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视角,分析了不同文明的思维体系如何映射其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并随着技术和权力关系的演变而悄然改变。
活动现场,麦克法兰表示,所谓宇宙观,是一整套关于信仰、观念和假设的思想体系,它处于最高层次,如同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是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底层思维框架。他引用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的名句生动地说明这种隐形性:“鱼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鸟乘风飞,而不知有风。”我们所处的宇宙观,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它高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paradigm)和福柯所说的知识型(episteme),是所有学科理论的基础框架。“范式”和“知识型”处理相对具体一些、不那么宏大的学术领域问题,而最底层则是各种具体的理论。麦克法兰指出,他这本新书的工作,正是试图将这种“不可见的”宇宙观变得“可见”,解释我们当今所具有的世界观是如何历史性地形成的。
那么,中西方宇宙观的本质是什么?麦克法兰指出,西方思维模式根植于希腊逻辑,其核心是二元对立。例如,善与恶、黑与白、男与女、天堂与地狱、真与假。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构建了整个西方价值体系的基础。在艺术领域,自文艺复兴以来,绘画(视觉艺术)与诗歌(语言艺术)就被视为分离甚至对立的领域,被称为“哑巴的绘画”与“盲目的诗歌”。而中国文明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强调阴阳调和与万物互联。赵鼎新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没有发展出复杂的技术与思想(如宋朝沈括的成就),而是中国文明很早就走向了不同于以归纳、分类为基本逻辑的西方科学的路径。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早期周代思想,更注重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理解。正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当我们为某个事物命名时,就可能丧失对某些无法以语言清晰表述出的本质的把握。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这种整体性、关联性的思维,早在量子力学理论确立之前就已出现,展现出其前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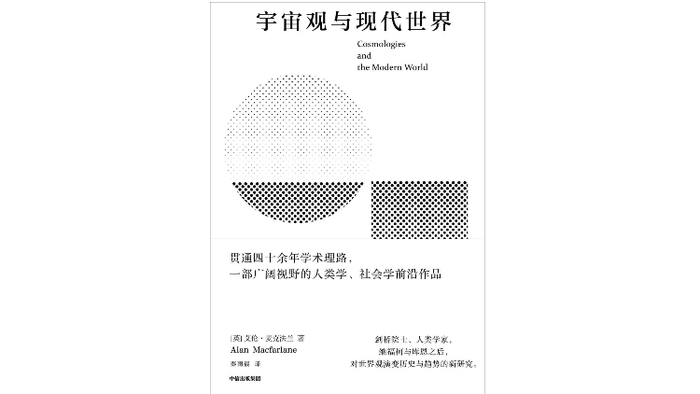
《宇宙观与现代世界》
作者:艾伦·麦克法兰
译者:秦雨晨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3月
宇宙观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这里,麦克法兰提出:思想体系的变化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在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曾将中国视为理性治理的典范,充满仰慕之情。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欧(尤其是英国)在技术与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后,这面赞赏的镜子骤然翻转。到了19世纪,在西方视角下,中国似乎迅速从“典范”跌落为“停滞”“落后”乃至“野蛮”的文明。麦克法兰坦言,这种“帝国的傲慢”曾是他所受教育中“隐性甚至显性”的一部分。当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对等时,时间观念不会有突出的改变。然而当一方明显掌握了权力,这一方就会认为自己更优越。
对于中国曾被西方认为“落后”的原因,赵鼎新认为,在西方传教士一开始接触中国时,曾经有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分歧,即为了更好地传达上帝的福音,是否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最后认为无须过多适应中国文化的多明我会等取得胜利,这也间接地导致中国的形象在此后开始被认为不如西方先进。不过,西方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从“典范”到“落后”),根本动力在于欧洲自身通过工业革命和扩张取得了军事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需要一套话语来证明其合理性,从而将中国构建为“停滞”的他者。传教士的争论只是这个宏大叙事转变中的一个侧面,而非决定性原因。而今,权力格局再次发生转变,问题变为:当中国变得强大时,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西方?这一动态深刻揭示了文明间的认知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常常是权力投射的影子。
2
学会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文明的多样性
在《宇宙观与现代世界》一书的序言中,麦克法兰曾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危机四伏且极度分裂的世界中。我个人采取的方式是深入研究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探索问题的根源……这种困局部分是西方文明所致,是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技术变革的产物,而其中的多数变革我都无力控制。这些变化已经持续数千年,如今,当我们从新冠疫情中逐步恢复,对生态、人工智能、文明兴衰等领域的新威胁和新机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这些变化进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这并非易事,因为它要求我们识别并应对周围的意识形态、社会及其他压力,如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就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中的苍蝇。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甚至找到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始理解围绕我们的‘瓶子’的本质。”
在对谈中,麦克法兰回顾了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信仰体系的摧毁性打击。19世纪末,西方坚信历史是线性进步的,文明如同阶梯,西方自居顶端,鼓励其他文明“攀登”。然而,1914年,这些自诩“理性”“优越”的国家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血腥屠杀,约千万人丧生。麦克法兰指出:“我们真的那么理性吗?我们的信念被彻底粉碎了。”那些自诩最先进的国家,却用最野蛮的方式互相屠杀,信仰体系随之崩塌,社会科学也从进化论转向了关注当下社会机制的功能主义。在这里,麦克法兰将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类比为一场堪比“一战”巨变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政治和经济。
麦克法兰提及自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收到大量年轻人的留言,他们倾诉对就业、人生意义、幸福真谛的困惑与焦虑,“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他强调,“西方年轻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正经历一场更深刻的存在主义危机。他们不仅担心工作,更开始怀疑民主制度本身、怀疑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能带来幸福、怀疑宗教的意义。”
面对差异和冲突,未来的出路在哪里?麦克法兰指出,有人认为不同文明最终会融合成一体,但这就像希望一棵橡树长成山毛榉一样,是不可能的。他给出了两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比喻。其一是树的共存:每条街道上都生长着不同的树,它们各自挺拔,共同构成美丽的风景。其二是交响乐:乐团里有钢琴、小提琴、鼓,它们各不相同,各司其职,但在一起能奏出宏伟和谐的乐章。他认为,未来的图景并非一种文明同化另一种,而是像油与水一样,虽然难以融合,但可以共存于一个容器中,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交响乐状态。“我们必须学会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文明的多样性。”他总结道,“差异不是威胁,而是创造力的源泉。”
记者/何安安
速记整理/王凯莉
编辑/刘亚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