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托克维尔的自由 不是美国人追求的自由
对托克维尔说“不”!
美国人极爱引用托克维尔的言论,但这位法国人的真实人生和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

我们印象中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一位有着忧郁眼睛和邋遢发型的法国人,但他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错误的印象统治着美国,几乎把托克维尔塑造成了一位现如今用法语进行写作的最著名之人。尽管他是一位已经185年没有踏上过美国领土的法国人,但他的名字却经常作为自由的象征,出现在美国本土的出版物中。
《纽约时报》就是一例。1月13日,在一篇名为《自由主义后还有生活吗?》的评论中,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就提到了托克维尔的大名。仅仅两周后,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了布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评论文章《共和党理智的篝火》的开篇。此外,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去年在社论中两次提到了这位永远年轻的法国思想家,前年更是提到过三次。去年,托克维尔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社论《出国让我更爱美国》之中。此外,在关于慈善事业、律师、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夏洛特维尔事件、高级法院、美国与亚洲及澳洲关系等话题的作品中,托克维尔的名字也频频出现。
首先要问的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美国人不该引用一位来自法国贵族阶层的思想家?为什么他在法国知识界却得不到赞赏?
本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直到你发现:托克维尔的著作早已绝版,学校课程里早已不再有他的名字,而他只有在80多年前才在法国有点名气,在美国,他的名字也直到内战后才开始出现。
托克维尔成名的过程,就如同制造大炮的秘密历史。他被塑造成了一位风格优雅、极富口才的冒险者。除了这位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是如何成为自由之象征的问题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重被人们遗忘的角色:阿尔及利亚大屠杀背后的领导者和理论家。
和他的表亲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不同,托克维尔在1859年去世后几乎马上被法国遗忘了。他在法国重新登场并不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流行度,而是来自20世纪的一个极少被后人验证的项目:反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在美国白人保守主义的影响下,这项探索让公众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批判更加激烈,带来的结果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连年热销,并成为许多参议员书架上的常客。美国白人思想家们并非想以什么艰难方式来维护保守思想(比如怀疑主义、传统、进化等原则),反而围绕着哈耶克的作品、以一种盲目崇拜来复兴《资本论》,旨在一边巩固资本主义的理论、坚持历史的经济原则,一边批评左派的教条主义。
托克维尔在法国反对马克思的思潮中成为了自由的象征,因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街道曾被五月风暴及其哲学席卷。托克维尔的复兴,背后是戴高乐主义最机敏的运作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隆反对萨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支持美国人和自由市场,他不仅是支持美国白人的自由派,更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经常到访华盛顿的巴黎人。
事实上,阿隆对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就是在美国开始的。通过1963年在伯克利举办的一系列会议(《论自由》的来源),阿隆把自己塑造成了马克思的竞争者和优胜者。1967年,他在《社会学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一书中称,托克维尔的成就绝不比涂尔干、孟德斯鸠和马克思更低。而面向法国大众的首版《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马上于1968年在法国出版了。
随着学生暴动逐渐成型,戴高乐总统并没有意识到现状,反而急忙赶去德国,确认法国随北约驻扎在莱茵河的智囊团仍然对国家忠诚。但阿隆对当时的危机了解更为清晰:“我利用了托克维尔,就像其他人利用了圣·鞠斯特、罗伯斯庇尔和列宁那样。”他马上意识到,那些武装了马克思思想的抗议活动已经破坏了戴高乐的民意权威,并因此让整个社会制度陷入了疑问(当戴高乐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在1969年辞职,选在第一次重要外交访问中去西班牙马德里问候佛朗哥将军)。
阿隆意识到他需要回击,他需要一位反马克思的人物,利用他的思想来解除学生们嘴上常挂着的“自由、平等、革命”三个大词。白人对哈耶克的狂热崇拜,更接近于仅仅要推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由市场一定会带来繁荣”);而阿隆的方式则与之不同,他对托克维尔的崇拜来自于1789年法国保守思想家们对革命思想的反对,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观。
让阿隆兴奋的是,《论美国的民主》呈现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二元对立。托克维尔称,人类之间越平等,因为墨守成规的“大多数人的暴政”,人们反而会得到更少的自由。托克维尔甚至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称,法国革命总是会回到路易十四统治下的集权政府状态。换句话说,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现有的结构已经根深蒂固,无法被起义所动摇,人们永远不能逃离旧体制。这些理念共同造就了阿隆的反资本论思想:国家不仅会征服所有的法国革命,自由和平等也并不会合人心意,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是一定不会得到允许的。
雷蒙·阿隆在1968年失去了精神和智力上的双重支持,但他赢得了战争。通过与财政和政治权威的谨慎合作(也许是因为他在华盛顿特区受到休斯顿研究所智囊团的影响),他成功地创造了托克维尔崇拜,并将其植入到了法国社会中。他的自由保守主义对当时巴黎学生的意义,不亚于取得高中文凭的意义。
这些穿过大西洋去纽约思考民主的知识分子本身很有意思,但那些穿过地中海去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主义的成熟政客却并非如此。

那么,真实的托克维尔是什么样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后来的那个托克维尔的肉身并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当知识分子们为一部作品共同树立了全国性的纪念意义时,他们选择忽略的东西才能真正让我们了解哪些是他们认为无关的事情,而这就透露了他们的价值观。事实是,托克维尔对平等的敌意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有所体现,并一直延续到了他晚期的作品和生活中。
改变了法国历史的那位托克维尔,并不是一位著名作家,而1839-1851年间的一位议会成员。他在1849年曾短暂担任法国外交大臣,并指派好友阿瑟·德·戈平瑙(Arthur de Gobineau,著有《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雅利安种族理论的来源)为他的内阁首长。这位托克维尔也是1847年臭名昭著的《阿尔及利亚报告》的起草者。“我知道有些我尊重的、但观点和我不同的人,”托克维尔写道,“他们认为,我们烧毁庄稼、清空粮仓、抓捕没有武装的人,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得已的举措,是任何支持与阿拉伯开战的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些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种必要的野蛮行为”。
法国的反马克思“新哲学”继承了雷蒙·阿隆的思想,进一步贬低了集权主义的概念。他们和哈耶克一样,在越来越合理的生存环境下,在社会民主的概念下,在现在的女权主义文化下,都认为集权主义是无处不在的。但和阿隆一样,他们忽略了托克维尔在阿尔及利亚的作为“毁坏了整个国家”。比否认更糟糕的是,他们忽视托克维尔的殖民主义与法国自由主义的结合,而这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对托克维尔的崇拜有着不同的根源,尽管都一样“选择性失明”,原因却不尽相同。《论美国的民主》在1835年出版时几乎马上成名,被认为是天才杰作,但在美国内战爆发后,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完全消失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的信心也消失殆尽,他开始疯狂阅读,作品也随之逐渐绝版。
1938年,历史学家乔治·威尔逊·皮尔森(George Wilson Pierson)拯救了托克维尔的名声。在大萧条悲剧发生的同时,美国人也正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皮尔森在《美国的托克维尔和博蒙》(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一书中重塑了托克维尔的思想。这让托克维尔在最伟大的“美国必胜”信念出现之时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对命运意义的寻求也得以在1945年再现。新版《论美国的民主》分别于1945年由科诺夫出版社、1947年由牛津出版社、1954年由复古出版社、1956年由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再版。这些蜂拥而来的版本立即登上了美国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等迅速发展领域的阅读清单上,立刻成为了美国文科政治教育的奠基石。
但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论美国的民主》并不是写于林肯总统执政时期,而是杰克逊时期。那时的美国正置身“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奇怪的是,写于这一时期的一本书,却是频繁地被用来形容美国那些最杰出的优点。确实,托克维尔作为废奴主义者,既谴责美国的黑人奴隶制,也反对对原住民的压迫。但他的民主并没有涉及到这些内容,他曾写过关于工作中的幸福奴隶的文章,也坚持认为“原住民永远不会文明开化,就算他们终于意识到文明的重要性,到时也为时已晚”。前者幸福地承受苦难,后者安静地消失,这就是托克维尔忽视的地方。
托克维尔似乎在阿尔及尔和密西西比发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感。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但从美国到阿尔及利亚的距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言。托克维尔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殖民主义的全景图:从刚刚解放的殖民地美国,到即将成为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美国是他对阿尔及利亚看法的灵感来源,他在1832年写道:“阿尔及利亚,就是非洲土地上的辛辛那提。”
托克维尔在阿尔及利亚再一次发现了缺陷。在写给阿瑟·德·戈平瑙(此时他的雅利安种族理论已经发展完善)的信中,托克维尔称,一项对《古兰经》的研究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宗教比伊斯兰教更致命”,它比多神论更糟糕,“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而不是与‘异教’有关的进步形式。”衰落、卑鄙、只服从暴力,这就是他对阿拉伯的看法。
这才是真实的托克维尔:他是一个认为自己的职业是众议院殖民专家的政客,主张法国在北非建立自己的“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既想“毁掉这个国家”,同时也强烈反对毕若将军(General Bugeaud)在阿尔及尔实行的“独裁制度”。托克维尔的愤怒点在于,法国在拖慢欧洲殖民的进度。他反对的是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独裁制度,至于阿拉伯问题,他强硬地支持军事制裁。他所希望的,是美国那种白人殖民者的民主出现在北非。他谴责瑞士殖民社会把家庭派去“北美最荒芜的地区”而非阿尔及利亚的做法,因为这些殖民者更喜欢民主化的机构和和平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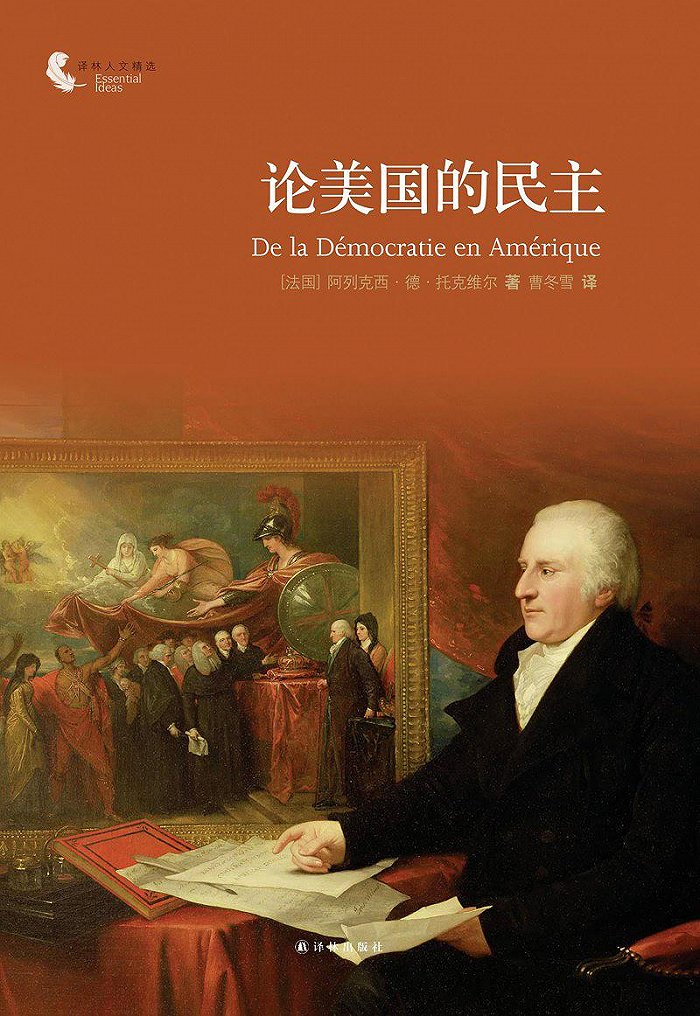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著 曹冬雪 译
译林出版社 2012年10月
在实现征服之后,托克维尔重新发现了他内心开明的君主主义者,于是劝说法国议会不要重复新世界屠杀式殖民的不人道行为,称这种行为会“给整个人类群体蒙羞”。但这并不代表他要放弃殖民主义,只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英国在印度的那种聪明绝顶的办法”。在1857年,那时的东印度公司几乎要撼动法国最强劲对手的帝国地位。他对英属印度很是着迷,甚至烦恼英国的退缩“可能会为文明和人性的未来带来灾难”。当1857年印度叛乱(Sepoy Mutiny)结束时,他庆祝这是“基督教和文明的一次胜利”。研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他未完成的杰作,是他伟大的殖民全景图的顶点。
美国人还应该继续读托克维尔吗?当然。但《纽约时报》专栏里那些谄媚和流利的引用,并不是从圣典里摘取出来的永恒真理,而是来自致力于分析和实现帝国主义的肿瘤。
直白地说,美国要学习的托克维尔,应该是那个把对白人殖民社会的赞美当作路标的作家。阅读这样的托克维尔,意味着承认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美国并不仅象征着民主,也象征着殖民。托克维尔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一样,认为在密西西比扩张着的这个伟大的白色帝国,是值得令人崇拜的。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我的论点并不是说它应该被再一次遗忘,而是说它不应该被当作富有远见的简单颂歌,被人们盲目引用。它带来的困扰远比这要多,同时也为我们揭露了更多事实。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