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
工程技术,地产投资,信仰家园,时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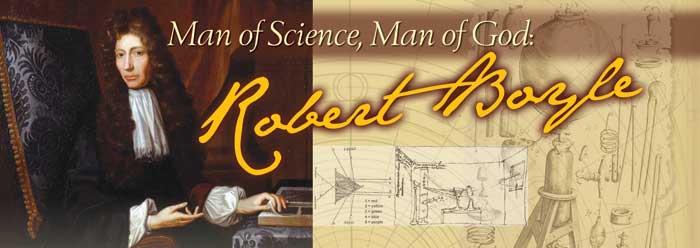
图: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英国化学家
每个人初中学化学的时候,都会学到“波义耳定律”:在固定温度下,气体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但是若问到波义耳是谁?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事实上,波义耳对后世有许多重大的贡献,他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波义耳定律”的发现者,是17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化学家。他设计的许多实验仪器和方法,成为后来化学实验的基础。

波义耳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家境富有。幼年曾就读贵族学校伊顿学院,并随家教老师学习拉丁文、法文及希腊文。12岁之后,他就再没有在任何学校接受过正规教育。
1638年-1642年,他随家教老师到欧洲游学,先去了法国、日内瓦和意大利。他阅读了伽利略的著作,这促成他终身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
1644年他17岁时父亲过世,暂住在姐姐家,并开始全心从事科学研究。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学研究者组成了“隐形学院”,常在伦敦、格莱珊学院或牛津大学彼此切磋。他一生没有得过任何高等学位,所有的知识都是靠自修,以及与隐形学院的学者交流得来的。
1654-1668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牛津,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实验(包括最著名的波义耳定律)。

17世纪,科学被称为“自然哲学”。波义耳最大的贡献在实验科学方面。他坚持以实验来印证所有的科学理论,而非仅仅是诉诸理性推论。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坚持所有的科学(包括化学),都应该以数学方式呈现的科学家。
波义耳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之一。波义耳希望借着研究科学认识造物主上帝的伟大。他有一句名言:“从对他工作的知识中,我们可以认识他。”
他的观点与德国天文学家、路德派基督徒克普勒,及其同时代许多清教徒科学家很相似。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而非经济利益成为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的主要动力。
1668年,他离开牛津,减少与外界的来往。1680年,他被推选为皇家学会会长,但被他婉拒了。他终身未婚。除了科学著作之外,他也写了不少有关圣经及神学的书。他过世前一年的最后一本著作是《相信圣经的科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是全世界最早的,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由民间发起的国家级科学协会。其前身“隐形学院”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在1663年的全体会员名单中,有62%是清教徒。

16世纪上半叶,英国国教一直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国教转回到基督新教的范围内,但仍留下许多罗马天主教的影子。于是,在英国教会内部,一直有“洁净教会”的呼声。这些异议份子或反抗运动者,就被后世称为“清教徒”。
但清教徒之间对于是否要与当权派妥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一些较激进的人,被称为“不妥协派”或分离派,他们不但成立自己的教会,甚至移民到北美洲,去寻求宗教自由的新天地。
那些采取妥协立场的清教徒,仍委曲求全地留在英国国教之内。其中除了少数人士仍担任牧职工作外,更多的人转入科学研究的行列,以传教的热诚,投入到刚刚萌芽的近代科学研究中,斐然有成。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莫顿在1938年写成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科技与社会》中指出,17世纪英国早期的科学发展与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们)密不可分。
德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大量数据分析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特别是加尔文神学)鼓舞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基督新教的“天职观”使每个人的职业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它激发出人的潜能,大大提升了生产力。
虽然韦伯的理论曾遭到批评,但基本上还是广受支持的。莫顿延续了此理论,发现17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也有明显的宗教因素,特别是英国清教徒运动及德国敬虔派的影响。
图:英国皇家学会
莫顿发现,17世纪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最主要的领导者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英国,而非崇尚天主教的欧洲大陆。即使在欧洲大陆,也是基督新教地区(如克普勒所在的德国敬虔派教区)的科学发展,比天主教地区发展得更快。
在英国,清教徒比英国国教信徒更多、更热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英国皇家学会最初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清教徒。
清教徒在宗教领域受到英国国教的打压,便将他们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领域。1620年-1660年间,投身于哲学或神学研究的大学生减少了一半,而研究科学的人则增加了一、两倍之多。年轻学子的大批涌入,带动了英国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
17世纪的清教徒科学家,如牛顿与波义耳普遍认为,研究科学及探讨宇宙的奥秘,乃是在研究上帝所赐的另一本“天书”——大自然。因此,研究科学乃是归荣耀给上帝的方式之一。这赋予了科学研究更高的神圣使命,肯定了科学研究的崇高价值和意义,使科学家们能够在不求名、不求利的纯正心态下,全心研究理论科学。
为何清教徒的思想,会促成科学研究的风气呢?因为清教徒的一些核心信念已逐渐重塑英国的价值和文化,成为全民共识。这些核心信念包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科学研究)去“荣耀上帝”;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独特礼物,因此每个人都该运用理性,去认识上帝和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理性思考应该依据经验的实证,而不只依靠逻辑推理,这一点对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有突破性的影响;知识的价值,是以其实用性为衡量的基准。
我们并不是说牛顿和波义耳等人的科学研究直接受到这些宗教理念所推动,而只是想指出,由于科学研究被这些清教徒所认可,因此,有许多像波义耳这样有天份的青年人,纷纷投身于科学研究的热潮,从而带来17、18世纪英国科学的迅猛发展。
过去100多年来,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之后,许多人总认为理性与信仰是彼此冲突、势不两立的。因此,他们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是无法接受任何宗教信仰的。
其实,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理性与信仰未必都是对立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曾主张:理性是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理性也是人类认识真理的途径。同时,柏拉图还进一步认为,理性固然使我们确定,万事万物都有其根源或因果,但当我们推论到最终极点的“第一因”时,我们要知道,那“第一因”就是“神”——他乃是万有之源,却非任何事物之果。
中古世纪的学者如阿奎那等,沿袭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也指出人是有理性的,这理性使我们确知有上帝的存在。甚至到了启蒙运动之前,笛卡儿、斯宾诺沙及莱布尼兹等人,仍然先后以理性的观点证明,“上帝的存在”从逻辑论证的角度来说,是必然的结论。
但是,到了启蒙运动(或称理性主义)时期,思潮就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个时期,经验主义蓬勃发展,其中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著名的怀疑论者休谟、不可知论者康德等。因此,自启蒙运动开始,人类才将感官经验(而非纯逻辑思考)等同于“理性”,来否定一切超自然事物的存在。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泛科学主义兴起,人们又进一步强调:唯有能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的才能算是“真理”,故全面性地将宗教信仰排除在真理的范畴之外。
然而,不可否认,人类的经验毕竟是有局限、不全面的。以此经验作为准绳,去判断一切真理,恐怕会造成坐井观天的错误。因此,当我们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时,我们就无法判断,在超越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所以,康徳等不可知论者就认为,人类有限的理性绝不可能辨别何为真理。因此,到了20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不相信有任何“绝对真理”存在。
但是,波义耳及同时代的清教徒科学家们则认为:人类可以知道部分真理,却不能知道全部;而单单依据所能知道的局部真理,就已经是铁证如山,足以令人确信有上帝的存在了。
过去科学与信仰的论战,主要是关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古世纪,天主教教廷主张,宗教应该凌驾于科学之上,这就是伽利略被审判时的背景。到了19世纪,许多科学家主张科学应该在宗教之上,即所有的宗教陈述都要合乎科学。
20世纪中叶,多数人的共识则认为,科学与信仰是两个“互不相属”的领域,应该和平共存。他们认为,科学探讨物质世界,宗教探索心灵世界;科学问“如何”的问题,宗教则问“为何”的问题;科学提供工具,宗教提供意义。科学与信仰也有交集之处,有可以对话与共同探索的领域。
当年,罗马教廷反对天文学家伽利略,依据的不是圣经,而是亚里士多德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这是当时主流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说,这不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模式转换时产生的模式之争。
但在当时的基督新教社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却并非垄断性的主流思想,也并非不得触犯的禁忌。波义耳也曾撰文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却未曾遭致批评或迫害。而且,同一个时期的基督新教,曾大力支持德国天文学家克普勒和英国牛顿的天文学研究。
图:达尔文进化论
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基督教对近代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举出其他非基督教地区,如希腊、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也曾经在科学上有过重大发现。因此,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天才人物、安定社会等因素,可能才是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最近,杜汉和贾基分别提出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上述外在因素固然是创造现代科学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我们需要找到其文明内在的哲学思想氛围,使科学能持续地长期发展,而非逐渐地消亡。
他们指出,下列条件可能是其共同特色:
这个文明的时间观必须是线性的、可量化的,因此,自然事件的因果关系才能明确;而像印度文化的循环性时间观(即轮回),因为强调万事万物的重复循环,就使科学的发展及演进变得毫无意义,也会压抑科学的持续发展。
泛神论式的有机性宇宙观也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如古希腊与中国,将星宿视为神明,就不太可能使天文学得到持续发展。
如果否定了宇宙万物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可探索的,就无法产生研究科学的动力,试想,谁会白费工夫去研究既不可知又无理可循的事物呢?因此,信心与理性的平衡是必须的。在这种社会,宗教界人士不排斥自然规律的存在,而科学家也不否定宗教真理的可能性。
由此,杜汉和贾基指出,基督教的世界观恰好符合上述大部分条件,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社会更成为发展近代科学的沃土。可以说,杜汉和贾基的理论呼应并证实了莫顿的理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