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86)
2010 (209)
2011 (252)
2012 (126)
2013 (146)
2014 (159)
2015 (119)
2016 (181)
2017 (128)
2018 (283)
2019 (295)
2020 (360)
2021 (299)
2022 (250)
2023 (208)
2024 (208)

《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应当都知道。它的作者是高玉宝,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2月5日,高玉宝去世了,终年92岁

随着高玉宝的离世,很多人想起了《半夜鸡叫》,又想起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于是各种评论充斥网络,好不热闹。
百度了一下,高玉宝的身世如下:
高玉宝是农民出身,1927年4月6日,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孙家屯村的一户贫苦农家。8岁时,他上了不到一个月的学,就被顶债去当长工。9岁时,他随父母逃难到大连当童工,15岁替久病的父亲到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1947年11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行军途中,高玉宝学会了识字写字。
高玉宝曾说:“那时我没有纸、没有笔,就找来十几块黑色瓦片背在身上,再把钉子磨尖了在瓦片上刻字来学习,在行军途中,我比别人多背了十几二十斤的瓦片。”
没有老师,他便请识字的人在瓦片上刻“红、黄、蓝、天、地、人”等字,在心里默念字的形状、笔画及其字意。后来,他做了军邮员,有机会要一些铅笔头和废纸,这才告别了瓦片与钉子。
凭着这样的毅力,高玉宝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部队南征北战,他也跟着从北方打到南方,一直打到湖南、广西、广东,先后立了六次大功,两次小功。一边行军,高玉宝一边写书。1951年1月28日,他终于写出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草稿。

美术片《半夜鸡叫》海报
《半夜鸡叫》竟是画出来的?
与其说写,不如说是“画”。因为很多字高玉宝都不认识,想写的故事又有很多,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不会写的字用图画或符号代替。
“半”字不会写,他画了半个窝头代替。“夜”字画了颗星星表示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画了一只鸡代替。“叫”字好像在课本上见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半夜鸡叫》就是这样“画”完的。
高玉宝的小说完成后,名字一直没有定下来,有人提议《童年的高玉宝》,有人建议《我的童年》。最后是罗荣桓看完小说一锤定音为《高玉宝》。
1955年,《高玉宝》出版发行,随即引起热烈反响。他每天都收到不少来信,最多时一天收到200多封,装了满满三大木箱。后来,根据其改编的儿童剧和电影《半夜鸡叫》更是家喻户晓,其中,恶霸地主“周扒皮”便出自于此。
《半夜鸡叫》的故事曾引起很多共鸣:地主周扒皮为了辞退辛苦一年的长工,不让他们拿到应得的工钱,想出了半夜学鸡叫的损招。当时,“周扒皮”成为了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直到今天,遇见黑心老板时,人们还是会骂上一句“周扒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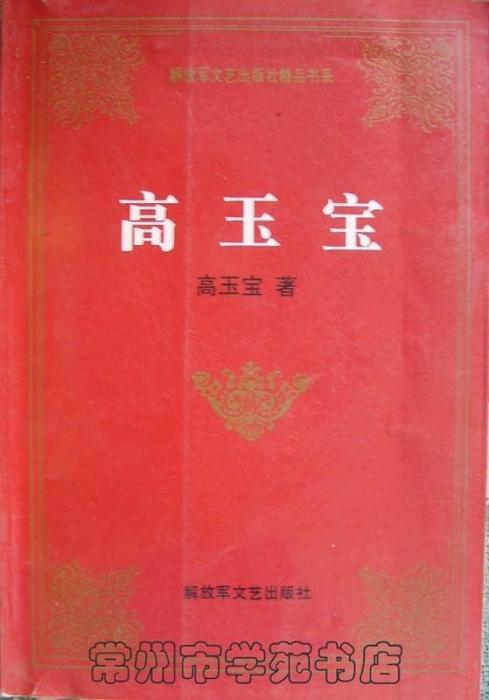
“能够工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1954年,高玉宝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1962年,高玉宝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成为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师级干部。
为了创作,他到部队、工厂、矿山、农村体验生活,获得丰富的写作素材。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
他曾说:“文学是一块净土,又是一座高山,也许我不会攀上峰巅,但我会全力以赴尽力拼搏。”
1988年,61岁的高玉宝正式退休。除了写书,他还把旧社会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新社会的巨大变化讲给大家听。几十年来,他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听众达500多万人次。
83岁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每每想到已牺牲的战友,就觉得自己能活到80多岁,能够工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他说:“我就觉得我不能停下来。”

网上看到一篇文,也是介绍高玉宝的,分享一下,让不大了解他的人,对他多一些了解。
《我所知道的高玉宝和“半夜鸡叫”》
作者:顾玉如
早年在大连的新闻单位供职,对《高玉宝》和他的“半夜鸡叫”故事知道的比常人多一些。最近看了网上关于批驳“半夜鸡叫”的文章,不禁会心一笑。这里讲一下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着了他的名子。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不能着荒草的名子,而要着高玉宝的名子,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职干部。
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ⅹ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着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我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结果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Ⅹ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Ⅹ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我当时了解到这些真象,心里很难过。真的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后来做新闻记者时间长了,整天也必须应合形势说些假话,对这些事也就麻木了。
现在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披露出来,也让人们了解过去,吸取教训。(摘自《每日文摘》)
92岁,算是长寿老人了,高玉宝的一生有苦也有甜,他没有虚度人生,至于说小说里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他生活在了那个年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都是人书写的,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但记录和书写下来的却不是自己,那么究竟有多少历史是历史事实呢?谁也不知道。
愿高玉宝一路走好!




周末愉快!
看了你的一些留言回答, 突然觉得自己还很欠磨练啊。 我累了烦了的时候, 或者意识到有人根本就是逻辑混乱却不自知,还有时根本就是有意胡搅蛮缠时就没了耐心,说话会冲。 我得向你学习,不是为了改变别人, 因为人是很难改变的。 TA 爹妈都没改变得了呢; 而是为了自己爱的人, 自己在意的人; 也为了自己能长命百岁哈。 谢谢晓青!
只要不剥削别人,压迫别人,那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其实,很多压迫剥削别人的人也在自己压迫和剥削自己,这个只有你做了当事人才有体会。一切理论上,甚至自以为明白的都不是事实。咱们谁真正了解高玉宝?周扒皮?谁知道谁到底为啥来美国,咋不在国内,咋不回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初衷还在吗?为啥要不忘初心?
周末愉快!
以本人亲属为例,父亲那边的地主们都不富,地不多,民愤也不大,地被分了之后受罪也不多,偶尔被象征性地批斗而已。
但母亲那边的地主们民愤较大,受罪不少,被赶出家门住破庙(试想一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就能让女儿们大学暑假时坐飞机回家的地主,不像周扒皮那样,能富吗)。
我觉得跟没当过地主和资本家的人说什么是剥削,白说。俺家样数很全,国的、共的、地主、资本家,台湾的、香港的、美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还有依旧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哈哈。你有了这么多的眼见为实,再看那些这个那个,也只能一笑了之。
只要给别人干活儿,都可以说是被剥削,但,你可以不干的。哈哈。是不是很多人都怕没人剥削呢?鸡不叫就主动起来干活的人很多不是吗?我周末的早上,都是鸡不叫就起来蒸馒头的,积极主动的:)
打工的不知老板的苦,老板靠打工的赚钱呢,能虐待你吗?至于你不满意,那可以不干,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好遗憾,我知道高玉宝,不过,也真是高寿了!
赞一下这段话,领导应景文,也看见不少写高玉宝的。
原来也听老妈说过,文革时,外公原来纺织厂里的工人都出来为他说话,说他对他们都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