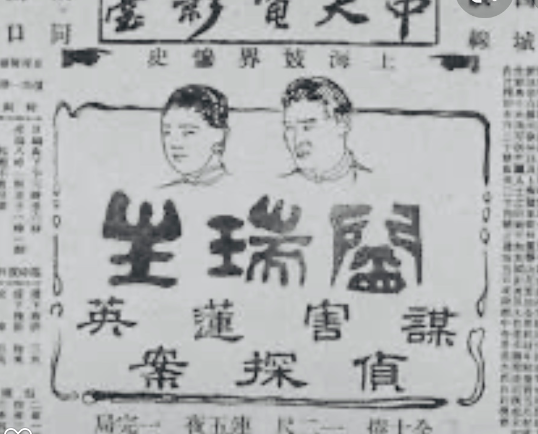佣人们知道林翔老爷启程去法国LeMans看24小时车赛不在家都多多少少有点儿放肆。看门的从家里带了只鸟笼子来放在转达室桌子上的信件和报纸上逗玩,洗衣妇掩了地下室洗衣房的门嗑了一地的瓜子壳儿,林翔的几件衬衫到下午了还没有烫完。管家吴妈看着只想骂人。丹凤回到家才得知他们的俄国司机德米特里也出去门旅行了。她明知父亲已走,可还是满栋楼里找了他一遍,到[
阅读全文]

男女关系最美的境界是中间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窗纸看对方,如镜中花,像水中月。那时镜子里的花比真花要美;水里的月晶莹透彻,摇晃不定,但触手可及。男人都偏爱镜子里的花;女人皆要那水中的月。倘若水里的月移到镜子里会大得吓人;镜子里的花不小心掉到水里很快也会变色。不幸的是那层窗纸捅破了才知道,原来镜中的花只是五名的杂草,水里的月亮上其实有好几[
阅读全文]

为了能上午准时赶回《字林西报》上班,温士顿在世雄订婚仪式一结束就买了早上六点钟的头班车票准备回上海了。杨家人进出门大多还是坐轿子,但温士顿现在死活不愿再被人抬着,更何况是半夜三更,并坚持要自己走到车站。世雄便嘱咐人弄了一辆汽车过来亲自起了个大早,带着万顺一道去送他。这英国人还没学会应付中国人的客套,来的时候只提了一只小箱子,走的时[
阅读全文]

下午拍摄结束的时候,那些学生群众演员们马上围住了邡林、玫瑰要他们签名,毕竟选角导演只说不能围堵导演,没说不能围堵明星嘛。玫瑰对丹凤仍是爱理不理的;但她却帮助丹凤明白了她的物理老师摇头晃脑三天都没解释清楚的一个原理:同性相斥。丹凤在更衣室外面的水龙头下咬着牙用脏兮兮的肥皂把脸上的油膏搓掉,然后去化妆室换上来时穿的衣裙。化妆师刘莉正把[
阅读全文]

远远望去,虹口游泳池里像饺子锅一样挤满了人。摄影机、聚光灯热辣辣地开着。丹凤不知所措地踅近泳池,一道聚光灯移到她的脸上,刺得她睁不开眼。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老王,她的道具呢?帽子要大得往下垂的那种。”
丹凤睁眼瞧见刚才那个身着米色绸衫的秃头男人拿着个喇叭筒正站在她旁边,身上散出很重的烟味。他要她坐在池前的一把长的躺椅上。[
阅读全文]

德米特里开车将丹凤带到银河影业公司大门口。昨天的门卫看见丹凤早已喜笑颜开,好像华丰泽老板对这个姑娘的重视是因为自己是个伯乐首先发现了她,将来升做星探也未曾可知。受丰泽事先嘱咐,他马上带丹凤去后面的五号摄影棚。那里闹哄哄地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个少男少女。丹凤没想到试个破镜头还会有这么多人,这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啊,正打算找一个地[
阅读全文]
丹凤去银河影业见华导演扑了个空后生父亲的气不想回家,便直接坐车去找她在上海中西女塾的老同学陈美兰聊天解闷儿。美兰住在公共租界南京路上的一个大公馆里。丹凤家没搬到法租界之前,两家隔的不远。美兰透露自己正跟香港来的表哥谈婚论嫁。丹凤听后大吃一惊。“你才多大就要结婚啊?”但暗暗地感到有些不平衡,心想美兰这样其貌不扬、又矮又胖的女孩儿[
阅读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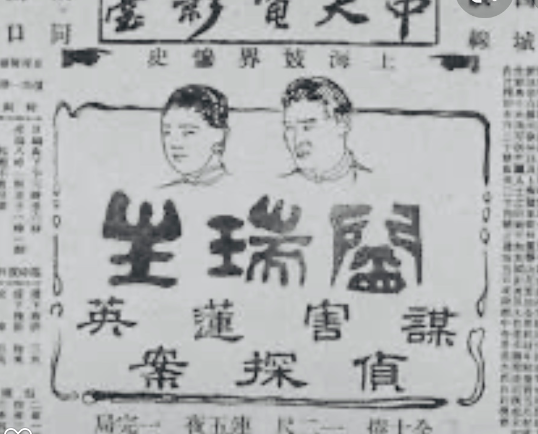
林翔忧心忡忡地在家里呆了几天,最后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去法国LeMans看24小时车赛。他在楼上自己卧室里收拾行装的时候,从窗子里注意到外面女儿丹凤一个人百无聊赖,不是坐在汽车驾驶座位上跟他们的俄国司机德米特里闲聊就是在花园里闲逛。这叫他颇为担心。他知道她的戏剧学校解散后她就无所事事。他真的希望能叫女儿继续读书,将来去国外念个大学什么的,但也知道[
阅读全文]

丹凤晚上的乐队排练因五卅之后上海接连不断的抗议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频频不断的戒严被取消了,她的戏剧学校的课也暂时告停。丹凤无所事事在家里闲着难受。高原连着好几天没来林公馆,可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但因为那儿比较近,丹凤便决定去找他消磨时间。这回长长的弄堂里没有了琴声,也没有玩耍的小孩子。走近大门的时候,正好一个上着月白色衫子、下穿黑布[
阅读全文]
后半夜气温下降了许多,温士顿睡得好一些。排窗上的晨曦将他唤醒。为不打搅他人,他换上白色中式练功服,自己走到大小鹅卵石子砌的白玉厅前打太极拳。园子里一个仆人正拿着一把大剪刀修理花圃,看见他的样子忍不住咧嘴笑了。温士顿也笑着向他挥挥手。
锻炼完后,温士顿回厅洗澡。澡盆是一个大木桶,在屏风后面。昨夜杨家女仆已经加满了水。隔了一夜水都凉了[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