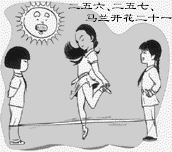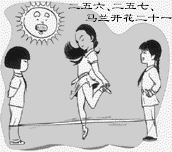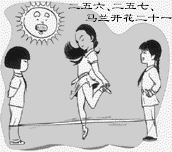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不再哭也不再找妈妈了,与爸爸、小弟弟和小妹(比我大两岁的小保姆)在一起开始了没有妈妈的生活。我们常常呆在家里,因为一到外面就会感觉到邻居们疑惑的眼神或听见年龄相近的孩子直接问:
“你妈妈到哪儿去了?”
我不愿去面对这一切,和小妹带着小弟弟躲在家里过着漫长的没有妈妈的日子..[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终于有一天,姨父语气沉重地告诉我:
“小平,你可以回家了,可是你爸爸忙,不能来接你,你要自己回去。”
听到可以回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姨父什么都没再多说。
两天后,姨父姨母一起迎着清晨的寒风送我到长途车站,一路上他们什么都没说,姨母搂着我静静地往前走,姨父也静静地在我身边一起往车站方向走去[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到安顺爸爸让学生们在接待站登记完毕住下后,带我到了安顺实验小学的姨母家。
姨母一家见到我们很高兴,进门后爸爸就叫我跟表妹出去玩,表妹兴致勃勃地要我到楼上她的房间去,我跟着表妹到房间角落上一个可移动的木楼梯前,木楼梯上端靠着一个一米见方的门洞,她很灵活地爬上楼梯,站在门洞前叫我上去,我们很快在阁[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我们一行九人在上海四川中路的接待站呆了整整半个月后,终于可以离开上海了。没有人对不去北京表示遗憾,大家似乎都跟爸爸一样急切地想回家了。
我们乘坐的这趟车是上海到昆明的直达快车,途径安顺,我们将在安顺站下车,然后乘长途客车回普安。这趟车离开上海站的时间是晚上,因是始发站,我们都有座位。我们的座位在[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1,在上海下馆子
离开上海滩后,爸爸带着我们一行九人到上海饭店用晚餐。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家饭店里就餐的人穿着都很讲究,男士们大多穿着毛呢短外套,女士们大多穿着毛呢大衣。
我们一行九人穿得都很随便,爸爸上身穿着已开始褪色的海军蓝短棉大衣,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卡其布裤子。我穿着一条已经穿了一个多月[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虽然我不时会关注爸爸的心情,但十二岁的我还很无知,很好奇,很调皮,注意转移仍然很快。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和谢萍每天不是跟着爸爸的学生们外出闲逛就是和谢萍在房间里玩,我们喜欢爬在窗台上看那个小黑棚子里的动静。有时在外面买了甘蔗,回到房间嚼甘蔗时,就爬在窗台上把甘蔗渣往下扔,以报谢萍的背被那年轻男士[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到达上海几小时后,我们顺利地住进了位于四川中路的串联学生接待站里。
这个接待站是一幢占地面积不大的十一层楼房,我们串联队的四女五男住在九楼相邻的两个房间里。房间面积不小,比我们在新寨农中的寝室宽敞舒服多了。接待站为大家提供了单人床,我们四个女生宽松地住一个房间里,爸爸和四个男生的房间在我们对面。
[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1967年2月3日,中央文革发出的停止串联的通知很含糊,因对何时停止串联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对接待站终止时间也没有明确时限,只要求各地劝阻串联学生不要继续北上,接待站要妥善对待串联学生的需求。因此在通知发出后,全国性的步行串联一下转变成了全国性的乘车串联。
1966年大串联开始后,就有不少参加串联的人打着红卫兵[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年初二,我和谢萍跟着爸爸和他的两女四男六个高中学生,一早起来,在接待站吃了早餐后,精神焕发地离开了长沙。我和谢萍已经有了步行串联的经验,我们背着自己的军用书包和水壶,戴着红卫兵袖套,只是没打绑腿也没戴军帽了,因为从贵阳乘车回家几天,乘车返回贵阳时,把这两件行头忘在家里了。感觉到平江的路很平直,[
阅读全文]

二青春的印迹-----参与大串联见证文革
在长沙的接待站住下后,第二天,我和谢萍跟爸爸的的学生们一起到接待站附近一个专门交换毛像章的街市上闲逛。我们跟着不少人羡慕不已地围着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瘦高个儿男士,他的军大衣右边贴身一面挂着的不同形状和尺寸的毛像章,他不时撩开棉衣露一下他拥有的毛像章,不时紧紧用棉衣裹着身体四处观看那些手里拿着一枚或[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