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开博一年有余,写了一些个文章,都是自娱自乐的。杜马小妹好心,问我想不想投稿报纸。说是加国魁省有一个华人报纸不错,他们经常刊登一些小文章,鼓捣我去投投稿。可以为加国魁省人民作一点奉献,还可以让加国魁省人民认识牛奶瓶,最后最重要的是:还有稿费。为加国魁省人民作奉献,这是一句口号,没有实质。让加国魁省人民认识牛奶瓶,我可以出名,不错;还有钱拿。有名有利,何乐而不为?
我对杜马小妹说,我最怕的是命题作文。这命题作文是我的软肋,从小就怕。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我则一直认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尽走神。”记得上小学,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写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一看这题目,我头就大了。我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读书就不喜欢上学,不喜欢上学就不喜欢老师:这语文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姓裘,很漂亮的上海小姐,但很凶,上课连动不让动;算术老师是一个部队复员的文化人,上课特死板,死板得就像那一加一永远都等于二一样的死板;美术老师一天到晚跟我们讲故事,说是一个外国人姓达的,每天画圈圈(鸡蛋),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一开始还行,画了几个圈圈后,就觉得无聊了,无聊得很;音乐老师我也不喜欢,本来我的嗓子就不好且五音不全,他偏偏叫我上讲台独唱,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嘛;挑来挑去找到了我们的体育老师—缪老师—一个小男青年,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腰板溜直,笑容可掬。喜欢他的课,可以踢球、玩攻城游戏、打沙战、爬树(他有时不管我们)。他也喜欢我,我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我们校队64年荣获杭州市小学足球的冠军。65年,与杭州市少体校足球队比,我们10:1大获全胜。于是,我就写了他是我最喜欢 的老师。也不知道写了什么,反正是缪老师好,不凶,对同学们好之类的。大概得了个3分吧,那时是五分制,三分是居中等。语文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据说体育课缪老师追求过她,但不成功。所以,我的这篇文章不会高分的。(对不起了,裘老师开个玩笑了。我都是五十五岁的人,您大概有七十五了吧?不会生气吧?其实,我现在一点也不生您的气,严师出高徒嘛,有我这个“高徒”您也会高兴的吧?)
杜马小妹说,不管你,是随笔。随你写,我这个人碰到自己喜欢的题目,就会思如泉涌,妙笔生花,一笔十行,宛如开了闸的三峡水,一泻千里。
还有,杜马小妹说,每篇文章不得超过1,000字。这又是一个难题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文章就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四、五千字是短文,一、二万字不算长,毕业论文是写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没有十几万字也有八、九万字了吧。而且现在有越写越长的趋势。
小时候,与此截然相反。小学时,还是那个裘老师,布置作文作业时,总是不会忘记加上一句:300字以上。就头疼那300字以上,只好多写标点符号,多分段落(一段前后空白可以揩油十几个字)。写没几行就开始数数,一堂作文课,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数数。
到了上海上中学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姓谢,非常慈详可亲。她老人家布置作文作业,从来不要求字数,更重要的是:可以抄书!!!按她的话说:你抄了书,就读了书,读了书就记住了书上的知识(部分或全部)。记得1965年江姐的儿子写了一篇文章记念他的妈妈。我在读书笔记的开头就整段地抄了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高歌欢庆新春来。”随后,说了彭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要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将来要努力云云。
后来到了部队,由于是城市兵又是初中生,成了宣传积极分子。部队是出黑板报,不大的地方,没有几篇文章可写,所以都是短文。当兵第一年的初评(那时评五好战士,一年一次。年中叫初评,不寄喜报;年底是终评,寄喜报回家。)我写一篇短文“评‘四气’”—即傲气、怨气、泄气和不服气,二、三百字吧。吕副指导员,63年的大连兵。拿着我的稿子,站在食堂里,当着全连一百八十多人的面大声地念着,一念就是二天。我那个得意劲,您就别提了。
再后来,到了地方。我是搞企业管理的,尽写那些个调研、可行性研究等。这下子,就开始写长篇大论了。长得连自己都不满意了。
我也知道这个理:小时候看过一本书《福尔摩斯侦探记》,那个序里福尔摩斯说过:一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房间,可以装很多东西。要把有用的东西装进去;把没有用的东西扔掉。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做起来谈何容易。房间是个实体,东西也是实体,你可以把它们存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扔掉。脑子是个实体,不假;可思想就不一样了,什么名啦、利啦、色啦、欲啦、性啦,你不想让它们进脑子,它们也一个劲地往里钻,赶都赶不了,扔也扔不掉。写文章也是,总以为自己写得东西,字字是金、句句是宝,这个也舍不得扔,那个也舍不得删,结果这文章就是越写越长。
文章刊登出来两个星期后,杜马小妹告诉我稿费来了,$9.00加币,扣税后$8.60,问我是寄给我,还是我去魁省取。这下可难了我了,寄给我可能不够那寄费,对不起小妹;我去取,不够汽油费,对不起我自己。后来,我告诉她不用寄了,我也不去取了。下次,回国时在上海南京路的吴越人家请我吃牛腩面,人民币¥28.00一碗,这点钱够两碗了。一碗请杜马的客,算是回扣;一碗请自己,算是犒劳我自己。就定在这个春节吧。要吃的XDJM早点报名了。截止今天上午以前,凡叫我舅舅、叔叔、伯伯的走廊同仁们,我就请客了(一人一客,严禁带家属)。
又:用WORD 工具一数,这字数又超过二千了。谁能压缩到一千字以内,投寄“笔缘”,如发表,稿费归你;属名归我。你得利,我出名。何乐而不为?
附:文章影印件一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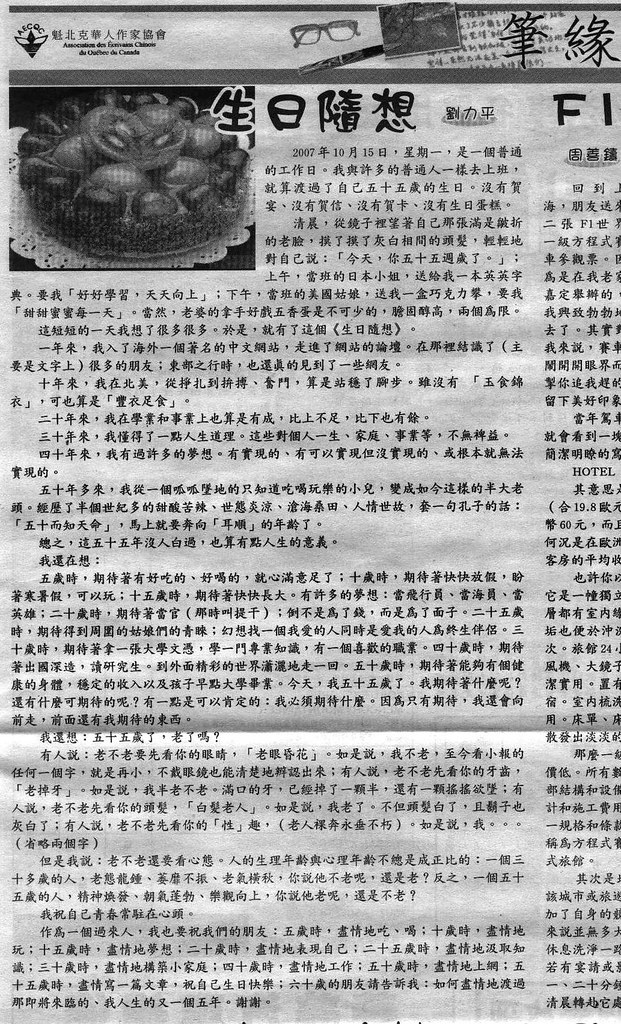





谢杜马。此杜马非彼杜马?哈哈,那张画就露馅了。
谢宝宝。等我们老了,那小辈不就请我们了。我在杭州前后一共六年,就是小学时期。我们那个小学是讲普通话的,与外界有点隔绝。只知道杭州的小丫儿,戴着帽儿,拿着扇儿,唱着歌儿......哎,说正经的:你回杭州,路过上海吗?我小年夜回沪,一直要呆一个月哩。如可能上海见面,吃牛腩面。嘿嘿。还有杜马。
你在杭州蹲了十多年,“解格套”滴意思总晓得滴吧?如果不晓得,那你一定要请偶吃面喽:“虾爆鳝”,奎元馆的招牌面,旧年子是二十七块洋钿一碗,明年恐怕涨价20%,有点贵滴,表肉痛噢。
又一次见识何谓"思如泉涌,妙笔生花,一笔十行,宛如开了闸的三峡水,一泻千里。。。”
然不知何方小妹借走俺老杜的名号也不作言语,纳闷中。。
HO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