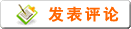王一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注:在本文中,比爾·克林頓將被簡稱為克林頓,而希拉裏·克林頓則簡稱為希拉裏)
上世紀最後幾年,在克林頓深陷萊溫斯基事件,對科索沃戰爭的界限最為搖擺不定的時候,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站到了最前麵,幾乎憑著一己之力扛住了五角大樓對於派遣部隊的質疑和壓力,並最終推翻了米洛舍維奇。
一段時間內,評論界喜歡把那稱之為“馬德琳的戰爭”,作為美國首位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於這個稱謂十分敏感,她指責到,“你們會將越南戰爭稱為麥克納馬拉(時任國防部長,對越戰的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的戰爭,就應該將科索沃稱為奧爾布賴特的戰爭,而不是馬德琳,這是對女性的歧視”。
有點兒微妙。她的意思其實是,你們不用刻意強調“馬德琳”這個女性名字來凸顯這是一位女性完成的戰爭,沒有必要說這些,收起你們的直男癌,在這場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和軍事活動中,女性和男性沒有什麽不同。
彼時還是1999年。時間過去了近20年,這些年裏,美國政壇接連出現了首位黑人國務卿、首位黑人總統、又一位女國務卿。而現在,甚至在稍稍偏多的人看來,美國很有可能出現曆史上首位女性總統。
今時今日,多元價值在美國政壇擁有無與倫比的合法性,任何具有明顯性別、種族、階級概念的觀點表達,都是極端的政治不正確。在首場辯論即將臨近的時刻,甚至是危險至極的。近期,連特朗普都收斂了自身的直男屬性,對待女性和少數族裔群體的態度明顯轉好。希拉裏摔倒之後,也沒有跟上去補刀她的健康問題。
談及這些,是想要預先埋下伏筆。或許本篇的某些段落,直男邏輯會不得已顯露出來,Feminist如果能夠擱置對於這些文字的閱讀不適,僅就其意欲揭示的道理進行理解,將是筆者極大的感激。

畢竟,我們沒有飽含對任何一方的同情抑或仇恨,這些文字的出發點僅僅是希望把問題說明白,而它也僅僅代表一種新的分析問題的角度,即:
——如果,僅僅是如果,希拉裏沒有成功當選美國曆史上首位女性總統,與其去對比她和特朗普差了些什麽,不如去對比她和那位更為熟悉,並且已經成功當選總統的克林頓先生差了些什麽。
某種程度上,她和她的丈夫之間的距離,就是她與橢圓形辦公室之間的距離。
不同點——誠信與聰明
作為任何一名政治活動家,誠信這一概念,幾乎是著身立命的全部依賴。然而作為一名極其出色的政治活動家,沒有人比克林頓更敢於把這不當回事。
早在小石城當州長之時,當地居民就給這名年輕力盛的州長先生起了個外號叫作“狡猾威利”(Slick Willie)。一方麵,選民們認為他做的不錯,在阿肯色這樣的小地方,他已經突顯出了自己極其出色的經濟治理能力,總是能夠擺平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然而他從不吐露自己的想法,永遠難以接近,政敵們對其居高臨下的嘲笑總是恨之入骨。另一方麵,大家都知道這是個好色的州長,幾乎注定會有很多風流韻事,隻是他永遠掩藏得很好。
克林頓的競選之路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沒有去越南”的問題,在那個人人都會操著“Nam”的簡稱以彰顯自己對越南事務之熟悉的年份,克林頓竟然先是通過後備訓練隊的借口非法逃掉了兵役,而後又通過一封虛偽而熱情的長信轉而拒絕了後備訓練隊這個借口,從而沒有承擔任何艱辛的個人義務,在牛津大學舒爽的宿舍裏休養筋骨。

1992年7月密蘇裏州St. Louis,希拉裏與丈夫參加總統大選。
當這些事情被他的對手們費盡心機揭發出來的時候,克林頓僅僅是通過一場脫口秀直播就將這一事件的誠信含義放鬆到了一個較為隨意的標準,釋義成一種年輕的調皮。對於那個年代的任何一個名競選者而言,對於越南義務的背叛相當於對於整個國家的背叛,然而正如評論員馬拉尼斯後來所說,克林頓“像一名象棋大師一樣應對了兵役”。
這種能力恰恰是希拉裏所不具備的。整個階段的競選,“郵件門”給她帶來的折衝實在太大,盡管企圖重走其丈夫的老路,把一切說成是所有人都會因偷懶而犯下冒失的錯誤。然而,時過境遷,克林頓夫婦不再是當初頑皮的少年映像,她看起來富於心計,參加了無數脫口秀節目,卻始終無法擺脫這個陰影。
從“郵件門”的1.0,2.0再到3.0,這種損耗是不斷綿延的,搖擺的選民和希拉裏自己一樣,永遠不知道下一個版本會出現什麽更為致命的信息,永遠不知道一個人還可以複雜到怎樣的程度,永遠不知道自己距離美國政治的真相有多麽遙遠。誠信的底線不斷被拉低,每一次新消息爆出來,就會有新的一撥選民轉身離開。更為致命的是,這是一種灰心和沮喪的離開,幾乎確定不會再恢複。
再去看她的丈夫。所有人都知道,克林頓極端聰明,聰明到可以充分利用選民對誠信的容忍邊界,最大限度地爭取個人利益。無論是兵役事件還是為其職業生涯帶來重創的萊溫斯基事件,每一次危機出現的時候,他都極有膽量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堅定地矢口否認,等到確鑿的證據被披露後,再轉而以克林頓式的方式搪塞一切,淡化這一問題的處理。
很多評論界人士都會提到,在那樣的醜聞下,如果被自己親口否認的事實狠狠地扇了一記耳光,換成任何一位總統,幾乎注定會如同尼克鬆一樣遭遇彈劾。而克林頓就是能夠做到雞賊般地苟活下來。
不僅活了下來,在萊溫斯基事件被坐實後不久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絲毫沒有受到影響,甚至反而贏得了更多的席位。人們驚訝地發現,克林頓已經和選民們達成了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人們會為他投票,但是已經學會了放棄對他的信任,人們隻是覺得國家有一個足夠善於總統事務的聰明人是可以的,至於他做的那些不甚重要的承諾,大可置之不理了。
克林頓成功地戲謔了誠信,成功地教化了選民。聰明可以代替誠信,成功的經濟繁榮可以代替失敗的個人道德,美國人民和他之間淡淡的關係就是一紙契約,選民對他的精明不亞於他對選民的精明。
然而這一切必須建立在聰明和誠信同時出現的前提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希拉裏的智商高於克林頓,她不過是一名畢業於威爾斯利學院和耶魯法學院的傑出律師,但在控製選民、深諳世故這方麵的本領,希拉裏遠遜於她精明的丈夫。甚至萊溫斯基事件的出現,表明她其實是這種精明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現在,如同被他的丈夫傳染,無論是“郵件門”還是“健康門”,她總是在事情爆發的第一時間負隅否認,又在稍晚的時候麵對被揭穿的窘境。然而她不具備回天的本領,在這場愈演愈烈的針對個人誠信問題的聲討中極為被動,甚至有可能因之失去一切。
如果擁有誠信,希拉裏可能如同往年任何一位樸實的候選人一樣以年邁而慈祥的姿態步入白宮;如果擁有聰明,希拉裏可以同其丈夫一樣把選民的忠誠玩弄於掌心,不過是另簽了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約;如果不夠聰明,又失去了誠信,事情或許就如現在這般窘迫,她的確位於天平的低處,但是一切已經在緩緩向對方傾斜。
不同點——能量與健康:
這一點希拉裏被欺負慘了。特朗普幾乎是以赤裸裸的性別優勢在踐踏希拉裏的個體尊嚴,這種踐踏他在競選初期可以用在傑布·布什身上,如果一個政治家族的代表深負眾望、文不禁風,看起來蔫蔫的,再怎麽諷刺都不為過。
但是希拉裏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性。這位女性二十五年前在與她的丈夫在新罕布什爾州首次亮相的時候是驚為天人的,沒有人在競選初期就能讓自己身邊的女人有南希般的第一夫人之感。這位女性後來在參議院的工作是年富力勝的,在國務卿的任上是極為勤勉的,或許因為過於勤勉,導致其非常疲倦,在退休之後許久都不肯表態是否競選總統。
現在有評論提到了,她是在評估自己的身體。2012年卸任之時,希拉裏的核心憂慮一定是——如果有四年的休息緩衝,是否還能夠換回兩個健康而完整的總統任期。

9月5號,希拉裏在俄亥俄州的一次競選集會的演講中咳嗽不止,持續了將近4分鍾,不得不猛喝水並吞下一粒止咳藥。
按照年齡來看,68歲並不算小,盡管美國政壇如裏根、哈裏曼這樣在古稀之年迎來自己政治巔峰的大有人在,然而希拉裏是第一位女性嚐試者,她的競選年齡在曆屆總統中排名第三。而按照一種直男式的解讀,女性在這樣的年紀,真心很柔弱。
二十五年前,當克林頓以46歲的年齡參選時,他是何等的“Energetic”(特朗普經常形容希拉裏Not Energetic)。在一次政府預算被國會駁回的尷尬中,克林頓找到了國會裏更為年輕氣盛的右翼代表紐特·金裏奇,接下來的這場對話讓這位一向不把克林頓放在眼裏的年輕人畢生難忘——
“你知道我是誰嗎?”“不知道。”“我是你小時候玩的那個大橡皮小醜,每次你一打它,它就會彈回來。”克林頓停頓了一會兒,又接著說,“這就是我,你打得我越狠,我彈回來得就越快!”
這真的是隻有在年輕人的嘴裏,才能夠聽到的話!在特朗普看來,或許一個總統就該有這樣的氣魄!
克林頓的第一個任期,整個國家的對外事務糟透了,特別是還出現了索馬裏危機這樣的讓美國政府名譽掃地的事件,克林頓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不久的海地危機中,美國強大的軍隊被香蕉共和國雇來的一群烏合之眾所趕跑,克林頓政府再次顏麵盡失。
在一次對俄羅斯的訪問中,美俄雙方的安全官員都獲得了可能會有暗殺活動的情報,然而克林頓堅持要完成訪問,他的理由是,“我絕不會像在海地一樣怯懦地離開。”
隨後不久,海地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克林頓終於在自己的對外事務上扳回一局。他的助手們發現,克林頓在麵對那些最為嚴厲的攻擊時,其反應著實令人歎服,在曆經個人的災難之後,克林頓會變得更加投入,竭盡全力向自己的目標靠近,在威脅麵前近乎殘酷、無情、瘋狂。他們認為,這是克林頓最大的政治優勢。
而這一點,加注在25年後的妻子身上,實在是有些過重了,希拉裏不可能再擁有這種負荷的能量儲備。即便沒有這次的摔倒事件,媒體也早就發現,希拉裏難以在巡遊演講中保持狀態的連貫性,如果中間沒有經過適當的休息,嗓子會啞得很明顯,咳嗽會顯著增多。

為打破謠言,希拉裏在一檔電視脫口秀節目中,徒手擰開一個罐頭蓋,以證明自己有勁兒,健康沒有問題。
最為可悲的是,在特朗普的挑釁下,希拉裏被迫采取了一種男性方式的競選風格。在希拉裏的演講中,我們常常能夠感覺到她吊著嗓子站在男性的聲帶高度發出標準的美式演說的聲音,那些必須要一浪高過一浪的連續的排比句對她來說難度太大,很多場競選視頻裏,都可以看到她十分吃力,在激昂處常常出現破音。
單從演講的角度講,她大可不必如此,特裏莎·梅的議會質詢中,她從來都是按照自己的聲音和字頻習慣快速地完成演說。然而美國大選畢竟不同於英國議會質詢,它需要一種宏大的演說意識和雄厚的感召力,這都是需要極為充沛的體能儲備的。
據說,在競選初期,希拉裏的團隊給她的人設其實是睿智祖母的形象,然而在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下,這位祖母的氣力被嚴重地消耗掉了。
事情永遠是這樣戲謔,她經過了極其審慎的深思熟慮,走出了參選的這一步,卻遭遇了生理意義上可能出現的最大挑戰。當一個滿負陽氣的男人站在你麵前微微抬起下巴,一個女性所意欲保持的剛愎節製是那樣的脆弱,出手抵抗又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相同點——精英欲望與個體自卑:
那種認為美國近三十年的政壇將連續為布什家族和克林頓家族交替統治的說法是極其失當的,布什家族由於部分地繼承了裏根總統的精英團隊和“康乾盛世”,可以勉強算作存在一種家族式的影響力。
然而克林頓夫婦沒有家族。這個家庭成立之時,兩個人幾近身無分文,甚至沒有自己的住房,直到後來希拉裏參加參議院競選時,才不得不根據參選要求在紐約購買了屬於自己的居所,而這筆費用還需要依賴籌資人的資助。
這個家庭成立以後,他們也不過隻有一個孩子。去看看布什、羅姆尼那樣的一張相框很難裝下的大家庭的合影,你就會知道克林頓夫婦是何等的逆襲,能夠走到今天又是有多麽不易。
他們所仰賴的是一種源自骨子裏的精英意識。這種意識的血脈從肯尼迪兄弟、邦迪兄弟到克林頓夫婦,是民主黨區分於共和黨的重要品質之一。
同所有政壇年輕的出類拔萃之輩一樣,克林頓是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在美國,這個獎學金可以定論終身,完美地解釋一個優秀的人的一切。而希拉裏在高中時進入了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競賽的決賽,是第一個在威爾斯利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的學生,並且在工作後兩次當選全美百名傑出律師。
克林頓是天生的政治家,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從不懷疑。在民主黨蟄伏的多年間,他一直在估價他的潛在對手的實力,並且一再得出結論,盡管沒有足夠的金錢和資曆,然而自己的政治技能和才華要顯著強於他們。
1991年的夏秋,老布什身攜冷戰和海灣戰爭勝利的巨大光芒,支持率一度高至90%。民主黨內所有稍有名頭的競選者全部退卻了。隻有克林頓敏感的捕捉到,長期的冷戰對峙嚴重壓抑了美國經濟的生長力,美國民眾已經對戰後的新圖景出現了巨大的期盼,而布什總統對於國內事務過於忽視,這將有可能讓他付出丘吉爾式的代價。(二戰期間丘吉爾挽救了整個英國,卻在戰爭尚未結束時被選舉下台,由被視為更善於經濟治理的艾德禮取代首相,該事件被譽為選舉政治中的“丘吉爾現象”。)
最終,他使這一切成為事實。
她的妻子同樣熱衷政治。她本可以簡單地選擇成為學曆最高、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如果那樣,她注定會比南希更知道如何做一隻美麗的花瓶。然而她選擇了在克林頓入主白宮後輔助政事,並牽頭負責了國家醫保改革和兒童健康保險項目。
在克林頓即將結束他的總統任期時,她已經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自己的參議員競選。在紐約州擔任州長期間,她贏得了東北部民主黨核心陣營的認可和支持,而在美國白人女性眼裏,她早已成為一麵具有極其深刻標榜含義的旗幟。
他們的精英意識貫穿整個政治生活的始終。即便在克林頓卸任以後,人們發現他仍然通過四處的演講、顧問、非正式外交渠道、自己的基金會和籌備希拉裏的競選班子深刻地影響著民主黨的政治風向。
直到這個基金會的很多做法被逐漸揭露,人們才意識到過往二十年,是克林頓夫婦在民主黨內枝繁葉茂的二十年。克林頓評價奧巴馬的那句“他以前隻配給我端咖啡”絕對不會是隨口說說。
這種精英意識是好的。自肯尼迪政府以來,已經很久沒有在總統的位置上出現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身影,我們有理由相信克林頓和希拉裏也能夠如肯尼迪一般,為國務院帶來一群出類拔萃之輩。
然而,他們又是自卑的。
上帝賦予了他們過人的才智,卻沒有賦予其在事業起步時足夠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他們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周圍人對他的認可。越是在其十分虛弱、毫無靠山的時候,維係於其內心的生存欲望就越強大,而這將必然給他們施政綱領的獨立性帶來極大的代價。
特朗普是聰明的,他比克林頓夫婦更為富裕,並依仗自己的富裕打壓希拉裏,意欲離析出美國的階級分野和仇恨。他感知到了民眾對於政治經濟聯姻現象的深刻憎惡,便打著對抗金錢政治的旗號脫引而出。然而希拉裏從本質上就沒有錢,她無法脫離克林頓強有力的募資班子,也無法不向東北部和西海岸的金融、科技勢力作出承諾。
這樣的事情本是美國選舉政治的常態,十幾年前在克林頓那裏甚至更為直接。克林頓首個任期的外交政策是布什總統的舊部在運作,經濟政策是各大財團代言人團隊的共同成果。在一次有關預算問題的關鍵辯論中,他幾乎是完完全全按照格林斯潘的意思作出了縮減財政赤字的決定,他的一個朋友曾經說,克林頓的身體裏沒有一根骨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生存。
這種個體自卑也將直接作用於他們對團隊的態度,他們並不會像肯尼迪相信邦迪和麥克納馬拉那樣相信別人。在克林頓的幕僚中,他對所有可能威脅到其當下和未來統治地位的人物都充滿防範。
其總統任內,國防部長換了三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換了兩屆,最為重要的國務卿之職或是給了克裏斯多弗這樣的和事佬,或者是給了奧爾布賴特這樣的話題女性,而剛剛贏得海灣戰爭身孚名望的鮑威爾將軍和公認的極為聰明出色的國務家霍爾布魯克始終無法進入其核心班底。按照某篇評論中的一句話,“克林頓政府的班子更像是一群從學院逃跑的難民,所有位置都遭到了不合適的安排”。
同樣的現象再次出現在希拉裏身上。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中,希拉裏沒有選擇曾擔任歐洲盟軍最高總司令的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裏迪斯將軍,也沒有能夠說服黨內僅次於桑德斯的進步派伊麗莎白·沃倫,而是又一次從國會山搬來一位約翰遜式的老參議員蒂姆·凱恩。
按照克林頓夫婦的習慣,自己必須要成為總統團隊中的最大話題,能夠壓住自己聲音的力量必須越少越好。這種自卑使得總統與身邊所有人都保持著淡淡的距離,克林頓的首任國防部長阿斯平曾向人抱怨,總統的很多想法都是從電視上或是報紙上聽到的,整個波斯尼亞危機期間他僅見過克林頓三麵。
相同點——缺乏外交事務的應有重視與職業敏感:
人人都知道,克林頓長於國內經濟事務。在他的首個任內,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幾乎翻了一番,失業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商業活動的方式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百萬和億萬富翁不斷增多。某種意義上,是克林頓養育了他們,在這對夫婦看來,現在他們做出一些反哺或許真的毫不為過。
經濟上的巨大成功衝昏了克林頓,也成功分散了國民注意力。幾年過後,當人們開始隨著保守派轉頭咒罵民主黨延誤了重要的發展契機的時候,他們驚訝地發現,這幾年,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成就少得可憐。
克林頓先天性地缺乏對外事務的基本敏感。一如其為人,整個任期沒有與任何主要大國建立起信任與真誠,卻囿於道德壓力戚戚於索馬裏、波斯尼亞、海地、科索沃等地的區域性人道主義危機,並一次次給自己帶來巨大的外交災難。
長期的冷戰使得美國的國務家和民眾對世界矛盾的認知單一化了,氣候已經鬆快,人們的意識卻仍然板結。克林頓順應著選民懵懂的對於和平建設和經濟複興的渴望獲得了任命,接下來卻不知該往哪兒走。
對於美國而言,冷戰結束以後的頭號任務應該是如何在對手消退的情況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國際角色。如果說整個九十年代隻剩下一個國家命題,那麽這個命題應該是“美國權力的界限”,而絕非國內的經濟發展。
很長一段時間,克林頓搞不清自己對於蘇聯留下的權力真空應有的態度,保持距離似乎有違勝利者的英明和道德義務,過分幹預則又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上世紀中葉在中南半島的噩夢,越南戰爭給民主黨留下太過嚴重的陰影和分裂,直接挫敗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政黨信念和合法性。
在最為重要的十年裏,民主黨人由於缺少國務運籌的宏觀戰略,踉踉蹌蹌地勉力完成了幾次維和任務的考驗,卻使得美國對戰後國際角色的定位這一重要的曆史使命被嚴重拖延,直至共和黨上台後並形成報複性反彈的保守勢力。
普利策獎獲得者,著名記者戴維·哈爾伯斯坦觀察到,“那些對自己的信仰懷有堅定立場,帶著滿腔政治進入國會的年輕保守黨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於超越了意識形態,成為強烈的個人攻擊”。
回到此刻,美國再次處於轉折的關鍵節點,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永遠是蘊藏著危險的,希拉裏站在門口,再次懵圈。
某種意義上講,她在任國務卿期間和奧巴馬共同采取的對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壓製策略頗有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遺風。然而伴隨中東地區的僭主一個個倒下,留下了馬蜂窩般的權力爛坑,無人收尾、無法撿拾。
而在亞洲,劇變正在發生。奧巴馬苦心孤詣的TPP遭到了所有總統候選人的集體彈劾,對南海的意誌力又嚴重不足,對介入存在極大的恐懼。甚至,連菲律賓這樣的哨崗也開始反叛,其引發的連帶效應將極大地動搖美國太平洋權勢的可信性,其深遠影響不可估量。
某種意義上,特朗普比希拉裏更能理解時代風貌,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是基於對於選民的心理判斷,在他看來,美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時代節點,虛無主義的文化認知將僭越多年來不必要的全球責任承載,形成更為主流的價值判斷。
希拉裏則沒有那麽複雜,她幾乎是本能的偏重於國內議題,這多半出於一種源自其丈夫的舊時習慣,她的團隊長於經濟,自然隻願談及國內事務;剩下一半,則源自特朗普“希拉裏是最差的國務卿”的高壓指責,很多對外事務希拉裏確實無法說清楚,而其中有一些,她注定要承擔責任。
這個節點的美國的確頗有風雨。如果特朗普當選,無論是戰後幾代人壘築的國際秩序還是美國的對外政策,都可能陷入一場無序;而如果希拉裏當選,或許陷入的不是無序,而是更為明確的衰退。
“自由世界”在守望“燈塔國”的國際角色定位,然而大家也都能夠淡淡地感到,無論怎樣,一種熟悉的美國治下的國際製度將成為舊跡,長達二十年左右的一號警察的角色,美國是無論如何不會再當了。
命途
以下的文字大概隻能算作泛泛而談。
克林頓夫婦或許還在一重意義上擁有共同點——所謂“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門”——他們看起來分享著幾近相同的命運。
代頓協議簽訂後,克林頓已經成功應對了波斯尼亞危機,肯尼迪敢於以畢生的勇氣用古巴導彈危機挽回自己在豬灣事件中的政治損失,克林頓也做到了。索馬裏和海地曾經讓他遭遇了幾近災難性的開局,甚至對盧旺達的恐怖不敢介入、視而不見,但是海地和巴爾幹局勢最終還是被他扳回來了。在第一個任期結束的時候,如果不言及戰略層麵的東西,他在對外事務上的評分是合格的,這使得他輕鬆獲得了連任。
然而萊溫斯基事件毀了這一切,輕鬆消耗掉了他在首個任期壘築的全部合法性,沒有能夠如其它曾經連任的總統一樣完成第一任期中由於缺乏政治力量和緊迫的經濟問題而被推後的事項。
全部總統班子的注意力被用來應付鎂光燈,克林頓本人則對於出頭露麵的場合更加挑剔,共和黨在長達三年的時間內瘋狂地攻擊他破壞了總統這一職位的神聖地位,剝奪了克林頓進行政治變革所主要依賴的道德權威。
克林頓熱衷於曆史學,在任的最後時間,他全力以赴,希望能夠以曆史的名義得以為人們所記住,然而他的第二個任期隻能在混沌與躲閃中度過。某次晚宴,他的身旁坐的剛好是美國曆史家協會的成員多麗絲·古德溫,這個協會剛剛完成一份對美國曆屆總統的評價排名報告,很遺憾,克林頓隻是普通地位於中間。這一晚的大部分時間,他放棄了應該處理的很多社交事務,不斷地表達自己對得到普通排名的不滿,為抬高自己的名次持續進行遊說。
凡事善始易獲,善終很難。
希拉裏現在最明白這個道理。她或許永遠沒有想到,這條競選之路充滿著如此多的非傳統性議題的挑戰,甚至是自己的健康。還有50多天的高強度工作,甚至第一場辯論即將舉行。即便是肺炎,即便是身強力健的成年人,也要靜養半月才能恢複,68歲的希拉裏確診6天後便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裏,她知道,留給她的時間沒有多少個6天了。
希拉裏現在用完了自己最後一張底牌,未來數日,在辯論場上、在電視機前、在巡遊拉票活動中,如果再次出現跌倒、噴嚏或者咳嗽,政治後果是致命的。人們會確信自己曾經懷疑的一切,毫不留情地瘋狂散去。如果能夠熬過這50天,或許,她能夠重生。
這場大選的核心風貌已經改變。人們會記住它,不僅僅因為它肥皂劇般的劇情,更因為它深刻動搖了美式民主的基石。這座屹立於山顛之城的經久信仰,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階級離間所質疑,在疑似俄羅斯的插手中被嘲笑,帶給了東西方大洋彼岸國家持續的不安。
選民們開始質疑從前大選中看過的那些家好月圓、和諧對抗的劇本,轉而思考自己在選舉中的角色和含義是什麽。從來沒有一屆選舉,兩派都在呼籲選民們深刻反思自己的肩頭使命,每一名選民都被一根根手指點著鼻子,特朗普們在問“你的階級立場是什麽!”希拉裏們在問“你要不要拯救美國和這個世界!”
老布什會為希拉裏投票,桑德斯的死士會為特朗普投票,階級區分首次挑戰到了黨派意識,而希拉裏是這一切變化的首位受害者。如果沒有特朗普掀起這一切,這本應是一場不能更為輕鬆的大選。沒有人知道,到底為什麽會發生這一切;也沒有人知道,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究竟在醞釀著什麽。
對於克林頓夫婦而言,這是命途。
尾聲
不久前結束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克林頓深情講述了他和希拉裏的戀愛故事,那是他的開場白。故事不到三分鍾,但劇情很豐富,畫麵很美好,一直以來人們喜愛克林頓的演講,一直以來人們也會質疑他們夫婦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如果某日,可以拋去一切浮華,這對夫婦或許本可以生活得很好。
希拉裏後來常常會談及從前的一段生活。在克林頓剛剛當選總統時最為晦暗的時刻,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經曆遠沒有想象的那麽簡單的政治生活和國家事務的許多挫敗。那段時間,據說總統和第一夫人經常是這樣開始一天的,他們一起吃早飯,其間希拉裏會挑選《時代》或者《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道或者專欄,跟他分析裏麵所有的對待他們的不公平。她敦促總統最好忽略這些事情,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
她說,這或許是他們最為美好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