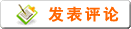近日读到几篇文章,讲述拔智齿时的痛苦,最甚者竟然动用了全身麻醉。虽然现代医学可以从专业角度说出若干理由,然而在我看来,拔智齿竟要全身麻醉,总有些小题大作、牛刀杀鸡的味道。由此我想起自己拔智齿的经历,那是多少带点传奇色彩的。
我的四颗智齿都是阻生齿,就是智齿斜在牙床里,长到一半被前面的牙顶住长不出来。阻生智齿疼痛难忍,只有拔掉一途。我的前两颗阻生智齿,是在读大学时先后拔除的。牙医说我的智齿长得结实,必须把齿槽骨去除一些,再把智齿凿碎,才能分而治之取出。眼见得牙医拿起锤子和凿子,我的心就凉了。当时的局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硬着头皮,听凭牙医在我嘴里叮叮当当地敲。虽说打过麻药不感到很痛,但满头脑被震得就像开裂一般。
有了如此痛苦的经历,我就期盼智齿们不要长出来了,免得再受罪。谁知1977年我三十岁时,剩下的两颗智齿还是顽强地要顶出来、却又顶不出来。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但即使这样,我也不愿再去受锤子和凿子的罪。
说来也巧,当年我出差到沈阳,家父任教于那里的辽宁中医学院(现更名为辽宁中医药大学)。他见我牙疼难忍,就说:“我们学院附属医院有位姓宫的牙医,掌握指压拔牙的绝技,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宫医生中等身材,四十多岁。他为我检查了一下,然后说:“好极了!你明天下午两点准时来,我把这两颗阻生智齿一起拔了。”从宫医生那里出来,我不禁有些疑惑:既然宫医生能手到病除,为什么非要我等到第二天,还说“好极了”?
疑惑归疑惑,第二天我准时到宫医生诊室,见他正接待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有七八个人。我坐上牙科椅,日本人就围在我前面。宫医生叫我张开嘴,用牙科锤敲敲两颗智齿,让日本人看到确实是坚固的。他用姆指使劲压住我智齿的牙龈部位,压了足有两三分钟。等我有了酸、麻、胀的感觉,宫医生拿起齿科钳,钳紧智齿。说那迟那时快,我只觉得智齿部位的牙床突然松了一下。几乎同时,我就看到被拔出来的智齿,带着两三点血丝,呈现在日本人面前,引起他们一片惊叹声。宫医生拿过棉球,嘱我咬紧压住创口。他向日本人解释,通常每次只能拔一颗牙,而指压法一次可以拔几颗牙。待我休息片刻,他用姆指压住另一侧智齿的牙龈部位,两三分钟后,他又钳到齿落,拔除了我另一颗智齿。
就这样,宫医生不打麻药,不钻洞,更不用锤子和凿子,仅凭一把齿科钳,十分钟就拔掉了两颗坚固的智齿。我几乎不感觉疼痛,只出了少许血,用棉球咬压几分钟即止住,三小时后便可进食,未服药物,也没有后遗症。这就是我亲历的指压拔牙,该算得是绝活吧?
那天的指压拔牙演示圆满结束,没想到又添了一段“余兴节目”。陪同日本客人的官员,正被牙痛困扰,就请宫医生顺便看看。宫医生检查后说有三颗病牙无可救治,只能拔除。这一回我改变了角色,得以在旁边观察,只见这位六十多岁的官员,满嘴牙齿被香烟熏得蜡黄。那三颗摇摇晃晃的病牙对于宫医生来说,简直如小菜一碟,连指压的时间都短得多。宫医生的手法极为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可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须臾之间,三颗黄牙已躺在白瓷盘中,日本人又发出惊叹声一片。
宫医生的这个绝活,被辽宁中医学院列入保留节目,经常向到访的外国客人演示。为了使外宾信服,演示中要拔的不能是摇摇欲坠之辈,最好是坚固的牙齿。宫医生的难处就在于演示当天,不一定有合适的患者。前一天他正为此发愁,怪不得见到我,要连声说“好极了”。
我所经历的指压拔牙,与麻醉拔牙相比,真是大异其趣。也许美国的牙医对此持怀疑态度者居多,说实话,我若不是亲身经历,大概也不会相信。很明显,指压拔牙之所以可行,关键在于指压能镇痛。因此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原来指压镇痛是老祖宗留下的绝技,据考证1851年清代名医吴亦鼎的著作《神灸经纶》就有记载。
指压拔牙须根据牙齿的部位来选择指压穴位:拔上前牙时,指压同侧的四白、颧廖;拔上磨牙时,指压同侧的下关、颧廖;拔下前牙时,指压同侧的承浆、颊车;拔下磨牙时,指压同侧的颊车、喜通或翳风下一寸。用拇指或食指按住相关穴位,采取按、压、揉三种手法,用力压迫穴位1至2分钟,待患者感觉酸、麻、胀、重,即可拔牙。牙齿拔除后,再轻微揉动穴位1至2分钟,以消除局部的不适感。
指压拔牙的优点,据介绍有三点。一是操作安全可靠,一般没有副作用和禁忌症,对高血压与心脏病患者,在严密观察和慎重操作下,也能安全拔牙。二是患者不感觉疼痛,拔牙创口出血较少。三是方法简便,不需专门器械和药物,易于掌握,特别适用于农村及作战前线。当然也有不适宜指压拔牙的情况:如果病齿开裂或断掉,或者阻生的智齿未突出牙龈,就不能用指压法拔除,还得靠麻醉法拔除。
至于为我实施指压拔牙的宫医生,大陆媒体在1979年有过专门报道,称他“先后用这种拔牙方法医治病例一万多例,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还为来我国访问的十几个国家的外宾拔了病牙,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如今宫医生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不知道他的这一手绝活是否后继有人。指压拔牙如能得到发扬光大,必能造福世界上更多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