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残阳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 是将来的历史, 我们不纠缠历史,我们创造历史!大清朝同治六年,是旧历丁卯年,公元1867年,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在一年却因两个帝国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大清帝国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大清帝国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帝国士人群体中的末流。对清帝国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直接关乎到帝国的前途命运

王韬此次欧洲之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就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言,也是影响深远。之所以如此申论,是因为王韬的身份非常地特殊。这种特殊的身份让他有幸成为那个时代游走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边缘的拓荒者。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其中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并曾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曾经饱读诗书,深受中学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王韬是幸运的,当1867年12月15日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图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让王韬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王韬很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开辟了大清帝国的通商口岸,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的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

只要想一下王韬的衣着打扮,再将他的行头与英国人比较一番,就知道他成为“怪物”的奥秘了。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们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虽然王韬的英语不行,但是他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还是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英文。因此,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伦敦小孩不辨雌雄,王韬虽不以为忤,却引发了他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感叹。他说,“忝此须眉,蒙以巾帼,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制谶语哉”!

1849年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这年夏天,他的父亲病故。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两年前,王瀚的父亲来到大清帝国的通商口岸-上海设馆授徒,维持生计。随后,王瀚也从江苏省甫里镇(今天苏州市甪直镇)老家赶到上海探望父亲。在上海,王瀚体验了通商口岸华洋杂处的文化氛围,也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1796-1857)。在父亲去世后,王瀚在1849年秋天担任麦都思在上海主持的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像王瀚这样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去为洋人打工,在那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不够体面的事情。

其后,王瀚跟随家父到上海,以靠给洋人“卖文”为生。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仍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怀疑和鄙视。作为走异路的文化人,王瀚与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的两个秀才李善兰(1810-1882)和蒋敦复(1808-1867)结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异民”。墨海书馆是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下属机构,在馆长麦都思的劝导下,王瀚先是成为基督教的“慕道友”,随后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成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
至少在形式上看来,王瀚新获得的基督徒身份让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是他的心还依然留恋着帝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王瀚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同胞掩盖他的基督徒身份,而在其生活方式上更加向传统士人回归。王瀚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即通过入教可以更好地获得其传教士主子的信任。一句话,王瀚的入教不过是一种事业发展的需要,就像孙中山受洗基督教一样。孙中山入教,并不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处理与基督教的关系上,王瀚与孙中山很相像,两人都是借此谋求洋人教会的支持,而他们真正信仰的是民族主义。

1860年2月20日清晨,王瀚与友人祝安甫一同又来到秦娘住处,听其弹奏数曲。秦娘的细指落处,琴声抑扬顿挫,顷刻数变。听到动情处,王瀚不仅想起大唐诗人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动人故事,顿生长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秦娘的高超琴艺和不幸遭遇,王瀚有字为证,他写道,“滑如盘走珠,朗如瓶泻水,宏壮如铁骑千群,银涛万顷,悲怨幽咽,如羁人戍客,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荡人神志也”。
自从屈身上海墨海书馆以来,十余年间,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一句话,他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弊病。如1859年,当英法两国提出“修约问题”,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派驻公使驻扎京师,但是清廷百般阻挠。对此,王瀚实在看不下去,他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变通。王瀚在这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大臣不能熟稔夷事,以为英酋驻扎京师,大失国体,大有龃龉。不知泰西各与国原有此例。两相遣使,互驻都中,使往来情事,不致壅于上闻,其实于大局并无损害。” 对于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无知,王瀚无奈地哀叹说:“以后之事,愈不可为矣”。 通过以上两次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有王瀚经常在两个精神世界里徘徊:在情感生活上他依然具有传统文人的情怀,忘情于琴艺声色之中,在政治观念上他已经认同于西方文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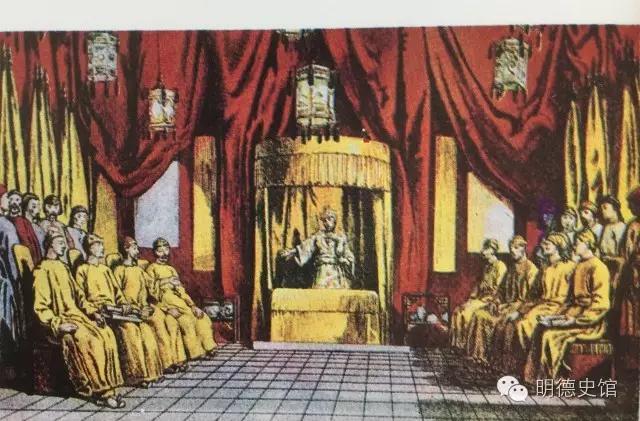
1862年元月,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立即返乡探母。一直到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时,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在苏褔省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议太平军应该暂时集中兵力进攻清军,不要进攻上海,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关于王瀚写这封信的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韬是为了讨好太平军,保护其家乡亲族的性命;有人说王瀚是受到英国人的指使。总之,当王瀚这封信在1862年4月4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就成为他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清廷很快查出,这个黄婉就是王瀚。1862年4月25日,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并着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办。

此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Wafter Henry Medhurst),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1862年10月4日,在麦华佗领事的建议下,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远赴香港避难。这个大清帝国的通缉犯,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