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辉煌的清华时代
1925 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门一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一定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来担任研究院导师。“导师”是当时中国二、三十年代清华教职中一个特殊的称谓,这使它有别于其他一般教授。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演说中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至今也是至理名言。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和清华大学照片,见图:

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同年3月,经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特别推荐,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正式聘请陈寅恪先生回国,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一起出任国学研究院教授。
关于聘请陈寅恪先生为国学研究院一事,以前大家过分相信陈哲三先生文章中的那段“传说”。在陈哲三先生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自称是引述其师,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征的原话: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他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此说常常被文史学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有几点不实予以订正如下:
- 推荐陈寅恪先生不在民国十五年,而在民国十四年。
- 1925年以前的陈寅恪先生尚未有“寥寥数百字”论文发表,如上文中说“也没有著作”。何谈“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 梁启超先生从来不称陈寅恪先生为“陈先生”,只是直称其名“寅恪”。
- 梁启超先生和曹云祥先生一向不和,他们二人很少能有上述谈话的机会。
- 查梁启超先生和曹云祥先生二人各类存世资料,并无上述内容的记录。
- 推荐陈寅恪先生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还有吴雨僧先生,至死不见吴雨僧先生道及此说。
- 蓝文征先生本人发表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和其它文章中也不见有此说。
- 至今不见有研究院的其它学生发表上述内容的文章,而当时只是陈寅恪先生的很普通的学生的蓝文征如何能知道上述内容的谈话?
- 陈寅恪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代材料中也不见有上述说明。
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先生及其和泰戈尔等人合影照片,见图:

此事之本末本来正如吴雨僧先生所说的“费尽气力”。
1925年2月13日这一天,根据《吴宓日记》记载:“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 Y.S.即曹云祥,P.C.即彭春。2月15日则是“事有变化,议薪未决”。2月16日则事再次找曹云祥“谈寅恪事”,这次果然就OK了。为了聘请陈寅恪先生,他连续三天和校长谈此事。此情此义,感人至深。作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雨僧先生和教授梁启超先生在国学研究院的会议上共同推荐陈寅恪先生:吴雨僧先生推荐的意义在于他的留学海外经历,使人相信陈寅恪先生的西学水准。梁启超先生推荐的意义在于他的国学水准和他与旧知识人的关系,使人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国学功力和家庭背景。吴雨僧先生在美国一见陈寅恪先生就“惊其博学”,他的推荐在情理之中。梁启超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一家三代有来往,如无陈寅恪先生祖父的大力提拔,梁启超先生不可能成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的推荐理所当然。此事之原委大体如此。或有人以为此事只是由吴雨僧先生推荐,以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是不确实的。
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9 月14日正式开学。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们照片,见图:

前排左起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李济先生。
清华学堂照片,见图:

1926年7月,陈寅恪先生正式到北京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上课,根据《清华周刊》第351期的记载,陈寅恪先生讲授的范围是:
年历学。
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
摩尼教经典回紇译文之研究。
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
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不难看出,陈寅恪先生一生的研究重点这里已经基本概括了。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最为平静和安逸的时期。
1928年春,陈寅恪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也是讲授佛经翻译文学。秋,他开始讲授蒙古源流研究。
1930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他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在中文系讲授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唐诗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在历史系讲授课程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
1930年开始,他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陈寅恪先生深切阐发了其重视历史的原因,即:
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仆、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
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与妹书》中说: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
这一研究核心后来集中表现在他的四篇“蒙古源流研究”论文中:即《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原载1930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原载1929年8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1930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两篇同载于1931年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册。
这些论文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主要贡献,标志着我国蒙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全家人合影照片,见图:

1934年,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蒋廷黻先生在《历史系近三年概况》一文中还专门介绍到了陈寅恪先生的教学和科研情况,他说:
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
短暂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随后的清华大学教授时期,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一生学术事业最为辉煌和自由的时期。也是他成就最多并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的地位时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11月,陈寅恪先生带领全家人经天津到达青岛,再到长沙和桂林,最后到香港。而他则只身一人任前往云南蒙自,执教那里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此后一年中,陈寅恪先生多次往来于香港和云南。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同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
1940年,陈寅恪先生的第一部中古史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问世。
同年9月,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陈寅恪先生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机到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后因为许地山先生的推荐,他留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根据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日记中的记载:
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先生留下,成为香港大学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在薄扶林运动场特地举行了欢迎陈寅恪先生的聚会。
1941年,许地山因病逝世,陈寅恪先生被大家推举成了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就在这里写完的,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
在此期间,他的一点心境记录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
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中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傥非其书喜众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
陈寅恪先生在香港大学期间和师生合影照片,见图:

在此期间,日伪政权多次派人找他出山。
见《陈寅恪书信集》一书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朱家骅等人信: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1942年,驻港难民太多,致使在港生活已经成为大问题,日军迫不得已开始了所谓的内地难民返乡运动,并开放了已经关闭了一年左右的通商口岸。于是,陈寅恪先生一家人利用这一机会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同年7月到桂林,并开始任教于广西大学。
在桂林短暂的安定期间,他的第二部中古史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得以完成。
陈寅恪先生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手迹照片,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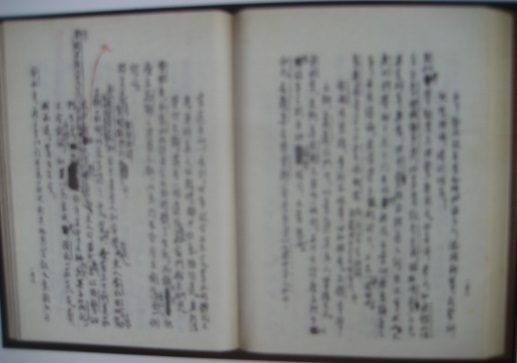
同年,陈寅恪先生当选为教育部聘任教授。8月,他已经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见《吴宓日记》1943年8月15日记载:“接寅恪8月4日桂林函……将于八月中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
1943年12月,陈寅恪先生带领全家到达大后方的成都,临时执教于当时南迁的燕京大学。
1944年3月,陈寅恪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名誉导师。
同年7月1日,陈寅恪先生前往中山大学讲学。见中山大学《本校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陈寅恪先生在校讲学》一文:
陈寅恪教授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中国学研究所主任,因欧战所阻未能赴聘,改任香港大学英庚款交换教授。现任教育部部聘史学教授执教于广西大学。本年度金校长特聘为本校研究院特约教授。陈氏以专门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与以梵文比对汉译佛经及精通十余种语言文字蜚声中外。其专门著作因欲矫今日轻易刊书之弊,甚少刊行,仅出版《唐史概要》一书。其重要论文散见于清华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先生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晨起床后,陈寅恪先生痛苦地发现:本来已经是右眼失明了,现在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根据他的女儿陈流求所写的笔记记载: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
《吴宓日记》在这一天记载为:“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
到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陈寅恪先生再次住入该院治疗。他在成都的存仁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是手术没有成功。从此以后,目盲成了制约陈寅恪先生独立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的致命伤。早在1944年11月23日,他就在致李济、傅斯年二先生的信中说: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1945年8月,赴英国治疗眼病。由著名眼科专家Steward Duke Elder男爵负责诊治,数月奔波,两次手术,只是对光的感受功能有些好转,但是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给陈寅恪先生治疗过眼病的大夫Steward Duke Elder男爵照片,见图:

见《胡适日记》1946年4月16日: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46年春,他自英国经美返回国后,回到北京,再任清华大学教授。他以后诗歌中所谓的短暂的“北归”生活开始了。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的照片,见图: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在蒋介石授意下,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开始了所谓的“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首先抢救的便是胡适、梅贻琦、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先生。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然后,他带领全家来到广州。
1949年1月,陈寅恪先生一家搬进了老朋友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的家中。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陈寅恪先生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月20日,《岭南大学校报》上特别刊登了《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的消息。
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已先行搬到了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教育部长杭立武二人多次电催陈寅恪先生坐飞机去台湾。均遭到了他的拒绝。
综观陈寅恪先生在这段时间内的科研活动,几乎全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取得的。
陈寅恪先生在海外留学期间就比较语言学,为此他学习了多种文字,这为他利用这些文字史料研究中国史,同时在方法论上在继承了乾嘉学者考据传统之后,又吸收了西方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运用中西结合的精密的史料考证方法,从许多相关和不相关的史料中考证出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关键所在。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特别是李唐氏族渊源和府兵制度研究)、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和佛经翻译、校勘、解释)、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音韵学和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和陈寅恪、姜立夫先生合影照片,见图:

陈序经夫妇和陈寅恪、姜立夫夫妇合影照片,见图:

1988年,冯友兰先生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评价说: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
接着,冯友兰先生主张:“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冯友兰先生这一评价是十分恰当的。陈寅恪先生自己当时已经准备好了要继续从事不古不今之学的研究,并公开地宣称其思想不在民国与新中国,仍然是停留在咸丰同治之世。因此,冯友兰先生的以夷齐说来解释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心境尤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