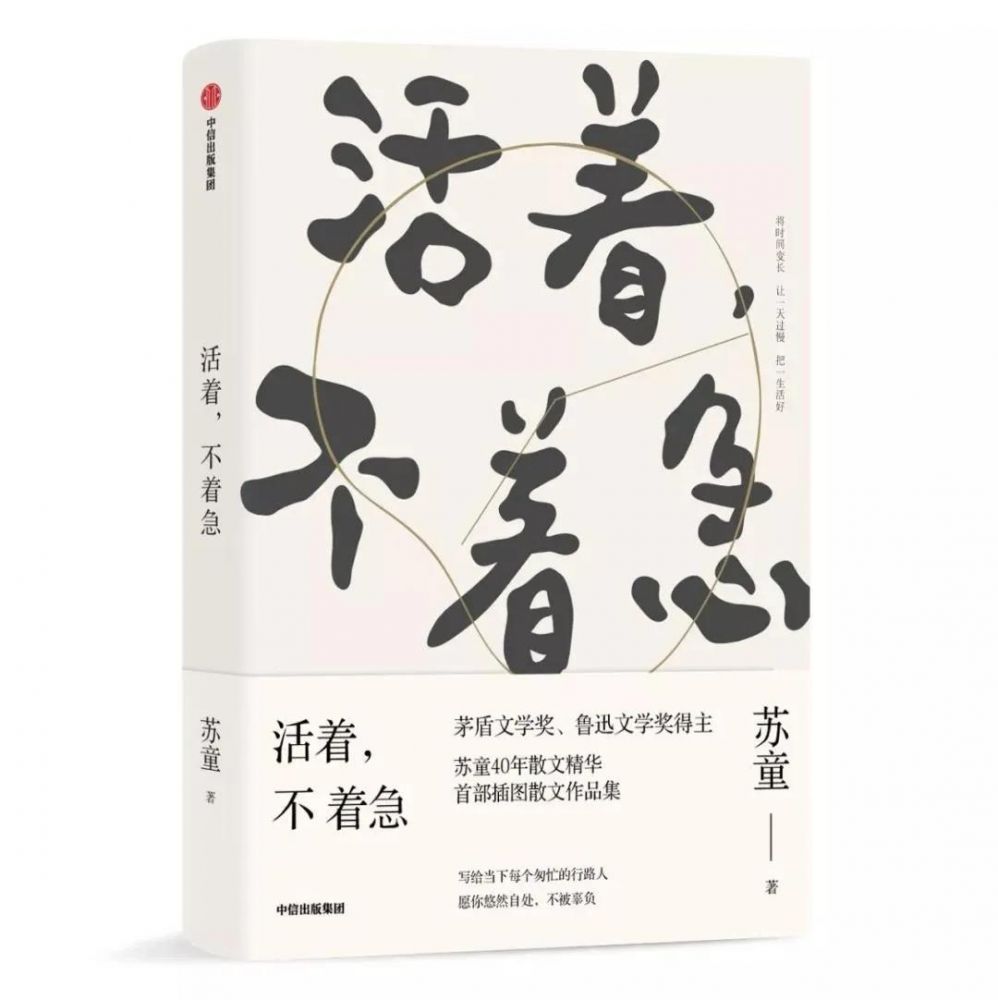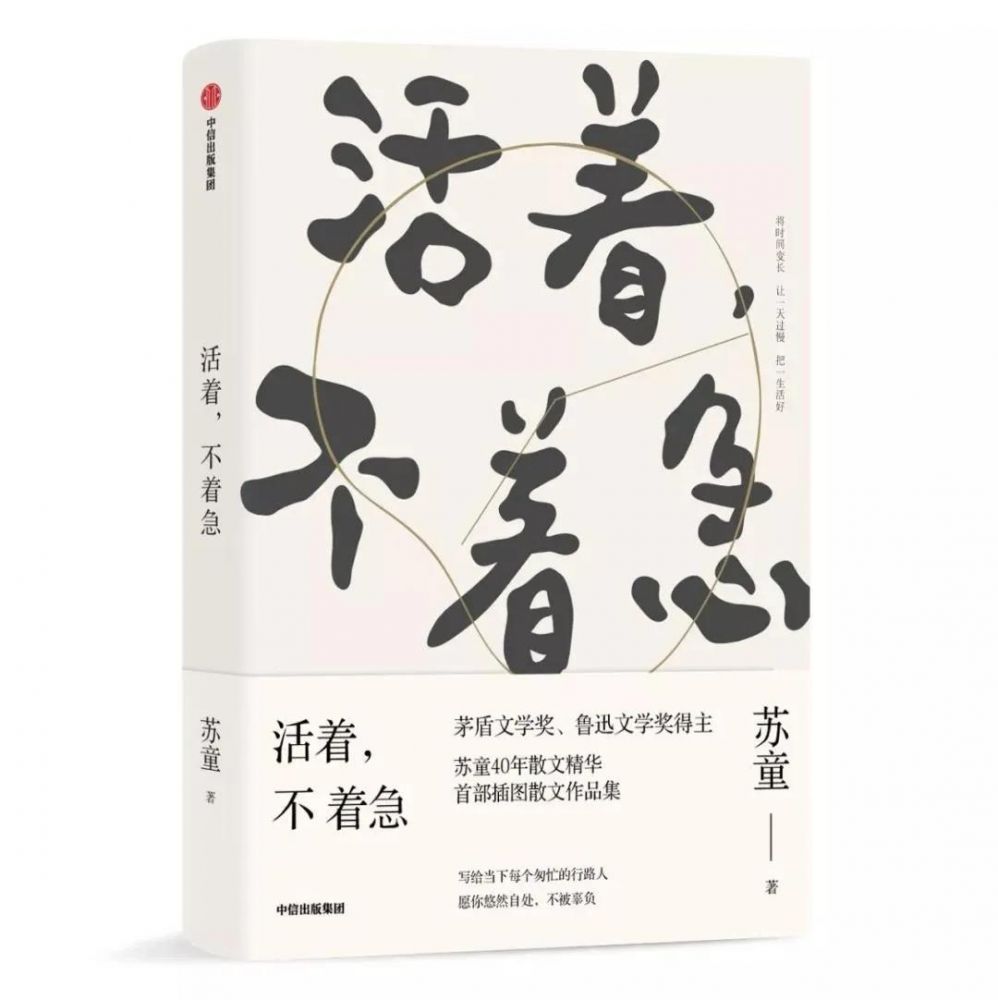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



将我的博客复制一份至《海外博客》
由于数据量较大,请您耐心等待复制完成
复制

正文
苏童 | 女人和声音
(2021-03-08 12:33:28)
下一个

作家苏童
苏童

屈指数来,我在苏州完整的生活也只有十八年。我生长在一条市井气息浓郁的街道上,我们那条街上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因此也不了解苏州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是有一些的,但那种女孩子羞答答的,平时把闺房门一关,她整天在干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所以如果让我来谈苏州的女人,我有信心描述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而且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此地女人与彼地女人,造成她们之间主要差异的,其实只是语言和声音。也许对不起一些严格的读者了,我就从声音说起,说三个苏州女人的声音的故事。如果你走在街上遇见敏儿他妈,你不会猜到她是个说评弹的女艺人,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严某某,就是那个围白丝巾的女人,她以前是评弹团的演员,你会说,这就对了,她一定是说评弹的——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否是说评弹的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致是 :声音清脆,而且拖着一丝歌唱性的韵脚,眼睛也会说话,更重要的是这些艺人会用眼睛微笑。我印象中这个姓严的女人非常喜欢阳光,主要表现在她对晒被子、晒毛衣、晒萝卜干甚至晒拖鞋的极度热衷上。她如此珍惜阳光,而她丈夫却天天浪费阳光,他常常端着一只茶杯坐在家门口与别人下棋。敏儿他妈就拿着藤拍子从丈夫的身边穿过来绕过去的,她的婆婆也坐在门口,不是下棋,也不看棋, 她漠然地看着媳妇忙碌,有时候整理一下盖在膝盖上的一块毯 子。看上去老妇人觉得媳妇如此忙碌是天经地义的,她的眼神在说:我忙了一辈子啦,现在轮到你啦。媳妇也任劳任怨,我记得她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用力拍打晾竿上的棉被,用她特有的歌唱般的声音对邻居们说 :“天气好得来,被子要晒晒!”说评弹的女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北农场插队,逢年过节才回来,长得像母亲,很英俊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上去脸色苍白,神情总是郁郁寡欢的。小儿子就是敏儿,也是相貌堂堂, 不过却是街上有名的问题青年,隔三岔五惹是生非。别人家的父母找上门来,找家长大人说理,这时候敏儿他爸照例是退到一边,向屋里喊,你快出来,快出来呀!做妈的就应声掀开了门帘,端端正正地走出来面对来人——不是一般地出来,是像上台说书一样,微笑着仪态万方地走出来,就像艺人面对听众那样,面对动了肝火的邻居。开场白是相似的,女人先把自己的儿子数落一顿,然后评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时仅仅是猜测或者分析,但让对方感到小辈的顽劣历历在目。当你开始点头称是,从前的女艺人话锋柔软地向左歪或者向右对齐了,她能说出一种令人信服的道理,意思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乒乒乓乓,更深的意思是孩子就是孩子,在外面打架斗气是正常的,做大人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吵来吵去倒伤了街坊邻居的和气。职业性的叙事手法使她的一字一句都心平气和,即使对方听着并不是真正的受用,却无法再做计较,因此总是讪讪而去。由于她在处理此类事情上成绩卓著,街上的其他妇女也经常围过去听她是怎么打发上门算账的人,但是效果你也能预料,没有用,许多事情是没法取经送宝的 ;再说,也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像敏儿他妈那样,说过评弹。当时我们那里的评弹团好像是解散了的。姓严的女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我有时候看到她提一只布兜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沿途用她清亮的声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里便暗想,她在书场里说评弹时什么样子,搭档是谁?她会不会唱那个余红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当然我无从知道关于她作为评弹艺人的任何细节。我知道许多吃艺术饭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却不吊,那么好的嗓子全浪费在与女邻居谈论阳光和被子上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也不能去问她,她就那么在家门口晒这晒那,在街上走来走去。过了好几年,我们城市的评弹团恢复演出了,市中心的书场门口经常贴出演出海报,还有演员的名字,我路过那里时不免要留意严某某这个名字,但是节目换了一档又一档,我从来就没有找到敏儿他妈妈的名字。我问我母亲,不是说敏儿他妈妈说评弹有点名气吗,怎么不见她演出?我母亲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测说敏儿他妈妈大概离开评弹团了。评弹后来在我们那里是老调重弹,不光是书场里,广播喇叭里,甚至在一些茶馆里,都有有名或者无名的艺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嗯嗯呀呀地唱,姓严的女人却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里。奇怪的是后来她不再忙于晒这晒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见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门口,指挥她丈夫收一匾萝卜干。她丈夫无法把竹匾顺利地搬进狭小的门洞,她婆婆在一边颤颤巍巍地帮忙,帮的是倒忙,萝卜干纷纷地掉在了地上。让我奇怪的是姓严的女人对此的反应,她一反常态,柳眉斜竖,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说,“笨煞哉,笨煞哉!我不来,你们搬点萝卜干都搬不来!”让姓严的女人生气的其实不是萝卜干,是她的病。我后来知道她不出来晒被子是因为得了病,乳腺癌。听说她的一只乳房被医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声音因此也被什么取走了。邻居们在街上拉住她儿子,就是那个叫敏儿的青年问,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敏儿头一拧,说,“她生病,关你什么屁事?”邻居们都吐舌头,说,“严某某那么好的女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再后来姓严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摄于六十年代的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白布上,着了色,很美很妩媚,嘴角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们那儿的殡葬是公开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见死者的丈夫、婆婆还有她的不听话的儿子都在哭,怎么会不哭呢,这户人家的顶梁柱没有了 ;邻居们也哭,怎么不哭?以后不会有人用那么美妙的声音与你谈论家务事儿女事了。坦率地说在她的灵床边我好奇多于悲伤,我心有旁骛,寻找着这个女人艺术生涯的实证。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墙上发现一只琵琶,那只琵琶静静地挂在那儿,似乎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在充斥着悲声哀诉的葬礼上,琵琶被所有人遗忘了,我想应该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边,但是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们街上,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却是逃逸的,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在哪家书场的台子上,罩着一层灰尘,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怀抱琵琶的样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个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她的评弹。我想让我去想象这件事有点荒诞,她既然是说评弹的,她既然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为什么从未听过她说评弹的声音呢?这个疑团大概是不会有人来解答的,暂且让那个女人安息, 我来描述第二个女人的声音——第二个女人的声音与评弹无关,但与广播喇叭有关。 这里所描述的女人,同样有着人们认为最甜美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她是我们家对面工厂的广播员,她的声音应该是甜美的,否则就不公平了,那家工厂有好多青年女工,大家都能说不卷舌的普通话,凭什么让她当广播员?她也一样不懂得如何卷舌,一样把“是”念成“四”,把“阶级敌人”念成“阶级涤纶”。早晨我经常被这个女广播员的声音从睡眠中说醒,我不用惊醒这个词,比较符合实际,一个动听绵软的声音是决不会让人受到惊吓的。她在河对面的高音喇叭里说话,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你的耳边嗡嗡地回旋,你慢慢地就醒了。我听见她在广播里说 :文章说——这是在摘引报纸上的文章,如此的播音结构最正常不过,但当时年少无知,偏偏又爱较真,听到她说“文章说”就纳闷,心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文章又不是人,文章没有嘴,怎么会说话呢?我一直认为那个女广播员播音有误,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错误和偏见。我母亲就在那家工厂工作,有时候我去那儿洗澡或者吃午餐,在厂区的路上偶尔会看见一个体态苗条梳两条辫子的年轻女子,穿的也是蓝色工装,但是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明显修改过了,修改得非常合乎女人人体的曲线,而且她的身上没有粉尘和油污,手里拿着的不是劳动工具或者机器零件,而是一卷报纸或者一本杂志,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得表情。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播音员,就是那个“文章说”。“文章说”走在厂里,好多人,男的女的都踊跃与她打招 呼,可见她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也很正常。就我所知,不管是在工厂、农村还是学校,当时的广播员各方面都要“过得硬”,群众关系不好,别人会说凭什么让她坐在广播室里念稿子抓革 命,让我们守着水泥窑汗流浃背地促生产?知识水平不高不行, 否则你老是念错别字会歪曲了《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的精神!你的思想觉悟不高就更危险,万一你利用宣传阵地喊出一句反动口号,如何是好?所以我相信女广播员是个优秀分子,但对她的“文章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她就不能换一种说法吗?有一年秋天,河对岸工厂的高音喇叭突然沉寂了几天,然后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的声音,那个姑娘说话结结巴巴,显示她是个播音战线的新兵。她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下面请听革命歌曲——等了半天,革命歌曲却始终响不起来,等得你心焦,她还没有把歌曲放出声音。于是那个紧张的声音更紧张了, 亡羊补牢地说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同志们,再见。新来的广播员让人丧气。凡事就怕比较,我猜在“文章说” 从广播站突然消失的那些日子,在工厂的高音喇叭所辐射的区域内,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文章说” 到哪里去了?“文章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与河对岸的广播生物钟般的联系似乎是被强行中断了, 不知不觉中我习惯并依赖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结果我原先并不自知。说我怀念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是词不达意的,但我讨厌新来的女广播员尖锐生硬的声音却是千真万确的。由此我也开始讨厌那个工厂的广播站,每天清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前奏曲把我惊醒时,我总是在床上痛苦地捂紧耳朵,说,吵死人啦!还是交代清楚那个女广播员的下落吧,这没什么关子可卖。那年元旦——或者春节?记不清了,反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节日,母亲带我去一家剧场,去看文艺演出。文艺演出中样板戏总是重头戏,建材系统的文艺演出也是相同的模式,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合唱,然后就是样板戏了,全本样板戏排练起来有困难,就来几个片段。《沙家浜》的智斗开始了,站在“春 来茶馆”牌匾下的阿庆嫂是谁?我觉得那么面熟,猛地就听见我旁边的观众狂热而骄傲地报出了一个名字,说,我们厂的广播员啊!她演阿庆嫂!果然就是那个消失了很久的女广播员。原来她到宣传队去了,这是更上一层楼的事。出于习惯我还是乐意当她的听众。我听她唱“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就跟着哼了起来,我看她翘着食指指向胡传魁、刁德一,觉得这手势比洪雪飞的手势更加英姿勃发。这会儿她是阿庆嫂,我忘了她在广播里的不足之处,她不再说什么“文章说”,整个人就显得完美无缺。这还不算什么,《沙家浜》下面是《红灯记》,留长辫穿红袄的李 铁梅粉墨登场了,我记得的是观众们的一片哗然,下面有人用惊叹句说 :啊呀,又演小铁梅又演阿庆嫂啊!不得了!依然是她,就是那个女广播员!那天坐在剧场的椅子上,我突然理解了她从广播站消失的必然性,她真不得了!七十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使用人才这个字眼,我也并不懂得如何去崇拜一个女人,但我从此对一个女人的才华铭记在心。这个“文章说”,她是一个广播员?她是阿庆嫂?她是李铁梅?她到底是谁?我想她就像一只万花筒,摇一摇,一定还能变出更多的花样。现在请大家回忆一下《沙家浜》里刁德一对阿庆嫂的评价。刁德一很警惕又很佩服地说 :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唱腔,就会想起那个女广播员,当然这说的是她的青年时代。后来呢?有人大概会追问。我其实不愿意描述女播音员的现状,现状的棱角显得那么尖锐,而且无趣,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相仿的命运。阳光和辉煌有时候只在你的额角上亲吻一次,然后就无影无踪,就像我这里说的那女广播员。她的现状不像我的文章一味追求完整——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宣传队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他们结了婚却失去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不是他们不求上进,是宣传队解散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女广播员不知怎么没有再进广播站,好像是在工会里做些难以总结的杂事。后来她有了个女儿,过了几年, 又有个女儿。一晃多年,再后来她当了外婆。九十年代的女广播员体形仍然苗条,但脸上的皱纹很多,给人饱经风霜的印象,这对一个女人的风韵来说并无多大益处。她上街买菜,抱着外孙去浴室洗澡,声音依然清脆甜美,但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听着无聊。种种迹象表明我文章中的女广播员属于过去,而现在的她,生活越变越寻常了。从前的女广播员如今走在荒芜的濒临倒闭的工厂中,停产的厂区安静得出奇。但即使是那么安静,她也听不见年轻时候回荡在厂区的声音了,文章说——外面的报纸越来越多,文章越来越多,但文章说什么,与她有何相干?她管不了那么多,最近她要下岗了。报纸上的文章说,竞争再上岗。不知这个女广播员现在跟谁竞争,也不知道她是否在考虑,去哪儿上岗对她最合适?不说下岗上岗的事了,我这就说到了第三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生活也与声音相依为命,只不过她的声音用途更加粗鄙更加世俗一些。这个女人的声音并不动听,动听也没用,因为她的声音主要是用来叫卖蔬菜鱼鲜的。她在街坊邻居的妇女堆中显得有点特别。特别处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容貌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粗俗;也不在她的衣着打扮,她的打扮也实在本分,大部分同龄妇女穿什么,她就穿什么。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职业,在严禁城市人口从事私有经济的年代,她竟然以贩卖蔬菜为生,她是一个女贩子!她是一个女贩子,这决定了她在孩子们眼中是一个形迹可疑鬼鬼祟祟的女人,投机倒把使她的眼神中有一种负罪感。但奇怪的是没有谁看见她在我们的视线里贩卖任何蔬菜。人们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去收蔬菜,然后到很远的农贸市场将那些蔬菜卖掉。这些贩卖的细节都在人们的猜度中,却得不到亲眼所见的证实,这是女贩子最特别之处,也是一些邻居议论纷纷的焦点。有与她熟络的人说,人家怕羞,人家爱面子,她不愿意在街坊邻居面前丢那个人。她丈夫是个工人,那个说话口吃性格木讷的男人把她从郊县农村娶进门,一口气与她生下三个孩子,却始终没能为妻子寻找到一个正当的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很难,那个女人虽出身于农家,却并不愿意过什么艰苦朴素的生活,别人家有手表她也想有,别人家有缝纫机她也想有。街上别的妇女认为这是要强,要强就要行动,这女人有一天就行动了,干的是贩卖蔬菜的勾当。女贩子行踪不定,有时候一连好多天看不见她的人影,这往往是她购销两旺的黄金季节。她早出晚归,除了她的家人, 别人是看不见她的,即使看见她也没什么用。一般情况下她空着手在街上走(不知她是把蔬菜筐存在什么地方的),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与刚刚从纺织厂下班回家的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有时候她一连几天闲在家里,手里拿着针线,坐在门口与女邻居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作为一个市井妇女,她当然也有市井妇女特有的爱好,喜欢看热闹,谁家夫妻吵架父子斗殴她都要站在前面观看,只是不怎么发言,显然怕让别人倒拔葱, 带出她的一把泥来。但看她的表情是很丰富的,同情或者谴责谁,站在谁的一边,脸上是一目了然。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时候往往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最热烈的当口,她按兵不动,在自家门口看看别人家的闲事,是非常明智的。她是文盲,不识字,但是算账很快,左右邻居卖废品的时候,都要拉着她算一遍,这样才能确保不吃亏。这样的算术才能无疑得益于她的小贩生涯。她人缘很好,除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经常痛骂他们的蠢笨和顽劣),从不得罪人,所以这个从事不法行当的妇女,得到了来自邻居的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有一次街上的孩子们听见女贩子家传来了嘈杂的声音,这使他们很兴奋,都拥到她家门口,看看这户人家有什么事情,但女贩子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像铁将军一样挡在家门口,只让大人们进去,不让孩子进去,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他们好像明白母亲刚刚遭受的屈辱,她在市场上遭到了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秤被折断了,蔬菜筐子被踩烂了,而且他们的母亲还被人打了。女贩子在屋里哭泣,她的子女就善解人意地放大人进去,让那些能言善劝的妇女去安慰他们的母亲,然而他们发现母亲的悲伤内容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她在里面突然大叫一声,我命苦哇!这种凄厉的呐喊使孩子们摸不着头脑,也只有大人才得其中之味。但是女贩子的女儿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她一定懂得母亲做贩子的艰辛,所以她站在两个弟弟的后面,一边替他们挡着门,一边呜呜地回应着母亲哭泣起来。这就说到了女贩子的几个孩子。女儿没什么可说的,人有点笨,却善良,后来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小伙子家境贫困,结果连新房里的家具都是女贩子打好了陪嫁过去,那姑娘嫁妆之丰厚让邻居们很是吃惊,他们都说没想到,没想到女贩子这几年贩蔬菜,贩出了个如此殷实的家底。没想到的事情尽出在女贩子家中,女贩子的大儿子长到血气方刚的年龄,正准备去下乡插队,有一天突然犯了心脏病,不明不白地就死在了床上。女贩子大病一场,过了一阵恢复过来了,对要好的邻居说,我这样躺下去不是件事情,大的没了,还有小的呢。我还要出去做。邻居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出去做”就是指贩卖蔬菜。可怜天下父母心,女贩子为了小儿子,戴着大儿子的丧带, 又出去“做”了。小儿子长得英俊,讨人喜欢,就是不听话,典型的不爱学习爱打架的中学生,总是有别的孩子家长吵到门上来,说自家孩子被他欺负了。女贩子不在家,这事由她丈夫处理,那男人就朝自己儿子扇耳光。扇了好多年,突然有一天,做父亲的手被儿子牢牢抓住,做父亲的胸口挨了儿子重重的一拳,儿子说,×你妈,你还打我呀,小心我灭了你。那就是女贩子唯一的儿子了。人们都预见了这个男孩的不妙的未来,只有女贩子盲目地为儿子构造着幸福的蓝图,后来这蓝图就被儿子亲手撕成两半,儿子终于在外面闯了大祸,他用西瓜刀把一个卖瓜人的肠子捅出来,警察当场就把他铐走。女贩子闻讯赶去要人,别人就指给她看西瓜摊前的血迹,女贩子不看血迹,一味地要儿子,警察当然不理她。那没脑子的儿子, 最后被送进了外地的一个劳动教养所。邻居们记得女贩子又是一场大病。那一阵子她卧床不起,连她丈夫都怀疑她是否能挨过又一次打击,但是我已经介绍过了,这是个特别的女人,她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职业,也在于她的坚强和信念。女贩子在探望过儿子以后,很快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她向邻居们抱怨有些人执法不公,谁家的孩子打架打出人命都没进去,靠的都是关系。她没有关系,只能让孩子去吃苦。邻居们似乎都不忍心质疑她无私的母爱,就问她以后准备怎么办?女贩子抹去眼泪,嘴角浮现出坚韧的积极向上的微笑,说:“我能怎么办?我就有两只手,出去做呀,赚点钱,等他出来了,要结婚要成家,还得靠我的两只手呀!”女贩子奇迹般地继续她的小贩生涯,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她也扩大了贩卖业务。后来听邻居们说,她不仅贩卖蔬菜, 也贩卖鱼虾,在秋季她还来往于阳澄湖甚至洪泽湖,倒卖当红的大螃蟹。还有的邻居,亲眼看见她在百货公司购买金戒指和金项链,她一转身就否认,还骗人说,买不起,是看看解眼馋的。她儿子后来从劳教所出来了,几年不见的不良少年,长成一个高大而英俊的青年。女贩子积存多年的母爱终于迎来了它的主人,这幸运的儿子用母亲的钱开了一家烟杂店,经过一番专政和教育的洗礼,他对打架斗殴失去了兴趣,对挣钱和享受则有了强烈的追求,无论如何算是走上了一条较为安全的道路。因为外形出众,这儿子很快找到了女朋友,他不反对女朋友结婚的要求,而且非常诚实地告诉她,他母亲手里有五十万,都是他的。女贩子的儿子,一个幸运的儿子,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安排女贩子的五十万家产的:结婚用二十万够了吧,剩下三十万先存到我的长城卡上, 慢慢花呗。什么?她不给?她敢!不给我就捅死这老× 养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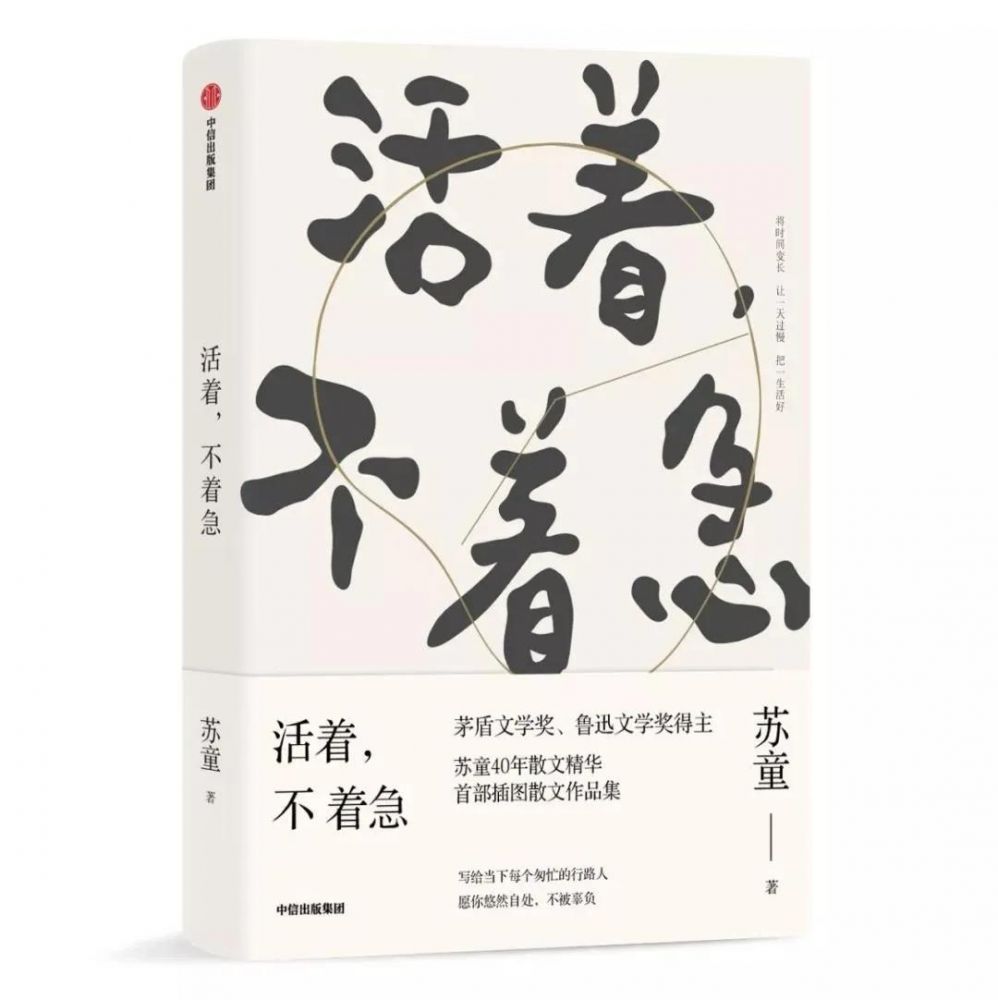
选自苏童散文集《活着,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