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黄永玉
一、我的念书过程:留了五次级
我是小学毕业,在我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非常野蛮的山里面长大的。在那里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当然在我的前辈里面有非常杰出的人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熊希龄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的街坊,这位先生后来就当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内阁总理。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
我们那里的小学校基本上是读古书为主,不是私塾, 是新学校里面古书读得比较多的一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省长叫何健,这个何健就提倡读经、读古文。所以小时候我们就受这种教育受得比较多,同时也受到蔡元培式的那种教育。
在那样的环境里新的老师教新的东西,旧学的老师就教我们旧学。那个时候有的人说学旧学不好,四五岁、五六岁孩子让他学古文,背得出来一点都不理解。 到了现在我才感觉到,不理解不要紧,利用小时候记忆力很强的时候把这个书记住了,我们到了二十岁,到了三十岁,再来反刍吧 ,慢慢地回味,得益匪浅。 所以有一个老先生,就是日本索尼厂的老板对我说过这个话,他说他现在写的几部书就谈儿童教育。 他是主张三岁让孩子学微积分,他说完全可以。 他说我们人用不着慢慢地等到十几、二十岁再来学这些高深学问。我就回顾了我自己那些过去的学习过程,我也感觉到小时候读点古文、学点诗词做法,那么到了二十岁、三十岁再来消化还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你没有机会背这些古书了。
(后来)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一个集美学校去念书。厦门集美学校那个学校30年代恐怕在全国来讲,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了。那个时候生活也比较苦,比较艰难,那个亲戚也帮不了很大的忙。仅仅是说不要学费呀,给点饭费,那个叔叔津贴我的饭费,没有钱买肥皂,买袜子也没有钱。所以一领到教科书以后我马上就卖掉了,把书卖掉了。上课就没书了,然后就到图书馆去。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我也看不懂。那么挑懂的看,慢慢、慢慢地也看懂了。
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呢,恰好是我的婶婶,我的远房的一个婶婶。那个婶婶很凶,看了我进去,尽借些不三不四的怪书,她简直太奇怪了,看我念书也念得不好,英文呀等于零,理化等于零,老是零分,老是零分。所以有时候就不借给我,意思是书没有读好,你看这么多书干什么?
在那个时候就在那里奋斗吧!经常去看书,有时图书馆关了门了,我就关在里面了,走不了,中午饭也吃不了啦。下午再开门我再出去,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所以在前两年我回到福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有的当研究院的院长,有的当大大夫,有的当将军,有的当这个那个,很多。到了厦门,他们有二百多人请我吃饭,有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人家都奇怪,你怎么这么多同学、这么多同班呢?人家同班有几十个才二十个,你怎么有二百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了。”

12岁时远离凤凰来到集美学校的黄永玉
一些女同学现在都是大大夫,大医院的院长什么的,很老实的。“哎呀!你还说得出来,这么难为情的事情不要说出来了。”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留级算什么。”基本上是在图书馆。读了不到两年又打架,把人家打坏了,打坏了嘛,我不能开除的,因为我是在战区。日本人把交通弄断了,我不能回去,而且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所以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说:“不要留了,我走了吧!”我就走了,后来到了个做瓷器很有名的师范学校,那个地方叫德化。读了两个月的师范学校,那是不要钱的,人家打架我帮忙。我知道坏了,所以我就躲到瓷器工厂,到瓷器工厂做小工。做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小工,在那里嘛,慢慢地变成一个名人了,因为我会画画,画老虎什么的啦。那个老板也很当回事,把那个盘子都装在橱窗里面让人家看。在那个地方俨然成家了,我还怀疑他可能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离开后到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要走很远的路到海边,在泉州。战地服务团没有要人家参加的,这个消息传错了,然后勉强又等一段时间,后来知道我还会画点画,会做点事情,也就不用考试就让我进去了。到了那里生活很好了,因为剧本上可以教育我们,在文学上可以培养我们。都是些大师们的剧本,曹禺、老舍这些人的剧本。
后来我们剧团要解散。在我们剧团到处演出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家人,这家人姓陈,陈先生是瞿秋白的学生,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呢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我在剧团的时候常常到他家里借书,他有很多很多书,从重庆、桂林、上海当年带回来的很多好书,到了剧团解散以后,这个陈先生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可爱的。“你不要到别处去吧!大伙都走了,你就住在我们家,我给你零用钱,你就看书,在我们家吃饭。”他自费办了一个剧团。他写剧本,写本地戏,叫莆仙戏,写现代戏。他养了个剧团,让那些演员们演他的戏。
“你呢,在这里帮我画画海报就可以了。”在他那里看书吃饭,一起玩。后来我到另外的地方教中学去了,到处教中学,到处投稿,反正就是这样。过年了就回到他家里,除夕一定赶到他家里,他家里有红的梅花开得很好的。要是哪一年没有回去的话,他就写信说:“花都开了,饭都等着你,以为晩上那顿饭一定赶得来,你看没有赶回来,你看花都开了。”我这一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不但是他对我好,而且培养了我的感情,拿这么大方的感情对待我,这一点对我一生来讲作用是很大的。也可以这么说,从十几岁到现在我都是在感情的灌溉底下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的,或者是到了今天的老年,都是在朋友的感情浸润之下生活下来的。
以后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剧团、在报馆、在教学这样一些单位工作。自已培养自己,一直到我从香港回到北京,那是1953年。1953年开始向中央美术学院拿工资拿到现在。我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二、我的学画过程:曾对弘一法师说“你的字写得不太好”
那么画是怎么画起来的呢?画先是刻木刻。曾经在泉州流浪的时候碰到过弘一法师,那时候我才十六岁,那以后的人就说我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教育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中间不到二十几天,见了他然后到他逝世。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世界上有个弘一法师,也不知道弘一法师。但是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写给丰子恺的信,有给丰子恺写的字什么的,夏丏尊呢,还有很多老先生。
我说:“你还认得他?”
他说:“那丰子恺是我的学生嘛。”
“你吹牛!”我说,“丰子恺是很伟大的,丰子恺怎么会是你的学生呢?”
我说:“你还会写字?”
“是呀!你看写得怎么样?”
“写得不太好。”
“为什么不好?”
“没有力量。”
过了几天,看他给这么多人写字,就说:“给我写一张吧!”
“你不是说写得不太好吗?”
我说:“现在看看有点好了。”

弘一法师《心经》
十六岁,那时才十六虚岁。后来他逝世了,逝世的时候我去看了他。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但是中间有很多的老先生对我很是有影响。 基本上美术界的少,文学界的多。 当时在上海二十岁,有位先生叫许天虹,不晓得各位知道不知道,翻译《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的。许天虹、唐弢、臧克家、楼适夷这些老先生,好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我很放肆嘛,二十几岁刚刚出头,生活这么困难。我刻了一张木刻,后来刻了两张,后来刻了三张拿去给他们,他们先给稿费然后给我推销,送给杂志、报纸去推销。先垫钱,知道这个孩子生活很苦的。后来碰到夏衍先生、徐悲鸿先生。我到美术学院的时候,徐悲鸿先看我的画,然后再见我的面,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哎呀!你怎么这么小!”那时候不到三十岁,二十八岁吧!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些老先生给予这种照顾关心,自己也有信心。大概有一个特点就是只会刻刻画画写点东西,刻刻木刻,什么事都没干过,而且穷得挺硬朗。
那么以后在美术学院工作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直到现在了。五十三年,1953年到现在。那么在座的有几位我的老学生呢,到西安也碰到一大堆老学生,真是显得老了,头发都白了,脸上皱纹比我还多,这么老了,当年呢,也是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书教的时间很短,间隙过程中间有一点高兴,有一点痛快,大部分时间很痛苦的。先生同学生之间隔了一层很厚的墙。
有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出来的时候就在什么宾馆吧,挺远的,什么宾馆不知道。侯宝林没有车他就搭我的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个车子回去,十几年前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最近还上课吗?”我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侯宝林一声不响,等到多少秒钟吧,车子不停地开吧,他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这就是生活,是吧!不要泄气,人嘛,总是这样的。但是毕竟我们等到今天的日子了,不容易。
三、谈谈艺术的问题: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有人问毕加索说:“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你懂吗?”
这个说明什么呢?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说我就是打野食吧!见到什么捡到什么就吃的那种人,不是像经过严格训练、很好的老师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也不大容易害病,吃什么都不会害病,也不会胃痛。因为没有教育嘛,所以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说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是这样。

黄永玉,《猫头鹰》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呢,讲这个东西,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了这话,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比如说原来有个好的东西,只所谓创新就是不要过去那个东西,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创新。那就包括摧毁那个旧东西了。我们那个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画国画、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相当好了,它不是普通的好了。但是到了前言呢,在美术馆前言上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过了几天这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
“你们这帮乡下人嘛,你画画得好可以画得更好,再画得更好嘛!你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又同你不认识,那个东西你摧毁它干什么,你又摧不毁。 你画你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还要摧毁别人的任务,你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自已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了。”
开玩笑,他们也笑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一辈子写小说的人写得好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的嘛,一辈子从事小说创作写得好有什么奇怪的,写不好就奇怪了。你一辈子写小说,写得不好就太奇怪了!”
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画家找我谈这个问题,想弄名、弄钱弄这些东西,北京、中国也是这样:想出名,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拼命地弄钱。我说你拼命弄钱的时候,拼命往上爬的时候,就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也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嘛,怎么能画好呢?还有你想弄钱了,为了钱画画你钱也弄不多, 你认真去画画,不想这些事情。你这么长年累月下去,钱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真是这样。 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不见效的这句话,你长期考虑考虑你就知道这是真话了。

黄永玉,《大吉图》
画画嘛,总有一个问题嘛,一个是自己快乐,画得得意,自己快乐,周围的朋友高兴。太高兴了,还有点钱。为了钱而钱,挣不到钱,那个因为你画得不好嘛,所以这个事情同别的事情一样。有的人说我今天不画这种写实的明天画抽象画了。抽象画画得这么容易,说画就画的?哪里这么简单呢?也要学,也得从头学起,必须从头学起,应非常严格、非常认真地学习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想到这个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了?我以前就讲过个例子,我说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我们某一个人从国外通过一种渠道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有啥意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说:“唉!你学它的,再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好讲的了。”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的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干的事情的。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这个蒸汽动力各个方面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公路的弧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画信服了,相信了,真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生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信服了,就不像开始的时候嘛!但是长期的闭塞、关在鸽子笼里头的生活,他们要求解放,他们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出现幻想,出现一些东西。不能满足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一下子、一下子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的出现,都是因为前面的原因才有了眼前的结果。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所以创新呢,某个时代的人有提供一点点表现上的功能就了不得了,很了不得。还有,一个人呢,永远只是代表一个人,没有“老子天下第一”的了,不可能的。尤其是硬求别人自己上来更不可能了。我也说过,艺术活动同别的一样,像踢足球一样,我们一辈子画几张好画,一辈子踢进几个好球、漂亮球。在什么地方进了几个球,像贝利一样进了一千个球根本是不容易了。踢球好了不要踢人,你朝着人家腿去踢,那就伤了人了。一个人进球别人就受伤也是犯规的。艺术活动往往像文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大家合起来使这个时代灿烂,而不是一个人灿烂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独钓寒江雪”,那个时代过去了,一本小说,几首诗,几本书大家不停地学,不停地学,倒过来都会背了,有什么用呢,整个时代的灿烂,汉唐这么一个灿烂。

黄永玉
艺术呢,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看法了,就是主题这个东西。那个历史画,或者有一定的情节的画,那么你没有主题不去认真研究它,你怎么画出来?当然需要对主题进行研究,对人物的刻画,认真去分析、去收集材料。我讲一般的画,讲我自己画画。包括看书,包括接触文化, 我都是从感觉出发,我不是从主题出发。
在画画里面我就讲首先是那个感觉。我有次在美术学院听报告,天气很热,里头坐满了人,我就在门口坐在那个台阶旁边的一个石凳子上。里面讲什么我也不注意听,反正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回家就是了。我眼睛看着那个门,那个门是用绿漆漆的,绿漆漆的那个斑斑驳驳的颜色,已经不是绿了,绿灰,里面还有很多层次。我起来就回家了。回家我画了一张荷花,拿感觉画了一张荷花。 谁是主题你说,荷花是主题吗?是那点感觉是主题,我借那个荷花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黄永玉,《荷花》
现在为什么在社会上常常感觉到画的画一样呢?你用什么方式来画,细的也好,粗的也好,什么也好,属于现代派也好,或者古典派也好,怎么一个样?就是给那个题目卡住了。比如我现在画这个花,花是主题,这个可把我们害了。大家都用学校课堂作业的方法把它画出来,个个一样。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今天处理的时候仅仅看它形体是它的主题,明天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花我们画它的质感,另外一个主题是画它的调子,用这种方式或者画它的纵深关系,画它的动感、画它的虚实,拿这个做主题,就千变万化。或者说我只用一种颜色黑白颜色画各种色彩。
我对摄影家讲过,你把彩色片拍得有单色效果,黑白片拍成彩色片效果。我说你不要让那个主题限制了你。画风景也是这样,一坐下来对着风景开始画,忙这个那个,然后笔法、色彩就上去了,一下子全出来了。你想一想嘛,我准备怎么处理它,我这一仗怎么打法。纵深关系是运动还是对比,还是怎么怎么样。哪怕是下着雨,那个街上雨水、潮湿是主题,不是那个街是主题。那么你原来的本领就能使出来了。永远不能停在课堂作业上,至于主题画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嘛。历史画,你除了把这个事情原始材料表达出来外,你可以赋予它艺术上的处理嘛。这样你的作品就灿烂了,就多种多样了。尤其是你能表现你的修养,你有多少修养你都能够使出来。
像傅抱石的画就把抽象同具体协调得非常合适。傅抱石画一张画,先画大山水,恐怕现在没有的,我是在解放前看见的。一丈多高的大中堂,呼噜哗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是。它里头夹了这么小的一棵大树,夹在某一个地方。把泉水稍微引一引,大树底下有一个更小的房子,还有特别小的两个人,再回头看看乱七八糟的是山水是雾什么什么的。把抽象和具体协调得合适,层次关系协调好,这是傅抱石的功劳。就这么一点功劳就推进他了,有了这么一点功劳,这是我认为的。很微妙的关系,他在宣纸上把它表达出来,过去没这样的。
我在米兰一个美术学院看到一张达•芬奇的画,就这么一张头像,我有机会这么近地去看他,我可真佩服他了。他把那个女孩子的皮肤的透明感,扎一针就流血的那种感觉画出来了。眼圈下睫毛从上眼帘到眼珠,眼薄膜上再下来到下眼帘有个影子,你仔细看看,感觉那个影子一般看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那个影子都出来了。周围这么大一张东西,你能画得这么精确这么妙。除了你画细以外,更多有更深的悟性,去理解它,体会到它你才能画得出来。体会到了还不算,还有这个手艺画出来。所以,这个画家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得到自信,都可以得到勇气。
四、讲讲读书:我读书是故意不认真的
讲读书是讲画家的读书,这个画家的读书是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画家的读书。我就是一个代表了,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爱看一些杂书的人。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用功,画画倒不是很用功了,画画嘛,顶多说勤劳就是了,使尽力气就是了。真的用功是读书。不是用功,是有兴趣,有极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看书。大概我这人没有堕落的话可能因为读书,因为那个旧社会是这么复杂,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几十斤书放在包包里逃,日本人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马上就要追到了,一本本地也不敢看,把那个书往后扔,一本一本地扔,还是背着书跑。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看。

黄永玉 ,《读书破万卷》
但是看书呢,如果不是念书的人,读书有一个特点,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太深的研究,就像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不要太求甚解,太求甚解,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并不是研究一种东西。看书是一种快乐,然后才是知识,才是本钱。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很多书,看得很快。看完就算了,记住书里面有哪些很精彩的感觉在里头,记住它。书当然不借给人家,借给人家就找不到了。把它放到那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了,把那个书从那个地方找出来就是了。
画画人的知识不是专门知识,他要面铺得很广的知识。有的事情你需要认真地去学习一下,比如说植物学、动物学。有的牵扯到规律问题,岩石学、地质学你要研究一下,因为画石头、画动物、画花呀,要认真学。有的东西你看过就算了。历史什么的看看就是了,历史年代、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有趣的人物、几个大战争、大政治变化记住。其他专门记那些有趣的事情、生动的事情,把面尽量铺广。然后就养成习惯了,发生兴趣了。那就不得开交了,研究之后从那里头得到很多快乐,画画有时候就能用上它。比如说在处理人物上、画面上那个情致、格调,你就可以多方面的就不至于那么单一了,这个明显看出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了,是书教出来的。这个尤其对我们没有机会进正式学校的朋友来讲的,我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了。其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我们如果能够有幸碰到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同他谈一次话就感到非常地快乐。书本本都是聪明的,读一本就碰到一个聪明的,读一万本碰到一万个聪明人,你说你多合算。
有时候我说,旧诗我会作的,平仄、押韵我都会。就是读的书太少,有系统地读的书太少,用不上,作诗也没有什么典,没有意思了,用同样的典也没有意思了。每次兴趣一来,旧诗作完了还挺费心的。作完了一看看不好,还不如作白话诗好呢,所以白话诗写一点东西,杂文呢,这个比较好。看别人的旧诗也是一样的。口味也很刁的,自己作起来就不很容易,也感觉到旧诗要作得好也不容易。我看看包括那些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们,哎呀!缺乏人味都是书,看起来挺难懂的,光见学问不见人性。

黄永玉
所以,我自己读书我是故意不认真的,读得快乐就行了,不一定记住很多很多的事。有可能人家说大脑贮藏有限,容量有限了。我很善于摆脱的。从生理学上讲,大脑皮层有一种抑制功能,产生抵消规律。什么可以得到,比如我们学习过,我们天天学的理论,其实早都知道了,在小组会上大家都互相监督,不能不学。那个地方同样的个问题,事情也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学但也不急躁,那就是有一种抵消的规律。看的东西看得太多,同样的东西重复得太多了,它自己会给你抵消掉,它有选择性的,但可以不必去理它了。好像装着在认真地学,学着在抵消,这种例子你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见的。啰嗦的人同你讲话老是不停地讲也不放你走,听吧,脑子就等于没有听,一样的。所以创作一种在画上看的见解,一种别人没有说过最好是这样的见解,没有说过的见解。不是画法上有什么创新,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有的在画法上有创新,搞那些东西,兜了一大圈,结果还得回来,还得老老实实地去画画。大概在见解或者什么地方有种发现,人家看见就高兴了,感觉到能够欣赏。
本文摘自

《黄永玉全集·文学篇·自述》
====================================================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96岁黄永玉送别爱妻张梅溪
黄永玉先生的太太张梅溪先生去世了,享年98岁。黄先生为妻子写了讣告,这个时代,能够得夫如此送妻最后一程,令人感佩。讣告文字是沉郁的,带着克制的哀伤,真心希望黄先生节哀,《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我们还期盼着继续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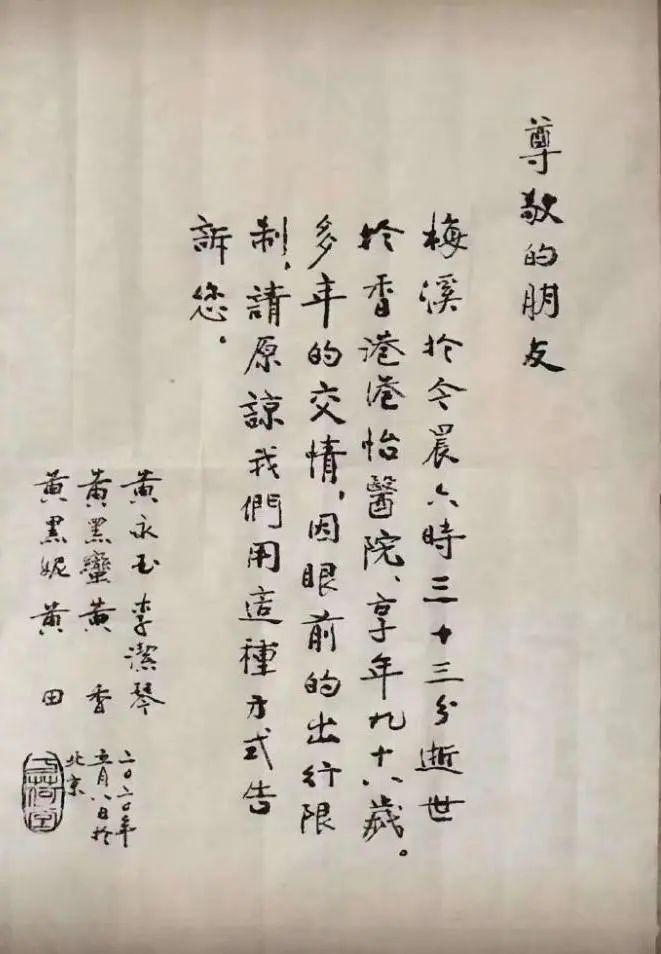
“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黄永玉曾为张梅溪写下这么一句津津乐道的情诗。
张梅溪,1927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942年到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工作,认识黄永玉并和他结婚,从此“只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今天湘声君带您重温这段爱情佳话。
湘西流浪小伙打动将军之女
1942 年,19 岁的黄永玉到了江西信丰。他去那里的目的本来是躲避战乱,没想到却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恋爱。
初相识,张梅溪是将军之女,相貌出众、气质不凡,从小在家庭熏陶下,她受到良好教育,酷爱文学艺术,而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当时许多人都在追求张梅溪,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赢得芳心,黄永玉选择定点吹奏小号,向她展开了攻势。终于两人成为了情侣。

后来看张朗朗的《大雅宝旧事》,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
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中国人,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肩膀上似乎只挂着两根带子,裙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五十年代的北京就没见有人这么穿过,甚至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 她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沙贝他们家的王大娘后来说,这黄太太哪儿哪儿都漂亮,就是她这胳膊、腿儿也忒细了。她哪儿知道人家香港人,觉着越瘦越美。香港人那会儿也不知道,老北京的一美是“胖丫头”。
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张梅溪父亲的反对,家人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为此,张梅溪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与黄永玉在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婚礼。
多年后,黄永玉说起追求起张梅溪的事,仍掩饰不住一脸的得意。

张梅溪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便是嫁给黄永玉:
我没到二十岁,在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做艺术工作的时候,当年的女朋友,我这个人没什么女朋友,只有这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黄永玉
十八岁的梅溪出身军官家庭,追求者不少,为什么选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穷小子?她显然无法预知将来,用世俗的眼光看,当时的黄永玉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张小姐的追求者中,最为显眼的是一位真·白马王子,这位青年长得帅,知道张小姐喜欢马,便牵着马带张小姐去郊游。黄永玉叫苦不迭,别说白马,自己连自行车一个轮子都没有。这让我想起当年吕恩老师讲的一则逸闻,赵丹追求秦怡的时候,见秦怡家门口停着豪车,便知是来接她的公子哥儿,于是带着哭腔对吕恩说:“看呀,有车来接她了呀!”
他们的第一面都是有些哭笑不得的,平时大大咧咧的黄永玉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话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这种表白有点类似现在的“你愿意埋在我家祖坟吗?”)
吕恩说,你在这里着急,为什么不用实际行动打动她?你不努力,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这句话便是黄永玉的最佳注脚。黄永玉的招数,是赵丹在《天涯歌女》里用过的——他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每天等张梅溪来上班,远远的就开始吹小号,“冀得自我士气之鼓舞”。
我有一把法国号,老远看到她我便吹号,像是欢迎她似的,看见她慢慢走来,她也老远便看见我,知道我在这里——黄永玉,CCTV访问
小号水平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显然,吹号的少年打动了少女的心扉。那时候的爱情,像是旧时摊子上做出来的棉花糖,一丝丝卷出来,轻盈如一朵云,初看不出甜,须得入口,才觉出蜜一般,立刻化了,入你的心里。一日,黄永玉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去见梅溪,梅溪说,去理发吧。黄永玉一摸口袋,只有八毛钱,要么去理发,可是自己还想要买一块木刻板。
为难踟躇之间,少女笑盈盈地说,两样都做吧,你去理发,我送你木刻板。
理完发出来,梅溪捧着木刻板等着黄永玉,很多年之后,黄永玉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觉得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很勤劳,我有时不想他搞这么多——张梅溪,CCTV访问
消息传到梅溪家人那里,家人联合反对,不允许她和黄永玉见面,他们甚至用了恐吓,告诉梅溪如果接受了黄永玉的爱,未来的日子便是“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
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一个人去了赣西。不久,他接到了电话,是梅溪打来的——她从家里跑出来,卖了金链子,坐了拉货的黄运车,来赣州找他。
少年多么惊喜啊,当晚就借了朋友的自行车骑行60公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少年的心里满是爱意。离赣州还剩10公里路时,天太黑没办法骑车,他找了个鸡毛店住下来,夜里没有被子,就把散落的鸡毛盖在身上。
一身鸡毛见到梅溪的时候,两个人笑了,哈哈哈哈。
笑着笑着,又哭了。
“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
“那要看是谁了。”
“那个人是我呢?”
“好。”
这是他的表白,这是她的回答。
他是她的初恋,她也是。
黄永玉曾在《音乐外行札记》中记录了他的爱情经历:“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50年前,一把小号打动芳心,见证爱情;50年后,重新买小号吹给同一个女朋友听。岁月悄然过,哪怕齿落发白,只想博你一笑。
“洪荒时代互相寻找的星星”
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他在上海闯荡,她便在香港教书。
他跟着张正宇到台湾,结果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差点被抓起来枪毙,跑到香港,她辞去在湾仔德明中学教书的工作,跟他一起住在偏僻的九华径。他们住在楼适夷一板之隔,他刻木刻画速写,她写点散文投稿,这样的日子,是想得到的清苦。
那时我们很贫穷,我们的家很小很小,但有一个窗,窗外面很多木瓜树,也可看到一口水井,当时他买了一幅窗帘回来,买了一幅很漂亮的窗帘回来,拍了一张很美丽的照片,他说,这是我们破落美丽的天堂——张梅溪

他接到表叔沈从文的信,决定从香港回北京,她默默收拾行李。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北京,他成为中央美院最年轻的教授。一搬进大雅宝胡同,黄永玉和张梅溪就给全院的孩子们表演了手风琴合唱:
黄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规矩派头儿,全然不同,全不沾边 ——《大雅宝旧事》
这段日子里,黄永玉在张梅溪的悉心照料下,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

黄永玉与张梅溪的爱情滋养了一个文艺之家。黄永玉以及儿子黄黑蛮、女儿黄黑妮都爱作画,张梅溪喜欢著书。
黄黑妮曾在张梅溪的著书《林中小屋》的序言中提到了黄永玉和张梅溪共同度过的那段“特别时期”。
她写道,“我的妈妈张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对人热情仗义。……大半个世纪以来,她洗衣做饭,骑着自行车招呼好几家亲友。特别是非常时期,她一直坚信爸爸是好人。没有她,爸爸也绝不会到这个份儿上。”

张梅溪是这本书的作者。

黄永玉与万曼两家人在葡萄藤下合影
梅溪的厨艺特别棒,“二流堂堂主”唐瑜曾经选出来“京城四大女名厨”,张梅溪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张光宇夫人汤素贞、戴浩夫人苏曼意和胡考夫人张敏玉)。
《二流堂纪事》里说,“二流堂分子”忽然灵光一现打算开饭馆,大家提议请张梅溪主厨,黄宗江“搜集了一堆餐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鲜;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说得如此热闹,饭店终于还是没开成,夏衍说:“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李小可,文化家园

在大雅宝宿舍孩子们的心目中,“黄妈妈”不仅做饭好吃,对孩子们有一种难得的尊重。张仃的儿子张大伟不爱说话,成天自己搬个小板凳在黄永玉家窗下听梅溪放唱片。
黄妈妈看见后大为吃惊,问:你听得懂吗?
他平静地只说了两个字:好听。
她连忙说:进来听吧。
——《大雅宝旧事》
听唱片,写童话,带大一双儿女,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她以为这就是永恒。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很快山雨欲来风满楼。


先是“四清”,黄永玉写了《罐斋杂技》,里面有一句“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这很快被批判为讽刺“大跃进”。
而后便是“猫头鹰”事件。当时黄永玉和吴冠中等去重庆写生,听见人说“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魔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当时还不知道,那个“有个人”,就是他。
在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比画画更重要。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家半夜三更还要画。孩子们睡了,梅溪拉上窗帘,在窗边守着,帮他放风。一有风吹草动,她便立刻帮他把东西收起来,停止画画。
作家聂绀弩写过一首诗,名字叫《永玉家》,描述黄永玉、张梅溪一家人在那段特殊到无法写出名称的时间中的生活:
夫作插画妻著书,
父刻木刻子构图。
四岁女儿闲不住,
画个黑猫妙矣呼。
此是凤凰黄永玉,
一家四口斗室居。
……
君家不乐谁家乐,
一体浑然盘走珠。
这首诗写于1961年,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黄永玉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屋里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焦急的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2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

因为画黑画被关“牛棚”,全家人被赶到一间斗室,是真的斗室,连窗子也没有。她不讲话,他知道她内心的煎熬,于是在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开满鲜花。
44岁生日,黄永玉被两个人拿皮带抽:“他们说只要我求饶,就不再打下去,我心里说‘喊一声疼,讨一声饶,老子就是狗娘养’!”两个人打到没有力气,黄永玉起身:“一共是224下。”
回到家,她见他血肉模糊,白衬衫已经脱不下来,粘稠的血肉粘在一起。她终于忍不住,哭起来:
她说,就算当初我叫你别回来,你也不肯的。
——黄永玉,《杨澜访谈录》
黄永玉去农场改造,一去三年,他知道她内心焦虑,于是写了一首情诗,这便是著名的“老婆呀!不要哭”:


真喜欢这首诗,充满了质朴的宽慰,蕴藏着的是一对夫妇患难中的慰藉:
一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
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
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
我吻你
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
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
吻你的永远的美丽
因为你
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黄永玉《老婆呀,不要哭》

究竟是什么使得黄永玉能够如此乐观?他给出了答案,是信念,是智慧。他最常对梅溪的一句话便是:“要相信这些迟早都会过去的。”是的,迟早都会过去的。
沧桑岁月,一转眼,吹小号的少年牵手买刻板的少女,已经大半个世纪过去了:
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雅人乐话》黄永玉
70年代末,黄永玉以60高龄破格考了驾照,考试时,考官问他:“某某零件坏了怎么办。”“坏了就换一个。”他在日本买了跑车,说要载老婆出去兜风。
梅溪喜欢养动物,他跑到通州建了个大房子,屋子大,养老婆的动物也方便,光是狗就养了十几条,最大的一只200多斤。除了名犬,还养过马,养过鹿,养过熊。梅溪想养什么就养什么。
《见字如面》里读了那首他写给曹禺的信,他说,自己写的最好的诗还是情诗,光歌颂老婆的诗就能出一本《黄永玉夸老婆集》。

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话打动人心:“心在树上,你摘便是。”
聪明人到了最后,便是这样坦荡,所以他才开得起这样的玩笑:
我的感情生活非常糟糕,我最后一次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参观自由女神像。


画画写个诗,也要@张梅溪:
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
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这是赤裸裸的秀恩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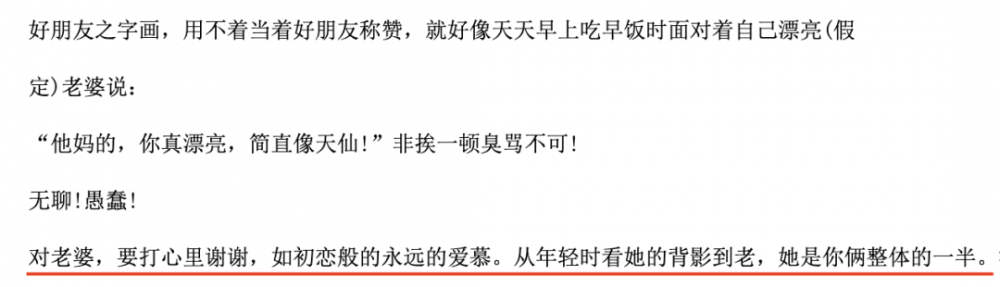
难怪那时候黄霑失恋,黄永玉安慰他“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一听,火冒三丈:“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
其实更有利的反击是,黄永玉,你一辈子只谈了一次恋爱,懂得毛线失恋!

2020年5月8日,98岁的张梅溪走了。“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表叔沈从文的这句话,用在张梅溪和黄永玉身上,再恰当不过。
她这一生,经历过坎坷,遭遇过挫折,可是回首往事,岁月凝结的,多半仍旧是甜蜜。这源自她最初的那个选择,无关金钱,无关权势,当年家人恐吓梅溪,要是嫁给黄永玉,未来便要“在街上讨饭”,但她仍旧做出了那个选择,那需要多么大的智慧,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所以她值得。

 黄永玉《老婆呀,不要哭》
黄永玉《老婆呀,不要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