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筛历史的细节
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傅立民英文名是Chas W. Freeman,Jr.,他生于1943年,是个神童级的人物,1960年17岁拿全奖上耶鲁,1963年就毕业了。1965年投身美国外交界,去过印度台湾,学了好几种语言,包括中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他是首席翻译。下面的内容,来自美国的外交事务口头历史项目(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中傅立民的采访,文中的“我”为傅自称。虽然只是摘录,还是比较长,第一部分讲傅立民学习中文的过程(都说美国人爱玩比较懒,看看神童小傅同学是如何拼命学习的),里面有对台湾大陆社会的观察,可以参考,多了解些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据说知己知彼是中国人的传统吗。第二部分介绍他参与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大陆的前前后后,当然,周恩来是一个重要部分,可以看看傅立民这样的神童极人物,对周恩来是怎么评价的,这绝不可能仅仅是对周恩来夸他年轻有为的投桃报李。本博结构比较乱,可以说除了懒以为,还有一个故意的因素在里面,不知道本博的内容会不会敏感。总之,我不博点击率(这也是我博客总的意图),先警告一下,您如果不喜欢可以现在离开。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乱,也是因为我是捡原文中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比较有信息量的,可供做对比,参照,等等的内容,所以有跳跃,段与段之间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或者时间,文法上的起承转合的线路。
想到一件事,可以说又是一个中国的坊间传言(city legend),说周尼会谈时,美方用了一个词Parallel,中方翻译翻成“两国平行性”,突然一位美方年轻翻译说:“总理,我能不能插一句?”周同意,美翻译说,我觉得Parallel这里翻译成“殊途同归”更贴切,周总理很赞赏。。。。不知是不是就是傅立民?另外周总理对美方团队的年轻化很羡慕,认为中国应该学习。。。
1971/72年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破冰,这是个改变世界的举动,应该认真地写写她的历史,资料也不少,美方有基辛格的详细记录,当然会对他自己有过誉之嫌,但是仍然是美方最高层参考资料的首选,而几位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学者用英文记录了中方近年公开半公开的内部资料(比如陈建(?Chen Jian)),这就象是符节的两半一样,虽不能严丝合缝,但是大模样出来了,同样有价值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恰恰是傅立民这样的参与者的细节描写,可以给大的框架贴上活生生的眉毛鼻子眼。。。
还有就是请勿转载!本来一直想翻译这篇,但是他们这个项目也有请勿转载的告示,后来看到已经有学术性的书中大量引用他们的资料(包括傅立民的,见唐耐心(Nancy Bernkropf Tucker)),所以我也不揣冒昧,发个摘译,但是,请勿转载!这也可以说是为什么本博比较乱的原因之三(还是四?)吧。不废话,下面是正文。
。。。。我离开了印度,集中精力学习中文,并继续关于中国和其它有关中国的阅读--苏联,当然还有印度,以及东南亚,同时拼命想挤进中文语言课程,他们不太想让我进入,因为我会说不少其它语言,可能外交系统(Foreign Service)考虑究竟为什么要再把培训费用花在我身上。不管怎么样,最后1969年新年后,我终于进入了中文课程。
在这之前,我被派到当时的东亚事务局(Bureau of East Asian Affairs)下的地区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Regional Affairs)工作,那个部门的Louise McNutt和Ruth Bacon这些人,在把共产党中国排除于联合国大会之外方面,作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我也成了这项工作的一分子,把他们拒于联大门外,这涉及各种花招(shenanigans),包括让美国海军去迎接马尔代夫代表团,然后再用飞机把他们送到纽约,赶上就阿尔巴尼亚议案投票。我们在这项不那么神圣的事业上占了上风,我也学了很多关于联大的知识。参加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我并不特别赞同它的旨意(Thesis),但是我发觉从技术角度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习过程。
1969年新年后第二天我就去中文课报到,另外有两个其他同学,都有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的研究生学位。但是管事的语言学家George Beasley(后来也加入了外交系统,在东亚地区主任位上干得非常出色)对他们进行了测试,发现他们的语法和发音非常糟糕,决定让他们从头开始,这对他们来说很丢人。我则感到对我来说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害怕我会拖他们后腿,在某种程度上毁了他们这次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下决心好好干,追上他们。我学的非常刻苦,结果是,大概三个月内我超过了他们,六个月内,我在中文上考了two-plus two plus(不清楚是什么个分数体系,应该是非常高的分数),这个分数据我所知是没有先例的(unprecedented)。所以,他们没让我在华府的外交学院(FSI)读下去,而是把我送到台中的语言学校去了。我是1969年8月到台中的,继续玩命学习。我说服了老师们让我每天上九个半小时的课,一般是从6:30开始。几个月后,我得了three-three(同前),这是两年课程的目标。我一心读书学习,最后在国语(Mandarin)上拿了个 four plus-four plus(同前,不清楚评分系统)。
这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我决定学习闽南话(Taiwanese),它跟国语的区别,就象荷兰语跟英语的区别一样。我的最后成绩是S three plus。进入1970年后,国务院寻找一位替代Don Anderson的翻译,1970年3月我接到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华沙作翻译,当时跟中国共产党的会谈在那举行(是中美大使级谈判,应该是最后几期了,最高层已经在互相试探接触了)。我到了美国驻台北使馆,读了有关中美会谈的记录资料,当然还有Kenneth Young的书(Young是亲历者,写了一本书《与中国共产党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1953-1967--,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华沙会谈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过程,以后有机会上博文)和其它的相关资料。
我可以说我在台中干的一件事就是把图书馆的书读完了(是不是想起了清华钱锺书?),结果我为学生们写了一本图书馆的书目注解(annotated bibliography),所以,即使我每天要早起为6:30的课写一篇千字论文,我还是在阅读。但是我减少了学习闽南话的时间,集中学习国语的使用,阅读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和人民日报这些东西,都是我没兴趣的内容。在台中的学生群体,我是唯一,(没有之一的唯一),不想去中国大陆的人,我想去台北。我心想,共产党大陆可以以后去,台湾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学习闽南话可以使我成为政治方面有价值的参与者。但是我还是同意接受这份翻译的工作。就在我一切就绪,准备去华沙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决定进攻柬埔寨,中国人取消了会谈以示抗议。本来会谈定于1970年5月20日举行。后来我就留在台中,接着捡起了闽南话学习,还开始学起了客家话,最后,1971年早期,我被调离。
我妻子来自新泽西,也学习中文,我们放弃了英语,在家只说中文,我的三个孩子都懂中文。我最小的孩子,到台湾时还是婴儿,离开的时候不懂英文,只会中文。我为孩子们看书说话把《指环王三部曲》翻译(sight translate,应该是一边看英文原版,一边用中文读,录下来)成中文,我可能是唯一(又是没有之一?)这么干的人。
有一次,我去了大使馆,有很多当地的高级领导们,都是1949年从大陆过去的说国语的,跟我们的官员说英语,然后他们互相说国语,很蔑视地评论我们的官员,而一些台湾本省人,则用闽南话,同样蔑视地评论说国语的外省台湾人,还有两个客家人,蔑视地评论台湾本省人。。。。。
.....
对我来说,当时最悲催的是,我对国语懂的多了以后(并且在1972年当我作为尼克松总统首席翻译去大陆的时候被严重确认),我发现,大使馆,美国,乃至台湾人都不理解台湾发生了什么,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初级阶段。中国的这块地方,正在形成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随后发生在台湾的好事的所有种子,就是使得她成为长长的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繁荣和管理的最好,以及在很多方面也是最受赞赏的中国社会的所有种子,都是那个时期生根发芽的。但是国民党意识形态强调,国民党才是坚持中国传统,并且代表了中国的过去。而共产党是破坏这个传统的。实际上,国民党无意中在台湾干的,恰恰是相当彻底地打破了中国的过去,而共产党,虽然努力要改变在大陆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是巩固了过去。家族系统,传统的大家庭,传统的作事方式,重官轻商,低看科技,好男不当兵,这些中国特色都在大陆得到加强,而在台湾则被现代化击碎了。那个时期,台湾在试验某种形式的地方选举,以及今天台湾享受的民主体制的过程。
我跟台湾(驻美)使馆的不少人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我尽力对他们坦率地表达我所理解的美国战略思维的演化,同时不泄露机密也不提供任何细节。我也同样对待日本人,我记得后来成为日本外交界很伟大的人物佐藤由纪夫(Sato Yukio)在基辛格访华后跟我说:如果我对你以前讲的话听得更仔细的话,这件事就不会那么令我震惊了。
国务卿罗杰斯,他不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句政治正确的真实意思是:他很笨),很喜欢打高尔夫。我生命中一个奇特的时刻就是给罗杰斯和姬鹏飞之间的谈话作翻译。姬当过兽医,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外界的消息,当然他不知道Sam Snead是谁(应该是高尔夫的大咖吧),罗杰斯是Sam Snead的粉丝,所以罗杰斯滔滔不绝地谈Sam Snead,而姬鹏飞听了不知所云。作为翻译,我无能为力,只能是他们说什么,我翻译什么。
P45,来自Administrative Bureau(可能相当于我们的中央办公厅管理局) 的John Thomas 必须得专门去处理其他人留下的灾难性后果,主要是由白宫打前站的Ron Walker造成的,Walker喜欢支使别人,干这个干那个,他在北京告诉韩叙(当时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必须得这样这样来安排美国方面的新闻媒体人,他跟韩叙说:"I don't give a rat's ass what you say, we're going to do it this way. We always do it this way."韩叙反问:“What's a rat's ass?”慢慢地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以后,韩叙非常愤怒,感觉被侮辱了,就不再跟Walker说话了,这一下就僵住了。所以John Thomas被派到北京去解决问题。
P46尼克松想看些有关中国的书,我借了一些给他(傅读过两千本关于中国的书,全部读完),但他从来没还我,我还专门给他写过信请他还我,我肯定他读过这些书,就是没还给我。那段为尼克松访问准备期间,我每天工作20,21个小时,吃的也很少,体重减轻很多。
我观察的尼克松其人,是个完全不会跟人闲谈,缺乏个人风度,也不懂在与人交往时所需保持的距离。
P47我们出发后第一站是夏威夷,在那我给罗杰斯作背景介绍,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不一会就没兴趣了,径直就去打高尔夫球了。然后我们又去了关岛,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问了很多人,仍然不得要领。
我们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我坐的是备用飞机,比尼克松的空军一号要早到达,所以我们是在上海很糟糕的小机场看着尼克松抵达。我之前给尼克松夫人写过些建议,比如不要穿红衣,因为在中国,红色要么是婚礼上穿,要么是妓女穿。但是她下机时穿的恰恰是大红外套。这就是所谓的建议的用处(确实是建议的用处,作为过来人,我知道,那个年代的大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了,妓女消失了20多年,还要再等10年才渐渐卷席重来,结婚则穿的越土越革命,况且,那时大陆中国人看老外就象看外星人,谁会在乎外星人怎么穿衣服呢?),不过红色到是挺上相的。后来我们到了北京,我还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基辛格虽然有很多很多优点,但是他不是个管理者,他不管细节,管理细节的是白宫的人,而他们主要是关注总统,所以其他人没人管了。
P48我们在北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我们有三个翻译,我是高级翻译,还有Cal Maehlert,中文非常好,他是从西贡抽出来参加尼克松访华的,另一个叫Paul Kovenach,他是由某个什么人招募来的。我们这一组人很奇特,Cal是极端亲台湾的,他是蒋经国的好朋友,访问归来后,他立即去了台湾,跟蒋经国一起去打猎,很可能把所有情况都告诉蒋经国了。他的所有相关资料(briefing book)都不见了,至少他说不出来那些资料到哪去了。Paul Kobenach则支持台湾独立。
到了钓鱼台,我们被叫到尼克松的别墅去,说到那就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到了,尼克松出来跟我们握手,说很高兴见到我们,然后就又进去了,还是什么也没说。当晚有个宴会,但是尼克松突然被告知要去见毛泽东,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都没去。2月21日晚八点过了一点,晚宴被推到九点半,我突然又被叫到总统的别墅去,那里有一些人,中国的翻译也在,冀朝柱,唐闻生,还有一些礼宾方面的人员。总统的日程安排秘书Dwight Chapin出来跟我说:你翻译今晚的祝酒词。我说,行啊。请把稿子给我看看,我好进行准备。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没有讲稿吧。
P49我说:我知道有讲稿,肯定有。中文可不是法语或西班牙语,要想翻得好,你得仔细考虑怎么翻。我肯定有讲稿,如果你能帮我弄到它,我非常感谢。他走进总统的办公室,出来说:没有讲稿,总统让你来翻译。我说:我敢肯定有讲稿,我真的需要拿到讲稿,我这人过目不忘,我只需要看一遍。Chapin又进去了,出来说:没有讲稿,总统命令你翻译。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今晚祝酒词的第一稿是我写的,有几句毛泽东的诗词插在其中,如果你以为我能在整个中国政治局成员面前临时把毛泽东的诗词翻回到中文去,那你就疯了。他说:好吧。然后就把讲稿从口袋里拿出来了,把讲稿给了中国人。最后是冀朝柱翻译的,他事前跟我讨论了一些翻译上的不少问题,里面确实有毛泽东诗词,如果由我来翻,结果会很糟糕。
宴会上,我坐在主桌上,尼克松周恩来,姬鹏飞,李先念,记得还有乔冠华,乔是外交部的主心骨,另外还有罗杰斯,当然尼克松夫人也在。我看到总统从桌子对面向我瞪眼,显然对我很生气。我仔细琢磨了为什么尼克松不愿意让我知道有一份讲稿,原因之一是,他喜欢脱稿讲话,想表现出是临场发挥的讲话,如果我站在那拿着稿子(当然我不会拿稿子的),那就露馅了;另外他还有个习惯就是用对方的翻译,这样就不会泄密给美国媒体和国会了。
P50,两天后,尼克松向我道歉。他把我叫过去,跟我说:“对不起,是我不好。那样做是错的,我不应该那样做。”他的眼里含着泪。后来他还作了些其它事,作为对我的补偿。
那个时候我不抽烟,戒了很长时间了,然后李先念,中国的计划经济专家,后来的国家主席,给了我一根烟,从那开始我就又抽起来了,那时我非常紧张。宴会上,罗杰斯又谈起了Sam Snead,尼克松夫人说了些家常话。周恩来和尼克松几乎没怎么说话,唐闻生负责那边,我负责其余的人。既然没有人说话,我就跟乔冠华和其他几个中国人说起了中文,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后来我翻译了外长级的会谈,非常紧张,乃至于一年后,我都能记得当时说的每一句话。我还能反着看中文,看桌子对面中方的资料简介(briefing book)。因为我以前自己专门练过,猜想能用得上。他们的外长,基本都是按着资料简介上的东西说话,而罗杰斯也是,按着我们的资料简介说话,我们还有人给他提示。
P51我们这块的谈话主要是在细节方面,另外就是互相抱怨,以及历史的解读之类的。其中某些部分对罗杰斯来说很不熟悉,比如朝鲜战争的起源和过程,以及美国在各个阶段的立场。中方拿出很多新闻资料,力图说明美国是霸权主义。他们的翻译和我,就某些关键概念争论的很厉害,比如deterrence,他们翻译成“恐吓”,而我不同意。当然他们有他们高度倾向性的词汇。他们没有受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他们不觉得在表述中加入价值观有什么不对。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使用主观性,而不是描述性的语言。可以想见,我们争得很热烈,但是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只是表达各自的观点而已。
在我们去之前,发生了913林彪事件。说起来,我可能是美国政府里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人,但我也是相当偶然发现的。我读到四川报纸的一篇文章,他们突然发起了批判孔夫子的运动。媒体上充满了这类文章,我在读那篇文章时力图从中寻找文章背后的逻辑,进而推出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运动。我的结论是,有人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我给上面写了份备忘录,但是没人相信。接下来我们知道了林彪的事。这件事说明,在毛之下是有分歧的。
周恩来总是毛的政策的忠诚而又文雅的执行者(implementer)--我说执行者,用的是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他能把宽泛的概念转化成可操作的事情。我读了很多关于周的资料,(p52)我记得哈马斯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50年代联合国大会主席,为了解决被中国大陆击落逮捕的美国飞行员而访问过中国,后飞机失事去世)对周的评论,大意是:当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感觉自己是站在一个文明人面前的很不文明的人(20190706补记:今天微信上看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鲁迅,里面提到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周恩来见联大秘书长,“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周恩来身上有一种非常高雅的风度和魅力。在我们访问的第二天的晚宴上,周恩来跟坐在桌子对面的我交谈,了解我的背景,在哪学的中文,我对这次访问的看法,诸如此类,中方的翻译在边上给总统翻译。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但是通过中方的默许,我偷偷跑了出来,到了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我想买一套《二十四史》。中国每一个朝代都为前朝作史,这些历史写得很客观,很专业,是现存所有人类文明中最完整的。我在情报资料中看到,他们出版了这套书,所以我带了很多钞票,想买一套。书店里的人告诉我,学者们还在忙着准备这套书的出版,目前尚未完成。周恩来手下显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天,午饭时他对着桌子对面的我说:“听说你想要《二十五史》?”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写了民国史,我俩就这个话题谈了一会,周恩来为了尼克松的缘故介绍了这套书。他说书还没出版,但是因为我对这套书感兴趣,他会送两套18世纪的原版给美国,一套给白宫,一套给国务院。确实,在国务院图书馆里,后来就有了这么一套带封套的百衲本(Bo Na Ben)二十四史(18世纪,清史还没完成吧?既然是百衲本,清史应该是后来补的)。他还另外送了我3本文学评论的书,是关于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由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个文人写的,这个人是中方某翻译的父亲,那位翻译与外交部长在恋爱,然后嫁给了他(不需要考证了吧?章含之,章士钊吗)
话说回来,就是这次谈话,导致在杭州,尼克松把我叫去跟我道歉,我上面提到过。在我给尼克松和周恩来的谈话翻译时,尼克松说了一些让人非常不好意思的话,他说:“总理,我请你注意这个年轻人,”我翻译了这句,然后他说:“因为他很可能是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那时我27,28岁,我暗想:上帝,他要么是说,30年后我们才能有中国大使馆,直到这个家伙长大;要么是说,他们要派最不重要的,最年轻的大使去中国。我很难堪,没有翻这句,是唐闻生翻译的。周恩来低语了一句,类似于“会有这一天的,”这件事就过去了。
P53,结束后,周恩来让我留步,我们又谈了一会,他问了一些我们的外交人员的情况和其它一些事。事后我感觉良好,总统道歉,总理夸奖。
我们到华东地区去的时候,遇到两位中国军官,这是周恩来自林彪事件后第一次来华东地区,军队都是提心吊胆的,我跟他们两人谈朝鲜战争,两位都参加了。喝酒时,我专门跟他们两位干,很快他们两人就喝高了,他们站起来,绕着桌子敬酒,他们很失态地跟周恩来说话,我在一旁听着,他们说:“自从那个不幸的事件,我们一直没见您到这来,我们想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忠心,总理。”在场的中国人很尴尬,认为都是我把他们给灌醉了。这么说,也不全错。于是乔冠华就冲着我来了,要把我灌醉,他酒量是出名的。他是中国指定喝酒的人,我记的我们喝了23杯茅台,
P54 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争议在于谁应该代表这个中国,在中美上海公报里,美方使用很有艺术性的语言指出,美方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此没有异议,这是美方的一个基本点。据我回忆,基辛格在公报的语言上还想作更大让步,想超出这个基本点。但是Marshall Green(Green在这个外交官口述历史项目中也有回忆录,谈到这个问题,基辛格的回忆录也简单提了,但是,就像前一篇Payne日记里顾维钧的说法,老派的外交官说话都是轻声低语,等到说自己的失察,可能都快听不见了。)出面劝阻,并让国务卿罗杰斯出面,结果没有让步,这一点上,Marshall Green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公报实际上是在杭州通过的,我和冀朝柱一起研究公报的中文版,我发现,中文的翻译尽了最大努力反映美方的保留意见,他们翻译的非常专业而又很有艺术性。(是不是这个原因基辛格对章文晋的书面英语非常赞赏?)
解释Hegemony。。。。。
我到一个地方,总要看看当地人读什么书,在北京,没人读书(70年代,兄弟,70年代,整个中国无书可读)。毛主席语录已经不再发行了,我还是在上海,逼着一位书店经理(应该是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主任)给我从柜台下拿了一本,这是一个文化沙漠。
---版权不归我有,双重请勿转载---
如果您坚持到了这儿,祝贺您!谢谢阅读,谢谢合作!
20180703 补记:
看到一张傅立民的照片,与邓小平握手,卡特总统站在一边。没说时间地点

来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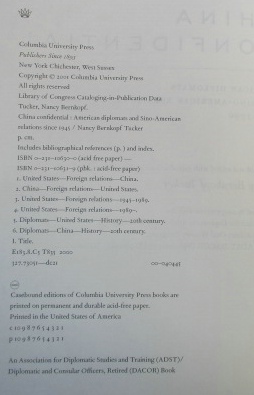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由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编辑,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殊途同归”那个翻译真是很棒,赞!
chen jian 很可能是陈兼。
那个评分系统当是美国政府的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Scale). 2+ 就已经是高级水平了。4+基本就是大山那个水平并且具备专业知识,比大多数中国人的中文都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