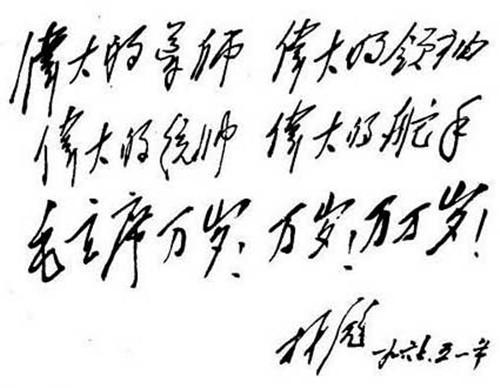赵县夏季也是一天三出工:早饭前、早饭后、午饭后。
告诉我分到了第6小队的女生叫秋芳,临睡前我托她第二天带我去生产队。她说:头一天还是吃了早饭以后再去吧,早上好好睡会儿。
在知青宿舍迎来的第一个早晨。玻璃窗没有窗帘,射进来的光线能通知时辰。外边还是灰蓝色,还没有一丝阳光,出工的钟声就从不同的方向传来。从睡意中能判断出还是半夜。我[
阅读全文]

摄于俺们庄北站
[
阅读全文]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自从网友jjzz在跟帖中说想再吃一次锦州的杜记馄饨以后,我就一直在记忆中搜索杜记馄饨,怎么也想不起来,怀疑自己没有去过那么高级的店。就算没吃过总该知道它在哪儿吧。百思不解,给锦州的叔发短信:知道杜记馄饨吗?回信:锦州人没有不知道的!我就不知道,我算不上锦州人了?从车站前数起:老马路、北门口、福德街、烧锅大坑、百货大楼[
阅读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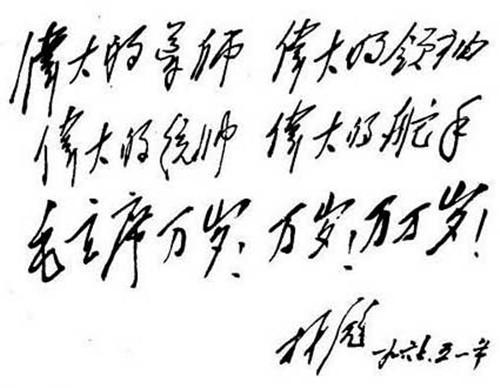
辽宁实行9年一贯制教育制时,河北仍然保持了初中—高中的升学体系。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才下乡,下乡完全是按照年龄,并不看你是否有知识。初中毕业后主动放弃读高中的孩子,要么在家呆到下乡年龄、要么到工厂去做临时工,挣两年钱以后再下乡。我去的青年点多数人有作“临时工”的经历,跟他们聊天,话题中多是“俺师傅”,很少听到“俺班同[
阅读全文]

长期居住海外,偶尔回趟国主要目的就是探亲访友吧;探亲访友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吧;一吃你就能感到祖国亲人亲、祖国食品丰富、祖国变化大,是吧。俺就没有那福气,若干年前开始,只要一吃点像样的东西,肠胃就闹得落花流水,闹得去打过两次点滴。别人都没事,就你闹事,这不是给人家请客的闹难堪吗?知道自己的短处就多注意啦。再吃饭时老老实实抱着米饭,眼盯[
阅读全文]

我离开锦州,爸没有了负担,也失去了精神支柱。爸每天魂不守舍,连正常出工都做不到了,以往只有雨天才能休息,才去城里逛逛。我不在了,爸再也不用撑出坚强乐观的样子,再也不用跟着太阳规律地出工挣工分了。爸进城只去两个地方:先到中央大街路东的大邮局,站在那里看挂在玻璃窗里的报纸,那是爸唯一能得到文字消息的地方;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去老马路十字[
阅读全文]

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多捞多得,日理万鸡,选霸干部,任人为闲,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
阅读全文]
1976年8月我带着一种盼望已久的回家感和就要自己去闯世的悲怆感回到石家庄。但这里不是终点,只不过是路过而已。
8岁时为了保住我的市民户口,妈把我转到锦州表姑家。16岁时为了将来能回到妈身边的城市那一线希望,又选择了到河北的农村插队,户口最终落到了农村。多折腾、多讽刺!那时,中国有多少人为了户口而奔波、为了户口而绞尽脑汁啊。如今,折[
阅读全文]
1969年春,知道我家要搬到31号院的时候,我还没有进院子就哭了,那天晚上爸为了哄我高兴背着我量屋子的进深,然后说:“一步半。记住咱们这屋子一步半,将来你写书的时候把它写上”。直到离开锦州我和爸一直住在这一步半的房间。如果那时没有搬到这个院子的话,对前五里营子的回忆也许不会这么丰富。
如果用我在学校学到的起绰号的本领给31号院[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