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
盘古开浑沌,昭然。雨露润万物,成长。家父之名号皆含其中。在其它网站的网名是:小皮狗,蒔花闲人,海樱子,筱君,有意无意,青青小草抚琴
正文
在回家路上,发现月亮特别的圆,也很大。像个大铜盆似的挂在天边。睡前,随手摸了一本书看几行,以便催眠。这本书是罗时进写的《唐诗演进论》。其中有关于孟郊的东野诗风介绍,倒是引起了大脑兴奋,有点睡不着了。于是索性又到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将其一些要点摘录出来,成一小文: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blog/329593/article-214280.html#ixzz3aY69MNs3
该文,本人曾经以小皮狗的网名在其它网站上发表(见以上链接)
罗先生在他的书中关于唐代孟郊诗的风格特色,最著名的评语是苏东坡的“郊寒岛瘦”,习惯上孟郊被视为元和诗人,而且被当作韩孟集团的主要成员来讨论。从孟郊留下的作品看,他的创作像元结一样,诗体多集中在乐府、古诗上,律诗写得很少,而乐府也多用汉乐府常见的民歌手法,明显可以看出有意复古的倾向。他在书中的精彩片段如下:
当然,正所谓“‘古’而需要‘复’,实在意味着‘古’已到了其道不行的地步”。而古道之所以要行,又意味着现实的让人不满足。回顾文学史上的复古,不是针对内容的淫靡、风格的矫揉造作,就是针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大都发自伦理的而非美学的要求。贞元八年(792),24岁的韩愈在长安初见孟郊,便倾倒于他“心追古人而从之”,年轻的韩愈才发现和明确了自己的志趣所在,而心悦诚服地追随孟郊。试观韩集,早期作品并无特别的尚奇倾向,自从结识孟郊,他的趣味和作风开始发生变化,日渐走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的方向。
孟郊的个性,直到遇见韩愈才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他人的赏识也常常是激发自己潜能的一种动力,尤其是在应试铩羽、倍觉挫折之际,韩愈等人的欣赏,对笃行古道的孟郊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增强他的自信和自持力。孟郊从古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看到一种与现时相通的东西,或者说超越历史时间的东西,因此复古就决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次打出“复古”的旗号,背后都有一种现实的变革要求,即使最为人诟病的明代前后七子也是如此。孟郊当然不能例外,诗型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复古毕竟只是他创作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表面化的倾向。他不只有古,还有僻和苦,那是他在唐诗中开辟的新境界,也是构成他风格印象的核心要素,甚至他的乐府都因此而亦古亦新,带有他很个人化的印迹。不过,这种属于他个人的新异色彩不是与他的艺术渊源直接相关,而主要是与他的身世、经历、性格,最终是与他的感觉方式紧密相连的。在一个以崇古为价值取向的国度,任何变革都只能到古代去寻找价值依据和理想的楷模,因而孟郊的复古口号也就是古代大多数诗人所选择的策略,即在复古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艺术目标。对于孟郊来说,那艺术目标就是矫激与奇峭。这种文字风格与他性格中的矫矫不群和愤世嫉俗正是相表里的。
在政治开明、人才辈出的唐代,俯拾青紫、平步青云对士人似乎都不是渺不可及的幻觉,而是确实可以期望的事。因此他们的自我期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当然会更加深大多数失败者的失意感觉。孟郊显然也是自我期待极高的,所以尽管他40岁出应科举,46岁进士及第,在唐代诗人中并不算最穷困的,但他的失落感却极为强烈,以至50岁得授溧阳尉,“有若不释然者”(韩愈《送孟东野序》),曹务多废,甚至分半俸以换取闲暇,最终竟辞官归去。《寓言》写道:“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在这对自我与世俗之尖锐对立的反复体认中,他的自我意识愈益清楚地确立起来。
相对于此前以典雅和谐为核心的那些诗美类型,奇险较之平易,是更极端的、紧张的和非和谐的美,也是更给人以刺激性的美,在中唐那极力寻求陌生化效果,以摆脱定型束缚的特定时期,它作为一种尚未被表现的诗美,一时成了诗坛共同追逐的时尚。韩孟一派诗风正是以奇、雄肆、异、瘦劲为主调,杂糅粗砺、险怪、枯涩、俚俗等元素而形成的。这些元素因诗人个性、境遇或艺术趣味的差异,被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加以组合,就产生了色彩变化丰富的风格群体。
韩愈称“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孟郊诗让人啧啧称奇,显示出其魔力。他经常用极度夸张的表现:“ 家具少于车、曲身成直身、泪滴穿乡书、情如刀剑伤。”它们不仅夸张,而且构想奇特,形象生动,让人过目难忘。《吊卢殷》(卷十)写诗歌对于人生的意义是:“有文死更香,无文生亦腥。”这类极度的夸张诚然已到“矫激”的地步,唯其如此,才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引起后生辈的群起效尤。孟郊每每用这种极度夸张的形容来传达强烈的情绪,以一种摒弃大历诗风的陈熟疲软而富有刺激性的犀利表现,来营造一种主观色彩强烈的奇峭风格。
孟郊诗在艺术表现上的这种特征也可以说是体现了时尚的趋势。在遣词造句方面也显示出由平易而趋于奇峭的艺术追求,显出鲜明的个人化色彩。“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经童音韵细,风磬清泠翩”“柳弓苇箭觑不见,高红远绿劳相遮”,例子弥不胜举。
孟郊在唐诗史上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就清楚地浮现出来。就如清末周实所指出的,“将嚣张之气、侧媚之态扫除尽净”。诗人孟郊同时能以“韩孟”和“郊岛”的并称标志着唐诗中两种影响深远的风格,仅此也足以显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屈指数来,这样的诗人的确是不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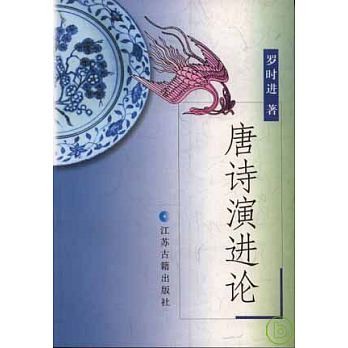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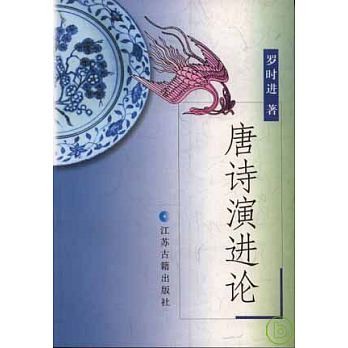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blog/329593/article-214280.html#ixzz3aY69MNs3
该文,本人曾经以小皮狗的网名在其它网站上发表(见以上链接)
评论
中村
2015-05-19 07:00:09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老朽' 的评论 : 我是在自娱自乐,谁强迫你来看了吗?!
老朽
2015-05-19 00:41:01
回复
悄悄话
现代人谁有闲功夫看又丑又长的东西,留着自娱自乐吧
老朽
2015-05-19 00:39:10
回复
悄悄话
。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