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截图)陈小平在“SELF格致论道”论坛上介绍“疟原虫治癌疗法”
起底“疟原虫治癌疗法”
2018年12月23日,在中科院计算所旗下“SELF格致论道”举办的公开论坛上,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陈小平发表了题为“疟原虫将成为抗癌生力军”的演讲,向公众介绍了他的“疟原虫治癌疗法”研究最新进展:“目前有近30例晚期癌症病人接受了疟原虫抗癌的治疗,10例已经观察了一年多,其中5例有效,2例可能已被治愈。”在他的描述中,治疗过程易如反掌:“我们给这个病人打1毫升含有疟原虫的血,这个治疗就完成了,就是打一针这么简单。”
疟原虫能治疗癌症的原因,陈小平在演讲中作了一个连初中生都能听懂的解释:因为癌细胞分泌一系列信号,让人类的免疫系统不工作;而疟原虫感染机体后,能唤醒免疫系统。同时,疟原虫还能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从而切断其营养供应。
癌症作为世纪难题,科研上的任何进展都牵动人心,更毋庸说陈小平直接提到了“治愈”二字。他的这番演讲,于一个月后被中科院官方微博转发,在春节期间立即吸引了众多自媒体及部分主流媒体的传播。但很快,来自同行与专业媒体的各种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疟疾疗法”前传
2017年9月,陈小平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回到母校广东医科大学作学术演讲,在那时,他就不遗余力地介绍他的疟疾与癌症的关系这套学说。广东医科大学前身为湛江医学院,陈小平于1977~1980年就读于此。据该校官网介绍,学制分5年制本科与3年制专科两种。后来,陈小平又在中山医科大学取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
2004年,中科院与广东省、广州市共建的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成立后,当时已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研究室主任的陈小平,成为该院第一批研究员并工作至今。
进入该院后,陈小平便集中精力从事疟原虫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包括疟原虫与肿瘤的相互作用、疟原虫与艾滋病毒的相互作用研究”。陈小平一直津津乐道于该研究灵感的来源:1985年,他读研一时,从一幅疟疾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图与一幅肿瘤死亡率的分布图受到启发,“好像哪里多疟疾,哪里肿瘤的死亡率就低。可能疟原虫感染对肿瘤有治疗作用。”在演讲视频中,他将自己描绘成一名坚持理想不为外界所动的科学勇士,宣称“我毕生的梦想与追求就是战胜癌症,希望疟原虫免疫疗法能够推广到全球”。
然而,种种公开信息却显示,陈小平并非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想到用疟原虫来治病的人,而该领域最有名的“先驱”、已经于2016年去世的亨利·海姆立克,与陈小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海姆立克是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因发明了“海姆立克急救法”,被称为“挽救生命最多的外科医生”,但在西方却有大量负面报道。他的儿子皮特·海姆立克谴责其一生是“50年未曾被发现的到处行骗史”。
皮特搜集了大量资料与报道,起底自己父亲这位“了不起的连环骗子”。其中,他特别提到,“我父亲最怪异的事莫过于‘疟疾疗法’,一个宣称通过感染疟疾来治愈癌症、艾滋病和莱姆病的骗局。”
利用引起疟疾的疟原虫来治病也不是海姆立克的发明。1917年,奥地利医生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发现,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发烧能够治疗梅毒。瓦格纳-尧雷格因此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40年代,青霉素发明后,梅毒的疟原虫疗法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海姆立克却在1980年代重新拾起了这种疗法。据美国杂志《新共和》2007年报道, 海姆立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癌症——尽管他毫无肿瘤学的背景。《华尔街日报》1982年第一次公开报道了海姆立克关于疟疾抗癌的想法。美国疾控中心、食药监局等均拒绝疟原虫疗法,并与其他医学专业人士及人权活动人士一起谴责其暴行。
由于得不到支持,海姆立克曾于1987年前往墨西哥进行推广,结果5个患者中,有4个接受治疗不到一年便去世。海姆立克不但没有放弃,却转而开始将疟疾疗法应用在莱姆病和艾滋病患者身上。这些治疗都不成功,且继续招致批评:疗法被认为毫无科学依据,并有生命危险。
海姆立克并未停止他大胆的试验。据《好莱坞记者报》等报道,他利用明星们的捐赠作为经费来源,开始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陈小平便是其中之一。《纽约时报》2003年的一篇报道指出,1993~1996年期间,海姆立克的疟疾治疗艾滋病项目在中国进行试验,他与陈小平为首的几位中国科研人员合作,在至少8位中国艾滋病人身上注射了含疟原虫的血液。其中有7人是来自云南的毒贩。事后,参与该项研究的多位美国研究人员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这些研究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残忍的罪行”。
陈小平与海姆立克的合作不仅于此。一篇于1999年发表在《浙江肿瘤》上的文章《疟疾疗法治疗晚期肿瘤的初步报告》显示,陈小平与海姆立克等人当时就已经进行了疟疾治癌的临床试验,选择了7例晚期癌症患者作为受试者。
该研究是在美国Rippel基金的资助下进行的。Rippel基金会是海姆立克的一个长期资助者,由美国一位金融家于1953年成立。此外,陈小平1998年博士论文即为研究疟原虫与HIV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而亨利·海姆立克则出现在他的指导老师小组名单中。
20年后,当陈小平在国内公开推介他的疟原虫疗法时,却只字不提这位与他有过密切合作、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先行者。一个在国外被业界频频批评和被媒体多次曝光的疗法,在近30年后,依然在中国找到了生存空间。
对此,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立铭引用《经济学人》于1月3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说,要警惕一种现象:“伦理倾销”——那些更富裕、监管更严格国家的科学家,将本国不被允许的医学研究搬到另一个可能较穷、监管较为松懈的国家去进行——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疟原虫的各种研究互相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国内关于疟原虫与癌症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有限;而国外医学界在这方面已有较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陈小平的研究与已发表的文献存在诸多相悖之处。
陈小平对1955~2008年间全球56个国家中30种癌症死亡率和这些国家的疟疾发病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疟疾发病率与全球癌症死亡率可能负相关。这一研究于2017年发表在《Infect Agent Cancer》期刊上。对此,王立铭分析说,整体而言,两个趋势之间的负相关性是非常微弱的。疟疾发病率变成原来的2倍,癌症发病率只会降低10%左右。
有学者直言,疟原虫与癌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或关系很弱——更糟糕的是,目前学界研究发现,疟疾被证实会增高某种癌症的发病率。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Ali Salanti以及温哥华前列腺癌研究中心的Mads Daugaard等人对于疟疾与癌症的关系作过研究。Ali Salanti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是很熟悉陈小平所作的研究,但我可以说,癌症与疟疾没有关系,除了伯基特淋巴瘤——同时感染埃博拉病毒与疟疾会促使肿瘤增大。除此之外,非洲关于疟疾流行病学的数据并没有显示二者之间有明显关联。”
过去50多年,医学界已经发现疟疾流行地区同时有伯基特淋巴瘤高发的情况,这是一种具有地方流行性的儿童期癌症,多发于非洲地区。2015年8月,美国洛克菲勒大学Davide Robbiani等学者在《Cell》上发表文章揭开了疟疾致癌的机制:小鼠试验表明,在长期对抗恶性疟原虫的过程中,B细胞DNA变得容易发生致癌突变。
关于疟原虫治癌的原理,陈小平解释说,疟原虫感染可以非常强烈地激活天然免疫细胞(NK细胞),这种细胞激活后可以杀灭一部分肿瘤细胞。当肿瘤细胞死亡后,它释放的抗原跟疟原虫感染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激活了T细胞。“我们知道,T细胞是抗病原体和抗癌的主力军,T细胞被激活,特别是肿瘤内部的T细胞被激活,可以非常有效地杀灭癌细胞。”
而疟原虫作为毒性病原体,能否真的激活免疫系统,似乎也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一个由来已久的看法是,激活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在有些情况下能够促使免疫系统去攻击肿瘤。一些科研人员也成功地研制出使用病毒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但Ali Salanti强调说,“疟原虫与病毒不同的是,它可以在人体内存活很长一段时间,这恰恰就因为它特别不擅长激活免疫系统。
因此,我并不看好在人体身上注射(疟原虫)这个试验可以实现(免疫系统)的激活。”霍普金斯医学院肿瘤系的一位遗传学博士也撰文指出,诸多研究文献已经表明,疟原虫感染甚至会抑制免疫系统。
该疗法的另一个生物学机制,陈小平声称,是疟原虫激活了免疫细胞的同时,还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从而切断营养供应,“饿死肿瘤细胞”。具体而言,疟原虫可以通过下调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受体蛋白VEGFR-2,来阻断血管生成的信号通路。该研究成果于2017年发表在杂志《Oncogenesis》 上。
显微镜下的疟原虫。陈小平的疟原虫治癌原理中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比如并未比较各种毒性不同的疟原虫是不是同样有效等等。
然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研究人员2010年发表的研究结论则与之相反: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感染导致人体的VEGF和VEGFR-2上调。
研究除了在理论模型上招致许多批评,多位业内专家并不认同陈小平对其临床试验结果的阐释方式,认为这不仅是不科学的,甚至会误导公众。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一般只有症状完全缓解、并持续五年的病例,才能称为临床治愈。
“从网上公布的临床结果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疗方式产生的效果超过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法。事实上,如果用严格的现代肿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来衡量,网上公布的现有10位病人接受一年治疗的结果,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疗法。”美国耶鲁大学肿瘤中心免疫学主任、PD-1免疫疗法理论的重要贡献者陈列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此外,一个不容忽略的科学事实是,多篇文献提示,抗疟药物对癌症治疗有效。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2017年在《Cancer Discovery》上发表的文献就指出,一种叫做DQ661的药物能够有效靶向PPT1这个酶分子,同时阻断调节癌细胞生长的mTOR和细胞自噬,而DQ661实际上是抗疟药物氯喹的二聚体形式。《中国新闻周刊》检索美国临床试验网发现,目前用抗疟药物青蒿素或氯喹治疗癌症的临床试验已共计20多个。
从陈小平疟原虫疗法临床试验的过程描述来看,受试者在出组时会被注射氯喹或者青蒿素以灭虫,因此,部分受试者的“治愈”或归功于抗疟药物而非疟疾本身;同时,这个结论也会削弱疟疾发生率与癌症死亡率负相关的论断,因为在疟疾流行的地区,抗疟疾药物的使用自然也更加广泛。
针对上述疑点,《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联系陈小平本人,电话均无人接听。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家钟南山也是该研究的参与者之一。在项目位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基地,钟南山和陈小平分别担任临床研究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尚没有充分的证据和足够数量的案例证实该方法有效,个别案例不足以说明问题。”钟南山2月8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目前该项研究仍有很多未知数,但是这个现象已经很肯定了。”他进一步说明,未来科研团队将提取疟原虫生物介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通过自然发生疟疾的方法,而是通过有效的生物介质来激发体内的自然发生细胞的活性。
存疑的伦理审查
从2016年起,陈小平团队连续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和云南昆钢医院合作,展开临床研究。除了最早的一批受试者,也就是在陈小平演讲中提到的已有结论的有10人,目前还有30多人在等候人体试验。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除了试验本身的科学原理站不住脚,陈小平的临床试验还存在较大健康风险:受试者被注射病原体,可能会带来的身体伤害;疟疾作为世界三大传染病之一,试验可能会引起疟疾传播进而危及公众安全。
以高烧为例,陈小平曾告诉媒体,“患者会颇有规律地,每隔一天发一次高烧,高至39℃甚至40℃,约两个月以后,病人不再发烧。”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受试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与另一位受试者都连续高烧,并出现感染。她的日记写道,“接种一个月左右,出现持续高烧不退的情况,并伴随咳嗽,整夜睡不着的情况,持续时间大概半个月。”
陈小平认为,能够为其伦理及试验风险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受试患者已是癌症晚期,无他法可试,且在患者及家属同意下采用这种方法。对此,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指出,晚期绝症患者的这种脆弱性很容易被利用,“科学家与医生是专业人员,我们不能利用公众的这种脆弱性与迫切性,我们应该有保护他们的责任心。”
“我们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评估,评估除了它有效没效之外,还要看它的风险与收益,目前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代替,会不会引起其他的大的一些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必须经过严格评估之后才会来作临床试验。”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解释说。
根据国家卫计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伦理委员会由开展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且成员应当从生物医学领域和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中遴选产生,人数不得少于7人。
与企业发起的药物临床试验不同,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只需要在相关临床试验管理部门备案,经由医院内部自行组织的专业和伦理委员会批准,就可开展。王立铭认为,由于较为宽松的申请和注册门槛,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确确实实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提供的该试验的《临床试验会议审批件》显示,其伦理委员会由11人组成,包括该医院的9位成员、一位社会律师以及越秀区计生办科长。另外两个试验伦理委员会未提供相关信息。
但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问题不仅在于程序规范与否,更重要的是,伦理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起到把关的作用,尤其是面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需要委员会成员有深入的知识。
“这种人文、伦理的问题,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都很生疏。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不是随便就几个人来就可以,它应当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吴一龙表示。?
伦理委员会是否进行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基于什么理由同意该试验?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多次尝试与三家医院临床试验的伦理委员会取得联系,但截至发稿时都未得到回应。
在演讲中,陈小平透露说,“从申请临床试验再到批准历经了3年的伦理答辩,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陈小平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曾透露,在2016年注册的第一个临床试验中,疟原虫疗法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组织的多次伦理答辩,且多次修改方案后,才开始在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进行试验。
翟晓梅表示,业界不仅要关注这个研究如何通过伦理审查,亦即“程序合法问题”,还应该关注更实质的科学价值问题:伦理审查委员会讨论一个科研项目的时候,首先要讨论实质伦理的问题,包括研究该不该做、是否有价值等。“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判断告诉我们,他这个研究在科学上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伦理学上的价值判断应首先受到质疑。”
另一个招致批评的问题是,陈小平的临床试验结果尚未在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就在公众平台上传播。“证据还不十分可靠的时候,就以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以一个完全可靠的、确定的一个事实报道给媒体,这种做法是不妥的。”翟晓梅指出,公众因为对研究的不了解,以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晚期癌症患者就会应声蜂拥而去,结果可能会伤害受试者,长远来看会伤害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
“医学进步不能营销希望,医学进步需要最高标准的透明度和同行评审,”复旦大学肿瘤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朱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透明度是保证成功可以复制,同行评审是保证内行看门道。”
疟原虫治癌背后的商业
从疟原虫抗癌疗法的受试者招募到临床试验,一直都有广州中科蓝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蓝华”)的身影。该公司官网信息显示,陈小平自2013年起担任公司创始人、CEO。
工商资料显示:中科蓝华于2013年成立,注册资本1900万元,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柯宗贵(持股比例为64%),柯宗贵也是创业板A股上市公司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控股股东。但从蓝盾股份最新的财报来看,中科蓝华并未贡献营收。
该公司在介绍中声称掌握四大原创核心技术,均与疟原虫有关。对于疟原虫治癌新技术,官网介绍“具有非常诱人的前景”,而其开发的新型抗疟疾药物DQ,“其体外抗疟效果优于青蒿素10倍。”
中科蓝华拥有三家全资子公司:广州蓝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癌症的疟原虫免疫疗法,并将成为临床研究的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广州蓝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型抗疟药的研发;广州蓝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癌症免疫治疗的宣传教育与推广。三家子公司分别成立于2015年、2016年、2017年,陈小平均担任经理一职。
癌症免疫疗法的市场热潮以及政府对生物科技行业的政策支持,让中科蓝华这类创新企业找到了“野蛮生长”的土壤。肿瘤免疫疗法,即通过刺激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被视为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后,癌症治疗领域的第三次革命。詹姆斯·艾利森与本庶佑由于发现免疫抑制机制,找到治疗肿瘤的新方法,荣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疗法在当前医学领域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在国家的创新大环境很好,创新新政策、新机制不断出台,也允许科学家办企业了,这些都为科学家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陈小平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外部环境对创新的作用。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副书记侯红明2018年5月造访中科蓝华时指出,在国家对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的政策支持下,广州生物院孵化出的高新技术及各项专利逐步与企业接轨合作,实现除了发表学术论文以外的技术产业化的实践道路。
据公开报道,2017年10月19日,中科蓝华宣布与上海思科瑞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者为中科蓝华注资数千万元。柯宗贵同时透露:“中科蓝华还要在肺、肝等领域继续做工作,也准备去纳斯达克上市。”2018年10月,柯宗贵再次表态:“中科蓝华正在探索攻克晚期实体肿瘤治疗的世界难题,把以疟原虫免疫疗法为基础的癌症治疗整体解决方案做成癌症免疫疗法领域的独角兽,准备两年左右的时间在香港筹备上市。”?
毕业于电子工程系并长期掌舵一家主营信息安全技术公司的柯宗贵,显然对陈小平的疗法非常乐观。他的乐观也有现实做支撑:在陈小平受到业界强烈质疑之后,2019年2月14日凌晨,中科蓝华招募晚期癌症患者参加临床试验的帖子,依然突破了10万+的浏览量。有人在网上评论说,“如果有机会,大部分癌症晚期患者还是愿意试一试吧。比起等死,既可以有机会康复,又可以为医学作贡献。传播未证实的消息是不好,但希望这不是谣言,而是希望。”
“PD-1是特异性免疫,即通路与机制相对明确,而‘疟疾抗癌’属于非特异性免疫,具体通路、机制均尚不明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科主任王理伟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耶鲁大学肿瘤中心免疫学主任陈列平则直言,“对一种尚未显示出明确效果的临床试验方法,探讨它的原理和前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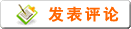

来源: bebe2014 于 2019-03-19 14:58:41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40 次 (38011 bytes)
字体:调大/重置/调小 | 加入书签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贴 | 当前最热讨论主题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3月2日,传来了珍宝岛的枪声。中苏关系骤然紧张,濒临战争边缘。在诸多叙述中,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说是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秘密与基辛格会谈,想要获得美国的首肯。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于是,美国政府把会谈秘密捅给了报社。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勃列日涅夫得知美国泄露了苏联的秘密,加上中国已经准备好要打一场核战争,只好不了了知。
这个说法过于夸张离谱,事实上,无论是多勃雷宁,还是基辛格,都从来没有承认过此事,也没有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叙述过他们曾有这样的会谈。《华盛顿明星报》的报道倒是确有其事,可这是一份没有名气的小报。
毛泽东发起了珍宝岛之战。中国在岛上先埋伏了一支部队,对上岛巡逻的苏军边防部队实施了突袭。
珍宝岛之战发生后,当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即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电话,遭中方的电话接线员拒绝。苏方随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谈判意愿和建议。中方的答复是正在考虑。一直拖到5月24日,中方才答应举行谈判。6月13日,苏联政府做出回应,建议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两国边界谈判。7月10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苏联政府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半个月后,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年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从这个过程来看,在《华盛顿明星报》报道之前,苏方一直在谋求与中方谈判,而美国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即便现在,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也没有谈到中苏之间曾有过这样一个秘密接触过程。9月11日,中苏双方终于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会见。柯西金是在参加胡志明葬礼后,从河内飞回莫斯科,在杜尚别停留时接到莫斯科指令,说中方同意在北京机场与其会面。柯西金马上又从杜尚别飞往北京。这一过程说明,苏方是多么重视与中方领导人的会面。珍宝岛事件出乎苏联领导层的意料,他们急于通过高层接触了解中方的真实意图。如果你留意的话,苏联最初的建议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而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会谈最终是在北京机场举行。中国实际上回绝了苏方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建议。
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面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四点,其间周恩来设便宴招待了柯西金及其一行。双方会谈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缓和了双方由珍宝岛之战引发的紧张关系。从珍宝岛之战发生到北京机场会谈,苏联锲而不舍地持续了半年的外交努力,所谓苏联要对中方动用核武根本是谣言。问题是:谁制造了这个谣言?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
“中苏军队在西伯利亚与中国边境接壤处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冲突,把尼克松的构想变成了一个机会。要不是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次来我办公室告状,白宫还不会那么快就注意到了这场冲突。在当时的冷战期间,苏联来向我们报告跟平时的话题——或者说跟任何事情——毫不相干的这么一件事,实为罕事。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很可能是苏联先动的手。而且他们在占领捷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我们作了这样一个通报,一定别有用心。兰德公司的艾伦?惠廷对中苏边境的冲突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更证实了我们的怀疑。惠廷的结论是:由于事件发生地点靠近苏联的后勤基地,与中方后勤基地相距甚远,因此侵略者很可能就是苏联。他还说下一步苏联可能要袭击中方的核设施。若中苏战争迫在眉睫,美国政府必须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要求进行部门间的审查。
结果表明,我们对冲突直接原因的分析有误,至少对珍宝岛事件的分析有误,但歪打正着,根据错误的分析却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近期的历史研究表明,正如多勃雷宁所说,珍宝岛事件的确是中方先动手。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境巡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上面第一段引文中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基辛格并没有说多勃雷宁就向中国动用核武器征求美国意见。多勃雷宁根本提也没提。第二,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是中方先动手,基辛格不相信。
第二段基辛格玩弄了一点文字游戏。前一段末尾他写道他命令调查,第二段已开始他写道,“结果表明……”,给人印象好像经过调查,美国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其实不然,他还是诚实地告诉读者:“近期的历史研究表明,正如多勃雷宁所说,珍宝岛事件的确是中方先动手。”基辛格是直到写作《论中国》时,也即2011年左右,才知道中方先动手,“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境巡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基辛格接着写道:
“但实际上,中国这一举动的效果适得其反——苏联加紧了在边境上的骚扰,在新疆边境上消灭了中方一个营。”
1969年8月13日,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战斗中,中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38人牺牲(一说28人),包括3名记者。基辛格不但把这夸大成一个营,而且开始渲染核大战:
“1969 年夏天,中苏可能发生战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署在中国边境上的苏联部队增加到了42 个师,达100 多万人。苏联的中层官员开始向全世界各国他们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核设施,他们各国会如何反应。”(基辛格《论中国》)。
发生边境冲突,苏联增加边防部队很正常。但是说苏联的中层官员向各国同级官员询问对核战的反应就太搞笑了。基辛格这么写是因为他找不到苏联高级官员要对中国打核战的真实言论。说中层官员就可逃避造谣的指责。中层官员千千万,谁会记得哪一个中层官员的姓名?
当时,他自己、也可能是让某个下属把自己造出来的这个谣言抛给了一个小报记者。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登载了苏联要对中国动核外科手术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基辛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他知道像《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都不会登这种没有可靠消息源的新闻,只有藉藉无名的小报才会干这种搏人眼球的勾当。
接下去,基辛格写了一连串美国政府对中苏可能的冲突和战争的表态,其中以9月5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学协会上的表态达到最高层级。然后基辛格总结说:“策划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对华开放政策作好心理上的铺垫。”
在经过最初的漠视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实现与中国和解的天赐良机:中国出于对自己遭受苏联攻击的担心,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换取美国的和解以及安全上的帮助。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寻求与中国更高层次的接触。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都认为是苏联挑起了冲突。多年之后,当他们得知是中国先动的手,不知还会认为这个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铁列克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叙述了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通过秘密外交渠道要求与中国谈判。中国拖了3个月才同意谈判。为什么要拖3个月?是因为在等美国的反应。珍宝岛之战虽然不全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但是打了之后美国人一定会看到。毛泽东深知珍宝岛的枪声会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精心挑选了珍宝岛之战的日期: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后一个半月。哪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那么笨,等了三个月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所以只好一边敷衍苏联人,一边继续等。苏联人耐性又等了3个月,中国还是没谈判的具体行动。苏联人火了,想赖还是怎么地?你挑起的冲突,说愿意谈判却没有行动,看来还得给你一下子你才会动,于是在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给了中国一下子。
这时候,美国才有了反应。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的核战消息出来了。9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发话:“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他们的争吵升级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我们则不得不深表关切。”
尼克松当局仍按照自己的需要继续渲染中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甚至核大战。中国也配合演出,大挖防空洞。演戏讲究的是逼真,要舍得花本钱。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苏联的全部档案。根本找不到涉及苏联准备向中国实施核攻击的档案资料。叶利钦痛恨苏联,没有必要销毁或者隐藏此类档案,所以,并没有历史证据可以确凿证明苏联当年曾企图对华实施核攻击。姑且存疑吧。当了冤大头的苏联依然看不懂美中两家在玩什么把戏。
就在全世界弥漫着中苏即将大战的诡谲气氛中,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把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送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上。周恩来在信中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特使。于是,1971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
揭秘陈小平疟疾疗法人体实验往事(组图)
文章来源: 财新网 于 2019-02-26 14:10:10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被阅读 8291 次)
这一遭受广泛批评的疗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今天的文章,基于海姆立克的儿子Peter Heimlich提供的历史资料、书信往来和其他文献资料,再现了广州的陈小平在1990年代如何把海姆立克的疯狂想法在中国落地执行的
1991年,海姆立克在陈小平身上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图片由Peter Heimlich提供。(知识分子公号)
作品来源:《知识分子》
撰文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责编 | 陈晓雪
[编者按:今年春节期间“疟疾抗癌”爆红,广州的陈小平声称自己从疟疾和癌症的发病图联想到利用疟疾治疗癌症。实际上,陈小平在1990年代的重要国际合作者、他称之为“亲爱的爸爸”的亨利·海姆立克更早提出疟疾抗癌。
2月15日,《知识分子》介绍了即使在没有任何动物实验的情况下,从1980年代开始,海姆立克是如何鼓吹疟疾治疗癌症、HIV/艾滋病和莱姆病的。在美国,疟疾疗法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为此冒险。海姆立克在从私人基金会和好莱坞明星那里筹集到经费后,选择在墨西哥做人体实验,又遭到美国和墨西哥的批评。
这一遭受广泛批评的疗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今天的文章,基于海姆立克的儿子Peter Heimlich提供的历史资料、书信往来和其他文献资料,再现了广州的陈小平在1990年代如何把海姆立克的疯狂想法在中国落地执行的。]
故事要从这张照片(头图)说起。仔细端详,照片右下角的黑板上写着几行粉笔字——“欢迎Cionci先生到我们站指导。” 照片中的人物,从左往右,第一位是广州卫生防疫站站长肖斌权,接着的这位外国人就是约翰·塞恩奇(John L. Cionci)先生,最右侧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广州卫生防疫站工作的陈小平。当时他应该拿到硕士学位才2年,34岁风华正茂。
这是1990年5月,受美国红十字会所托,塞恩奇去中国几个城市讲艾滋病。这极可能是陈小平最早知道,还有用疟疾治疗癌症和艾滋病这回事。
塞恩奇来自美国费城,曾是一名整骨医生,和美国海姆立克(Heimlich)基金会主席、海姆立克研究所所长亨利·海姆立克(Henry Heimlich)是老朋友。早在1980年,塞恩奇第一次去中国时,就是去教授海姆立克的成名作,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吃东西噎住后,施救的人站在病人身后,挤压病人腹部以排出食物。那次,塞恩奇认识了南京人民医院的医生华宏顺。
华宏顺在我们这个故事中,牵线搭桥、鞍前马后,是海姆立克的得力助手,没有他,海姆立克在中国开展癌症和艾滋的疟疾疗法实验会难很多。华认识海姆立克要晚一些,应该是在1986年到位于辛辛那提的海姆立克研究所参观时,自那之后,他就负责在中国推广“海姆立克急救法”。用海姆立克自己的话说,正是由于华,“我的名字才变得家喻户晓”。
至于海姆立克本人,本刊之前一篇已有所介绍,比如他在1977年62岁的时候被辛辛那提犹太医院开除并吊销医师执照,他的儿子彼得·海姆立克(Peter Heimlich)称他为“一个了不起的骗子”。本文写作所引用的近700页的信件文档,即由彼得从美国公共图书馆等公开渠道获得后提供。
海姆立克在1980年代开始相信疟疾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并获得了一些私人基金会的捐助,在几个欠发达国家,如墨西哥开展人体实验。事实上,即使实验并没有在美国进行,海姆立克在美国国内也长期受到包括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CDC)、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FDA)、医生和研究者不断的批评与抗议,这里暂不详述。
1980年代的中国,毫无疑问是贫穷落后的。海姆立克既然选择了中国,就不得不简单说几句他和中国的“渊源”。据他自己说,他在二战期间曾在中国参与抗日,1984年还被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
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形象显然被很多人所接受,乃至于后来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要授予他名誉主席时,站领导还极尽赞扬称“海姆立克博士对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有巨大贡献,现在与我们在癌症和艾滋病疟疾疗法的合作,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又一巨大贡献”。
“中国人从不遗忘,他们甚至比墨西哥人更加有热情,更愿意合作。” 在1988年7月即将赴北京之际,海姆立克给资助他的美国的一家基金会的信中这样写道。
的确,从初期他和中国方面的合作来看,非常顺畅。
这一年的10月,受北京癌症研究所徐光炜邀约,海姆立克踏上了中国,开启了他与中国多家机构合作的癌症、艾滋病疟疾疗法的人体实验。
2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故事的主人公是陈小平,就暂把叙述的重点放到广州。
如开篇所述,在1990年5月,塞恩奇到广州之后,陈小平对用疟疾治疗癌症、艾滋病的想法印象深刻。9月,在得知海姆立克要塞恩奇陪同在南京开展临床实验后,他给塞恩奇写信,力劝将临床实验改到广州。
陈小平提的几条理由,也耐人寻味,比如他说“广州有很好的肿瘤医院,且广州肿瘤研究所所长(director)和肿瘤医院主任(dean)都是我的老师和我岳父的同学,他们都是著名的肿瘤专家,且人好”;“广州或广东是疟疾的流行区,很容易找到疟疾病人,也就是说,你可以简单通过将疟疾病人的血接种给其它人进而人工制造疟疾。”
一般的读者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先简单地描述下海姆立克设想的疟疾治癌症、艾滋的实验过程。实验分四个阶段,首先是找好病人;然后疟血接种,也就是把疟疾病人的血静脉注射入癌症或艾滋病人体内诱发疟疾;在病人高烧发热一定轮数后用氯喹治愈疟疾;之后进行一段时间的随访。对于癌症,会测量治疗前后患者肿瘤大小、体重等指标;对于艾滋,会在患者治疗前,发热期间,随访期间,检查身体、采集艾滋病人血样进行分析。
明白了这个实验过程,还需要明白,像这样充满风险的临床试验,而且直接在人体上进行,必须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病人的知情同意。当然,实验还需要获得资金资助,招募的病人要符合特定要求,而要获得可复现、可靠的结果,也要控制一系列因素,包括足够的样本量、设置对照、排除可能的干扰项等,魔鬼往往在细节里。
自从陈小平给塞恩奇写信后,塞恩奇就把陈小平的想法转达给了海姆立克。海姆立克随即指示华宏顺,尽快联系广州方面,打电话报告进展。之后,广州卫生防疫站的副站长刘树国,广州肿瘤医院的院长(Director)Yu Chang-tao给海姆立克和华宏顺写信称,经过专家讨论后,他们很确定想参加“疟疾疗法治癌”的合作项目。
1992年6月15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海姆立克研究所给第一批10位癌症病人每位支付3000美元,涵盖了治疗费、6个月的随访以及提交病人记录和报告的费用。
这些癌症病人是如何选择的呢?海姆立克曾在邮件中向陈小平解释,鳞状细胞癌、腺癌、黑色素瘤,可见的肿瘤,比如鼻咽癌、黑色素瘤,摸得着的肿瘤或者X射线可见的肿瘤(如肺癌),能让我们测量结果的(都可以)。海姆立克还说,这些癌症是通过标准处理如手术、放疗或化疗没法治好的,“因此也不会对病人有什么风险还有潜在受益的可能”。
这些癌症病人收治时的情况,在陈小平、海姆立克等人发表的文章中有详细的描述,总共7位病人,每个人所患的癌症都不同[1]。陈小平也曾披露这些病人接受疟疾治疗后的存活状况,7位病人按顺序分别是,22个月、拒绝随访、4个月、8个月、4个月、超过36个月、3个月,他发表的论文也是这么记录。
1997年8月,陈小平向海姆立克报告7个癌症病人接受疟疾疗法后的生存周期。本文件由Peter Heimlich提供。
但同样是来自陈小平,不同场合透露的信息却有出入。
有一次,也许是为了“威胁”海姆立克及时付钱到账,陈小平写道——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考虑第7位病人的报告有点用,我就给你这个报告。不过,我坚持认为你应该为此报告付钱,因为我们在这项治疗上花了很多时间、花了钱,随访也是一样的,尽管这名病人在完成疟疾治疗之后仅存活了一个月。这不是我们选择病人不当,相反,病人和病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复杂,这个病人没啥效果,因为在接受治疗之前,他的情况是好好的。” 这个病人的情况似乎并不属于上述7个病人中的任何一个。
不过,海姆立克的态度也很强硬,不久,他在邮件中“质问”陈小平:病人3和5在死之前是否做了随访?病人4和6没有收到随访报告,病人7死因究竟是什么,是否验尸,是否有数据表明疟疾疗法的作用,是否有活检信息显示癌细胞正在坏死?海姆立克说,“除非你能给我一个完整的报告表明癌症的状况,我们才会考虑为这名病人付费。” 他还提醒陈小平“遵照合同,按时提交数据”。
类似这样因为经费问题“来回扯皮”充斥了整个实验过程。作为陈小平研究的资助机构,海姆立克研究所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各个私人基金会筹钱,路数基本上是报告实验结果如何的好,现在很缺钱。
可能是中国这边的人体实验花钱多,原先的合同安排无法覆盖,陈小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向海姆立克写信要钱,时而要挟不给钱就不继续做实验,时而诉苦解释如何困难,甚至都开始叫海姆立克为“爸爸”(比如他第一次这么叫可能就是因为做第三组癌症疟疾疗法实验时缺钱了)。
整个的癌症实验从1992年开始,陆续有病人随到随疗,虽然中间因为经费短缺有所延迟,但在1993年底基本结束。
联系到2019年年初陈小平宣讲的利用疟疾疗法(简称为“疟疗”)治疗癌症的人体实验,以及他20多年前开展的癌症疟疗,耶鲁大学肿瘤免疫学教授陈列平评论道——
“这篇1999年的文章和现在做的实验相似,二十年后再做一遍几乎没有改进,这个很奇葩呀!最近宣布的实验结果也和1999年文章的结果相似,7例中有2例出现部分缓解,但不持久,因此对长期存活无或少有贡献。”
他进一步指出,这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实验最大的问题是伦理。“首先,这些病人没有用标准治疗(比如化放疗),直接一线用疟疗,这个以现在的伦理标准是不允许的。因为标准治疗有一定效果(很大可能不比疟疗差或更好),只有标准治疗失败的病人才允许用新疗法。其次,用疟疾病人的血或血清,居然伦理也能过。实验材料不纯,问题一大堆。比如到底是不是疟原虫起作用?因为输异体血也会引起发热。”
针对发热的问题,这里可以顺便补充其它各地进行癌症疟疗的情形。1993年10月,华宏顺曾到全国几个城市监督考察疟疗情形,在给海姆立克的信中,他提到南京的2名病人,虽然发了7次热,但没有在血里发现疟虫;徐州的6个病人,仅2人在血里发现了疟虫。
3
看完陈小平20多年前的癌症疟疗,我们再来看他另一项“毫不逊色”、花了更大精力的人体实验:用疟血治疗艾滋病。
根据陈小平在2001年写给海姆立克的信件,他在1993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向站长肖斌权提出用疟疾疗法治疗艾滋病;两个月后,海姆立克写信给他,也提出用疟疾疗法治疗艾滋病,“我和肖站长都十分惊喜,两人有同样的看法,后来我们约定,请海姆立克再次访问广州,讨论疟疾疗法治疗艾滋病的可能性”。
陈小平对艾滋疟疗很有热情,他在这一年的4月8日写信给海姆立克说:“我们已对用疟疾治疗艾滋病人深思熟虑过了,用疟疾疗法治疗癌症已经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没有什么理由不确信,对治疗艾滋病,这个方法也可以是有效和安全的;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此刻对艾滋病人实施疟疾疗法。”
应该说,陈小平的来信正合海姆立克的心意。1993年初,一份有关用疟疾疗法治愈艾滋的筹款方案在美国流传,项目的首席调研员就是海姆立克,他希望在1993年底完成10名艾滋病人的治疗。有意思的是,这份筹款方案还附了几个问题与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其它政府机构的资助?
筹款方案上的回答是——
“我们起初确实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初步临床试验,结果告知要获得人的临床试验的资助必须用实验动物先进行一系列基础研究。可这样的研究需要几百万美金,超过5年才能完成。另外,我们相信动物中用来模拟艾滋的病毒类型和人的艾滋病毒是不可比的,疟疾也不一样。我们质疑(动物研究)与人的艾滋研究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们不参与或者不支持动物研究。”
最终,这份筹款书被泄漏了出来,并引发了很多医生、研究者的抗议,美国CDC也认为这种实践没什么合理性[2]。“没有体外或体内的证据支持疟疾抑制艾滋病毒的感染或延缓艾滋病发病的这一假设,而使用间日疟原虫感染可能导致不良健康后果,在HIV感染者中诱发疟疾感染是不合理的。”CDC在1993年4月29日发布警告称。
也就是说,正当海姆立克的艾滋疟疗方案在美国遭受批评和抗议时,差不多的时间,陈小平殷切地希望在广州开展此项人体实验。
那么,这项实验是否经过卫生部门批准了呢?陈小平后来在一封邮件中回忆,“约1993年9月,广州单方面向市卫生局申请,并经过多次专家论证会的论证,最后通过”。但实际上,在9月27号,陈小平也只是声称得到了口头批准。根据我们获得的资料,陈小平的实验是否得到书面批准并不清楚。
这似乎没有影响实验照常进行。10月22日陈小平收治了第一位艾滋病人,从东南亚回国时在广州海关查出HIV阳性的一名男子。27日,这名病人接受了疟血接种。紧接着在12月14日,第二名艾滋病人接受了疟血接种。
没有太多治疗艾滋经验的陈小平很快遭遇了病人的死亡。1994年2月,为了催促海姆立克帮助自己去美国短期访学,陈小平在信中透露一名收治的艾滋病人已经死亡。
“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在你的帮助下去美国学习艾滋病,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艾滋病的治疗经验;顺便提一句,两周之前,一名艾滋病人在收治一周之后死了,部分归咎于我们在艾滋病治疗方面缺乏实践。求您在这件事上帮我个忙,好么?首先非常感谢您,我亲爱的朋友和爸爸。” 陈小平写道。
在1994年2月17日的一封信中,陈小平透露一名收治的艾滋病人已经死亡。本文件由Peter Heimlich提供。
到国外短期访学是陈小平的一个愿望。在1993年5月刚开始商量合作艾滋疟疗项目时,陈小平就提出,“因为体外培养艾滋病毒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无法开展,但我听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说,如果美国给予财政支持,为中国短期培训一名艾滋病医生,比如3个月,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获准开展艾滋病毒体外培养和其它相关项目。” 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明确说出这名医生是谁。
之后一次偶然机缘,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者约翰·法赫(John Fahey)终于给陈小平提供了机会,让他如愿以偿,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两名艾滋病人已经接种疟血后,海姆立克终于在1994年4月9日到达广州,一是为了接受广州卫生防疫站给他的名誉主席,二是签订下一阶段艾滋疟疗项目的协议(之前双方并没有签约)。
4月22日,广州卫生防疫站和海姆立克研究所签约,广州方的陈小平为主要研究员,肖斌权、卢月恒、刘树国是协作者。根据协议,广州要在15个艾滋病人身上做人体实验,并提供治疗前后以及3个月、6个月、一年、一年半、2年的随访报告,病人被收治在广州益寿医院;海姆立克研究所为前2名艾滋病人支付每人1万美金,收取2年随访等报告,而之后的艾滋病人分阶段支付总额5000美金,用于治疗、随访和提交报告。
签约之后,新一轮的艾滋病人找寻工作启动。7月初,陈小平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瑞丽县(Yuili County)千里迢迢弄来了7名HIV病人,全是吸毒者,并在7月27日接受了疟血接种。这样共9名病人接受了疟疗,但他们都无艾滋病的症状,只是HIV病毒检测呈阳性。
对于这次从云南运输病人,陈小平知道是违法的。这从他当月给海姆立克的信里可以看得出:“广州无法通过PCR检测艾滋病毒浓度,可是也无法(把样品)送到北京,因为北京一定会问这些病人是从哪来的,可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从云南弄来这些艾滋病人是暗地里做的。”
这些病人在医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陈小平在给海姆立克的一份信中曾这样描写——
“我建议你一定要再来广州,你最好早点来,因为一旦完成治疗,我们必须马上送这些艾滋病人回家;因为医院很难管理他们。他们中一些是囚犯、小偷,都是吸毒者。住院期间,他们偷走了钱、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的东西,经常互相打架,与其它病人打架,甚至与医护人员打架。他们闹得医院里一团糟,所以我们必须在治疗结束后立即送他们回家。如果益寿医院的领导早知道会发生这些,他们当初肯定不会接收这些人。”
被海姆立克派去监督陈小平工作的华宏顺,也承认“这种病人对我们项目来说,并不是合适的候选人。” 终于,1994年9月初,7位病人结束了治疗,返回了云南老家。
这次疟疗实验,由于经费短缺、秩序混乱给陈小平等人造成了心理阴影。9月7号,在华宏顺与陈小平等人的总结会上,刘树国强调——“艾滋病在这个国家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了进行这个项目,我们担负了沉重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因为除了云南,不允许做任何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对该项研究保密。”
随着治疗结束,陈小平开始了随访,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跋涉在偏远的云南,有些村子甚至连量体重的秤都没有。
他一方面要及时提交随访报告,但同时也要不停的乞求海姆立克付钱。他曾诉苦说,钱都不够支付病人的住院和交通费,“付了医院14000美元后,还欠着钱,如果完全按照我们的协议,三个月后由于经费短缺随访就会有困难。” 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期待海姆立克能给他找到三个月访学的机会。
那么,病人的情况如何呢?1995年6月,陈小平做完前两名艾滋病人一年半,后6位艾滋病人6个月的随访后,告诉海姆立克——
“说老实话,云南的这6位病人的生活方式十分复杂,当我在5月27号看他们的时候,两位病人,病例4和病例5在监狱里面,所以没有能给他们照相和称重,仅仅取了血样。只有一例病人,病例7,他的状况是非常好的,完全戒了毒,其他人都通过静脉注射再次吸海洛因了。”
在云南的6位病人随访1年之后,陈小平报告“另外6名的背景非常复杂,病例7的CD4细胞数量降低很多(低于200),全血细胞减少,怀疑患有结核,但村子没有X射线来确诊,在那样的地方做研究是有困难的”。过了一个月,云南的艾滋病例6于1996年7月5日死亡,死因不详。
4
不过也是在这一困顿时刻,陈小平终于等来了出国访学的机会。一项更大的艾滋疟疗计划也随之展开。
资助他的是来自UCLA免疫与疾病研究中心的主任约翰·法赫。1996年8月在温哥华举办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法赫见到了海姆立克。之后,法赫邀请海姆立克到UCLA,具体敲定了双方的合作。法赫也有一个国际艾滋病合作项目,资助环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艾滋研究和人员培训,借此陈小平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1997年3月,当陈小平来到UCLA,法赫不仅督导他的学习,而且帮助分析他从广州带来的第一批次8名艾滋病人的血样。不料,法赫发现了不少问题。在陈小平结束访学回到广州之后,法赫写信告知海姆立克——
“由于无法确定大多数患者治疗有关的样品的获取时间,我们在解释方面遇到了难题。希望您有更准确的数据。陈小平在逗留期间,在不同时间,给的信息都不一样。患者4003和4004可能是最清楚的……其他患者存在的问题是,不知道第一个值是处理前还是在疟疾治疗期间或之后不久获得。这些一手数据确定性的缺乏(它们只代表疾病,还是疾病加上疟疾疗法,还是疾病加上一些其他感染),对于后续数值的解释造成了困难。”
即使过了很久,法赫对陈小平的第一批样本与疟疾治疗的关系仍持保留意见,乃至于法赫在帮忙修改相关文章时,提出“没有必要将我包括在作者中,致谢就够了”。
同时,在UCLA期间三方筹划的下一轮的艾滋疟疗遭到中断。原因还是资金的纠纷,只不过,这一次陈小平代表的广州方语气较为严厉——
“肖医生说,你并没有为癌症患者多付了钱,还欠我们1000美元。他说,这1000美元我们不要了,但我们必须收回你欠我们的艾滋病项目的6000美元。请记住,我们总共治疗了8名艾滋患者,不是你信里提到的7名。事实上,我们治疗了9名艾滋病患者;你还记得第9例患了复杂的黄疸,我们在治疗结束前终止了疟疗,然后我们再次做了Western Blot,结果为阴性?但我带了他的血样到UCLA进行进一步测试,结果显示为阳性,但我们把这个病人去掉了。”(见1997年8月陈小平给海姆立克的邮件。)
需要解释的是,9名艾滋患者是头2名艾滋患者加后来从云南找的7名艾滋患者。这7名患者在1994年7、8月间在广州接受了疟血接种,陈小平随即发现,病例9几个检测指标都是阴性,但却接种了血疟,他怀疑是瑞丽健康防疫站的误诊,他还问海姆立克,是不是可以作为阴性对照放到组里,海姆立克没有同意。但讽刺的是,当陈小平带着这名病人的血样到UCLA检验后,却发现结果为阳性。至于海姆立克认为的7名,也可能是不算随访期间死去的病例6。
陈小平显然已经对海姆立克只让自己干活,不给钱的行径失去了耐心,他口气强硬地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一次临床实验,这完全取决于你,我的朋友”。
此时,海姆立克也正忙着向一些基金会筹款,只不过这一次更加急切。
“当接下来的10名患者接受治疗并且效果良好时,我们已经谈到治疗100名艾滋病患者并为此预算了150万美元。我们的工作很成功,我们不能拖延。我们不应该等待进一步的结果,那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我们也不需要等到我们能够筹集完全部150万美元的费用。相反,我们现在就开始筹集资金,并且每筹措1万,就治疗一名艾滋病患者。”1997年8月27日,海姆立克在给长期支持他的一个私人基金会的信里写道。
对于新一轮广州的10名艾滋病人的选择与方案设计,法赫也加入了进来,他亲赴广州,参观查验陈小平所在的卫生防疫站。法赫建议陈小平,在整个研究中应包括至少2名不吸毒的艾滋患者,因为现在大部分患者是药物滥用者。他还提醒,“重要的是,在疟原虫疗法之前、期间和之后,你要有一个系列评估方案,评估还包括对其他疾病,如肺结核、肝炎或其他感染。每次一定要保存大量血浆,因为你需要它来进行病毒载量测试和其他研究。”
一个月后,陈小平称找到了20个艾滋患者,其中3个是性传播,其余为吸毒传播。
陆续地,20个艾滋病人接受了疟疗,同时,法赫要求陈小平每4-6个月给UCLA寄病人血清。
不过之后三方的合作由于遭遇资金短缺的老问题,出现了裂隙。先是法赫停止了试剂供应,接着陈小平向海姆立克“追债”,比如他认为在法赫停止供应试剂后,海姆立克研究所理应支付的84000美元只支付了14000美元。
陈小平还说,第二轮艾滋疟疗项目遭遇资金困难时,他们努力说服中国政府资助这项研究,最后从几个部门得到了资助,结果是虽然“该项目已经完成,但也导致了主要资助来源,由海姆立克研究所变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和其他机构。”
同时,一桩新的争议浮出水面,陈小平开始和海姆立克来回争辩,究竟谁首先提出用疟疾治疗艾滋病的。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争论显得无聊而乏味。
2003年,熟悉非洲情况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Mary Beth Nierengarten指出:疟疾致病最糟糕的正是艾滋病毒最泛滥的地区[3]。2005年美国西雅图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与非洲研究人员合作发表论文,通过研究非洲几百人得出结果,患有疟疾的艾滋病人,其艾滋病毒的含量高于没有疟疾的艾滋病人,说明疟疾不仅不会预防或治疗艾滋病,而可以加重艾滋病[4]。2006年,美国科学家在《科学》发表论文,指出非洲有4千万人感染艾滋病、逾五亿感染疟疾(逾百万因疟疾而死亡),而它们两者之间有相当的地域重叠:艾滋病加重疟疾,疟疾也加重艾滋病[5]。
也许,那时的陈小平认为,疟疗艾滋首创者还是值得争一争的,但事实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他是在塞恩奇1990年5月时了解到了这一想法,之后他不过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首次做了人体实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John Fahey曾被调查在中国的疟疾治疗艾滋病研实验的角色。图片来源:ucla.edu
2003年4月,UCLA在经过调查后发表声明称,参与这项实验的法赫未事先得到UCLA的批准,违反了联邦法律以及UCLA的关于人类受试者研究的保护政策[6,7,8]。不过,法赫之后仍然继续在UCLA工作,并一直到2008年退休。2014年,89岁的法赫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城去世。
而当年一手执行疟疗人体实验的陈小平,在十几年后又如法炮制了当年的人体项目,而且发表公开演讲,大规模招募病人,引发了国人激烈争论。
对于陈小平在1990年代疟疾疗法应用于癌症患者和HIV/艾滋患者,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评论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有了对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但由于当时对国内涉及人的受试者的研究的尚无具体要求,故该委员会主要是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审查,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如果陈小平当时的临床实验由美国私人基金资助,可能也就同时规避了美国伦理审查要求的的监管。”翟晓梅说。
她同时指出,即使是在当时,很多国际SCI期刊发表论文,已经需要出示伦理审查的批件。因此,如果陈的关于疟疾治疗癌症患者、HIV/艾滋患者实验的相关论文发表在高水平的期刊,也会因为伦理审查批准文件的缺失而遇到困难,“但我国对出版的伦理学审查文件的要求是较晚提出的”。
陈小平关于疟疾疗法治疗癌症、HIV/艾滋病患者的部分论文列表
2007年,卫生部印发《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这才有了关于规范生物医学研究行为、对医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的法规[9]。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发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进一步细化伦理审查、知情同意内容和规程等。
如果说,陈小平在1990年代因为我国的法制不健全而“幸运”地钻了空子,那么在相关伦理审查法规非常全面的今天,他又是如何启动新一轮的人体实验的呢?
陈小平最新的疟疗人体实验进展如何?各专家学者如何看待?请关注《知识分子》后续报道。
魏宇心、杨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疟疾疗法治疗晚期肿瘤的初步报告
2. DONALD G. MCNEIL JR., Malarial Treatment for Chinese AIDS Patients Prompts Inquiry in U. S., March 4,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04/health/malarial-treatment-for-chinese-aids-patients-prompts-inquiry-in-us.html
3. Nierengarten MB(2003) Malariotherapy to treat HIV patients?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3:321.
4. Kublin JG, Patnaik P, Jere CS, Miller WC, Hoffman IF, Chimbiya N, Pendame R, Taylor TE, MolyneuxME (2005) Effect of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on concentration of HIV-1-RNA in the blood of adults in rural Malawi: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365:233-240.
5. Abu-Raddad L, Patnaik P, Kublin JG (2006). Dual infection with HIV and malaria fuels the spread of both disea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Science 314:1603-1606.
6.http://dailybruin.com/2003/04/15/ucla-ties-doctor-to-lab-miscon/
7. http://dailybruin.com/2013/05/06/son-of-henry-heimlich-questions-ucla-researchers-involvement-in-his-fathers-controversial-malariotherapy-study/
8.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4-10-30/news/mn-56686_1_heimlich-maneuver
9.http://www.moh.gov.cn/qjjys/s3581/200804/b9f1bfee4ab344ec892e68097296e2a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