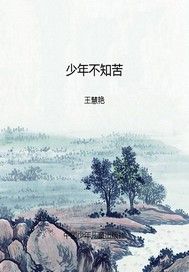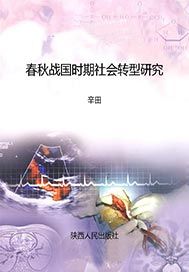12、初现转机
向天歌把一份当天的《海江晚报》贴在会议室的白板上,上面登了一个通版的河滨小区开盘的广告,设计得很空灵,绝大部分是留白,只在中线偏右的地方开了一大扇窗,大海深沉地倚窗而立,一个女模特扮作他的太太,端着一只咖啡杯,偎在大海肩头,文案写得也有味道:眼前是大海,才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版面的右下角是一行小字——广告发布代理:莱奥美广告公司。
向天歌用一支红笔在大海的脸、广告语和“莱奥美广告”几个字上画了圆圈,静了片刻,他说:“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个信号,莱奥美倚仗晚报的背景,眼下的势头咄咄逼人,和我们的竞争不仅公开化,而且白热化,我们刚用影星江河给雄牌矿泉水做了代言,他们跟着就用歌星大海,这说明两家的理念和路数是趋同的,也说明我们的存在已经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而且,从宁可犯撞车大忌这点看,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想在声势上压倒我们。其实对于受众来说,理念是很虚的东西,他不懂,也用不着懂,一个创意,他看了,觉得美、觉得新、觉得好玩,甚至觉得腻味,可能就记住了。莱奥美给了我一个启发,干广告的不存在战线长短、强项弱项问题,首要的是订单,有了项目,才是报社地位和影响力的标志,不要担心干不了,我们干不了的,还可以转包,批出去不但赚钱还能赚人情。现在回头看看咱们,房地产和汽车是我们致命的软肋,虽然近来楼市低迷,但它们仍是目前投入最大的两宗项目,而我们只是散打,缺少像爱天使那样的具有绝对打击力和控制力的品牌,也缺少那样的垄断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中心,怎么杀入房地产和汽车界?”
沈唱举手示意:“向总,您不是反复强调以活动带广告吗?今年是奥运年,亮点多,卖点也多,我想了一个系列活动,不知能不能把地产和汽车行业嫁接进去?”
艾小毛也列席了这个会。作为特立独行的女人,她很欣赏沈唱的锋芒,这样的职场新贵由于身材惹眼,相貌出众,才华横溢,博得领导天然好感的同时,也给同事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失落。
沈唱接着说:“2001年7月13日,不是在莫斯科宣布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吗?我想今年我们就主打奥运牌,做足莫斯科的文章,北京奥运会的大排序是第29届,咱就挑选29名市民组成奥运足迹寻访团,再找29个企业负责人组成奥运经济考察团,再找29个中学生组成奥运天使励志团,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个百人团了,一个人收一万的话,就是87万,另外,还可以选择一个汽车品牌,组成个车队,选在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从北京出发,7月13日开到莫斯科,然后把车体广告卖给地产商做并列冠名,各位老师,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
向天歌越听越灵感迸发,连声称好,沈唱也受了鼓舞:“艾老师的美文给了我许多启发,莱奥美不是请大海做楼盘的代言人吗,咱们为什么不逆向思维,把大海请到服装节的开幕式上唱主题曲?大海的着装在一线歌星里是最有个性的,他又是海江人,不一定有多难吧?”
向天歌在记事本上写了几组大大的字:大海,服装节,莫斯科,观摩团,冠名权,运营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创意,活动历时半年,跨度和声势有了,效益应该非常可观。
向天歌觉得现在的自己快成社会活动家了,整天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纠缠得动弹不得。哪一件不管似乎都不合适,艾小毛曾经提醒过他,小心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向天歌一回到办公室,就看见文书留给他的字条:给朱老师回电话。向天歌纳闷,什么时候冒出个朱老师,就按照纸上的号码拨过去。对方问:“是向天歌吗?我是朱光晨朱老师呀。”向天歌一听,才想起原来是他的大学老师,因为主讲训诂学,枯燥得很,向天歌常常逃他的课,印象比较淡,但老师就是老师,他忙说:“朱老师呀,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学生先给您请个安。不瞒您说,刚一说朱老师,还真没想到是您,怎么,有事吗?”朱光晨长叹一声:“天歌,我是看到海江日报‘编读往来’版上刊登你的杰出员工事迹才知道你的近况的,老师遇到点烦心事,拿不准注意,你在社会上闯荡多年,比我的见识广得多,如果你能抽出空来,最好见个面,这个事情不是电话里能说得清的。”
向天歌看看表,五点刚过,就说:“朱老师,您在家等我吧,我这就过去接您,咱们找个地方吃个饭。”
朱光晨在门口的一家饭馆定了个小雅间,夫妇俩和向天歌依次坐下,没有寒暄,朱光晨就讲起了他的心事。朱师母从市七中退休后,和一直是同事的年轻时的闺中密友合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朱光晨被推到法人代表的位置上,主外,朱师母负责师资和生源,主内。由于教学质量高,学生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国办重点中学。但是从去年寒假开始,市教委发了文件,说民办学校必须实行校舍、财务、师资三独立,这些正是我们的软肋,前提条件不具备,就不能招生,慌不择路之下,经人搭桥认识了天明学校。
朱师母给向天歌夹了口菜,说:“光晨,你别光顾说了,和天歌这么多年不见,多喝两杯。”向天歌说:“没事,这故事好像刚开始,等朱老师讲完了再喝。”
朱光晨叹了口气,喝了口酒,说:“天歌,这几年和经营打上交道,心思可不像教你们时那么单纯了。我的体会是没有害人之心的人,也没有防人之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去防。我现在遇到这些搞不懂的事情就去问我的学生,在人际关系上,我以前的学生现在都是我的老师。你们的师母可笑到什么地步,给人家送礼,自己却像做贼一样,头低得快碰着了膝盖,要不就把脸扭在一边,连看都不敢看人家一眼,好像做了多么亏心的事。哎,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干嘛非要去蹚经营的浑水,也真难为人了,我们现在是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协调各方面关系上,真正用在办学上的心思倒很可怜。”向天歌说:“朱老师,很多道理,我们也是碰了墙之后疼出来的。上学时,别看总逃您的课,可是我们受您的影响还是挺深的,记得您说过讲解道理的人永远总结不出道理,当时不太明白,后来工作了,慢慢琢磨出里面的含义,因为讲解道理的人只会遵守,不会创造。可也有您的好多观点,我们拿去和现实比对,很多都吻合不上了。也许,这就叫时过境迁吧,一个时代,咱不说得那么大,一段时间,总得有个衡量成功的标准吧,您说,现在,除了钱,还有什么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哪一个成功的人是穷困潦倒的?我告诉您,没钱的人不一定都没能耐,但有钱的人一定都有能耐,不管是哪方面的能耐,这就是真理,而且,适度的拜金并不代表着社会的倒退。”朱光晨边听边点头:“说的是呀,原来我们想得太幼稚了,谁知道这连教育圈里也有这么多的道道。”
向天歌插了一句:“干经营是很缠人的,哪路神仙伺候不好都会带来麻烦。我还不是和您一样,天天周旋在那些大鬼小鬼之间。做上广告以后,您就体会去吧,一个阶段有一种感觉,现在我把能赚着钱的人概括成三种,一种是有大背景的,一种是高智商的,还有一种是特别能受累的。但是不管哪一种,都得先有防人之心。”朱光晨十分感慨:“我和你师母如今是骑虎难下,连后悔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实,做个教书匠不是挺好吗,这一下海,根本不知深浅,弄得不人不鬼的。做生意,谁管你是个文人呢?”向天歌说:“是呀,我最不爱听的称呼就是儒商,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不明不白的词?商人就是商人,没有这个商和那个商的区别,在商言商,能挣钱就是好商,就是能力和实力的象征,打不开局面时,市场也不可能念及您是文人就放您一马。还有啊,朱老师,您知道为什么买的没有卖的精吗?因为卖的知道底牌,只有知道底牌才能自如地操控局面,而买的则不同,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特别是在货比三家之前,更是被动,每一条信息都是卖方传递过来的,是便宜还是当只能凭自己感觉,您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神仙也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您吃亏是吃在了您一直在算计学问,而人家一直在算计人。”
朱光晨的情绪很低落,说:“是呀,当时双方谈妥,我们这边儿出任法人、副董事长,天明学校那边儿是董事长和校长,然后各自拿出50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口头协议上。我们想反正马上就是一家人了,花谁的钱不一样,一张支票,50万拨过去了,因为校舍在人家手里,所以装修、进设备,我们看到的只是实物和发票,对里面的偷手一无所知,但是对方最后一共才投入了3万多块钱,而且打着去教育局办批文的幌子把财务章、校名章、法人章都拿到他们手里,我虽然是法人,可是花一分自己的钱,却要看人家的脸色,他不给我盖这个章,我还就没有一点办法,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都觉得可笑,说天底下哪里有上级告下级的道理,双方不是对等的主体,根本就不够立案的条件,你们是民办校,法人的权力至高无上,他是你的办公室主任,扣着章不给,你完全可以解雇他呀,还用得着跑法院来劳神?天歌,你说说,这不是千古奇冤吗?也好,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以前我太傻了,一板一眼地抓教学质量,抠学生分数,你看看别的民办校,就是一门心思抓钱,至于分数,反正都是自己老师判卷,想撩多少就撩多少,最后,给家长这么一交代,皆大欢喜。”向天歌不解地问:“可是不还有市里、区里的会考吗,这样做,不是很容易穿帮吗?掩耳盗铃岂能长久?”朱光晨说:“咳,你哪知道,一行有一行的黑幕,来私立校的学生基础都不太好,家长们又能说什么?就像那些卖癌症药的,吃完症状缓解算他的功劳,吃了不见效那是你这病本来就该死,哪里还用负什么责任!”
向天歌心说,对呀,考试有枪手,论文能买卖,真是一行有一行的黑幕,一行有一行的腐败,看着朱老师两鬓泛出的白发,他感到一种寒彻心底的悲哀,以前的文人雅士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生活没有断炊之虞,但是都在追求质量,就又恨不能将五斗糙米都变成香米,人的欲望真是没有止境的。他端起杯,说:“朱老师,学生敬您一杯,一是感谢栽培之恩,二是有什么需要学生出力的尽管吩咐。您先别着急,咱们慢慢想办法。”朱光晨说:“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你在报社,认识的人多,我是不想再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如果能够调和,还是想调和一下,何必两败俱伤呢,实在不行,再考虑一刀两断,彻底分家,看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让他们明白,你有人但是没理,我有理但不一定就没人!”
向天歌在脑子里搜索着有可能帮上这个忙的名字,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马自达,但是马上就否定了,宣传部是个务虚的地方,和教委的关系不会很紧密,再说,一个堂堂的副部长,去过问一所私立校的纠纷,不是牛刀杀鸡吗,最后,还是决定找绳子仁,反正同学之间,用不着太多的客套,况且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下面多少要买些面子。
向天歌把想法和朱光晨说了,朱老师觉得可行,就起身出去了,向天歌知道他是去结帐,也没说什么。这时,朱师母对向天歌说:“为什么我和你朱老师这把子年纪还舍不得离开学校,真不是图那几个钱,实在是喜欢那些孩子。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笑话。初一有一篇课外辅导读物,写的是天安门,老师拿出一张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挥手检阅的照片,问:‘同学们,你们看,这是谁呀?’学生们有的说是毛主席,有的说是毛爷爷,老师很满意,心想孩子们还真不简单,还认识毛主席,就又问,哪位同学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干什么呢?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毛主席打‘的’哪!”向天歌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没想到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难怪,那个时代的事情离这些孩子太远了,将过去的背景放在现实的放大镜下一照,变成什么形状是无法预料的。正笑着,朱光晨推门进来,说:“天歌,你怎么能把账结了呢?老师难道还请不起你一顿饭?”向天歌忙说:“朱老师,您误会了,就当今天这顿饭是我的谢师宴吧。等给您办成了事,您再请我。”
谢真真下午告诉向天歌今晚将留宿娘家,在报社吃过晚饭,他回到家,沐浴更衣后,将财务总监给他出的本月报表铺在写字台上。看着那一行行的数字,他顿觉无比温暖。接手海江都市报八个月来,这是最扬眉吐气的一个月,除去人员工资、印刷费、办公费等所有支出,还有15万元的利润。这可是里程碑似的15万啊,简安祥时代,海江都市报之所以表面繁荣,是因为每月拖欠印务中心巨额印刷费,将其挂在集团账上。向天歌希望这张报表作为转折点,掀开“海都”真正走上自我造血的良性发展一页。
躺在床上,向天歌又想到了孩子。看着同事们一家三口同来同往,他的脸上写满羡慕,就连他们抱怨孩子调皮的表情在向天歌看来都是幸福的。孩子是大人奋斗的动力源泉,是弥补大人一生遗憾的唯一机会,更是天伦之乐的甜蜜载体,可是,谢真真对这一切都是排斥的,和向天歌结婚十四年,她并未觉得膝下冷清,反而十分受用这种没有拖累的生活。
向天歌的思绪从孩子又转向了艾小毛。和她的几次深谈,让向天歌反而找不到准星。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有了这么一种强烈的渴望,把艾小毛的身份由知己变成伴侣。但是无论他把这个过程设计得多么巧妙,把未来的结局安排得多么周全,只要一往前推理,就会感觉大前提的根基是空虚的,无风自晃,稍一质疑,就摇摇欲坠。
向天歌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时过境迁。人这一辈子,到山说山色,到水看水景,没有办法把它们捆在一起,要求一成不变。攀高枝的人,无论男女,人生的结局都不会以喜剧收场。女人还好说,反正是相夫教子,有了一个深厚的靠山,不但娘家挣足了面子,孩子加大了保险系数,自己也省下许多打拼的精力;男人可不一样,不仅时刻背着“他是靠老丈人起来”的包袱,还要长久保持感恩戴德的心态,稍有不恭,忘恩负义的指责就跟来了。男人不怕辛苦,就怕心里窝囊。向天歌从来不否认谢真真一家在他起步时的帮衬作用,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他又觉得当年谢真真锁定自己,也是一种投资,把他当作一只潜力股,按照长线的路数一点点做起来的。这样算来,其实谁也不欠谁的,我得了实惠,你有了希望,而且,对于显赫的家庭,希望是远远重于实惠的,因为自家的孩子无法完成维持显赫的使命,就要通过婚姻吸引外资,把原本不相干的一根木料雕琢成支柱,立在家族最重要的地方。
向天歌有些举棋不定,心里的两个自己又开始争执起来。一个抱着怀疑的态度提问,婚内婚外的艾小毛万一判若两人怎么办?一个信誓旦旦地回答,没有尝试,凭什么断定艾小毛就不是做好妻子的材料?
向天歌最担心的,就是他和绳子仁提到过的离婚成本,另外还有如果谢真真不肯善罢甘休怎么收场?僵持起来,对向天歌肯定不利,一旦影响了未来的正常发展,感情就成了无本之木,甚至艾小毛还会不会在这里落脚都是疑问。向天歌不停地创意,又不停地动摇,最后想起不知谁说的一句话:要想打败强大的对手,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先犯错误。可是谢真真除去逛街,就是泡在娘家,没有什么交往,既不用操持家务,也不想在仕途上有太大的发展,基本上算是无欲无求,向天歌很发愁,凭他这段日子的公关经验看,人的破绽都是在欲望附近找到的,像谢真真这样的人,一时还真的无从下手。
转天下午的例会刚开完,回敬轩就打来电话说,全年预算和报纸整体运作方案已经改了两稿,李彩妮提出来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议一议。向天歌一下就想到“大帝豪”夜总会,觉得那里是块福地,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运气。
向天歌带上叶子凡、艾小毛和沈唱,到了服务台,领班说回先生订的还是每次要的巴黎厅。向天歌猛然想起来回敬轩让他帮着找个外经贸方面的专家,赶紧拿出手机,搜索着有用的线索。沈唱在旁边说:“向总,我算是服了,什么事都要找人,我在广告部干了两年,实际上干的就是天天找人的活,生孩子得找人,有病了得找人,扣个车得找人,上个学得找人,只要找了人,该罚的可以减,该办的可以免,该急的可以缓,像变戏法一样,全在嘴唇一碰了,有时想一想真觉得烦,真没意思”。向天歌说:“怎么办,这就是道,老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现在是风气氛围之谓道,你不合拍就会被无情地甩掉,再烦也得办,不然就寸步难行”。艾小毛说:“在这里干一年,等于你十年寒窗的总和,就像是速成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啊!”向天歌说:“你们知道人是怎么老的吗?就是在这一句一句的感慨中老下去的,要不为什么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呢?”
正说着,回敬轩和李彩妮、李彩强都到了。坐下后,向天歌说:“为了省点时间,我就私自做主了,小毛安排的菜,她定了个补脑、补心、补血的三补菜单,给几位老总加点能量。”
话音未落,一道十全滋补火锅已经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里面浓浓地烩了一锅的料子,除了针蘑、枸杞、桂圆、生姜这些常规的作料,大部分红红绿绿的都叫不上名字。
向天歌招呼着下箸,想起刚才找人的话题,他借题发挥地说:“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放进滚烫的锅里,它马上就跳了出去,可是如果把它放进只有十几度的水里,它就会静静地呆在那儿,直到水温慢慢升高,最后烫死在锅里。这和送礼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下子太猛了,可能把人吓回去,如果一点点洇着,对方就会不知不觉地陷进你的套子里。”
李彩妮和李彩强啧啧称赞:“文人就是文人,眼光和一般人都是不一样的。看问题一下子就看进火锅里去。”一句话,说得满桌大笑。
这时,回敬轩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向天歌接过一看,是一张海江电台广告部的发布合同,内容是海江都市报的形象宣传,上面写着:广告单价4万元,加急费5千元,扣除优惠2千元,扣除代理费2千元,播出次数20次,总计4万1千元。
向天歌不屑地一笑,对回敬轩说:“老回呀,给你这个单子的人是欺负你外行,你看看这价码,是广播要了电视的价。”回敬轩问:“那实价大概是多少?”向天歌说:“顶多一半,找找人,还能少。”
李彩妮要过去扫了一眼,说:“向总,你能不能也尽快搞出一个新的广告刊例来,要实在一点的,以前‘海都’的刊例水分太大,弄得像小店里卖的皮鞋似的,标价680,最后30块钱就能拿走。我看整版定在6万差不多,报眼和一版可以贵一点,10厘米通栏或者20厘米半通栏之类的就可以压下价来,另外一些热门消费品,像房子、车子、机子等可以考虑买一赠一,软稿消化到时尚、通讯这些版里边去,回总,你看怎么样?”
回敬轩说:“我看可以,只是运转一段时间,如果广告效果不理想,要防止代理公司杀价回本,这一点,最好在代理协议上有所体现,价钱一乱,市场就散了,报纸的名声也就跟着臭了。另外,是不是补充一个广告刊登须知,保留预收款和内容删改等权利,外地有的报纸出事,还就是出在了广告上。”
向天歌抖着一张薄薄的海江市广告承揽合同说:“回总说得极是,价格一定砸死,不能朝令夕改,要有一段稳定期,最好是公开的,全部透明的,分好几个梯队,业务员几个点,主任几个点,老总几个点,心明眼亮,对内对外都是个监督,客户的钱也花得明白。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在海江市的传媒界会一炮走红,无形中,我们会树立起一个品牌,海江都市报,是一张在广告上拒绝暗箱操作的报纸。”
李彩妮边听边点头,她说:“做了这么多年服装,我想媒体和服装的道理差不多,面料是次要的,关键在款式。面料是共享资源,你弄得到,我也弄得到,只有款式才是个性的,才有可能谋得附加值。所以,包装很重要,包括对营销方式的包装,我看向总的想法可以再细化一下,现在,零售业不是常常亮出成本价销售的大旗吗,咱们不妨就做媒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七个人议着,都觉得轮廓渐渐明朗,信心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看李彩妮兴致很高,向天歌又想起了存了许久的一桩心事。尽管李彩强早已揭开谜底,但他一直想让李彩妮亲口证实。忍了忍,向天歌问李彩妮:“李总,有个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迷,我们第一次谈裁剪生活、设计自我大赛时,你说有一个广告公司的报价比我低了一大截,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彩妮想了想,说:“噢,有一个叫靳克晓的,拿着市工商联副主委的条子,让我们参加海江夏日广场时装秀,我就说正在谈着类似的活动,可能资金周转不开,结果,那个靳克晓就反复强调活跃市民夏季生活是市里边主要领导的意思和他们最合适的价位,我不好拂主委的面子,但是又舍不得你们的创意,就想两全其美,压下点价钱,给靳克晓甩过去一点。”向天歌终于验证了原来的猜测,但是仍然好奇:“那后来呢?”李彩妮说:“后来不知为什么,靳克晓给我打电话,说活动取消了。”向天歌说:“再后来,李总可能就不知道了,靳克晓取消活动可不是主动退出,而是给公安局七处打了招呼,说咱们准备采用的氢气球不符合防火要求。”李彩妮有些吃惊:“我是后来才听说你们之间的过节的,至于吗?靳克晓放着生意不好好做,这么编排你们干什么?”向天歌说:“嫉妒。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这时,果盘端上来了,舞曲也跟着响起来。向天歌欠欠身,朝李彩妮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李总,赏光跳一曲吧。”李彩妮翩翩离座:“怕跳不好,靠你带了。以后,别总李总李总的,多生分,直接叫我彩妮吧。”向天歌第一次与李彩妮这种距离站在一起,她的腰肢算不上纤细,但是很匀称,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很结实。
向天歌不喜欢跳舞,他觉得那是刻板之人做的事情,但是三步、四步的基本功还是过硬的,在舞场上完全可以应付自如。旋转时,李彩妮不够轻盈,有两次差点踩到向天歌的脚,她歉意地笑着:“你看我,平时走路习惯一路小跑,这么一板一眼的还真不适应。”
一曲终了,向天歌和李彩妮回到座位,他打趣道:“原来跳舞最累的是胳膊,名义上是搂着舞伴,实际上只是个摆设,心里有把尺子,时刻都要检测和腰之间的距离与松紧度的。”李彩妮笑着说:“什么话一到你嘴里,交响乐也能变成快板书。”
向天歌的胃口越来越大,喷绘、印刷、网络,凡是广告能够辐射到的,都想染指。向天歌清楚记得大学时的现代汉语老师专门讲过“染指”、“觊觎”两个贬义词经常被人错用为褒义,但向天歌并不觉得“染指”有何不妥,做广告广泛撒网无可厚非,即便没有赚到钱,将指头染上点失败的颜色,对今后的选择也是个提醒。
向天歌把自己这大半年走过的路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从做工程到做项目再到做概念,这是三个不同层面的阶梯。玩概念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圈别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越是大多数人懵懂的时候就越是少部分人赚钱的时候,等人们差不多都明白了,商机也就找不到了。
这时,向天歌和沈唱,李彩强和艾小毛也跳了一曲,回敬轩一个劲地喊头晕,就坐到了后面的沙发上,艾小毛和李彩强一起跟过去,嚷嚷着让他看手相。向天歌听着他们说得热闹,也凑过去,对回敬轩说:“老回,我才听说,你还是看相的高手,今天也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几个人围过来一同起哄,要回敬轩真人露相,现场解读向天歌。
回敬轩喝点酒就变成了人来疯,一点也不推辞,他拉过向天歌的手,看着上面的纹路,说:“从五行上看,你是属于水盛的,水盛则财旺,是个干生意的好材料,但是另一方面,你的阴气过重,阳性不足,那么意味着你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很难再突破了,必须要有外力来激活你的魄力。”向天歌说:“老回,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回敬轩说:“你非让说,就当玩笑话说的,我只是平时喜欢看些周易之类的书,看过之后,就自己琢磨琢磨,完全是些皮毛。找机会我带你去正式算一卦,城北有一个瞎子李,很灵的,特别是看财运和桃花运。”向天歌说:“我不大信这个的。”回敬轩说:“这种事,宁信其有,瞎子李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便你的流年不利,他也是有破解办法的。找他的人,好多都是比咱们有钱有背景的。你记住了,越往高处走,不可预测的因素越多,人嘛,每到闯荡了一段时间,就应该梳理一下,找个明白人点拨一下,该停的就要毫不犹豫地停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时站一会儿,是为了后面走得更快。今天给你透个底,你提出来和彩妮合作前,我就去问了一卦,瞎子李告诉我,近日将有贵人相助,说我的后半生将从女人处得财,但是必须由一个男人穿针引线,所以你那几句话一出口,我就信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瞎子李的托儿呢!”几句话,说得向天歌有些动心,要是果真神算,倒是个人物了。一个人总是遇见好事的时候,就离霉运不远了,这是规律,也是概率。向天歌对此深信不疑。生活优裕的人和有能力疏通关节的人是最迷信的,因为他们还有可能改变现状,真正潦倒到底的人反倒不期待什么奇迹发生。这么多年,他还真没有正经地算过自己的命运,以前他总觉得如果一切尽在掌握,那么人生将少了许多悬念,也自然少了许多乐趣和刺激。可是有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很多事情都陷入胶着状态,择不清,扯不断,理不出个头绪,倒不妨找个先生算一算,哪怕不准呢,也算给些事情找个借口。向天歌想起了他在定福庵拿到的《叹世万空歌》条幅,但是那上面毕竟灰暗了些,只有叹没有解,生生把心境搅乱了,却于事无补,因为太阳要照常升起,烦了的、腻了的、恨了的生活都要往下过,没有对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艾小毛改过的版本又明显带着安慰色彩,没有因果规律在里面,更像是励志的吉利话。想到这些,向天歌答应:“行,找个时间,我开车,咱们跑一趟。”
向天歌用一支红笔在大海的脸、广告语和“莱奥美广告”几个字上画了圆圈,静了片刻,他说:“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个信号,莱奥美倚仗晚报的背景,眼下的势头咄咄逼人,和我们的竞争不仅公开化,而且白热化,我们刚用影星江河给雄牌矿泉水做了代言,他们跟着就用歌星大海,这说明两家的理念和路数是趋同的,也说明我们的存在已经让他们感到了威胁,而且,从宁可犯撞车大忌这点看,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想在声势上压倒我们。其实对于受众来说,理念是很虚的东西,他不懂,也用不着懂,一个创意,他看了,觉得美、觉得新、觉得好玩,甚至觉得腻味,可能就记住了。莱奥美给了我一个启发,干广告的不存在战线长短、强项弱项问题,首要的是订单,有了项目,才是报社地位和影响力的标志,不要担心干不了,我们干不了的,还可以转包,批出去不但赚钱还能赚人情。现在回头看看咱们,房地产和汽车是我们致命的软肋,虽然近来楼市低迷,但它们仍是目前投入最大的两宗项目,而我们只是散打,缺少像爱天使那样的具有绝对打击力和控制力的品牌,也缺少那样的垄断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中心,怎么杀入房地产和汽车界?”
沈唱举手示意:“向总,您不是反复强调以活动带广告吗?今年是奥运年,亮点多,卖点也多,我想了一个系列活动,不知能不能把地产和汽车行业嫁接进去?”
艾小毛也列席了这个会。作为特立独行的女人,她很欣赏沈唱的锋芒,这样的职场新贵由于身材惹眼,相貌出众,才华横溢,博得领导天然好感的同时,也给同事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失落。
沈唱接着说:“2001年7月13日,不是在莫斯科宣布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吗?我想今年我们就主打奥运牌,做足莫斯科的文章,北京奥运会的大排序是第29届,咱就挑选29名市民组成奥运足迹寻访团,再找29个企业负责人组成奥运经济考察团,再找29个中学生组成奥运天使励志团,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个百人团了,一个人收一万的话,就是87万,另外,还可以选择一个汽车品牌,组成个车队,选在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从北京出发,7月13日开到莫斯科,然后把车体广告卖给地产商做并列冠名,各位老师,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
向天歌越听越灵感迸发,连声称好,沈唱也受了鼓舞:“艾老师的美文给了我许多启发,莱奥美不是请大海做楼盘的代言人吗,咱们为什么不逆向思维,把大海请到服装节的开幕式上唱主题曲?大海的着装在一线歌星里是最有个性的,他又是海江人,不一定有多难吧?”
向天歌在记事本上写了几组大大的字:大海,服装节,莫斯科,观摩团,冠名权,运营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创意,活动历时半年,跨度和声势有了,效益应该非常可观。
向天歌觉得现在的自己快成社会活动家了,整天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纠缠得动弹不得。哪一件不管似乎都不合适,艾小毛曾经提醒过他,小心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向天歌一回到办公室,就看见文书留给他的字条:给朱老师回电话。向天歌纳闷,什么时候冒出个朱老师,就按照纸上的号码拨过去。对方问:“是向天歌吗?我是朱光晨朱老师呀。”向天歌一听,才想起原来是他的大学老师,因为主讲训诂学,枯燥得很,向天歌常常逃他的课,印象比较淡,但老师就是老师,他忙说:“朱老师呀,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学生先给您请个安。不瞒您说,刚一说朱老师,还真没想到是您,怎么,有事吗?”朱光晨长叹一声:“天歌,我是看到海江日报‘编读往来’版上刊登你的杰出员工事迹才知道你的近况的,老师遇到点烦心事,拿不准注意,你在社会上闯荡多年,比我的见识广得多,如果你能抽出空来,最好见个面,这个事情不是电话里能说得清的。”
向天歌看看表,五点刚过,就说:“朱老师,您在家等我吧,我这就过去接您,咱们找个地方吃个饭。”
朱光晨在门口的一家饭馆定了个小雅间,夫妇俩和向天歌依次坐下,没有寒暄,朱光晨就讲起了他的心事。朱师母从市七中退休后,和一直是同事的年轻时的闺中密友合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朱光晨被推到法人代表的位置上,主外,朱师母负责师资和生源,主内。由于教学质量高,学生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国办重点中学。但是从去年寒假开始,市教委发了文件,说民办学校必须实行校舍、财务、师资三独立,这些正是我们的软肋,前提条件不具备,就不能招生,慌不择路之下,经人搭桥认识了天明学校。
朱师母给向天歌夹了口菜,说:“光晨,你别光顾说了,和天歌这么多年不见,多喝两杯。”向天歌说:“没事,这故事好像刚开始,等朱老师讲完了再喝。”
朱光晨叹了口气,喝了口酒,说:“天歌,这几年和经营打上交道,心思可不像教你们时那么单纯了。我的体会是没有害人之心的人,也没有防人之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去防。我现在遇到这些搞不懂的事情就去问我的学生,在人际关系上,我以前的学生现在都是我的老师。你们的师母可笑到什么地步,给人家送礼,自己却像做贼一样,头低得快碰着了膝盖,要不就把脸扭在一边,连看都不敢看人家一眼,好像做了多么亏心的事。哎,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干嘛非要去蹚经营的浑水,也真难为人了,我们现在是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协调各方面关系上,真正用在办学上的心思倒很可怜。”向天歌说:“朱老师,很多道理,我们也是碰了墙之后疼出来的。上学时,别看总逃您的课,可是我们受您的影响还是挺深的,记得您说过讲解道理的人永远总结不出道理,当时不太明白,后来工作了,慢慢琢磨出里面的含义,因为讲解道理的人只会遵守,不会创造。可也有您的好多观点,我们拿去和现实比对,很多都吻合不上了。也许,这就叫时过境迁吧,一个时代,咱不说得那么大,一段时间,总得有个衡量成功的标准吧,您说,现在,除了钱,还有什么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哪一个成功的人是穷困潦倒的?我告诉您,没钱的人不一定都没能耐,但有钱的人一定都有能耐,不管是哪方面的能耐,这就是真理,而且,适度的拜金并不代表着社会的倒退。”朱光晨边听边点头:“说的是呀,原来我们想得太幼稚了,谁知道这连教育圈里也有这么多的道道。”
向天歌插了一句:“干经营是很缠人的,哪路神仙伺候不好都会带来麻烦。我还不是和您一样,天天周旋在那些大鬼小鬼之间。做上广告以后,您就体会去吧,一个阶段有一种感觉,现在我把能赚着钱的人概括成三种,一种是有大背景的,一种是高智商的,还有一种是特别能受累的。但是不管哪一种,都得先有防人之心。”朱光晨十分感慨:“我和你师母如今是骑虎难下,连后悔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实,做个教书匠不是挺好吗,这一下海,根本不知深浅,弄得不人不鬼的。做生意,谁管你是个文人呢?”向天歌说:“是呀,我最不爱听的称呼就是儒商,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不明不白的词?商人就是商人,没有这个商和那个商的区别,在商言商,能挣钱就是好商,就是能力和实力的象征,打不开局面时,市场也不可能念及您是文人就放您一马。还有啊,朱老师,您知道为什么买的没有卖的精吗?因为卖的知道底牌,只有知道底牌才能自如地操控局面,而买的则不同,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特别是在货比三家之前,更是被动,每一条信息都是卖方传递过来的,是便宜还是当只能凭自己感觉,您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神仙也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您吃亏是吃在了您一直在算计学问,而人家一直在算计人。”
朱光晨的情绪很低落,说:“是呀,当时双方谈妥,我们这边儿出任法人、副董事长,天明学校那边儿是董事长和校长,然后各自拿出50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口头协议上。我们想反正马上就是一家人了,花谁的钱不一样,一张支票,50万拨过去了,因为校舍在人家手里,所以装修、进设备,我们看到的只是实物和发票,对里面的偷手一无所知,但是对方最后一共才投入了3万多块钱,而且打着去教育局办批文的幌子把财务章、校名章、法人章都拿到他们手里,我虽然是法人,可是花一分自己的钱,却要看人家的脸色,他不给我盖这个章,我还就没有一点办法,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都觉得可笑,说天底下哪里有上级告下级的道理,双方不是对等的主体,根本就不够立案的条件,你们是民办校,法人的权力至高无上,他是你的办公室主任,扣着章不给,你完全可以解雇他呀,还用得着跑法院来劳神?天歌,你说说,这不是千古奇冤吗?也好,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以前我太傻了,一板一眼地抓教学质量,抠学生分数,你看看别的民办校,就是一门心思抓钱,至于分数,反正都是自己老师判卷,想撩多少就撩多少,最后,给家长这么一交代,皆大欢喜。”向天歌不解地问:“可是不还有市里、区里的会考吗,这样做,不是很容易穿帮吗?掩耳盗铃岂能长久?”朱光晨说:“咳,你哪知道,一行有一行的黑幕,来私立校的学生基础都不太好,家长们又能说什么?就像那些卖癌症药的,吃完症状缓解算他的功劳,吃了不见效那是你这病本来就该死,哪里还用负什么责任!”
向天歌心说,对呀,考试有枪手,论文能买卖,真是一行有一行的黑幕,一行有一行的腐败,看着朱老师两鬓泛出的白发,他感到一种寒彻心底的悲哀,以前的文人雅士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生活没有断炊之虞,但是都在追求质量,就又恨不能将五斗糙米都变成香米,人的欲望真是没有止境的。他端起杯,说:“朱老师,学生敬您一杯,一是感谢栽培之恩,二是有什么需要学生出力的尽管吩咐。您先别着急,咱们慢慢想办法。”朱光晨说:“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你在报社,认识的人多,我是不想再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如果能够调和,还是想调和一下,何必两败俱伤呢,实在不行,再考虑一刀两断,彻底分家,看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让他们明白,你有人但是没理,我有理但不一定就没人!”
向天歌在脑子里搜索着有可能帮上这个忙的名字,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马自达,但是马上就否定了,宣传部是个务虚的地方,和教委的关系不会很紧密,再说,一个堂堂的副部长,去过问一所私立校的纠纷,不是牛刀杀鸡吗,最后,还是决定找绳子仁,反正同学之间,用不着太多的客套,况且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下面多少要买些面子。
向天歌把想法和朱光晨说了,朱老师觉得可行,就起身出去了,向天歌知道他是去结帐,也没说什么。这时,朱师母对向天歌说:“为什么我和你朱老师这把子年纪还舍不得离开学校,真不是图那几个钱,实在是喜欢那些孩子。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笑话。初一有一篇课外辅导读物,写的是天安门,老师拿出一张毛主席当年在天安门挥手检阅的照片,问:‘同学们,你们看,这是谁呀?’学生们有的说是毛主席,有的说是毛爷爷,老师很满意,心想孩子们还真不简单,还认识毛主席,就又问,哪位同学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干什么呢?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毛主席打‘的’哪!”向天歌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没想到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难怪,那个时代的事情离这些孩子太远了,将过去的背景放在现实的放大镜下一照,变成什么形状是无法预料的。正笑着,朱光晨推门进来,说:“天歌,你怎么能把账结了呢?老师难道还请不起你一顿饭?”向天歌忙说:“朱老师,您误会了,就当今天这顿饭是我的谢师宴吧。等给您办成了事,您再请我。”
谢真真下午告诉向天歌今晚将留宿娘家,在报社吃过晚饭,他回到家,沐浴更衣后,将财务总监给他出的本月报表铺在写字台上。看着那一行行的数字,他顿觉无比温暖。接手海江都市报八个月来,这是最扬眉吐气的一个月,除去人员工资、印刷费、办公费等所有支出,还有15万元的利润。这可是里程碑似的15万啊,简安祥时代,海江都市报之所以表面繁荣,是因为每月拖欠印务中心巨额印刷费,将其挂在集团账上。向天歌希望这张报表作为转折点,掀开“海都”真正走上自我造血的良性发展一页。
躺在床上,向天歌又想到了孩子。看着同事们一家三口同来同往,他的脸上写满羡慕,就连他们抱怨孩子调皮的表情在向天歌看来都是幸福的。孩子是大人奋斗的动力源泉,是弥补大人一生遗憾的唯一机会,更是天伦之乐的甜蜜载体,可是,谢真真对这一切都是排斥的,和向天歌结婚十四年,她并未觉得膝下冷清,反而十分受用这种没有拖累的生活。
向天歌的思绪从孩子又转向了艾小毛。和她的几次深谈,让向天歌反而找不到准星。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有了这么一种强烈的渴望,把艾小毛的身份由知己变成伴侣。但是无论他把这个过程设计得多么巧妙,把未来的结局安排得多么周全,只要一往前推理,就会感觉大前提的根基是空虚的,无风自晃,稍一质疑,就摇摇欲坠。
向天歌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时过境迁。人这一辈子,到山说山色,到水看水景,没有办法把它们捆在一起,要求一成不变。攀高枝的人,无论男女,人生的结局都不会以喜剧收场。女人还好说,反正是相夫教子,有了一个深厚的靠山,不但娘家挣足了面子,孩子加大了保险系数,自己也省下许多打拼的精力;男人可不一样,不仅时刻背着“他是靠老丈人起来”的包袱,还要长久保持感恩戴德的心态,稍有不恭,忘恩负义的指责就跟来了。男人不怕辛苦,就怕心里窝囊。向天歌从来不否认谢真真一家在他起步时的帮衬作用,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他又觉得当年谢真真锁定自己,也是一种投资,把他当作一只潜力股,按照长线的路数一点点做起来的。这样算来,其实谁也不欠谁的,我得了实惠,你有了希望,而且,对于显赫的家庭,希望是远远重于实惠的,因为自家的孩子无法完成维持显赫的使命,就要通过婚姻吸引外资,把原本不相干的一根木料雕琢成支柱,立在家族最重要的地方。
向天歌有些举棋不定,心里的两个自己又开始争执起来。一个抱着怀疑的态度提问,婚内婚外的艾小毛万一判若两人怎么办?一个信誓旦旦地回答,没有尝试,凭什么断定艾小毛就不是做好妻子的材料?
向天歌最担心的,就是他和绳子仁提到过的离婚成本,另外还有如果谢真真不肯善罢甘休怎么收场?僵持起来,对向天歌肯定不利,一旦影响了未来的正常发展,感情就成了无本之木,甚至艾小毛还会不会在这里落脚都是疑问。向天歌不停地创意,又不停地动摇,最后想起不知谁说的一句话:要想打败强大的对手,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先犯错误。可是谢真真除去逛街,就是泡在娘家,没有什么交往,既不用操持家务,也不想在仕途上有太大的发展,基本上算是无欲无求,向天歌很发愁,凭他这段日子的公关经验看,人的破绽都是在欲望附近找到的,像谢真真这样的人,一时还真的无从下手。
转天下午的例会刚开完,回敬轩就打来电话说,全年预算和报纸整体运作方案已经改了两稿,李彩妮提出来找个好地方聚一聚、议一议。向天歌一下就想到“大帝豪”夜总会,觉得那里是块福地,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运气。
向天歌带上叶子凡、艾小毛和沈唱,到了服务台,领班说回先生订的还是每次要的巴黎厅。向天歌猛然想起来回敬轩让他帮着找个外经贸方面的专家,赶紧拿出手机,搜索着有用的线索。沈唱在旁边说:“向总,我算是服了,什么事都要找人,我在广告部干了两年,实际上干的就是天天找人的活,生孩子得找人,有病了得找人,扣个车得找人,上个学得找人,只要找了人,该罚的可以减,该办的可以免,该急的可以缓,像变戏法一样,全在嘴唇一碰了,有时想一想真觉得烦,真没意思”。向天歌说:“怎么办,这就是道,老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现在是风气氛围之谓道,你不合拍就会被无情地甩掉,再烦也得办,不然就寸步难行”。艾小毛说:“在这里干一年,等于你十年寒窗的总和,就像是速成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啊!”向天歌说:“你们知道人是怎么老的吗?就是在这一句一句的感慨中老下去的,要不为什么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呢?”
正说着,回敬轩和李彩妮、李彩强都到了。坐下后,向天歌说:“为了省点时间,我就私自做主了,小毛安排的菜,她定了个补脑、补心、补血的三补菜单,给几位老总加点能量。”
话音未落,一道十全滋补火锅已经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里面浓浓地烩了一锅的料子,除了针蘑、枸杞、桂圆、生姜这些常规的作料,大部分红红绿绿的都叫不上名字。
向天歌招呼着下箸,想起刚才找人的话题,他借题发挥地说:“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放进滚烫的锅里,它马上就跳了出去,可是如果把它放进只有十几度的水里,它就会静静地呆在那儿,直到水温慢慢升高,最后烫死在锅里。这和送礼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下子太猛了,可能把人吓回去,如果一点点洇着,对方就会不知不觉地陷进你的套子里。”
李彩妮和李彩强啧啧称赞:“文人就是文人,眼光和一般人都是不一样的。看问题一下子就看进火锅里去。”一句话,说得满桌大笑。
这时,回敬轩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向天歌接过一看,是一张海江电台广告部的发布合同,内容是海江都市报的形象宣传,上面写着:广告单价4万元,加急费5千元,扣除优惠2千元,扣除代理费2千元,播出次数20次,总计4万1千元。
向天歌不屑地一笑,对回敬轩说:“老回呀,给你这个单子的人是欺负你外行,你看看这价码,是广播要了电视的价。”回敬轩问:“那实价大概是多少?”向天歌说:“顶多一半,找找人,还能少。”
李彩妮要过去扫了一眼,说:“向总,你能不能也尽快搞出一个新的广告刊例来,要实在一点的,以前‘海都’的刊例水分太大,弄得像小店里卖的皮鞋似的,标价680,最后30块钱就能拿走。我看整版定在6万差不多,报眼和一版可以贵一点,10厘米通栏或者20厘米半通栏之类的就可以压下价来,另外一些热门消费品,像房子、车子、机子等可以考虑买一赠一,软稿消化到时尚、通讯这些版里边去,回总,你看怎么样?”
回敬轩说:“我看可以,只是运转一段时间,如果广告效果不理想,要防止代理公司杀价回本,这一点,最好在代理协议上有所体现,价钱一乱,市场就散了,报纸的名声也就跟着臭了。另外,是不是补充一个广告刊登须知,保留预收款和内容删改等权利,外地有的报纸出事,还就是出在了广告上。”
向天歌抖着一张薄薄的海江市广告承揽合同说:“回总说得极是,价格一定砸死,不能朝令夕改,要有一段稳定期,最好是公开的,全部透明的,分好几个梯队,业务员几个点,主任几个点,老总几个点,心明眼亮,对内对外都是个监督,客户的钱也花得明白。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在海江市的传媒界会一炮走红,无形中,我们会树立起一个品牌,海江都市报,是一张在广告上拒绝暗箱操作的报纸。”
李彩妮边听边点头,她说:“做了这么多年服装,我想媒体和服装的道理差不多,面料是次要的,关键在款式。面料是共享资源,你弄得到,我也弄得到,只有款式才是个性的,才有可能谋得附加值。所以,包装很重要,包括对营销方式的包装,我看向总的想法可以再细化一下,现在,零售业不是常常亮出成本价销售的大旗吗,咱们不妨就做媒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七个人议着,都觉得轮廓渐渐明朗,信心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看李彩妮兴致很高,向天歌又想起了存了许久的一桩心事。尽管李彩强早已揭开谜底,但他一直想让李彩妮亲口证实。忍了忍,向天歌问李彩妮:“李总,有个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迷,我们第一次谈裁剪生活、设计自我大赛时,你说有一个广告公司的报价比我低了一大截,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彩妮想了想,说:“噢,有一个叫靳克晓的,拿着市工商联副主委的条子,让我们参加海江夏日广场时装秀,我就说正在谈着类似的活动,可能资金周转不开,结果,那个靳克晓就反复强调活跃市民夏季生活是市里边主要领导的意思和他们最合适的价位,我不好拂主委的面子,但是又舍不得你们的创意,就想两全其美,压下点价钱,给靳克晓甩过去一点。”向天歌终于验证了原来的猜测,但是仍然好奇:“那后来呢?”李彩妮说:“后来不知为什么,靳克晓给我打电话,说活动取消了。”向天歌说:“再后来,李总可能就不知道了,靳克晓取消活动可不是主动退出,而是给公安局七处打了招呼,说咱们准备采用的氢气球不符合防火要求。”李彩妮有些吃惊:“我是后来才听说你们之间的过节的,至于吗?靳克晓放着生意不好好做,这么编排你们干什么?”向天歌说:“嫉妒。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这时,果盘端上来了,舞曲也跟着响起来。向天歌欠欠身,朝李彩妮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李总,赏光跳一曲吧。”李彩妮翩翩离座:“怕跳不好,靠你带了。以后,别总李总李总的,多生分,直接叫我彩妮吧。”向天歌第一次与李彩妮这种距离站在一起,她的腰肢算不上纤细,但是很匀称,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很结实。
向天歌不喜欢跳舞,他觉得那是刻板之人做的事情,但是三步、四步的基本功还是过硬的,在舞场上完全可以应付自如。旋转时,李彩妮不够轻盈,有两次差点踩到向天歌的脚,她歉意地笑着:“你看我,平时走路习惯一路小跑,这么一板一眼的还真不适应。”
一曲终了,向天歌和李彩妮回到座位,他打趣道:“原来跳舞最累的是胳膊,名义上是搂着舞伴,实际上只是个摆设,心里有把尺子,时刻都要检测和腰之间的距离与松紧度的。”李彩妮笑着说:“什么话一到你嘴里,交响乐也能变成快板书。”
向天歌的胃口越来越大,喷绘、印刷、网络,凡是广告能够辐射到的,都想染指。向天歌清楚记得大学时的现代汉语老师专门讲过“染指”、“觊觎”两个贬义词经常被人错用为褒义,但向天歌并不觉得“染指”有何不妥,做广告广泛撒网无可厚非,即便没有赚到钱,将指头染上点失败的颜色,对今后的选择也是个提醒。
向天歌把自己这大半年走过的路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从做工程到做项目再到做概念,这是三个不同层面的阶梯。玩概念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圈别人的钱来办自己的事,越是大多数人懵懂的时候就越是少部分人赚钱的时候,等人们差不多都明白了,商机也就找不到了。
这时,向天歌和沈唱,李彩强和艾小毛也跳了一曲,回敬轩一个劲地喊头晕,就坐到了后面的沙发上,艾小毛和李彩强一起跟过去,嚷嚷着让他看手相。向天歌听着他们说得热闹,也凑过去,对回敬轩说:“老回,我才听说,你还是看相的高手,今天也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几个人围过来一同起哄,要回敬轩真人露相,现场解读向天歌。
回敬轩喝点酒就变成了人来疯,一点也不推辞,他拉过向天歌的手,看着上面的纹路,说:“从五行上看,你是属于水盛的,水盛则财旺,是个干生意的好材料,但是另一方面,你的阴气过重,阳性不足,那么意味着你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很难再突破了,必须要有外力来激活你的魄力。”向天歌说:“老回,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回敬轩说:“你非让说,就当玩笑话说的,我只是平时喜欢看些周易之类的书,看过之后,就自己琢磨琢磨,完全是些皮毛。找机会我带你去正式算一卦,城北有一个瞎子李,很灵的,特别是看财运和桃花运。”向天歌说:“我不大信这个的。”回敬轩说:“这种事,宁信其有,瞎子李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便你的流年不利,他也是有破解办法的。找他的人,好多都是比咱们有钱有背景的。你记住了,越往高处走,不可预测的因素越多,人嘛,每到闯荡了一段时间,就应该梳理一下,找个明白人点拨一下,该停的就要毫不犹豫地停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时站一会儿,是为了后面走得更快。今天给你透个底,你提出来和彩妮合作前,我就去问了一卦,瞎子李告诉我,近日将有贵人相助,说我的后半生将从女人处得财,但是必须由一个男人穿针引线,所以你那几句话一出口,我就信了,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瞎子李的托儿呢!”几句话,说得向天歌有些动心,要是果真神算,倒是个人物了。一个人总是遇见好事的时候,就离霉运不远了,这是规律,也是概率。向天歌对此深信不疑。生活优裕的人和有能力疏通关节的人是最迷信的,因为他们还有可能改变现状,真正潦倒到底的人反倒不期待什么奇迹发生。这么多年,他还真没有正经地算过自己的命运,以前他总觉得如果一切尽在掌握,那么人生将少了许多悬念,也自然少了许多乐趣和刺激。可是有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很多事情都陷入胶着状态,择不清,扯不断,理不出个头绪,倒不妨找个先生算一算,哪怕不准呢,也算给些事情找个借口。向天歌想起了他在定福庵拿到的《叹世万空歌》条幅,但是那上面毕竟灰暗了些,只有叹没有解,生生把心境搅乱了,却于事无补,因为太阳要照常升起,烦了的、腻了的、恨了的生活都要往下过,没有对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艾小毛改过的版本又明显带着安慰色彩,没有因果规律在里面,更像是励志的吉利话。想到这些,向天歌答应:“行,找个时间,我开车,咱们跑一趟。”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