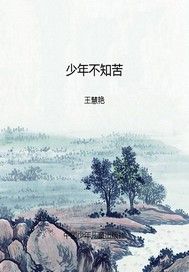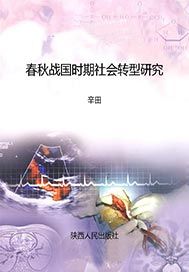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悦读MOOK(第四卷)
> 寻访鲁迅东瀛足迹
寻访鲁迅东瀛足迹
◎ 吴中杰
因为研究鲁迅的关系,早就想到日本去寻访鲁迅早年留学时生活过的地方,并和日本学者交流研究心得,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内子高云到日本东京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想去探亲兼访学,日方邀请手续都办好了,但严绍宗副校长找我谈,说校方的意思是,叫我不要去探亲,以后派我出去讲学。我接受这一安排,只好暂时不去。但到得中文系准备派我出国讲学时,学校的领导班子已经换届,新任校长杨福家教授把我从出国讲学的名单中拉了下来,说是超过五十五岁的人都不能公派出国讲学——其时我已经有五十七岁。前任校长华中一教授、前任常务副校长强连庆教授,都还记得过去的许诺,他们主动对新校长说,吴中杰的情况有点特殊,应该让他去讲学,但杨福家校长坚持不肯,说现在要按照他的规矩办,前任校长们也没有办法。不过此后超过五十五岁的教师出国讲学者却不乏其人,而杨福家教授与我同年,也仍穿梭于世界各地,仆仆风尘,这当然又另作别论了。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当然不再有公派讲学的机会,但如自费出国旅游,倒是不受限制了。我和高云虽然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腿脚尚健,于是决定东行,以了我多年心愿。先是想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不但自己不必操心签证及住行问题,而且经费上也比较合算,但没有一家旅行社的游程表上是有鲁迅遗迹参观项目的。这也难怪,一般游客,要看的是樱花、古迹、商场,谁会对百年前的什么学院、医专感兴趣呢?我想参加旅游团,游罢一般景点后再自行寻访鲁迅遗迹,但中国大陆的旅游团都要“团进团出”,不能自由行动的,于是只好另想办法。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指导过一名日本进修教师——信州大学的松冈俊裕,他看我没有公派赴日的机会,曾提出由他个人出钱邀请我到日本去看看,我没有接受。这次我提出请他发函邀请,我自费赴日,他也同意,这事很快就办成了。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工作,她们到日本无需签证,听说我们要到日本旅游,就全家过来陪我们一起去玩。只是她们休假时间不长,游过一般的景点,就先走了,我和高云则留下来再寻访鲁迅的足迹。好在旅日的复旦学子甚多,我们随处都能得到照顾。
我先前的博士生张岩冰恰好在东京国学院大学做交流学者,她为我们安排了住处,并陪同参观。但她只不过比我们早两个星期到东京,带我们看博物馆、美术馆还可以,但对一百年前的鲁迅旧址却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徐鹏兄的研究生孙猛,要他带路。他在早稻田大学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也算是老东京了。孙猛与我也是老朋友,非常热情,但这位王大隆先生的再传弟子,是专治版本目录学的,谈起黑口白口、宋版明版来,当然非常熟悉,而对于鲁迅的旧迹,也很茫然。为了不负我所托,他就到处打听,却又到处碰壁。最后,一位吴先生(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吴朗西先生的公子)给了他一个藤井省三教授的电话,说只有去问问他了,但又说,藤井现在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名的教授,非常之忙,一般人都不见了,怕未必会理会你这等事。孙猛打电话时也很惴惴,但藤井却非常客气,说是一九七九年他在复旦进修时,曾听过我的课,我到东京他非常高兴,只是他马上要到美国开会,不能陪我寻访,但要请我次日去吃午饭。
于是我和高云、孙猛、张岩冰一行四人,遂于第二日(四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到了东京大学藤井研究室。那天是星期六,他还在工作,正与一位青年人谈话,大概是他的研究生罢。我们进去后,他把青年人打发走,与我叙起旧来。他说,我大概不会记得他了,因为听课的人多,老师不可能认得那么多人,而讲课的老师只有一个,所以他是记得我的。他领我们到一家日本餐馆吃生鱼片寿司,老板见是藤井教授带来的客人,很是客气,亲自操作,我们看着他做,他做一道,我们吃一道,老板还送一道特别的菜,表示对中国教授的欢迎。
此次赴日旅游,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即是全民对于教师的尊重。其实我们过去也是尊师重教的,后来多次政治运动都把知识分子当做靶子,还动员学生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尊师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现在要恢复起来,恐怕还需一些时日。
关于鲁迅在东京住过和学习过的地方,周作人原有一些介绍,当然,他说的是当时的情况。藤井送我一份鲁迅之会的会报,是“鲁迅在东京”的特集,则对这些地方的现状也有所调查。从鲁迅一九○二年四月到日本之初暂住的三桥旅馆,到他读书的弘文学院,以及从仙台回东京后的几处住所:伏见馆、中越馆、伍舍、一轩屋,还有听章太炎讲课的民报社,都有专文加以介绍。但鲁迅于一九○九年离开日本之后,东京经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地震和四十年代的战时轰炸,后来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早已面目全非,旧屋荡然了。但我想,伍舍原是夏目漱石故居,日本人对夏目很重视,保存了他的许多旧物,此屋或许也会保留罢。孙猛说,听说夏目的旧物都原样拆迁到一个地方去了。藤井却说,伍舍也早已拆除了。这使我很失望。但既然到了东京,总得找一处鲁迅活动的遗址来凭吊一下罢。告别藤井之后,我们决定去寻访弘文学院旧址,心想这个学校在当时很有名,周围的老人或者还有所闻吧。
弘文学院原址在牛■区西轩町三十四番地。这地方离早稻田大学不太远,孙猛说他可以找到。但到达西轩町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三十四番地了。问店家,问住户,问居民委员会主任,问警署,都说不知道。看看路边的街道图,顶多只有十三番地。与当地人谈及弘文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倒是有很多人知道,但所知的不是教育家的嘉纳,而是体育家的嘉纳——因为嘉纳第一个创办了日本柔道馆,对体育事业有贡献,所以喜爱柔道的日本老百姓都还记得他,至于他办学的成绩,却早为人所忘却。我们想,既然现在西轩町最多只有十三番地,那么当初的三十四番地一定也在这最后一番地了,就对着这一片高楼大厦大拍其照,事后孙猛再到警局查询,得知原三十四番地果然并入现在的十三番地了。但说实话,我们在这里什么遗迹也没有看到。
离开西轩町之后,就到神田去逛书店。这也是鲁迅常去的地方。许寿裳记他们当年购书的情况道:“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种“苦的经验”,不但当事人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就是我辈后学者读到此处,也很神往。神田真是一条繁荣的文化街,看过去满眼都是书店,远比上海福州路为多。但要寻找鲁迅的遗迹,也已不可能了。我们走进内山书店,这还与鲁迅有些关系,虽然已是后期住在上海的事了。这家书店是内山完造在战后回日本时所开,先后搬了三次家,才搬到这里。现在是完造弟弟的三子内山篱主持。店里主要卖中国书籍,还设有鲁迅专柜,内有鲁迅本人的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品种颇多。
走出内山书店,已是满街灯火。我们只好结束这一天的寻访。
如果说,在东京已经很难找到鲁迅的遗迹,那么,仙台的鲁迅遗迹就保存得较多、较好了。
四月二十五日,我和高云到仙台,东北大学的荣誉教授阿部兼也先生带了两位“鲁迅医学笔记研究组”成员日下女士和■野小姐到车站来迎接。十多年前,阿部教授到复旦演讲时,我参加过接待工作,曾有一面之交,这次,在日本跟他进修过的华东师大吴俊教授将我要到日本寻访鲁迅遗迹的事告诉他,他一口承诺为我安排仙台的旅程。阿部先生比我小一岁,也已进入古稀之年,我只希望他能为我找好住处,再提供一张路线图就可以了,不料他竟全程陪同。
当天下午,他就陪我们将仙台的鲁迅纪念地和纪念物参观遍。先是看东北大学校园内的鲁迅雕像,再参观东北大学校史室,那里有鲁迅专柜,陈列着鲁迅入学志愿书和学业履历书之类的文物,然后去看当年鲁迅听课的梯形教室,这间教室是特地为纪念鲁迅而保存的,平时关闭着,有人参观时才打开。阿部教授事先约好管理员来开门,才得以进入。但教室外面有一条很宽敞的曲尺形木条走廊,不像是原物,阿部教授告诉我,这是江泽民来参观时,特别为他建造的,而且教室的位置也移动了一下,他举手指一指说,原来是在那边的,为了集中保存一些旧屋,就原样移到这边来了。进入教室一看,觉得同复旦的梯形教室也没有什么不同。阿部教授说,鲁迅常坐在第三排听课,叫我坐在这个位置拍张照。过一会,他在后排忽然有了新发现,我过去一看,原来课桌上画有斧头镰刀,还有一些革命口号。阿部考证说,这不会是鲁迅同学写的,那时候还没有十月革命,一定是后来的学生写的。
出了梯形教室,他又带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在一间藏书室里,我们看到了两尊雕像:鲁迅和藤野严九郎。阿部说,这个鲁迅像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送的,藤野像是他的故乡福井县送的,现在正在设计基座,准备放在图书馆门口。
当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是与第二高等学校放在一起的,前几年二高校友聚会,出资修整老校门,却把医专的校牌去掉了,只挂了第二高等学校的校牌。但旧校门却保存下来,使我们得以见到当时的样子。
出了旧校门,向北走不远的路,就到了鲁迅在仙台的第一个住处:佐藤屋。这老屋虽然破旧,但却保存完整,而且还有人住着。我们按门铃,想进去到楼上看看鲁迅当年的居室,但无人应声,大概主人上班去了。阿部转身带我们到旁边一家公司的三楼阳台上,那里可以俯瞰佐藤屋,而且还可以看到对面的监狱原址。就是因为佐藤屋老板兼办对面监狱囚人的饭食,仙台医专的老师认为鲁迅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使他只好搬家。现在,监狱早已不存在,那里已是一家什么工厂了。从佐藤屋朝反方向走,在医专校门南边不远处,有鲁迅在仙台的第二个住处:宫川宅,也是一所老屋,仍无法进去,我们在屋外拍了几张照片就驱车到仙台市博物馆附近去看鲁迅纪念碑了。
鲁迅纪念碑的照片我看到过多次,现在到了现场,别有一番感受。碑后是一片树林,衬托得纪念碑更显肃穆。旁边又多了一尊鲁迅塑像,是中国绍兴鲁迅纪念馆所赠,表现出鲁迅不屈的性格。阿部教授对我说,鲁迅纪念碑的建造是在一九六○年,原初想放在东北大学校园里,但文部省不同意,而仙台市却愿意接受,所以就建在这里了。那一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的呼声很高,文部省不愿意纪念鲁迅。
在日本,纪念鲁迅已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所以有时会和政治斗争搅在一起。我想,现在东北大学图书馆要在入口处摆出鲁迅和藤野的大塑像,是否也表明文部省的新态度呢?
第二天,阿部教授穿了一身和服,仍请■野小姐开车,一起陪我们游松岛。这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离仙台不远,据说鲁迅当年也曾来过。但谁也搞不清他游览过哪些地方,感受如何?我们就拣风景佳丽处走了一圈,有些还是外人不大走得到的地方。当时正是仙台樱花盛开的时候,连老树枯枝都开满了繁花,我对它的生命力感到惊奇。阿部先生说:我也是老树了,我也还要开花。我和高云都说:我们都是老树了,我们都要学它一样,开出繁花来。
归途中,阿部带我们到一家温泉去洗澡。他说,仙台的温泉是有名的,你们体验一下吧。不过现在的澡堂与鲁迅时代已不一样了。据许寿裳说,当时仙台浴堂的构造,男女之分,只隔一道矮的木壁,故鲁迅曾有神来之笔,道:“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现在的浴室,则男女完全分隔,即使有阳狂的同学,也无从窥视了。但是否还有男女同浴的温泉,我就不知道了,我所说的,只是阿部带我去的那一家。在这之前,我们到金泽时,李庆老弟带我们去洗的那家温泉,也是男女分隔的。
回到仙台市内,东北大学鲁迅研究会的五六位同仁,已聚候在一家中国餐厅里,等待我们入席了。他们点了中国菜,叫了绍兴酒,说是用鲁迅的家乡菜招待我们。酒确是绍兴老酒,菜却是东北菜、广东菜、浙江菜都有,不但并无绍兴风味,而且已不是纯正的中国菜了。不过心意可嘉,我们仍很领情。席间,阿部教授将我送他的一套盒装的《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集》出示,大家都对这部书的装帧非常赞赏,大村泉教授要我回到上海后,寄赠给东北大学鲁迅研究会一部,我当场答应了。
过了一会,他忽然提问道:“在你的评点本里,《藤野先生》是放在散文里,还是放在小说里?”
我说:“鲁迅自己将它收在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我当然也把它放在散文里。”
大村忽然激动起来,连珠炮似的,发了一大通议论,弄得翻译佐藤由美小姐一时语塞,急得不知怎样翻才好。这位佐藤小姐是东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的研究生,曾到复旦大学留学一年,汉语水平不低,刚才我们在车上还聊得很好,现在是被大村的气势和语速吓住了,阿部先生只好自己出马来翻译,但也没有全译,只说大村先生认为《藤野先生》是小说,他的观点在网上受到中国学者围攻,所以很不高兴。
我对大家说:“大村先生的论文,发表在去年出版的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鲁迅:跨文化对话》中,我到日本之前已经看到过,所以对他的论点有所了解。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中有些细节与事实不符,有些人物和事件没有写上去,所以不能算是散文,应该归入小说一类。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散文虽是记实的文体,但也不可能每件事每句话都按照原样有闻必录,它必然有所选择、有所概括,其中突出某些人、某些事,而将另一些人事略而不写,是正常的。鲁迅说,《朝花夕拾》中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那就是说,它是记实的,不是虚构的;但又说,‘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可能会有记忆上的错误。另外有些小改动,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比如,‘鲁迅’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但在《朝花夕拾》中却记载着早就有人叫他‘鲁迅’了,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时,‘鲁迅’已成为他的通用名,也是这篇文章的署名,为了避免在散文中作繁琐的注释而作的小改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算是不实的虚构。”
但大村泉教授仍坚持他的观点道:“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课程,鲁迅明明没有考及格,他为什么说自己的成绩是六十分以上呢?”
这个问题没有等我开口发言,阿部教授就抢着回答了。他拿起书来先读鲁迅的原文:“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接着说:“鲁迅是批评当时有些日本青年的偏见,并没有正面说自己哪一门课的成绩是多少。”
大村教授没有接阿部的话茬,仍按照他的思路说:“我希望吴教授能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新成果,在以后的文章中改变观点。”
我说:“我很重视仙台朋友的新研究成果,但新成果并不一定能改变老观点。我没有上网看有关的争论文章,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我只能说:对新观点进行围攻我是不赞成的,但提出新观点者也不能要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都跟着他走,这样也太霸道了。我是赞成各种观点平等地进行讨论、争鸣的。”
我的解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因为大村教授很固执自己的意见,在散席时,他还拿出一本名为《新文化》读物的修订本,翻出目录给我看,说这是日本高中教科书,每年有几十万读者,《藤野先生》一文就收在小说栏里。当然,我也不为所动,我的理由是:学术讨论是不能由某种教科书来下结论的。
鲁迅研究会的同仁们都微笑着看我们争论,不想介入。他们送我两本有关鲁迅的书,并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为纪念。一是中文版的《鲁迅与仙台》,一是日文版的《藤野先生与鲁迅》。而大村教授也很热情地提出,要我参加今年十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与藤野塑像揭幕仪式,说是他也要去参加。我说,这种揭幕仪式一般是所在单位的成员和其他官员参加的,我是一名退休教授,不可能跑到北京去参加。他的执拗劲又上来了,说:我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是好朋友,我一定要他们邀请你参加!我也只好说:如果他们邀请,我就去参加。我们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和高云离开仙台,直奔神户而去,准备再游历几个地方,然后从关西机场乘机回国。阿部教授自己开车将我们送到车站,而且还买了站台票一直送上火车,帮我们安顿好行李,并送了两个柑子,说这是原生态的,没有污染,然后依依惜别而去。■
因为研究鲁迅的关系,早就想到日本去寻访鲁迅早年留学时生活过的地方,并和日本学者交流研究心得,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内子高云到日本东京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想去探亲兼访学,日方邀请手续都办好了,但严绍宗副校长找我谈,说校方的意思是,叫我不要去探亲,以后派我出去讲学。我接受这一安排,只好暂时不去。但到得中文系准备派我出国讲学时,学校的领导班子已经换届,新任校长杨福家教授把我从出国讲学的名单中拉了下来,说是超过五十五岁的人都不能公派出国讲学——其时我已经有五十七岁。前任校长华中一教授、前任常务副校长强连庆教授,都还记得过去的许诺,他们主动对新校长说,吴中杰的情况有点特殊,应该让他去讲学,但杨福家校长坚持不肯,说现在要按照他的规矩办,前任校长们也没有办法。不过此后超过五十五岁的教师出国讲学者却不乏其人,而杨福家教授与我同年,也仍穿梭于世界各地,仆仆风尘,这当然又另作别论了。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当然不再有公派讲学的机会,但如自费出国旅游,倒是不受限制了。我和高云虽然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腿脚尚健,于是决定东行,以了我多年心愿。先是想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不但自己不必操心签证及住行问题,而且经费上也比较合算,但没有一家旅行社的游程表上是有鲁迅遗迹参观项目的。这也难怪,一般游客,要看的是樱花、古迹、商场,谁会对百年前的什么学院、医专感兴趣呢?我想参加旅游团,游罢一般景点后再自行寻访鲁迅遗迹,但中国大陆的旅游团都要“团进团出”,不能自由行动的,于是只好另想办法。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指导过一名日本进修教师——信州大学的松冈俊裕,他看我没有公派赴日的机会,曾提出由他个人出钱邀请我到日本去看看,我没有接受。这次我提出请他发函邀请,我自费赴日,他也同意,这事很快就办成了。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工作,她们到日本无需签证,听说我们要到日本旅游,就全家过来陪我们一起去玩。只是她们休假时间不长,游过一般的景点,就先走了,我和高云则留下来再寻访鲁迅的足迹。好在旅日的复旦学子甚多,我们随处都能得到照顾。
我先前的博士生张岩冰恰好在东京国学院大学做交流学者,她为我们安排了住处,并陪同参观。但她只不过比我们早两个星期到东京,带我们看博物馆、美术馆还可以,但对一百年前的鲁迅旧址却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徐鹏兄的研究生孙猛,要他带路。他在早稻田大学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也算是老东京了。孙猛与我也是老朋友,非常热情,但这位王大隆先生的再传弟子,是专治版本目录学的,谈起黑口白口、宋版明版来,当然非常熟悉,而对于鲁迅的旧迹,也很茫然。为了不负我所托,他就到处打听,却又到处碰壁。最后,一位吴先生(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吴朗西先生的公子)给了他一个藤井省三教授的电话,说只有去问问他了,但又说,藤井现在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有名的教授,非常之忙,一般人都不见了,怕未必会理会你这等事。孙猛打电话时也很惴惴,但藤井却非常客气,说是一九七九年他在复旦进修时,曾听过我的课,我到东京他非常高兴,只是他马上要到美国开会,不能陪我寻访,但要请我次日去吃午饭。
于是我和高云、孙猛、张岩冰一行四人,遂于第二日(四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到了东京大学藤井研究室。那天是星期六,他还在工作,正与一位青年人谈话,大概是他的研究生罢。我们进去后,他把青年人打发走,与我叙起旧来。他说,我大概不会记得他了,因为听课的人多,老师不可能认得那么多人,而讲课的老师只有一个,所以他是记得我的。他领我们到一家日本餐馆吃生鱼片寿司,老板见是藤井教授带来的客人,很是客气,亲自操作,我们看着他做,他做一道,我们吃一道,老板还送一道特别的菜,表示对中国教授的欢迎。
此次赴日旅游,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即是全民对于教师的尊重。其实我们过去也是尊师重教的,后来多次政治运动都把知识分子当做靶子,还动员学生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尊师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现在要恢复起来,恐怕还需一些时日。
关于鲁迅在东京住过和学习过的地方,周作人原有一些介绍,当然,他说的是当时的情况。藤井送我一份鲁迅之会的会报,是“鲁迅在东京”的特集,则对这些地方的现状也有所调查。从鲁迅一九○二年四月到日本之初暂住的三桥旅馆,到他读书的弘文学院,以及从仙台回东京后的几处住所:伏见馆、中越馆、伍舍、一轩屋,还有听章太炎讲课的民报社,都有专文加以介绍。但鲁迅于一九○九年离开日本之后,东京经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地震和四十年代的战时轰炸,后来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早已面目全非,旧屋荡然了。但我想,伍舍原是夏目漱石故居,日本人对夏目很重视,保存了他的许多旧物,此屋或许也会保留罢。孙猛说,听说夏目的旧物都原样拆迁到一个地方去了。藤井却说,伍舍也早已拆除了。这使我很失望。但既然到了东京,总得找一处鲁迅活动的遗址来凭吊一下罢。告别藤井之后,我们决定去寻访弘文学院旧址,心想这个学校在当时很有名,周围的老人或者还有所闻吧。
弘文学院原址在牛■区西轩町三十四番地。这地方离早稻田大学不太远,孙猛说他可以找到。但到达西轩町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三十四番地了。问店家,问住户,问居民委员会主任,问警署,都说不知道。看看路边的街道图,顶多只有十三番地。与当地人谈及弘文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倒是有很多人知道,但所知的不是教育家的嘉纳,而是体育家的嘉纳——因为嘉纳第一个创办了日本柔道馆,对体育事业有贡献,所以喜爱柔道的日本老百姓都还记得他,至于他办学的成绩,却早为人所忘却。我们想,既然现在西轩町最多只有十三番地,那么当初的三十四番地一定也在这最后一番地了,就对着这一片高楼大厦大拍其照,事后孙猛再到警局查询,得知原三十四番地果然并入现在的十三番地了。但说实话,我们在这里什么遗迹也没有看到。
离开西轩町之后,就到神田去逛书店。这也是鲁迅常去的地方。许寿裳记他们当年购书的情况道:“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种“苦的经验”,不但当事人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就是我辈后学者读到此处,也很神往。神田真是一条繁荣的文化街,看过去满眼都是书店,远比上海福州路为多。但要寻找鲁迅的遗迹,也已不可能了。我们走进内山书店,这还与鲁迅有些关系,虽然已是后期住在上海的事了。这家书店是内山完造在战后回日本时所开,先后搬了三次家,才搬到这里。现在是完造弟弟的三子内山篱主持。店里主要卖中国书籍,还设有鲁迅专柜,内有鲁迅本人的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品种颇多。
走出内山书店,已是满街灯火。我们只好结束这一天的寻访。
如果说,在东京已经很难找到鲁迅的遗迹,那么,仙台的鲁迅遗迹就保存得较多、较好了。
四月二十五日,我和高云到仙台,东北大学的荣誉教授阿部兼也先生带了两位“鲁迅医学笔记研究组”成员日下女士和■野小姐到车站来迎接。十多年前,阿部教授到复旦演讲时,我参加过接待工作,曾有一面之交,这次,在日本跟他进修过的华东师大吴俊教授将我要到日本寻访鲁迅遗迹的事告诉他,他一口承诺为我安排仙台的旅程。阿部先生比我小一岁,也已进入古稀之年,我只希望他能为我找好住处,再提供一张路线图就可以了,不料他竟全程陪同。
当天下午,他就陪我们将仙台的鲁迅纪念地和纪念物参观遍。先是看东北大学校园内的鲁迅雕像,再参观东北大学校史室,那里有鲁迅专柜,陈列着鲁迅入学志愿书和学业履历书之类的文物,然后去看当年鲁迅听课的梯形教室,这间教室是特地为纪念鲁迅而保存的,平时关闭着,有人参观时才打开。阿部教授事先约好管理员来开门,才得以进入。但教室外面有一条很宽敞的曲尺形木条走廊,不像是原物,阿部教授告诉我,这是江泽民来参观时,特别为他建造的,而且教室的位置也移动了一下,他举手指一指说,原来是在那边的,为了集中保存一些旧屋,就原样移到这边来了。进入教室一看,觉得同复旦的梯形教室也没有什么不同。阿部教授说,鲁迅常坐在第三排听课,叫我坐在这个位置拍张照。过一会,他在后排忽然有了新发现,我过去一看,原来课桌上画有斧头镰刀,还有一些革命口号。阿部考证说,这不会是鲁迅同学写的,那时候还没有十月革命,一定是后来的学生写的。
出了梯形教室,他又带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在一间藏书室里,我们看到了两尊雕像:鲁迅和藤野严九郎。阿部说,这个鲁迅像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送的,藤野像是他的故乡福井县送的,现在正在设计基座,准备放在图书馆门口。
当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是与第二高等学校放在一起的,前几年二高校友聚会,出资修整老校门,却把医专的校牌去掉了,只挂了第二高等学校的校牌。但旧校门却保存下来,使我们得以见到当时的样子。
出了旧校门,向北走不远的路,就到了鲁迅在仙台的第一个住处:佐藤屋。这老屋虽然破旧,但却保存完整,而且还有人住着。我们按门铃,想进去到楼上看看鲁迅当年的居室,但无人应声,大概主人上班去了。阿部转身带我们到旁边一家公司的三楼阳台上,那里可以俯瞰佐藤屋,而且还可以看到对面的监狱原址。就是因为佐藤屋老板兼办对面监狱囚人的饭食,仙台医专的老师认为鲁迅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使他只好搬家。现在,监狱早已不存在,那里已是一家什么工厂了。从佐藤屋朝反方向走,在医专校门南边不远处,有鲁迅在仙台的第二个住处:宫川宅,也是一所老屋,仍无法进去,我们在屋外拍了几张照片就驱车到仙台市博物馆附近去看鲁迅纪念碑了。
鲁迅纪念碑的照片我看到过多次,现在到了现场,别有一番感受。碑后是一片树林,衬托得纪念碑更显肃穆。旁边又多了一尊鲁迅塑像,是中国绍兴鲁迅纪念馆所赠,表现出鲁迅不屈的性格。阿部教授对我说,鲁迅纪念碑的建造是在一九六○年,原初想放在东北大学校园里,但文部省不同意,而仙台市却愿意接受,所以就建在这里了。那一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的呼声很高,文部省不愿意纪念鲁迅。
在日本,纪念鲁迅已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所以有时会和政治斗争搅在一起。我想,现在东北大学图书馆要在入口处摆出鲁迅和藤野的大塑像,是否也表明文部省的新态度呢?
第二天,阿部教授穿了一身和服,仍请■野小姐开车,一起陪我们游松岛。这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离仙台不远,据说鲁迅当年也曾来过。但谁也搞不清他游览过哪些地方,感受如何?我们就拣风景佳丽处走了一圈,有些还是外人不大走得到的地方。当时正是仙台樱花盛开的时候,连老树枯枝都开满了繁花,我对它的生命力感到惊奇。阿部先生说:我也是老树了,我也还要开花。我和高云都说:我们都是老树了,我们都要学它一样,开出繁花来。
归途中,阿部带我们到一家温泉去洗澡。他说,仙台的温泉是有名的,你们体验一下吧。不过现在的澡堂与鲁迅时代已不一样了。据许寿裳说,当时仙台浴堂的构造,男女之分,只隔一道矮的木壁,故鲁迅曾有神来之笔,道:“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现在的浴室,则男女完全分隔,即使有阳狂的同学,也无从窥视了。但是否还有男女同浴的温泉,我就不知道了,我所说的,只是阿部带我去的那一家。在这之前,我们到金泽时,李庆老弟带我们去洗的那家温泉,也是男女分隔的。
回到仙台市内,东北大学鲁迅研究会的五六位同仁,已聚候在一家中国餐厅里,等待我们入席了。他们点了中国菜,叫了绍兴酒,说是用鲁迅的家乡菜招待我们。酒确是绍兴老酒,菜却是东北菜、广东菜、浙江菜都有,不但并无绍兴风味,而且已不是纯正的中国菜了。不过心意可嘉,我们仍很领情。席间,阿部教授将我送他的一套盒装的《吴中杰评点鲁迅作品集》出示,大家都对这部书的装帧非常赞赏,大村泉教授要我回到上海后,寄赠给东北大学鲁迅研究会一部,我当场答应了。
过了一会,他忽然提问道:“在你的评点本里,《藤野先生》是放在散文里,还是放在小说里?”
我说:“鲁迅自己将它收在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我当然也把它放在散文里。”
大村忽然激动起来,连珠炮似的,发了一大通议论,弄得翻译佐藤由美小姐一时语塞,急得不知怎样翻才好。这位佐藤小姐是东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的研究生,曾到复旦大学留学一年,汉语水平不低,刚才我们在车上还聊得很好,现在是被大村的气势和语速吓住了,阿部先生只好自己出马来翻译,但也没有全译,只说大村先生认为《藤野先生》是小说,他的观点在网上受到中国学者围攻,所以很不高兴。
我对大家说:“大村先生的论文,发表在去年出版的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鲁迅:跨文化对话》中,我到日本之前已经看到过,所以对他的论点有所了解。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中有些细节与事实不符,有些人物和事件没有写上去,所以不能算是散文,应该归入小说一类。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散文虽是记实的文体,但也不可能每件事每句话都按照原样有闻必录,它必然有所选择、有所概括,其中突出某些人、某些事,而将另一些人事略而不写,是正常的。鲁迅说,《朝花夕拾》中的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那就是说,它是记实的,不是虚构的;但又说,‘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可能会有记忆上的错误。另外有些小改动,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比如,‘鲁迅’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但在《朝花夕拾》中却记载着早就有人叫他‘鲁迅’了,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时,‘鲁迅’已成为他的通用名,也是这篇文章的署名,为了避免在散文中作繁琐的注释而作的小改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算是不实的虚构。”
但大村泉教授仍坚持他的观点道:“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课程,鲁迅明明没有考及格,他为什么说自己的成绩是六十分以上呢?”
这个问题没有等我开口发言,阿部教授就抢着回答了。他拿起书来先读鲁迅的原文:“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接着说:“鲁迅是批评当时有些日本青年的偏见,并没有正面说自己哪一门课的成绩是多少。”
大村教授没有接阿部的话茬,仍按照他的思路说:“我希望吴教授能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新成果,在以后的文章中改变观点。”
我说:“我很重视仙台朋友的新研究成果,但新成果并不一定能改变老观点。我没有上网看有关的争论文章,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我只能说:对新观点进行围攻我是不赞成的,但提出新观点者也不能要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都跟着他走,这样也太霸道了。我是赞成各种观点平等地进行讨论、争鸣的。”
我的解释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因为大村教授很固执自己的意见,在散席时,他还拿出一本名为《新文化》读物的修订本,翻出目录给我看,说这是日本高中教科书,每年有几十万读者,《藤野先生》一文就收在小说栏里。当然,我也不为所动,我的理由是:学术讨论是不能由某种教科书来下结论的。
鲁迅研究会的同仁们都微笑着看我们争论,不想介入。他们送我两本有关鲁迅的书,并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为纪念。一是中文版的《鲁迅与仙台》,一是日文版的《藤野先生与鲁迅》。而大村教授也很热情地提出,要我参加今年十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鲁迅与藤野塑像揭幕仪式,说是他也要去参加。我说,这种揭幕仪式一般是所在单位的成员和其他官员参加的,我是一名退休教授,不可能跑到北京去参加。他的执拗劲又上来了,说:我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是好朋友,我一定要他们邀请你参加!我也只好说:如果他们邀请,我就去参加。我们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和高云离开仙台,直奔神户而去,准备再游历几个地方,然后从关西机场乘机回国。阿部教授自己开车将我们送到车站,而且还买了站台票一直送上火车,帮我们安顿好行李,并送了两个柑子,说这是原生态的,没有污染,然后依依惜别而去。■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