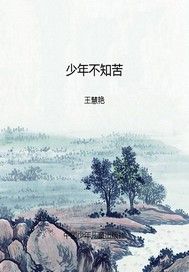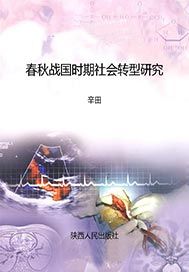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悦读MOOK(第四卷)
> 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之死
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之死
◎ 鲲 西
据《纽约时报》记者Allan Kozinn的专栏报道,当代最著名的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波维奇四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去世,他一度在巴黎治疗,最终还是在祖国的大地上离开人世。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还出席在克里姆林宫特意为他举行的生日庆祝会,并且接受普京总统颁发的最高荣誉奖。
在教堂举行过追思会后,罗斯托波维奇遗体被安葬在Novodevichy墓地,在他的前辈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一侧。稍远处也埋葬着不久前去世的叶利钦总统。罗和普罗菲科耶夫及肖斯塔科维奇严格地说是两代人,但躺在这花岗石墓地下的这三个灵魂,不仅有师生之谊,同时也经受着相同的苦难。
罗斯托波维奇一九二七年出生于阿塞拜疆的巴库一个音乐世家的家里,四岁学钢琴,七岁跟父亲学大提琴,而他的父亲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提琴大师Pablo Casal的受业者。这一幅躺在他父亲大提琴盒子里尚是婴儿的罗,幼稚的心灵,予人以圣洁的感觉。
罗斯托波维奇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确立作为大师的地位,尤其可贵的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两位前辈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他曾跟他们学习作曲法,他们是他的恩师,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反抗专横统治上,他比他的前辈表现得更顽强,走得更前。肖斯塔科维奇不堪斯大林时代对音乐对艺术的专横的指责和禁锢,他转而把一腔悲愤化入他晚期的作品中,尤其是他晚期创作的四重奏中。罗斯托波维奇却表现得更为无所畏惧,以下是典型的一例:他直接给当时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请告诉我是什么给予那些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人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每一个人都应享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不是只能当做应声虫。”《真理报》理所当然地不予发表,但西方的报纸却刊登了。这样,罗在国内的演出时好时坏,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官方取消。到一九七八年他和他妻子的护照终于被吊销,也就是说他被剥夺了苏联的公民权。
罗斯托波维奇终于看到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的独联体也逐渐趋向开放,罗并且和戈尔巴乔夫结上了私人的友谊。在他恢复公民权以后,他做的第一桩事就是率领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前往莫斯科。那是一场在红场举行的露天音乐会,为了让买不起音乐厅门票者享受一次精彩的演出。这一场音乐会听众有十万人之多。作为乐队指挥的罗,连他自己也深深地受感动,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俄罗斯人正需要这样的场合向全世界人证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玷污了不少,但听音乐的此刻告诉人们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毫不虚饰的自豪,一种对于自身民族的完全的自信。读Allan Kozinn这篇报道,至此会对斯拉夫民族上世纪以来在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伟大成就,应有肃然起敬之感。
这里展出的一张照片是柏林墙推倒之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罗斯托波维奇在离墙不远处为群众演奏巴哈的无伴奏组曲,那些不约而来的老少群众记录着这一历史时刻。罗作为成名的音乐大师,他也是这一历史长流中的一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他加上这样的称号——大师和苏维埃时期的异己者。当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受迫害时,是罗斯托波维奇为他提供了庇护所。这就是罗斯托波维奇。他身后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那些他生前演奏的曲集。然而最大的遗产是他的献身精神,为艺术为自由。
罗斯托波维奇家族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在巴库的故居,现在已用罗斯托波维奇父子的名义向外开放,供人瞻仰。■
据《纽约时报》记者Allan Kozinn的专栏报道,当代最著名的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波维奇四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去世,他一度在巴黎治疗,最终还是在祖国的大地上离开人世。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还出席在克里姆林宫特意为他举行的生日庆祝会,并且接受普京总统颁发的最高荣誉奖。
在教堂举行过追思会后,罗斯托波维奇遗体被安葬在Novodevichy墓地,在他的前辈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一侧。稍远处也埋葬着不久前去世的叶利钦总统。罗和普罗菲科耶夫及肖斯塔科维奇严格地说是两代人,但躺在这花岗石墓地下的这三个灵魂,不仅有师生之谊,同时也经受着相同的苦难。
罗斯托波维奇一九二七年出生于阿塞拜疆的巴库一个音乐世家的家里,四岁学钢琴,七岁跟父亲学大提琴,而他的父亲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提琴大师Pablo Casal的受业者。这一幅躺在他父亲大提琴盒子里尚是婴儿的罗,幼稚的心灵,予人以圣洁的感觉。
罗斯托波维奇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确立作为大师的地位,尤其可贵的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两位前辈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他曾跟他们学习作曲法,他们是他的恩师,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反抗专横统治上,他比他的前辈表现得更顽强,走得更前。肖斯塔科维奇不堪斯大林时代对音乐对艺术的专横的指责和禁锢,他转而把一腔悲愤化入他晚期的作品中,尤其是他晚期创作的四重奏中。罗斯托波维奇却表现得更为无所畏惧,以下是典型的一例:他直接给当时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请告诉我是什么给予那些对艺术一无所知的人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每一个人都应享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不是只能当做应声虫。”《真理报》理所当然地不予发表,但西方的报纸却刊登了。这样,罗在国内的演出时好时坏,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官方取消。到一九七八年他和他妻子的护照终于被吊销,也就是说他被剥夺了苏联的公民权。
罗斯托波维奇终于看到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的独联体也逐渐趋向开放,罗并且和戈尔巴乔夫结上了私人的友谊。在他恢复公民权以后,他做的第一桩事就是率领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前往莫斯科。那是一场在红场举行的露天音乐会,为了让买不起音乐厅门票者享受一次精彩的演出。这一场音乐会听众有十万人之多。作为乐队指挥的罗,连他自己也深深地受感动,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俄罗斯人正需要这样的场合向全世界人证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玷污了不少,但听音乐的此刻告诉人们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毫不虚饰的自豪,一种对于自身民族的完全的自信。读Allan Kozinn这篇报道,至此会对斯拉夫民族上世纪以来在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伟大成就,应有肃然起敬之感。
这里展出的一张照片是柏林墙推倒之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罗斯托波维奇在离墙不远处为群众演奏巴哈的无伴奏组曲,那些不约而来的老少群众记录着这一历史时刻。罗作为成名的音乐大师,他也是这一历史长流中的一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他加上这样的称号——大师和苏维埃时期的异己者。当小说家索尔仁尼琴受迫害时,是罗斯托波维奇为他提供了庇护所。这就是罗斯托波维奇。他身后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那些他生前演奏的曲集。然而最大的遗产是他的献身精神,为艺术为自由。
罗斯托波维奇家族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在巴库的故居,现在已用罗斯托波维奇父子的名义向外开放,供人瞻仰。■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