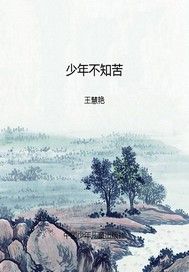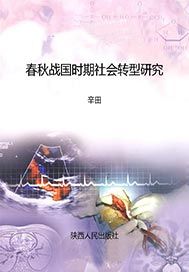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二十六章 闯关游戏
禹州知县朱光宇对联庄会最终走向攻城造反应该是有心理预期的,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在写给上司的书信里如此大胆地使用“抗粮造反”一词。在朱光宇的意识里,刘化镇、岳三教等人肯定会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一步一步走向“造反”。
其实在镇压乡民这件事上,朱光宇曾经也有过犹豫。毕竟前任知县程佶是被逼辞职的,前路吉凶未卜,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做出妥协和让步。为此,他还利用扶乩招仙这些民间巫术,祈求冥冥之中有神仙相助,为自己指一条光明大道。
他扶乩后,得到这样一首诗:“阳翟新祠宇,高阳旧酒徒。回头郊原望,一片血模糊。”
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这首下三滥的诗歌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阳翟是禹州的旧称。祠宇即祠堂神庙,是供奉贤能圣者的地方。而“祠宇”之“宇”,又正合“朱光宇”之“宇”。高阳旧酒徒,指明末分巡大梁道李乘云。李乘云是明末的忠臣良将。李自成攻打禹州城时,李乘云率部坚守,破城后不屈而死。
朱光宇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处理抗粮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搞不好就会陷自己于不利。一旦乡民真的造反,上面追究下来,自己作为地方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希望通过这种不靠谱的巫术,得到神灵的庇护。朱光宇从扶乩得来的这首诗中获得利好消息,那就是他将来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成为圣贤英烈,进入祠宇受世人供奉。
这首乩诗虽然在文字上禁不起任何推敲,却正中朱光宇的下怀。四句诗就好像神灵专门为他开出的一剂灵丹妙药,不但消解了他的精神顾虑,也使他笼罩在一种虚妄的神圣使命感之中,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逼民造反的恶吏,而是要将精忠报国进行到底的贤臣良将。
在扶乩占卜言论的蛊惑之下,就算联庄会不造反,朱光宇也要将他们生生逼反。乡民不造反,又怎么能够成全自己的忠烈之名。既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么每一步都要走得步步惊心。
正因为如此,朱光宇才会在冲突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上书巡抚,指控联庄会会众抗粮造反。他完全是以一种挑衅的姿态来对待那些联庄会乡民,激怒对方将其逼反才是目的。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挑衅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岳三教等联庄会骨干的强烈要求下,官逼民反的重头戏如期上演。
朱光宇果然不负自己“健吏”的名号,在这件事上完全摆出一副铁血酷吏的嘴脸。唯恐天下不乱,使自己无法成就一番功名。朱光宇内心深处的邪恶让这场戏从最初的荒诞走向最终的惨烈,他急于想用一场战争将自己推向政治生命推向巅峰。围城之战打响后,朱光宇的表现完全够得上“健吏”二字。当时河南巡抚派遣的增援部队杀到禹州城下时,联庄会的围城民众早已撤离现场,朱光宇并不甘心到手的功名就这样飞了。他亲自领着官兵追击,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人。接着又传檄密县知县,围剿逃入密县境内的联庄会人众,又杀死了11人,俘虏15人。俘虏人员也全部被其斩杀,尸首悬于城门示众。虽然刘化镇这时候已经自杀,可是朱光宇仍然不放过这位联庄会的带头大哥,将其掘墓戮尸,家产全部藉没。
联庄会虽然遭到重创,可是并没被完全消灭。如果说当初刘化镇起兵造反是受到联庄会内部好斗分子的蛊惑,那么在他和大部分首领死了以后,联庄会的残余势力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豁出命去做最后的挣扎。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联庄会的分会首领李贤、袁西成率领部众聚集到密县大隗镇。密县知县胡燕清在收到线报后,亲自带人前去捕拿,不料却中了联庄会的埋伏。在这场伏击战中,一名叫王青山的低级军官被杀。这场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埋伏战,可以说是联庄会起兵以来打得最为漂亮的一次翻身仗。
打了胜仗的联庄会员们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决定去找地方官胡燕清算账。联庄会分兵两处,一处留下与知县胡燕清继续缠斗,另一处潜入密县城。潜入县城的乡民趁夜放火焚烧了县衙,又杀死了知县的老婆。等到胡燕清带人赶回来时,这帮人早已不知踪影。几次偷袭得手,让联庄会的首领们昏了头,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他们居然想要一鼓作气拿下郑州。
两下比较,我们就会认识到联庄会攻打郑州的做法有多么荒诞。联庄会起事之初,以岳三教为主的主力部队攻打禹州,尚且不能攻克,更何况是郑州这样的河南重镇。李贤等人只是联庄会的残余势力,以联庄会的残余势力攻打河南重镇,其结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这些人很快就败在了郑州知府黄见三的手下。
联庄会的郑州之战虽然一败涂地,但是却惊动了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如果说联庄会残余势力攻打郑州是一种非理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惊动皇帝这件事就像是经过策划的理性之举。从刘化镇举兵造反到遭受重创,联庄会一路走来就像是误打误撞的孩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没有章法可循。其实联庄会本可以与外围的太平军呈呼应之势,实现更大的战略意义。
联庄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军事人才的辅佐,虽然李贤和袁西成率领的联庄会残余势力赢得了一次伏击战的胜利,可随后又接连遭到打击。因此那样一次胜利,也就让人感觉像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的意外。
无论怎样,这件事还是能够惊动了当今的皇帝。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咸丰皇帝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密、郑密迩省城,突有土匪窃发,何至如此披猖?据府县禀,又无起衅根由,显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意存讳饰。著英桂查明具奏。”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禹州联庄会不是选择造反起事,而是选择告状,遵循体制规则一层层告上去,一直告到咸丰皇帝那里,咸丰皇帝必然会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贪婪无状的地方官,然后下诏免除浮收,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这条在体制内告御状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说,这条帝国体制安排的向上管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国的金字塔形社会里,从塔底通往塔尖的路是一条遥远而曲折的过程,或者说,在理论上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可能会走得通。只是说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就如同在玩一场闯关游戏,一路上阻力无数,险关重重。险关就是各级衙门,阻力则来自于各级官员。
在权力集团内部,每一个层面上的食权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皇帝忌讳造反,而官员们则忌讳上告,因为他们的劣迹传到自己上司那里,他就很可能会被治罪,从而丧失手里现有的特权。
为了防止自己的恶行在老百姓的越级上访中败露,他们往往会采取非常规手段阻止地方乡民赴省、赴京告状,尤其是告御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当他们受了坏官员的欺负而求告无门之后,终极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告御状,将自己的屈辱遭遇上达天听,让皇帝为自己当家作主,下旨惩罚那些做恶多端的坏官恶吏。
告御状的成本极高,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够负担起的。告御状往往告的是官,不是告官员贪污腐化,就是告他们滥用公权力。老百姓之间的利益纠纷,是绝对不会去请皇帝仲裁的。
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其实这里说的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民与官斗的成本实在太高,尤其是告御状。其它不说,光是赴京的交通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起的。过去没有宝马、奔驰这样的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进京,只有徒步或者骑驴骑马。等到他们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晃悠到京城,告状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连黄花菜也凉了。
另外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告御状可以说是恐怖的地狱式考验,按照史家所言,普通老百姓去刑部申冤或者当众拦轿首先要掌嘴五十,如果敲响皇宫前的“登闻鼓”,则是要滚钉板。民间传说就更加玄乎,滚钉板不算,还要在滚动中背出诉状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错才能被受理。就算皇帝肯为你出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当年慈禧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前前后后下了十几道旨才摆平此事。
在封建制度下,民告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几乎不可能。除非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告了御状也等于白告。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损害了统治阶层内部规则,或损害了其他多数统治阶层内部人员的利益。另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虽然没有损害统治阶层内部利益,但却激起了被统治的百姓中大部分人的不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整个统治阶层为了维护整个阶层的统治利益,出于无奈的牺牲掉这个官员。
咸丰皇帝在诏书里只是简单点出了地方官员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揪住不放。他在诏书里要求河南巡抚英桂查明原因上奏,这里可以将其视为咸丰皇帝对禹州知县朱光宇等地方官员的警告,同时又给他们预留了极大的补救空间。
所谓最好的补救方法,不过就是在暗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那些“披猖”的“土匪”剿灭。其实在这里咸丰皇帝已经知道这些所谓的“土匪”究竟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是因地方官府的浮收勒折而被逼造反的乡民。他不满意的地方是,地方官府没有说清楚缘由,有事瞒着他这个皇帝,以至于事态蔓延。他警示那些处事不利的地方官员,以后做事不要拖泥带水,要当断则断,不要留下任何后遗症。
面对官民争利局面,皇帝轻轻放过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对那些被逼造反的联庄会乡民却无情地背过脸去。其实咸丰皇帝又何尝不想通过这样的事件来整顿吏治,可是时局容不得他在权力系统做过多的文章。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果此时再对这些效忠于清廷的地方官们下手整饬,恐怕会进一步动摇政治体制,在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咸丰皇帝选择了牺牲那些闹事的百姓,而对叛乱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在封建官家制度下,如果我们把皇帝看做一部权力机器,那么官员则是机器上的零部件,普通老百姓则是权力机器运作的具体对象。权力机器通过它的各个零部件来掌控着老百姓的一切,并凭借其强制力量索求百姓们的供奉。
老百姓虽然不是权力机器的一部分,可他又实在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
皇帝做为帝国权力的一把手和帝国意志的抽象化身,他知道皇权存在的根本基础并不在于官,而在于的是天下百姓。只有百姓归心,他的权力机器才会平稳运转。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老百姓供奉钱粮,官员们则享受着俸禄。由此俸禄就成了权力机器零部件运转的润滑剂,如果俸禄太少的话,权力机器会锈迹斑斑,难以运转;润滑剂太多的话,机器容易打滑,同样运转不利。
如果我们将老百姓和官员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称量,没有哪个聪明的皇帝会看不出来官员的那一段会高高地翘起,因为老百姓要重的多。当官员出了问题,影响到权力机器运转的时候。皇帝不但不反对,甚至鼓励百姓告官。在这里,百姓告官,事实上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从某方面可以起到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作用。
对于皇帝来说,百姓可以遵循体制规则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诉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对皇帝,对抗体制,将自己与所生存的世界对立起来。这是皇帝们绝不允许的。所以,将联庄会叛党与虽有劣迹但是听用的知县放在一起二选一,咸丰皇帝严惩叛党而放过知县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河南巡抚英桂本来就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手,他很容易地就从咸丰皇帝的诏书中读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在接到诏书之后,加大了地方平乱的力度,派遣新任开封府知府赵书升率领精锐部队猛攻联庄会余众,擒杀百余人。咸丰皇帝在收到捷报后,就再也没有责问过地方官员违法之事,而是再次下诏命令追剿散匿于郑州、密县和禹州各地的余匪。
对于联庄会最终走上造反之路,作为联庄会首领之一的岳三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主战派的嚣嚷下,刘化镇才被裹挟进这场抗粮造反运动。攻城失败后,他又与刘化镇一起逃到了密县。意志早已崩溃的刘化镇见大势已去,只好选择自杀。虽然岳三教南下襄城联结当地联庄会取得成功,但是在禹、密两地官兵的联合围剿下,依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两地联庄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有自身原因,但也和他们遇上自己的命中克星——禹州知县朱光宇有很大的关系。
朱光宇的彪悍作风在这次平乱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脖颈被飞弹击伤,仍然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督兵奋战。他亲率人马追杀至顺店东的颍河边,溃逃的联庄会人员一半赴水溺亡,一半被官兵围歼。岳三教虽然在这场毁灭性的战斗里得以侥幸逃脱,但是不久之后还是遭到了官兵擒杀。
事情发生后,有人不仅为襄城联庄会的命运唏嘘感叹。他们认为襄城联庄会本不应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事情的起源与他们无关。其实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利益连锁效应的,我们常说,一根绳上的蚂蚱需要共担风险。其实一根绳上的蚂蚱在共担风险之前,他们考虑的却是共享利益。
襄城联庄会之所以被裹挟进去,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地方的乡民有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赋税减免。当时受到地方官府盘剥的不止一个禹州,任意抬高浮收标准的也不止禹州城的两任知县。银价骤涨引起的官吏灰色收入锐减,这是地方官员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加浮勒折,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襄城和禹州之间的联合,并不是始于叛乱止于叛乱。前任禹州知县程佶要求提高浮收标准,也是受到其他州县的影响。他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个人,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朱光宇署任之后当然不会轻易破坏这个游戏的规则,如同联庄会的会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栓在一根绳上,那么同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官员又何尝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没有必要故作清高,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
对于朱光宇这样的地方官来说,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的结果:一是放弃这笔可以装进自己腰包的钱财,既然是灰色收入,自己就没有放弃的理由。二是因为不遵守利益攻守规则,被淘汰出官场。
提高浮收标准的做法,禹州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当时在禹州联庄会起事之前,许州、尉氏的百姓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抗粮斗争;随后,滑县、封邱、孟县、汜水、辉县等地也是紧跟其上。当时的禹州归许州所辖,而许州的叛乱也早于禹州。四面烽火起,整个河南境内已经没有一处安静之所。在这样一种动荡的时局下,我们又怎能苛求利益博弈以握手言和的方式来完成。
在这根绳上栓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这个利益共同体有人踏出第一步,那么就会有人前赴后继踩出一条路。河南巡抚英桂传檄各地建立联庄会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会产生这个后果。他建立联庄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动群众对抗太平军和捻军,为权力集团卖命。当然这只是官府一厢情愿的想法,当联庄会的权力交接,由乡绅大户转手乡民(乡间能人),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做为地方自卫武装,联庄会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自己人的利益。当反党叛贼掳掠他们时,他们自然会站在官府一边抵御反党叛贼,然而当掠夺者变成了官府,他们会用抱团取利的方式来捍卫自己少得可怜的权益。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底,禹州联庄会带领乡民起事。也就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咸丰皇帝就颁发了诏书,他要求各级官府务必采取严酷手段,惩治“为首倡谋之犯”。
作为权力集团的一把手,皇帝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动摇自己政权的。
这份诏书是发给河南巡抚英桂的,诏书里并没有提到禹州之乱。这份诏书指的是河南境内的共性问题,而不是某个点上的特例。咸丰皇帝在这道诏书里质疑了乡民们闹事的原因(起衅根由)。他在诏书里为整个事件做了准确地解读,那就是地方官员“浮收勒折,以致民情不服”。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对地方官员在地方事务中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还是心知肚明的。
可是并不糊涂的皇帝,转过脸又做了一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事。他没有拿起王法去惩戒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而是将重拳直接砸向了那些联庄会的带头大哥们。皇帝在诏书里明确指使河南巡抚英桂“查有刁生恶棍把持挟制鼓惑乡愚者,即将首犯按法处治,毋得将就了事,致长刁风。”
对于皇帝来说,官家的权力边界有着不容民间社会触碰的敏感地带。在这个敏感地带里,规则可以通行,利益可以保障。而皇帝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将天下臣民的一切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官员有官员的权力地盘,乡民有乡民的利益空间。不同的是官员的地盘,是公权力撑起来的;而乡民的空间,是自己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虽然说有时候利益就像是女人的乳沟,挤一挤总会有的。可是作为乡民,他们手中没有任何保障自己利益不受侵犯的资源。当天下纷扰,官员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当自己的利益与民间社会利益同时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又会利用民间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皇帝、官吏与乡民的三方博弈中,要始终保持一个量的均衡。
在一个政治体制相对平和的年代里,三方力量是均衡的;当一个王朝陷入动荡,三方力量的均衡状态就会被生生打破。
当百姓的利益被那些坏官恶吏压至最低点,皇帝会想办法保护百姓不受官吏欺负;当官吏受到地方百姓冲击时,皇帝又会转身支持官吏去对付百姓。无论三方博弈如何演绎,有几个不争的事实始终存在。一是皇帝既是参与者,又是仲裁者。皇帝就像是赌球的裁判,吹的永远是黑哨。官吏是裁判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们捞取的灰色利益养活了整条权力食物链,也稳定了帝国的权力系统。二是乡民无法自己保护自己,就算他们不想玩这场打假球游戏,可也无法逃脱游戏规则的束缚。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逃出体制之外,去寻求其他解决途径。
对于禹州知县朱光宇这样的朝廷“健吏”来说,他们宁可将地方乡民逼急了造反,也不愿意与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只要能够将其逼反,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用公权力将其捕杀。这么做,既可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动摇,又可以对皇帝和上司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平乱可以成就自己的功名。
河南各地抗粮事件暴发后,地方乡民也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权力系统锈迹斑斑的时代里,老百姓想要依靠皇帝来治官,显然是不靠谱的。在咸丰皇帝的诏书里说得很明白,“大府庇该州县,不肯罪官,而但罪民。”也就是说,上级只会袒护下级,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联庄会里那些闹事的乡民头上。
上级袒护下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大家在一根绳上栓着,那么就要遵守权力世界的攻守同盟。你沦陷,我也不会好过,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能糊弄尽量糊弄过去,只要能够瞒过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所以,皇帝所代表的体制为老百姓安排的上控道路其实上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让百姓们产生一种在体制内有路可走的假象,而这条路就像是一个迷宫,老百姓在里面转得晕头转向也难得偿所愿。等到老百姓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官家集团又会反过来指责老百姓放着正路不走,偏走歪路。
这样的体制安排将老百姓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使他们规避由体制带来的风险。对于地方乡民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方式和能力参与社会博弈,在社会分配体系里添加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规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普通乡民想要生存下去,首先要磨练好自己的生存技巧。
何为生存技巧?就是说一个活在体制内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去迎合体制,懂得迎合官员以及官府。当个人利益与官府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学会放弃个人利益。当官员和官府施以小恩惠时,要懂得如何感恩。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学岳三教与公权力掰手腕,不要试图与地方官吏争利益。
作为底层民众,他们在很多时候往往表现的很纠结。比如说,地方官吏加大盘剥的力度,如果他们自己不去争取,皇帝也懒得做恶人,毕竟自己给官员发的薪俸还不足以养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哑巴吃黄连做顺民,要么像岳三教那种暴脾气去拼。
在这次抗粮事件发生不久以后,也许是咸丰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在颁发的诏书里明令禁止州县浮收。皇帝有心解民困,可结果并不能遂人愿。就算乡民们提着自己的脑袋换得了朝廷的回应,可具体执行政策的还是那些地方官员。县官不如现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业已腐烂的官僚系统会不打折扣地贯彻皇帝安民的旨意,比如身为禹州知县的健吏朱光宇。县志载:“禹州事已上闻,明诏查参,而朱光宇仍负固不悛。”也就是说,皇帝都同意的事,一个七品知县的芝麻官都胆敢不买账。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河南学政张之万上书朝廷,道出地方浮收的原因及解决之道。巡抚英桂在朝廷的饬令下无法再替自己的下属兜拦,朱光宇不得已与绅民们坐下来商议减免浮收之事,并很快收到效果,并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下令取缔浮收部分,恢复过去的标准。
朱光宇在前面之所以敢于在皇帝下诏后仍旧不买账,正是因为他领会了权力机制的奥秘,知道皇帝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什么。联庄会起义被朝廷镇压之后,他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依旧稳坐知县之位。这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被证明的还有:这时候的帝国体制已经彻底不适合金字塔底的草民生存了。如果这时候不是张之万上书言事,正本清源,使得巡抚英桂也没办法为地方开脱,就算刘化镇他们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献给皇帝,也解决不了问题。
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咸丰皇帝正式下诏,谕令解散联庄会。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份,角子山捻兵进犯禹州。从这以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过禹,凡十七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流寇巨匪抄掠禹州,有时甚至一年数至。官府既不能为地方乡民提供足够的庇护,民间也不能再结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百姓形如鱼肉,匍匐在这片砧板一样的大地上,任由制订规则和破坏规则的权力者凌夺与宰割。
其实在镇压乡民这件事上,朱光宇曾经也有过犹豫。毕竟前任知县程佶是被逼辞职的,前路吉凶未卜,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做出妥协和让步。为此,他还利用扶乩招仙这些民间巫术,祈求冥冥之中有神仙相助,为自己指一条光明大道。
他扶乩后,得到这样一首诗:“阳翟新祠宇,高阳旧酒徒。回头郊原望,一片血模糊。”
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这首下三滥的诗歌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阳翟是禹州的旧称。祠宇即祠堂神庙,是供奉贤能圣者的地方。而“祠宇”之“宇”,又正合“朱光宇”之“宇”。高阳旧酒徒,指明末分巡大梁道李乘云。李乘云是明末的忠臣良将。李自成攻打禹州城时,李乘云率部坚守,破城后不屈而死。
朱光宇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处理抗粮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搞不好就会陷自己于不利。一旦乡民真的造反,上面追究下来,自己作为地方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希望通过这种不靠谱的巫术,得到神灵的庇护。朱光宇从扶乩得来的这首诗中获得利好消息,那就是他将来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成为圣贤英烈,进入祠宇受世人供奉。
这首乩诗虽然在文字上禁不起任何推敲,却正中朱光宇的下怀。四句诗就好像神灵专门为他开出的一剂灵丹妙药,不但消解了他的精神顾虑,也使他笼罩在一种虚妄的神圣使命感之中,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逼民造反的恶吏,而是要将精忠报国进行到底的贤臣良将。
在扶乩占卜言论的蛊惑之下,就算联庄会不造反,朱光宇也要将他们生生逼反。乡民不造反,又怎么能够成全自己的忠烈之名。既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么每一步都要走得步步惊心。
正因为如此,朱光宇才会在冲突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上书巡抚,指控联庄会会众抗粮造反。他完全是以一种挑衅的姿态来对待那些联庄会乡民,激怒对方将其逼反才是目的。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挑衅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岳三教等联庄会骨干的强烈要求下,官逼民反的重头戏如期上演。
朱光宇果然不负自己“健吏”的名号,在这件事上完全摆出一副铁血酷吏的嘴脸。唯恐天下不乱,使自己无法成就一番功名。朱光宇内心深处的邪恶让这场戏从最初的荒诞走向最终的惨烈,他急于想用一场战争将自己推向政治生命推向巅峰。围城之战打响后,朱光宇的表现完全够得上“健吏”二字。当时河南巡抚派遣的增援部队杀到禹州城下时,联庄会的围城民众早已撤离现场,朱光宇并不甘心到手的功名就这样飞了。他亲自领着官兵追击,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人。接着又传檄密县知县,围剿逃入密县境内的联庄会人众,又杀死了11人,俘虏15人。俘虏人员也全部被其斩杀,尸首悬于城门示众。虽然刘化镇这时候已经自杀,可是朱光宇仍然不放过这位联庄会的带头大哥,将其掘墓戮尸,家产全部藉没。
联庄会虽然遭到重创,可是并没被完全消灭。如果说当初刘化镇起兵造反是受到联庄会内部好斗分子的蛊惑,那么在他和大部分首领死了以后,联庄会的残余势力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豁出命去做最后的挣扎。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联庄会的分会首领李贤、袁西成率领部众聚集到密县大隗镇。密县知县胡燕清在收到线报后,亲自带人前去捕拿,不料却中了联庄会的埋伏。在这场伏击战中,一名叫王青山的低级军官被杀。这场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埋伏战,可以说是联庄会起兵以来打得最为漂亮的一次翻身仗。
打了胜仗的联庄会员们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决定去找地方官胡燕清算账。联庄会分兵两处,一处留下与知县胡燕清继续缠斗,另一处潜入密县城。潜入县城的乡民趁夜放火焚烧了县衙,又杀死了知县的老婆。等到胡燕清带人赶回来时,这帮人早已不知踪影。几次偷袭得手,让联庄会的首领们昏了头,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他们居然想要一鼓作气拿下郑州。
两下比较,我们就会认识到联庄会攻打郑州的做法有多么荒诞。联庄会起事之初,以岳三教为主的主力部队攻打禹州,尚且不能攻克,更何况是郑州这样的河南重镇。李贤等人只是联庄会的残余势力,以联庄会的残余势力攻打河南重镇,其结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这些人很快就败在了郑州知府黄见三的手下。
联庄会的郑州之战虽然一败涂地,但是却惊动了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如果说联庄会残余势力攻打郑州是一种非理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惊动皇帝这件事就像是经过策划的理性之举。从刘化镇举兵造反到遭受重创,联庄会一路走来就像是误打误撞的孩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没有章法可循。其实联庄会本可以与外围的太平军呈呼应之势,实现更大的战略意义。
联庄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军事人才的辅佐,虽然李贤和袁西成率领的联庄会残余势力赢得了一次伏击战的胜利,可随后又接连遭到打击。因此那样一次胜利,也就让人感觉像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的意外。
无论怎样,这件事还是能够惊动了当今的皇帝。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咸丰皇帝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密、郑密迩省城,突有土匪窃发,何至如此披猖?据府县禀,又无起衅根由,显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意存讳饰。著英桂查明具奏。”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禹州联庄会不是选择造反起事,而是选择告状,遵循体制规则一层层告上去,一直告到咸丰皇帝那里,咸丰皇帝必然会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贪婪无状的地方官,然后下诏免除浮收,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这条在体制内告御状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说,这条帝国体制安排的向上管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国的金字塔形社会里,从塔底通往塔尖的路是一条遥远而曲折的过程,或者说,在理论上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可能会走得通。只是说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就如同在玩一场闯关游戏,一路上阻力无数,险关重重。险关就是各级衙门,阻力则来自于各级官员。
在权力集团内部,每一个层面上的食权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皇帝忌讳造反,而官员们则忌讳上告,因为他们的劣迹传到自己上司那里,他就很可能会被治罪,从而丧失手里现有的特权。
为了防止自己的恶行在老百姓的越级上访中败露,他们往往会采取非常规手段阻止地方乡民赴省、赴京告状,尤其是告御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当他们受了坏官员的欺负而求告无门之后,终极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告御状,将自己的屈辱遭遇上达天听,让皇帝为自己当家作主,下旨惩罚那些做恶多端的坏官恶吏。
告御状的成本极高,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够负担起的。告御状往往告的是官,不是告官员贪污腐化,就是告他们滥用公权力。老百姓之间的利益纠纷,是绝对不会去请皇帝仲裁的。
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其实这里说的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民与官斗的成本实在太高,尤其是告御状。其它不说,光是赴京的交通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起的。过去没有宝马、奔驰这样的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进京,只有徒步或者骑驴骑马。等到他们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晃悠到京城,告状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连黄花菜也凉了。
另外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告御状可以说是恐怖的地狱式考验,按照史家所言,普通老百姓去刑部申冤或者当众拦轿首先要掌嘴五十,如果敲响皇宫前的“登闻鼓”,则是要滚钉板。民间传说就更加玄乎,滚钉板不算,还要在滚动中背出诉状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错才能被受理。就算皇帝肯为你出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当年慈禧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前前后后下了十几道旨才摆平此事。
在封建制度下,民告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几乎不可能。除非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告了御状也等于白告。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损害了统治阶层内部规则,或损害了其他多数统治阶层内部人员的利益。另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虽然没有损害统治阶层内部利益,但却激起了被统治的百姓中大部分人的不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整个统治阶层为了维护整个阶层的统治利益,出于无奈的牺牲掉这个官员。
咸丰皇帝在诏书里只是简单点出了地方官员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揪住不放。他在诏书里要求河南巡抚英桂查明原因上奏,这里可以将其视为咸丰皇帝对禹州知县朱光宇等地方官员的警告,同时又给他们预留了极大的补救空间。
所谓最好的补救方法,不过就是在暗示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将那些“披猖”的“土匪”剿灭。其实在这里咸丰皇帝已经知道这些所谓的“土匪”究竟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是因地方官府的浮收勒折而被逼造反的乡民。他不满意的地方是,地方官府没有说清楚缘由,有事瞒着他这个皇帝,以至于事态蔓延。他警示那些处事不利的地方官员,以后做事不要拖泥带水,要当断则断,不要留下任何后遗症。
面对官民争利局面,皇帝轻轻放过了那些蠹民的地方官,而对那些被逼造反的联庄会乡民却无情地背过脸去。其实咸丰皇帝又何尝不想通过这样的事件来整顿吏治,可是时局容不得他在权力系统做过多的文章。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果此时再对这些效忠于清廷的地方官们下手整饬,恐怕会进一步动摇政治体制,在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下,咸丰皇帝选择了牺牲那些闹事的百姓,而对叛乱分子的无情打击,也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在封建官家制度下,如果我们把皇帝看做一部权力机器,那么官员则是机器上的零部件,普通老百姓则是权力机器运作的具体对象。权力机器通过它的各个零部件来掌控着老百姓的一切,并凭借其强制力量索求百姓们的供奉。
老百姓虽然不是权力机器的一部分,可他又实在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
皇帝做为帝国权力的一把手和帝国意志的抽象化身,他知道皇权存在的根本基础并不在于官,而在于的是天下百姓。只有百姓归心,他的权力机器才会平稳运转。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老百姓供奉钱粮,官员们则享受着俸禄。由此俸禄就成了权力机器零部件运转的润滑剂,如果俸禄太少的话,权力机器会锈迹斑斑,难以运转;润滑剂太多的话,机器容易打滑,同样运转不利。
如果我们将老百姓和官员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称量,没有哪个聪明的皇帝会看不出来官员的那一段会高高地翘起,因为老百姓要重的多。当官员出了问题,影响到权力机器运转的时候。皇帝不但不反对,甚至鼓励百姓告官。在这里,百姓告官,事实上也是加强皇权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从某方面可以起到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作用。
对于皇帝来说,百姓可以遵循体制规则做一切事,有冤申冤有怨诉怨,但是你不能造反。造反就是反对皇帝,对抗体制,将自己与所生存的世界对立起来。这是皇帝们绝不允许的。所以,将联庄会叛党与虽有劣迹但是听用的知县放在一起二选一,咸丰皇帝严惩叛党而放过知县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河南巡抚英桂本来就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手,他很容易地就从咸丰皇帝的诏书中读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在接到诏书之后,加大了地方平乱的力度,派遣新任开封府知府赵书升率领精锐部队猛攻联庄会余众,擒杀百余人。咸丰皇帝在收到捷报后,就再也没有责问过地方官员违法之事,而是再次下诏命令追剿散匿于郑州、密县和禹州各地的余匪。
对于联庄会最终走上造反之路,作为联庄会首领之一的岳三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主战派的嚣嚷下,刘化镇才被裹挟进这场抗粮造反运动。攻城失败后,他又与刘化镇一起逃到了密县。意志早已崩溃的刘化镇见大势已去,只好选择自杀。虽然岳三教南下襄城联结当地联庄会取得成功,但是在禹、密两地官兵的联合围剿下,依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两地联庄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虽然有自身原因,但也和他们遇上自己的命中克星——禹州知县朱光宇有很大的关系。
朱光宇的彪悍作风在这次平乱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脖颈被飞弹击伤,仍然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督兵奋战。他亲率人马追杀至顺店东的颍河边,溃逃的联庄会人员一半赴水溺亡,一半被官兵围歼。岳三教虽然在这场毁灭性的战斗里得以侥幸逃脱,但是不久之后还是遭到了官兵擒杀。
事情发生后,有人不仅为襄城联庄会的命运唏嘘感叹。他们认为襄城联庄会本不应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事情的起源与他们无关。其实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利益连锁效应的,我们常说,一根绳上的蚂蚱需要共担风险。其实一根绳上的蚂蚱在共担风险之前,他们考虑的却是共享利益。
襄城联庄会之所以被裹挟进去,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地方的乡民有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赋税减免。当时受到地方官府盘剥的不止一个禹州,任意抬高浮收标准的也不止禹州城的两任知县。银价骤涨引起的官吏灰色收入锐减,这是地方官员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加浮勒折,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襄城和禹州之间的联合,并不是始于叛乱止于叛乱。前任禹州知县程佶要求提高浮收标准,也是受到其他州县的影响。他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个人,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朱光宇署任之后当然不会轻易破坏这个游戏的规则,如同联庄会的会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栓在一根绳上,那么同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官员又何尝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没有必要故作清高,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
对于朱光宇这样的地方官来说,将自己从这根绳子上摘出来的结果:一是放弃这笔可以装进自己腰包的钱财,既然是灰色收入,自己就没有放弃的理由。二是因为不遵守利益攻守规则,被淘汰出官场。
提高浮收标准的做法,禹州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当时在禹州联庄会起事之前,许州、尉氏的百姓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抗粮斗争;随后,滑县、封邱、孟县、汜水、辉县等地也是紧跟其上。当时的禹州归许州所辖,而许州的叛乱也早于禹州。四面烽火起,整个河南境内已经没有一处安静之所。在这样一种动荡的时局下,我们又怎能苛求利益博弈以握手言和的方式来完成。
在这根绳上栓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这个利益共同体有人踏出第一步,那么就会有人前赴后继踩出一条路。河南巡抚英桂传檄各地建立联庄会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会产生这个后果。他建立联庄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动群众对抗太平军和捻军,为权力集团卖命。当然这只是官府一厢情愿的想法,当联庄会的权力交接,由乡绅大户转手乡民(乡间能人),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做为地方自卫武装,联庄会首先考虑的必然是自己人的利益。当反党叛贼掳掠他们时,他们自然会站在官府一边抵御反党叛贼,然而当掠夺者变成了官府,他们会用抱团取利的方式来捍卫自己少得可怜的权益。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底,禹州联庄会带领乡民起事。也就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咸丰皇帝就颁发了诏书,他要求各级官府务必采取严酷手段,惩治“为首倡谋之犯”。
作为权力集团的一把手,皇帝是绝对不允许有人动摇自己政权的。
这份诏书是发给河南巡抚英桂的,诏书里并没有提到禹州之乱。这份诏书指的是河南境内的共性问题,而不是某个点上的特例。咸丰皇帝在这道诏书里质疑了乡民们闹事的原因(起衅根由)。他在诏书里为整个事件做了准确地解读,那就是地方官员“浮收勒折,以致民情不服”。可见皇帝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对地方官员在地方事务中所采取的非常规手段还是心知肚明的。
可是并不糊涂的皇帝,转过脸又做了一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事。他没有拿起王法去惩戒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而是将重拳直接砸向了那些联庄会的带头大哥们。皇帝在诏书里明确指使河南巡抚英桂“查有刁生恶棍把持挟制鼓惑乡愚者,即将首犯按法处治,毋得将就了事,致长刁风。”
对于皇帝来说,官家的权力边界有着不容民间社会触碰的敏感地带。在这个敏感地带里,规则可以通行,利益可以保障。而皇帝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将天下臣民的一切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官员有官员的权力地盘,乡民有乡民的利益空间。不同的是官员的地盘,是公权力撑起来的;而乡民的空间,是自己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虽然说有时候利益就像是女人的乳沟,挤一挤总会有的。可是作为乡民,他们手中没有任何保障自己利益不受侵犯的资源。当天下纷扰,官员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当自己的利益与民间社会利益同时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又会利用民间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皇帝、官吏与乡民的三方博弈中,要始终保持一个量的均衡。
在一个政治体制相对平和的年代里,三方力量是均衡的;当一个王朝陷入动荡,三方力量的均衡状态就会被生生打破。
当百姓的利益被那些坏官恶吏压至最低点,皇帝会想办法保护百姓不受官吏欺负;当官吏受到地方百姓冲击时,皇帝又会转身支持官吏去对付百姓。无论三方博弈如何演绎,有几个不争的事实始终存在。一是皇帝既是参与者,又是仲裁者。皇帝就像是赌球的裁判,吹的永远是黑哨。官吏是裁判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们捞取的灰色利益养活了整条权力食物链,也稳定了帝国的权力系统。二是乡民无法自己保护自己,就算他们不想玩这场打假球游戏,可也无法逃脱游戏规则的束缚。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逃出体制之外,去寻求其他解决途径。
对于禹州知县朱光宇这样的朝廷“健吏”来说,他们宁可将地方乡民逼急了造反,也不愿意与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只要能够将其逼反,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用公权力将其捕杀。这么做,既可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动摇,又可以对皇帝和上司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平乱可以成就自己的功名。
河南各地抗粮事件暴发后,地方乡民也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权力系统锈迹斑斑的时代里,老百姓想要依靠皇帝来治官,显然是不靠谱的。在咸丰皇帝的诏书里说得很明白,“大府庇该州县,不肯罪官,而但罪民。”也就是说,上级只会袒护下级,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联庄会里那些闹事的乡民头上。
上级袒护下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大家在一根绳上栓着,那么就要遵守权力世界的攻守同盟。你沦陷,我也不会好过,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能糊弄尽量糊弄过去,只要能够瞒过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所以,皇帝所代表的体制为老百姓安排的上控道路其实上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让百姓们产生一种在体制内有路可走的假象,而这条路就像是一个迷宫,老百姓在里面转得晕头转向也难得偿所愿。等到老百姓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官家集团又会反过来指责老百姓放着正路不走,偏走歪路。
这样的体制安排将老百姓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使他们规避由体制带来的风险。对于地方乡民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方式和能力参与社会博弈,在社会分配体系里添加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规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普通乡民想要生存下去,首先要磨练好自己的生存技巧。
何为生存技巧?就是说一个活在体制内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去迎合体制,懂得迎合官员以及官府。当个人利益与官府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学会放弃个人利益。当官员和官府施以小恩惠时,要懂得如何感恩。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学岳三教与公权力掰手腕,不要试图与地方官吏争利益。
作为底层民众,他们在很多时候往往表现的很纠结。比如说,地方官吏加大盘剥的力度,如果他们自己不去争取,皇帝也懒得做恶人,毕竟自己给官员发的薪俸还不足以养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哑巴吃黄连做顺民,要么像岳三教那种暴脾气去拼。
在这次抗粮事件发生不久以后,也许是咸丰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在颁发的诏书里明令禁止州县浮收。皇帝有心解民困,可结果并不能遂人愿。就算乡民们提着自己的脑袋换得了朝廷的回应,可具体执行政策的还是那些地方官员。县官不如现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业已腐烂的官僚系统会不打折扣地贯彻皇帝安民的旨意,比如身为禹州知县的健吏朱光宇。县志载:“禹州事已上闻,明诏查参,而朱光宇仍负固不悛。”也就是说,皇帝都同意的事,一个七品知县的芝麻官都胆敢不买账。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河南学政张之万上书朝廷,道出地方浮收的原因及解决之道。巡抚英桂在朝廷的饬令下无法再替自己的下属兜拦,朱光宇不得已与绅民们坐下来商议减免浮收之事,并很快收到效果,并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下令取缔浮收部分,恢复过去的标准。
朱光宇在前面之所以敢于在皇帝下诏后仍旧不买账,正是因为他领会了权力机制的奥秘,知道皇帝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什么。联庄会起义被朝廷镇压之后,他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依旧稳坐知县之位。这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被证明的还有:这时候的帝国体制已经彻底不适合金字塔底的草民生存了。如果这时候不是张之万上书言事,正本清源,使得巡抚英桂也没办法为地方开脱,就算刘化镇他们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献给皇帝,也解决不了问题。
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咸丰皇帝正式下诏,谕令解散联庄会。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份,角子山捻兵进犯禹州。从这以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过禹,凡十七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流寇巨匪抄掠禹州,有时甚至一年数至。官府既不能为地方乡民提供足够的庇护,民间也不能再结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百姓形如鱼肉,匍匐在这片砧板一样的大地上,任由制订规则和破坏规则的权力者凌夺与宰割。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