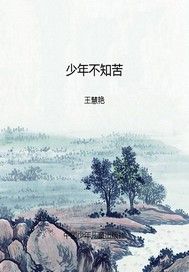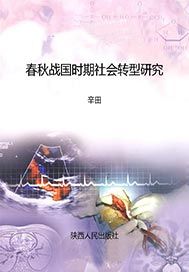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二十五章 带头大哥的风险值
程佶就这样被迫退出这场利益博弈游戏,准确地说是逃离了眼前的生存困境。一个做着升官发财梦的知县,就这样因为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官民冲突而选择逃出官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此时的禹州在程佶看来,就像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随时有喷发的可能。他可不能为了升官发财,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
在程佶逃离禹州官场之后,朝廷很快就派了一个叫朱光宇的官员来接替他的位子。本来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有人的地方就不缺当官的人。
根据《禹州县志》记载,这个叫做朱光宇的官员,堪称“健吏也。”就是说,朱光宇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既然上级能够在官民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将其遣派过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具有灭火队员的潜质,能够为领导分忧。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也是最考验一个官员的时候。无论是对官员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应对困境的精神能量,都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程佶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的临阵脱逃,一半是被那些闹事的群众吓得,一半是被自己吓得。虽然禹州之前的历任地方官吏也同样收刮民资民膏,可收刮得程度和手段并没有今天这么厉害,乡民虽有怨言,但是还没有酿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程佶的逃离更多是因为联庄会的异军突起,乡民有了联庄会这个组织撑腰,就不再是个体与官家的对抗,而是集体与权力的博弈。又加上联庄会有了刘化镇、岳三教这样敢于公然为乡民伸张正义的带头大哥,像程佶这样胆小的地方官员又怎能不有所忌惮?事态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程知县还是嗅出了不祥的气息,民间与官府的对立情绪开始蔓延。
无法走出博弈困境的程佶只好选择离开,用未知的前途来赌未知的命运,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对于新任知县朱光宇来说,他所接手的这盘没有下完的棋虽然不是一盘死棋,但是要想走活这盘棋又谈何容易?他要想真正走活眼前这盘棋,唯有将前任知县滥加的浮收全部减免掉。只有这么做,才能够消解民怨,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气氛。
本来乡民抱团就是源于利益上的诉求,一旦官府做出让步,那么他们对抗官府的理由和动力就会随之动摇。如果官府再寻找机会改组或者取缔联庄会,那么抱团的村民就会从乡团组织的母体上被生生剥离出来。失去组织庇护的乡民陷入单兵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失去了向官府和官员叫板的实力,失去了他们在底层社会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点话语权。其实底层社会的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乡民发出的声音,而是一帮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人集体吼出来的声音。
如果朱光宇接受了上面的这个建议,也就赢得了事态发展的转机。可是朱光宇好像与闹事的乡民在较劲似的,他偏偏没有选择妥协。他不但没有妥协和让步,反而沿着前任知县开辟的错误道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如此一来,乡民们实在坐不住了。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岳三教等乡民代表在联庄会带头大哥刘化镇的带领下,前往县衙向新任知县朱光宇请愿,希望朱知县能够体谅民众的疾苦,能够将前任程佶加派的那些浮收减免。乡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是这场请愿行动并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实际效果,新知县朱光宇根本就不愿意做出半点让步。真是让人搞不明白,朝廷怎么会安排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到禹州地界来充当救火队员。
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他到是来救火的?还是来浇油的?如果是救火的,他应该想办法畅通官民交流的渠道,不应该将其堵死。在综合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得过去。那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那些加派到老百姓头上的税赋,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何况这个收入,基本上都会化为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进了个别人的腰包。不要小看了这笔灰色收入,他通常是正俸的好多倍,当时官员发财就是发的这部分财。朱光宇既然被时人评价为“健吏”,就说明他不是一个草包,他在权力运作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朱光宇不愿意向乡民妥协,并不能说明他这个新知县就不知道如何去平息这件事。他不愿意妥协,是因为他舍不得放弃那些唾手可得的灰色收入。正因为他是一个“健吏”,他才觉得自己有不妥协就能够摆平一切的能力。其实在此之前,他的前任程佶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么想的。这是大部分官员的通病,他们的自负虽然是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说到底还是公权力壮了他们的怂人胆。
他们在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就像是一个被打足了气的足球,而权力就像是充实在他们身体内的气体。一旦权力丧失,他们就会瞬间变为一只瘪足球。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拥有了公权力,就等于是拥有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权和利益索取权。在官与民的权力博弈中,双方实力悬殊。作为官家制度的履行者,无论是昨天的程知县,还是今天的朱知县,他们在走马上任之时,都坚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
我们再来看一看,官员眼中的抗粮“刁民”提出的削减赋税是不是无理要求。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乡民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皇纲国法相抗衡,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对于那些该缴纳的皇粮国赋,包括那些不合常理,已经成为陋规惯例的火耗平余,他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提出抗议的,要求减免的,是那些滥加进去的不合理收费。他们没有奢望官府能够免税,而是要求减去另外增加的部分。清朝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抗粮风潮也是此起彼伏。
当时的河南学政张之万在他的奏疏里就陈述了这一点,他说:“奸民之纠众,皆谓减价完纳,非敢谓抗不完纳也。皆谓求减差徭,非敢谓不应差徭也。”被称为“奸民”的农民们不是不愿承担赋税,也不是不能忍耐不公平的滥派和浮收,但是请不要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并不是所有人的忍耐都可以没有底线。当他们退无可退的时候,兔子被逼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人。
联庄会的几位带头大哥刘化镇、岳三教等人本来就是以民权代言人的身份成功上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将乡绅大户取而代之,就是因为他们是站在“民”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而联庄会首领的身份让他们在这件事上要有所担当,最起码不应该退缩。退,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民间地位,同时背上一个勾结官员、与民争利的骂名。
正因为如此,当知县朱光宇严词拒绝了刘化镇等人要求减免浮收的请愿后,联庄会首领们的胸中怒火被彻底点燃。这些人在与知县争执无果后,骂骂咧咧就离开了衙门。可是就在他们跨出县衙大门的那一瞬间,被衙门口的看门人喊住质问。也许是为了向自己的主子邀宠卖乖,这个衙门里的小吏与刘化镇等人就在衙门口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这些乡民代表本就对官府雇佣的这帮胥吏恨得牙痒痒,这帮人无品无级,就因为披上了权力马甲才为所欲为。官家制度下的权力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这帮人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皆须其力”。按照有的人的说法,胥吏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因此,他们手上都掌握着官府赋予的或大或小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敲诈勒索,滥肆搜刮。作为公权力的帮凶,由于他们身份低贱,所以很多时候既不受封建道德的约束,也不受官家体例的束缚。
这个张姓小吏如今见这帮乡民代表还没走出衙门口,就开始骂自己的主子。也许是护主心切,就与乡民对骂起来。其实小吏还真不是多管闲事,毕竟乡民要求减免的浮收里也有自己的那一点点分成。他仗着自己是衙门里的人,与刘化镇等人争执不下。乡民代表在朱光宇那里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愁找不到地方发泄,于是一股脑全部宣泄到这个张姓小吏的身上。
在刘化镇、岳三教等人的带领下,他们捣毁了张姓小吏的住宅,还顺带着将一个叫田子昌的胥吏家的房子也给捣毁了。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知县朱光宇听闻后,极为震怒。他立即会同营讯长官带兵去捉拿当事人方在颍河北校场展开对峙。刘化镇等人以为经过这么一折腾,朱光宇应该见识到他们这些地方乡民的手段,态度能够有所缓和。于是乡民代表再次要求官府能够减免税赋,不然后来很严重。刘化镇等人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在这件事上,知县朱光宇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这一次,朱光宇决定让乡民们领教领教“健吏”的手段。
刘化镇等人的怒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他们再次谩骂着,咆哮着。朱光宇命令兵勇上前捉拿肇事者,如果遇到反抗,就地正法。双方撕扯一处,联庄会里有个叫赵仁的乡民代表在冲突中被杀死。不管是失手误杀,还是被故意击毙,总之在闹哄哄的现场,有人死了。
我们可以还原下事发现场,赵仁命丧当场,当事双方都感到万分震惊,喧闹的现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按照常理来推断,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肯定会就击毙赵仁一事给出交代。要知道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不是闹着玩的,都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重罪。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就连那些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跟在后面瞎起哄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也要杖责一百,以儆效尤。
官民双方见闹出人命,不再缠斗一处,很快各自散去。按理说,乡民被杀应该是整个事件的爆点。可是事件被推向爆点后,却自行平息,双方不战而退。应该说刘化镇等联庄会会员在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杀之后,内心的愤怒是难以想象的。可是愤怒并没有让刘化镇等人昏头,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刘化镇知道,此时若要杀官复仇,自己这个带头大哥就会背上诛灭九族的重罪。当然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联庄会会首的身份,极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他抓人杀人,表现得极其野蛮粗暴。当闹出人命时,面对着人多势众的联庄会会众,他在权衡利害之后选择了暂时忍耐,任由对方怀恨而去。事后,为了推卸责任,朱光宇上书河南巡抚兼提督英桂,说禹州老百姓抗粮造反,闹出人命。他在上书中只强调“抗粮造反”,却只字未提地方县衙滥加浮收之事。当时,太平军在河南境内正闹得沸腾,“造反”二字是最为敏感的字眼。河南巡抚英桂在接到朱光宇的呈报后,于第一时间派出军队前往禹州平乱。
官民双方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就在镇压官兵整装待发之际,联庄会已经集结好自己的武装开始攻打州城。这是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刘化镇等人在退回乡里后,会再次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卷土重来,这等于正式向官方宣战,将“造反”的罪名坐实?唯一的解释就是,联庄会内部氛围这时候已经完全被岳三教等好勇斗狠之人所掌控。
民间武装力量毕竟不是正规部队,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禹州历来都是中原重镇,城高墙厚,不要说是联庄会,就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了,一时半会想要攻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联庄会的乡军久攻不下时,省府派遣的平乱部队距离禹州已经不到十里的路程。围城的乡民得到情报后,不敢在此恋战,只好再次散去。朱光宇不亏是个“健吏”,他率众一路追杀至联庄会的总部,放火烧毁了联庄会设在高庙的总部所在地。虽然刘化镇带领部下逃到了密县超化镇,可仍旧遭到了地方官兵的围追堵截。
朱光宇传檄密县县令胡燕清,希望能够与之共同围剿刘化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的刘化镇只好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刘化镇的自杀来得过于突然,让所有人都大为不解。这时候的联庄会虽然处于被动局面,可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从刘化镇自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做为联庄会会首的刘化镇虽然有为民请愿的热情,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为乡民利益而造反。他虽然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乡民首领,但却不是有天下蓝图的军事革命家。他希望能够当上带头大哥,不过是为了替乡民主持公道,或者壮大宗族的势力。在艰难的世道里求生存,刘化镇虽然只是个杂货铺或铁匠铺,难以实现人生的大富贵,但是对于一个底层民众来说,他的日子要比一般老百姓富足。
刘化镇在自己的人身没有遇到更大的伤害时,内心受到民间侠义精神的召唤,才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民争利,替那些受到伤害的底层民众谋求公义与公理。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官府将联庄会的行动定位为“造反”时,这要人命的罪责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乡民。
在这种如火烹油的局面下,作为“带头大哥”的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进退得失,对自己所做的事做出新的判断与取舍。
当初,刘化镇出面为乡民伸张正义,并由此成为联庄会会首的时候,估计连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走上一条江湖不归路。当他在沸腾的民意裹胁之下,一跃升级为对抗官府的带头大哥时,他在被迫承担道义责任的同时,内心的惶恐要远远大于“带头大哥”给自己带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造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罪责,不光会让自己陪了前世今生,还会让自己的整个家族受到牵连。刘化镇知道,事已至此,如果仅仅依靠那些目光短浅,且遇事冲动的乡民,事态的发展将会远远超出想象。
刘化镇曾经想过聘用一个有些文化素养的人,作为自己的师爷或者军师。他也曾经邀请过同城举人王成业来担当这个角色,可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聘请举人来担当自己的师爷,他是出于两方面考虑。既可以借用文人的理性来调和联庄会组织内部的非理性因素,同时王举人的特殊身份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规避风险。
王成业在道光年间曾经中过举人,并没有进入官场,一直在家乡做私塾先生。乡间的文化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又加上王成业中过举人,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曾经依照保甲法制订了《民约》,成为维系地方秩序的民间约法。
如果能够将王成业聘请到联庄会,那么将会在联庄会和官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民间社会的权力序列里,举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一个举人犯了罪,地方官府是没有权力将其直接问罪的。只有先上奏朝廷,取消他的举人身份,然后才能进入法律程序。
应该说刘化镇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可毕竟是他的一厢情愿。在王成业这样的乡间文人看来,联庄会聚集的都是一些乡间的好斗分子。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王成业拒绝了刘化镇地好意,他可不想和这些没文化的人搅合在一起。
刘化镇最终在岳三教等好勇斗狠者的裹胁下,一脚踏进了被迫造反的死亡泥潭。刘化镇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和朝廷对抗。当朝廷镇压的消息传来时,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在官兵还没有杀到眼前时,他就选择了自杀了断。
刘化镇的悲剧在于,他只是个有着侠义心肠的江湖之士,而不是可以做大事的领袖人物,他没有领袖的韬略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却不幸被推上了领袖的位置。而他的侠义意识,又使他明知事态日益恶化,却又做不到激流而退明哲保身,在岳三教等人以民怨和义气为感召,提出莽撞的攻城报仇的计划时,他也同样无法后退。而当攻城失利,巡抚派出的镇压大军开到之后,已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他崩溃了。
在程佶逃离禹州官场之后,朝廷很快就派了一个叫朱光宇的官员来接替他的位子。本来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有人的地方就不缺当官的人。
根据《禹州县志》记载,这个叫做朱光宇的官员,堪称“健吏也。”就是说,朱光宇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员。既然上级能够在官民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将其遣派过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具有灭火队员的潜质,能够为领导分忧。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也是最考验一个官员的时候。无论是对官员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应对困境的精神能量,都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程佶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的临阵脱逃,一半是被那些闹事的群众吓得,一半是被自己吓得。虽然禹州之前的历任地方官吏也同样收刮民资民膏,可收刮得程度和手段并没有今天这么厉害,乡民虽有怨言,但是还没有酿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程佶的逃离更多是因为联庄会的异军突起,乡民有了联庄会这个组织撑腰,就不再是个体与官家的对抗,而是集体与权力的博弈。又加上联庄会有了刘化镇、岳三教这样敢于公然为乡民伸张正义的带头大哥,像程佶这样胆小的地方官员又怎能不有所忌惮?事态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程知县还是嗅出了不祥的气息,民间与官府的对立情绪开始蔓延。
无法走出博弈困境的程佶只好选择离开,用未知的前途来赌未知的命运,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对于新任知县朱光宇来说,他所接手的这盘没有下完的棋虽然不是一盘死棋,但是要想走活这盘棋又谈何容易?他要想真正走活眼前这盘棋,唯有将前任知县滥加的浮收全部减免掉。只有这么做,才能够消解民怨,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气氛。
本来乡民抱团就是源于利益上的诉求,一旦官府做出让步,那么他们对抗官府的理由和动力就会随之动摇。如果官府再寻找机会改组或者取缔联庄会,那么抱团的村民就会从乡团组织的母体上被生生剥离出来。失去组织庇护的乡民陷入单兵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失去了向官府和官员叫板的实力,失去了他们在底层社会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点话语权。其实底层社会的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乡民发出的声音,而是一帮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人集体吼出来的声音。
如果朱光宇接受了上面的这个建议,也就赢得了事态发展的转机。可是朱光宇好像与闹事的乡民在较劲似的,他偏偏没有选择妥协。他不但没有妥协和让步,反而沿着前任知县开辟的错误道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如此一来,乡民们实在坐不住了。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岳三教等乡民代表在联庄会带头大哥刘化镇的带领下,前往县衙向新任知县朱光宇请愿,希望朱知县能够体谅民众的疾苦,能够将前任程佶加派的那些浮收减免。乡民们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是这场请愿行动并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实际效果,新知县朱光宇根本就不愿意做出半点让步。真是让人搞不明白,朝廷怎么会安排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人到禹州地界来充当救火队员。
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他到是来救火的?还是来浇油的?如果是救火的,他应该想办法畅通官民交流的渠道,不应该将其堵死。在综合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得过去。那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那些加派到老百姓头上的税赋,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何况这个收入,基本上都会化为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进了个别人的腰包。不要小看了这笔灰色收入,他通常是正俸的好多倍,当时官员发财就是发的这部分财。朱光宇既然被时人评价为“健吏”,就说明他不是一个草包,他在权力运作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朱光宇不愿意向乡民妥协,并不能说明他这个新知县就不知道如何去平息这件事。他不愿意妥协,是因为他舍不得放弃那些唾手可得的灰色收入。正因为他是一个“健吏”,他才觉得自己有不妥协就能够摆平一切的能力。其实在此之前,他的前任程佶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么想的。这是大部分官员的通病,他们的自负虽然是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说到底还是公权力壮了他们的怂人胆。
他们在大部分时候的状态就像是一个被打足了气的足球,而权力就像是充实在他们身体内的气体。一旦权力丧失,他们就会瞬间变为一只瘪足球。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拥有了公权力,就等于是拥有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权和利益索取权。在官与民的权力博弈中,双方实力悬殊。作为官家制度的履行者,无论是昨天的程知县,还是今天的朱知县,他们在走马上任之时,都坚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
我们再来看一看,官员眼中的抗粮“刁民”提出的削减赋税是不是无理要求。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乡民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皇纲国法相抗衡,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对于那些该缴纳的皇粮国赋,包括那些不合常理,已经成为陋规惯例的火耗平余,他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提出抗议的,要求减免的,是那些滥加进去的不合理收费。他们没有奢望官府能够免税,而是要求减去另外增加的部分。清朝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抗粮风潮也是此起彼伏。
当时的河南学政张之万在他的奏疏里就陈述了这一点,他说:“奸民之纠众,皆谓减价完纳,非敢谓抗不完纳也。皆谓求减差徭,非敢谓不应差徭也。”被称为“奸民”的农民们不是不愿承担赋税,也不是不能忍耐不公平的滥派和浮收,但是请不要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并不是所有人的忍耐都可以没有底线。当他们退无可退的时候,兔子被逼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人。
联庄会的几位带头大哥刘化镇、岳三教等人本来就是以民权代言人的身份成功上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将乡绅大户取而代之,就是因为他们是站在“民”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而联庄会首领的身份让他们在这件事上要有所担当,最起码不应该退缩。退,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民间地位,同时背上一个勾结官员、与民争利的骂名。
正因为如此,当知县朱光宇严词拒绝了刘化镇等人要求减免浮收的请愿后,联庄会首领们的胸中怒火被彻底点燃。这些人在与知县争执无果后,骂骂咧咧就离开了衙门。可是就在他们跨出县衙大门的那一瞬间,被衙门口的看门人喊住质问。也许是为了向自己的主子邀宠卖乖,这个衙门里的小吏与刘化镇等人就在衙门口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这些乡民代表本就对官府雇佣的这帮胥吏恨得牙痒痒,这帮人无品无级,就因为披上了权力马甲才为所欲为。官家制度下的权力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这帮人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皆须其力”。按照有的人的说法,胥吏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因此,他们手上都掌握着官府赋予的或大或小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敲诈勒索,滥肆搜刮。作为公权力的帮凶,由于他们身份低贱,所以很多时候既不受封建道德的约束,也不受官家体例的束缚。
这个张姓小吏如今见这帮乡民代表还没走出衙门口,就开始骂自己的主子。也许是护主心切,就与乡民对骂起来。其实小吏还真不是多管闲事,毕竟乡民要求减免的浮收里也有自己的那一点点分成。他仗着自己是衙门里的人,与刘化镇等人争执不下。乡民代表在朱光宇那里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愁找不到地方发泄,于是一股脑全部宣泄到这个张姓小吏的身上。
在刘化镇、岳三教等人的带领下,他们捣毁了张姓小吏的住宅,还顺带着将一个叫田子昌的胥吏家的房子也给捣毁了。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知县朱光宇听闻后,极为震怒。他立即会同营讯长官带兵去捉拿当事人方在颍河北校场展开对峙。刘化镇等人以为经过这么一折腾,朱光宇应该见识到他们这些地方乡民的手段,态度能够有所缓和。于是乡民代表再次要求官府能够减免税赋,不然后来很严重。刘化镇等人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在这件事上,知县朱光宇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这一次,朱光宇决定让乡民们领教领教“健吏”的手段。
刘化镇等人的怒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他们再次谩骂着,咆哮着。朱光宇命令兵勇上前捉拿肇事者,如果遇到反抗,就地正法。双方撕扯一处,联庄会里有个叫赵仁的乡民代表在冲突中被杀死。不管是失手误杀,还是被故意击毙,总之在闹哄哄的现场,有人死了。
我们可以还原下事发现场,赵仁命丧当场,当事双方都感到万分震惊,喧闹的现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按照常理来推断,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肯定会就击毙赵仁一事给出交代。要知道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不是闹着玩的,都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重罪。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就连那些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跟在后面瞎起哄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也要杖责一百,以儆效尤。
官民双方见闹出人命,不再缠斗一处,很快各自散去。按理说,乡民被杀应该是整个事件的爆点。可是事件被推向爆点后,却自行平息,双方不战而退。应该说刘化镇等联庄会会员在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杀之后,内心的愤怒是难以想象的。可是愤怒并没有让刘化镇等人昏头,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刘化镇知道,此时若要杀官复仇,自己这个带头大哥就会背上诛灭九族的重罪。当然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联庄会会首的身份,极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他抓人杀人,表现得极其野蛮粗暴。当闹出人命时,面对着人多势众的联庄会会众,他在权衡利害之后选择了暂时忍耐,任由对方怀恨而去。事后,为了推卸责任,朱光宇上书河南巡抚兼提督英桂,说禹州老百姓抗粮造反,闹出人命。他在上书中只强调“抗粮造反”,却只字未提地方县衙滥加浮收之事。当时,太平军在河南境内正闹得沸腾,“造反”二字是最为敏感的字眼。河南巡抚英桂在接到朱光宇的呈报后,于第一时间派出军队前往禹州平乱。
官民双方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就在镇压官兵整装待发之际,联庄会已经集结好自己的武装开始攻打州城。这是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刘化镇等人在退回乡里后,会再次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卷土重来,这等于正式向官方宣战,将“造反”的罪名坐实?唯一的解释就是,联庄会内部氛围这时候已经完全被岳三教等好勇斗狠之人所掌控。
民间武装力量毕竟不是正规部队,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禹州历来都是中原重镇,城高墙厚,不要说是联庄会,就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了,一时半会想要攻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联庄会的乡军久攻不下时,省府派遣的平乱部队距离禹州已经不到十里的路程。围城的乡民得到情报后,不敢在此恋战,只好再次散去。朱光宇不亏是个“健吏”,他率众一路追杀至联庄会的总部,放火烧毁了联庄会设在高庙的总部所在地。虽然刘化镇带领部下逃到了密县超化镇,可仍旧遭到了地方官兵的围追堵截。
朱光宇传檄密县县令胡燕清,希望能够与之共同围剿刘化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的刘化镇只好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刘化镇的自杀来得过于突然,让所有人都大为不解。这时候的联庄会虽然处于被动局面,可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从刘化镇自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做为联庄会会首的刘化镇虽然有为民请愿的热情,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为乡民利益而造反。他虽然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乡民首领,但却不是有天下蓝图的军事革命家。他希望能够当上带头大哥,不过是为了替乡民主持公道,或者壮大宗族的势力。在艰难的世道里求生存,刘化镇虽然只是个杂货铺或铁匠铺,难以实现人生的大富贵,但是对于一个底层民众来说,他的日子要比一般老百姓富足。
刘化镇在自己的人身没有遇到更大的伤害时,内心受到民间侠义精神的召唤,才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民争利,替那些受到伤害的底层民众谋求公义与公理。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官府将联庄会的行动定位为“造反”时,这要人命的罪责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乡民。
在这种如火烹油的局面下,作为“带头大哥”的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进退得失,对自己所做的事做出新的判断与取舍。
当初,刘化镇出面为乡民伸张正义,并由此成为联庄会会首的时候,估计连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走上一条江湖不归路。当他在沸腾的民意裹胁之下,一跃升级为对抗官府的带头大哥时,他在被迫承担道义责任的同时,内心的惶恐要远远大于“带头大哥”给自己带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造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罪责,不光会让自己陪了前世今生,还会让自己的整个家族受到牵连。刘化镇知道,事已至此,如果仅仅依靠那些目光短浅,且遇事冲动的乡民,事态的发展将会远远超出想象。
刘化镇曾经想过聘用一个有些文化素养的人,作为自己的师爷或者军师。他也曾经邀请过同城举人王成业来担当这个角色,可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聘请举人来担当自己的师爷,他是出于两方面考虑。既可以借用文人的理性来调和联庄会组织内部的非理性因素,同时王举人的特殊身份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规避风险。
王成业在道光年间曾经中过举人,并没有进入官场,一直在家乡做私塾先生。乡间的文化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又加上王成业中过举人,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曾经依照保甲法制订了《民约》,成为维系地方秩序的民间约法。
如果能够将王成业聘请到联庄会,那么将会在联庄会和官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民间社会的权力序列里,举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一个举人犯了罪,地方官府是没有权力将其直接问罪的。只有先上奏朝廷,取消他的举人身份,然后才能进入法律程序。
应该说刘化镇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可毕竟是他的一厢情愿。在王成业这样的乡间文人看来,联庄会聚集的都是一些乡间的好斗分子。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王成业拒绝了刘化镇地好意,他可不想和这些没文化的人搅合在一起。
刘化镇最终在岳三教等好勇斗狠者的裹胁下,一脚踏进了被迫造反的死亡泥潭。刘化镇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和朝廷对抗。当朝廷镇压的消息传来时,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在官兵还没有杀到眼前时,他就选择了自杀了断。
刘化镇的悲剧在于,他只是个有着侠义心肠的江湖之士,而不是可以做大事的领袖人物,他没有领袖的韬略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却不幸被推上了领袖的位置。而他的侠义意识,又使他明知事态日益恶化,却又做不到激流而退明哲保身,在岳三教等人以民怨和义气为感召,提出莽撞的攻城报仇的计划时,他也同样无法后退。而当攻城失利,巡抚派出的镇压大军开到之后,已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他崩溃了。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