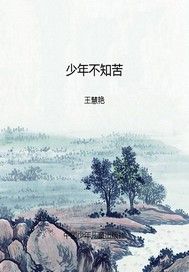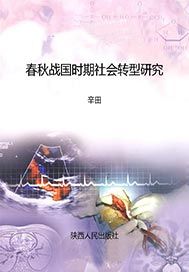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以利益为中心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版图的中央地带,清朝自建国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风平浪静。既然是太平之地,朝廷也就放松了武装戒备,将这一地区的驻防官兵逐步裁减。裁减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我们就拿境内的禹州城来说:在清朝建制之初,基本上市按照明朝的旧制,设立分巡大梁道,驻扎于城内。康熙年间,这个地方大量裁军,就连最基本的防御性武器也撤去不少:“大炮二十八尊,三眼枪二十八杆,俱解省讫,铅子、硝黄并革。”
等时间到了道光年,朝廷又对地方驻军进行了削减,城内所有的马步兵加起来也只有区区四十五名。估计当时稍微有点势力的地方乡绅豢养的民间武装都会超过这个规模。这点人,这点武器,平时扛着武器出来吓唬吓唬那些平日不敢惹事的老百姓还差不多。如果真的碰上不要命的造反者,根本不顶用。
这些守城的军士,并不是清朝的经制军队绿营军。在这里找到一份当时河南绿营军兵力布防情况说明:河南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25人左右,分防汛弁后,小汛只有1—6人,守城兵少的不到10人。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守城的军士官只是地方负责民政工作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守城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临时抽调的丁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民兵,在当时称之为“勇”。
守城当然需要士兵和武器,更少不了粮饷的支持。当时的军队给养,通常是以每人每年食米3石5斗计,一支1000人的部队至少需要3500石。这些粮饷基本上都是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全部取自于民,用之于兵。非但如此,就连那些用来打硬仗的正规军所需要的粮饷也是依靠底层社会的捐输。而基层统治构成的诸多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地方乡绅就成了上层权力系统的依赖对象,州县以下皆自治,这里的自治就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作用力。
这些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在非常时期为朝廷卖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们担负起地方的防御职责,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一方面结寨自保,另一方面也真刀真枪地攻防。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河南省境内,不光一个禹州城的武装力量薄弱,其它各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装备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那些锈迹斑斑的枪炮只是政治走秀时用的道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没来得及渡过黄河的太平天国小股部队,在河南境内能够长驱直入的最根本原因。
河南巡抚陆应谷就是因为剿防不力被朝廷革职,而接任巡抚一职的是满洲正蓝旗人英桂。英桂为了避免重走前任的老路,他在就任河南巡抚之后,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之后,传檄河南各地,着令地方乡绅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
联庄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简单说,也就是联合各村庄武装力量的民团组织,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兵预备役。这种民团组织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有突发性事件,会互相照应、互相支援,进行自卫还击。
既然朝廷的正规军无法担当起抵御流寇侵扰的重任,那么地方官府索性就发动民间武装力量,通过开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经过实践证明,这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既不需要朝廷资粮助饷,更不需要地方官府劳心费力;在化解朝廷眼前困境的同时,又能够让权力集团打着保护老百姓私人利益的旗号将民间力量都争取到自己身边,为己所用。
正是基于以上目的,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河南巡抚英桂才会做出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的决定。
建立联庄会固然是非常时期的一种无奈之举,可也的确能够起到御敌保境的作用,算是纷乱时局下的上选之策。官府号召乡民们拿起武器保护私人财产和自己的家园,在这里地方官府没有提到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只是说保护好老百姓自己的私有财产。
对于乡民们来说,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家资才是最为现实的眼前利益。相对于乡民的私产,而官府更为看重的是地方的稳定。建立联庄会,既可以孤立那些举旗造反的“暴民”,又能够起到节约兵力的目的。
有了官府的支持,乡民“剿匪”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高涨。等到太平军或捻子队伍再次奔袭而来时,他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四散逃命的官兵和老百姓,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乡团举着武器向自己迎面扑来。
这些占据乡土,在自己家门口抵御外敌的联庄会让那些流动作战,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流寇们伤透了脑筋。联庄会的会众是以逸待劳,通常是整乡整族总动员,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可想而知。另外直接参与组建联庄会的,都是那些地方上的乡绅和大户,在地方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实权人物。
联庄会这种民间组织之所以能够以滚雪球的态势发展起来,除了有乡民自保的成分在里面,还有民间社会抱团自肥的谋利行为在其中。在利益的双轮驱动下,其发展势头焉有不快之理。
中国的社会形态其实就是一张庞大的“家国网络图”,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被置于“国”与“家”的大网络体系中。我们习惯了只见国家行使权力,不见社会争取权利。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言,那些寄生于“国”的概念下的权力结构其实是较为粗放的形态;而“家”的概念下基层社会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更多体现于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权力结构末端的补充。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与“国”双线调整下的波浪式推进。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绵延不断,没完没了的匪患和兵祸,使得这种双重权力格局更加凸显无遗,并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由于晚清官场腐败导致上层统治对国家权力逐渐失去掌控力,使其在双重权力格局中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洪秀全的太平军所过之处,各地方政权、绿营军望风而逃。太平军经常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在各府州县城如入无人之境。清廷花大钱打造的绿营军毫无战斗力,进不能战,退不能守。
古代官家制度的权力设置始终处于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悬浮状态,皇权只是高高端坐于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即使有着光芒万丈的辐射力也不能做到通透彻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县衙,县级以下则属于权力自治的范畴。在上层权力格局失去主动权的同时,县以下基层社会统治在双重权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下层权力格局并不需要正式权力的过多介入,它通常是在民约乡规和宗族制度的规范下运行的。这里临时组建起来的民间乡团组织往往会推举那些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乡绅作领袖,承担起维持乡土秩序的责任。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当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绅士代表,完全做到了以乡政取代县政,他们将民间社会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
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其绅士代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试图摆脱这种双重权力格局的束缚,不再尽心竭力地支持上层政权。
在纷乱的社会时局下,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就这样被生生打破,或者说是被撕扯得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中的上层统治也开始渐行渐弱,与之相对应的是下层统治逐渐走强的状况也开始变得日趋明朗化。官府要求地方建立联庄会,他们指定由那些地方的强势人物牵头组建。这些地方强势人物大多是大户出身,家里田产众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要优于普通民众。但是话又说回来,当太平军、捻军或其他匪寇到来时,最先受到冲击的也正是这样一拨手里有钱,地里有田的人。无论是分田,还是分资产,作为有产阶级的他们都要首当其冲。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权力集团无从指望的时候,这些地方大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于筹建地方自卫武装将会变得非常卖力。而在官府之外,也只有这些大户和乡绅们,才有充分的财力和地方影响力,去动员整个乡土社会,联合起来建立联庄会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
当联庄会建立起来之后,这帮人也自然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地联庄会的带头大哥,有钱有田才好说话。
接到现任巡抚英桂的檄令后,禹州城率先行动起来。当然这时候不行动起来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环境可以让那些地方上的脸面人物捞到实在好处,以巩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因为太平军的骑兵曾经一度抵达禹州城下,形成围城之势。禹州城的守城负责人没废多少周折,就在最短的时间里于各里甲建起了联庄会。
在这件事上,官府与民间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短暂的共识。为什么说是短暂的共识,因为在官府、民间力量和太平军三方力量处于利益博弈状态时,这种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识是存在的;可是当其中一方的利益伤害值逐步缩小,他就有可能不再去冒险,甚至撤离利益博弈的困局,那么以利益为纽带的共识也就自然消解。
这时候禹州城内的三方博弈还处于胶着状态,可偏偏节外又横生枝节。禹州城辖区内有一处叫紫金里的地方,当地有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因为某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闹到要告官的程度。在告官之前,双方就找到了紫金里的联庄会首领来主持公道,不出意料的是接到申述的联庄会首领早就被富人花钱买通了。收到好处的首领完全弃公平公正于不顾,在仲裁时明目张胆地偏袒富人。
联庄会首领本身就是地方大户,属于地方上的富人群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这么做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以群分,其实分离的界限往往就是现实利益的界限。另外作为地方大户,他们与那些穷老百姓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隔阂。事情发生之后,地方上下舆论哗然。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紫金里一个叫做刘化镇的人耳朵里。此人是个有侠义心肠,爱打抱不平的人。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出面替这个被欺负的穷人说话,当众指责联庄会首领这么做太不地道,有点欺负穷人的意思。
这个刘化镇并不是普通的乡民,他是一个开过杂货铺的小商人,也有人说他开的是铁匠铺。这种人在民间社会虽然不能与那些财势双全的地方大户相提并论,但也算是乡民中的能人,在民间社会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化镇是个为人仗义,急人所难,有意于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人。其实在底层权力结构中,这种民间能人往往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地方官府当初要求组建联庄会时,像刘化镇这种人也应该是积极分额中一员,甚至还考虑过谋取个首领位置。
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与老实巴交的乡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生存根基并不是完全扎根于土地,他们往往有个一技之长或者脑子比较活泛,会做点小本生意。如果说底层社会的大部分人赚取的是活命之资,那么乡间能人走的就是富裕之路。他们的生存收益介于大户与普通乡民之间,比大户底子薄一些,比普通乡民底子厚一些。可是在注重门阀资历的乡土宗法社会里,像刘化镇这样的社会能人的社会地位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始终不上不下,上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够,下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确还有一些实力。
这种上下不得的状态又让他们心有不甘,始终在寻找利益突围的机会。
恰恰就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这场发生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刘化镇也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才上演了这样一幕,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发并驳斥联庄会首领违背公义,不配做乡民的领头人。
联庄会首领面对刘化镇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感觉到理屈,只好辞去了首领一职。
造成这种局面,至少可以表明两层意思:一是这个辞职的地方大户尚有羞耻之心,还算是个明白之人;二是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刘化镇与普通乡民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在民间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要高于普通乡民。
如若不然,心黑脸皮厚的地方大户绝对不会因为他的两句指责就将首领之位拱手相让。
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他们并不甘心长期居于乡绅大户之下。他们热衷于公众事务并不是学雷锋,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自己民间话语权的最大化,当然并不排除他对于联庄会首领一职的向往。
联庄会首领虽然算不上正式权力系统的官衔,但至少是民间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
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相比,那些大户对于担任联庄会这种武装组织首领却表现得很是纠结。首先拥有乡绅的社会身份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这个身份也让他们成为沟通民间与官方的中介人。危急存亡之际,官府让他们挺身而出成立联庄会,以保家的名义保卫国家现有的权力机制。对此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只要是动刀动枪的事都会有风险,而且是随时会要人命的大风险。那些“流寇”杀来的时候,做为抵抗武装力量的带头大哥,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来自于政治与人身安全两方面,前者的风险性要大于后者。一旦己方在战斗中溃败,那么就会受到对方的惩罚。就算战争结束后找替罪羊,只清算一个人,作为落败方的领头人必然首当其冲。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乡绅大户支持官府在民间设立联庄会,并不代表他们就想站出来当这个带头大哥。
他们对联庄会的热心还是源于利益上的考量,对于出任联庄会首领一职,他们内心的纠结也同样源于利益。
当刘化镇在乡民前面斥责大户不公时,大户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驳,就势辞职。
当这件事传播开来,其他里甲大户好像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路经,也跟着纷纷辞职。
由刘化镇事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很快在禹州以及周边地区的乡绅大户中掀起一股辞职风潮。有人说这是大户之间抱团博利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说这是富人之间讲究“圈子”义气。但是问题是,这种由大户“圈子”所表现出来的援助方式,不是联合,不是抱团对抗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采取了一种决绝的方式——辞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富人“圈子”走的是抱团博利的路子,或者结有政治和利益联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是以退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而是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死磕到底。
为了保护个人丰足的家资,这些大户们对于建立地方武装以自卫的积极性是有的。但是他们对于担任地方武装的带头大哥这件事还是很纠结的,毕竟当带头大哥的风险性在那里摆着。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押在利益博弈的台面上,自己宁愿守着既得利益苟安于世。黄金虽值钱,生命价更高。这是一项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与选择。
地方的乡绅大户以刘化镇事件作为借口,纷纷辞职。没有办法,官府只好将刘化镇这样经济实力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具有公道和侠义之心的人推向前台,更主要的是这帮人有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当时有一大批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成为各地联庄会的新带头大哥,比如岳三教、武宣文、李贤、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纯等等。这些人共同推举刘化镇为会首,并且将联庄会的总部设在了紫金里的高庙。
刘化镇等人就这样由乡间能人转型为乡间强人,而联庄会也由乡绅大户领导的地方团练,转型为普通民众为骨干的地方武装组织。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刘化镇事件的发生,联庄会的转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其实这种转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身份转换。从表面上看,乡间能人接过了联庄会的权柄就有成为乡间强人的可能。可现实却并不是这么简单,作为底层权力结构中的博弈三方,无论是普通民众、乡绅大户,还是地方官府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型带来的祸患。
联庄会的发端是由官方发起的,官方的本意是想借着民间力量来制衡民间力量,以达到利益自保的目的。可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与民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官员可以动用公权力和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可以让公权力成为自己掠夺民间利益的工具。而普通乡民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现实,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们好像永远是弱势的一方。
就算有人并不甘心在现实面前低头弯腰,可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官员在公权力的庇护下,向民间索利的手段更加花样百出,也更加酷烈。食权者恨不得脚下踩的这片土地是中东地区,随便刮地三尺都能见到油水冒出来。此时禹州知县程佶就是这样的官员,他将盘剥乡民的手段用到了极致。
清朝中后期,天下兵祸不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光老百姓会失去生存的安全感,就连那些朝廷官员也同样会迷失于纷乱的时局中。老百姓担心形势的恶化会让他们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将失去,时代洪流不知要将他们这些命运的浮萍卷向哪里?而像禹州知县程佶这样的朝廷官员最担心的两件事,一是现有的权力格局被生生打破,让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或者被完全颠覆;二是像联庄会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正在发展壮大,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前者只会让他陷入更加疯狂的贪婪境地,后者又会让他陷入权力和财富的双重不安之中,他担心正在发展壮大的民间力量一旦拥有和自己坐下来谈条件的资格,结果将会不堪设想。
程佶决定采取行动,既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要扩大自己的利益外延。在当时,一个知府的利益外延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他所能够拥有的正式权力指数,也就是官员的品级;二是他的非正式权力范畴究竟有多宽泛以及他对老百姓的伤害程度有多深。作为一县之长的程佶要保护自己的灰色收入,只能从普通乡民身上下手,通过损害地方乡民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对于一个知县而言,捞取灰色收入的通道主要是来自于赋税,准确地说是正税之外的附加部分。其实纷乱的时局对于官员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国内战争的爆发,让地方官员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当官都愿意当太平官,没有人愿意当一个灭火队员,代价太高,风险性也太大。可乱世有乱世的好处,比如说纷乱的时局能够为他们提供乱中取利的一方舞台,同时也为他们增加赋税捞取私利提供堂而皇之的借口。
禹州知县程佶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于乱世取利的官员,他以地方军费为名,每两银税又加收了340文钱,每斗米则在650文钱之外加收200文。按照《禹县志》记载,当时禹州城的正供赋税为40000余两银子。如果这套方案能够得以顺利推行的话,按照上面的标准推算,禹州地方官府将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每年要多收1000多万文铜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禹州地界的老百姓刚刚经历过蝗灾、旱灾和兵灾的“三灾”洗礼。
当时禹州地界大约有30万人口,官府增收的1000多万文的赋税虽然不是小数目,但是要平摊到30万人的头上,也成不了压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身上都具有很强的生存弹性,松一松,他能够活下去;紧一紧,他同样能够活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官府强加于他们的那一套又一套灰色章程。无非是穷一点,再穷一点。虽然他们清楚,官府这么做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朝廷法度。可没有触及到他们生存的底线,他们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大不了背地里放声骂骂娘也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要了解普通乡民在在缴纳税赋时需要经过多少道程序的盘剥,首先要搞清楚“火耗”究竟是怎么回事。
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老百姓基本上是以银子来抵赋税,也就是由征粮变为征银。老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有多少之分,为了图方便,征银大多是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可是各州县衙府在汇总上缴国库的时候,也为了方便起见,又将老百姓上交的碎银熔炼成大块,然后再上缴。
火耗,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火中耗去的那部分银钱。也就是碎银在火中熔炼过程中会发生损耗,损耗部分总要有人来补足,比猴还精的州县官吏不会认这个账,最后只有将损耗部分摊派给老百姓。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就要多缴纳,多缴的部分也就是“火耗”。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的官方标准,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可是由老百姓认下的“火耗”却要远远大于这个数,据资料显示,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每两银子加耗三四钱,最高的竟然要高达七八钱。当然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的原因,除了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夺外,还与当时官员实行低薪制,朝廷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来变相提高自己的收入有关。清朝建立之初,一个知县的年俸仅有45两,远远不够养家糊口、聘用师爷、贿赂上司、迎来送往的诸多开销。当时像禹州知县程佶的俸银是每年80两银子,但是实际上拿到手只有24两左右。这点钱恐怕连家都养不起,更不用说升官发财了,这显然不符合程佶这样的功利主义文人进入官场谋私利的初衷。
作为知县,程佶只好从火耗征收上来打主意。在征收银钱之外,朝廷也需要大量的粮米,用以皇室和大批京官的利益吞吐。粮米在运送的过程中,是需要运输成本的。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不发达,运输成本也相对较高。而这个运输成本,朝廷将其压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又毫无例外地加摊到了纳税人(农民)身上。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官民利益的二次博弈。很多时候,拥有权力工具的官府衙门和官员也就有了二次侵害纳税人的机会,作为纳税人的乡民也只有接受二次伤害的命运。官府衙门也趁此机会大肆加派,以至到了在一石粮米的正税之外,再加一石米的额外损耗,甚至更多。而这多余的部分,不用说也都中饱了各级官吏的私囊。-
如果说征收银钱是利益集团的供血管道,那么在这条供血的主管道上又分出了若干条支管道。要了解这些利益管道,我们就要先弄清楚几个简单概念。比如说在银钱征收过程中出现的火耗银子、依靠汇率而多收的那些铜钱、以及额外加征的粮米,叫做“羡余”,又叫“平余”。这些所谓的平余银钱,就是地方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州县官吏对多征的火耗也不敢一个人装进腰包,在这条权力生态链上,每个食权者都有分肥的资格。帝国的权力底层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中心血站,知县是这个血站上游的第一节管道,这条管道沿途要先后经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中央衙门和大臣。除了主管道需要奔腾不息的血源,次管道同样需要底层血库的供血,毕竟维系一个官员的权力运转,并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兵作战。但凡有些权力的朝廷命官,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壮大自己的权力产业,毕竟他还要通过自己的权力收入来豢养管家、门客、师爷等等。
道光年间,河南禹州乡民的赋税额目是每两正供税银,加上火耗之后,折算征收制钱2600文;漕米的成本损耗,则是每斗加收650文。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朝廷的军费开支也徒然升级,国家可供利用的库银也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银价跟着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还按照原来的额度来征收铜钱,那么将其折换成银子之后,除去应该上缴国库的那部分,地方官员能够获取的灰色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
混迹官场多年的程佶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是促使程佶伸手向老百姓刮地皮的根本原因。作为知县程佶的政治经验还是很有一套的,但是他信奉的那套顺民可欺的定律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成立。比如说当乡民抱团与官争利时,这个定律就会失去作用。
这时候的禹州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以程佶为首的官府与民争利;一面是以刘化镇为首的联庄会与官府争利。当然这里的两个“利”,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灰色收入,后者是自己的应得之利。
禹州还是那个禹州,乡民也还是那些乡民。不同的是,作为个体的乡民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乡民组织——联庄会。当官府派出的胥吏拿着鸡毛当令箭踢开门催粮时,乡民们去寻求组织的庇护。联庄会本来就是乡民组织,随着那些乡绅大户从领导层退出,联庄会比以往更具有平民化。尤其是刘化镇、岳三教这样的带头大哥成功上位后,完全是以民间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乡民面前。只要乡民有难,就会激发他们身上那股江湖儿女的侠义热情,路见不平一声吼。做为带头大哥,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乡民伸张正义。当然这也是乡间能人成为乡间强人所必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然他们拿什么让乡民信服。
如此一来,联庄会就成了乡民维护个体利益不受侵害的民间组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基层工会。乡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必然要动用力量与侵害者对抗,也就是抗粮。这也是清朝建制以来,禹州农民第一次以民间组织的形式与官府直接对抗,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帮人的抗争,这是底层社会权力形式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这种变化是禹州知县程佶始料未及的,他遇上了超出自己政治经验之外的权力困境。
那些准备动用暴力机器的胥吏,在面对一个民间组织时,就像是一条狗围着一个刺猬打转,却不知道从何处下嘴。这种局面如果打破不了,最后的结局不是狗疯狂了,就是狗与刺猬两败俱伤。
无所适从的程知县就这样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来改变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话,民众沸腾的情绪将有可能酿出更大的祸端。这是程佶最为担心的事,当务之急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捞取灰色收入,结果却激起了民愤,酿出了民变。禹州城外,太平军虎视眈眈;禹州城内,官民碰撞对抗。对于程知县来说,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要想真正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修改征粮方案,尤其是降低强加于老百姓的赋税标准。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地方官员在这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动权正在逐步丧失。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那就是以官府的暴力机器作为制度的开道手段,继续向乡民施加压力,强制征赋,为此不惜激起民变,然后再用一场血腥的杀人游戏来镇压那些抗粮到底的乡民。
虽然程知县是个财迷加官迷,可是他此时却没有继续再走下去的勇气和胆量。对于程知县来说,他既不想重新修改已经颁布的规章制度,免得世人以为官家制度是闹着玩的儿戏。更重要的是,一旦他废除或者降低修改标准,那么他就等于是破坏了官员生存游戏的潜规则,等待着他的还有来自于权力系统上游的惩罚。这真是一道让人纠结的选择题,可他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时此刻,知县程佶必然会为当初加派浮收的举动追悔不已。经过内心的百般纠结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辞官。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索性撂挑子不干,至少在现实世界里可以做到明哲保身。
等时间到了道光年,朝廷又对地方驻军进行了削减,城内所有的马步兵加起来也只有区区四十五名。估计当时稍微有点势力的地方乡绅豢养的民间武装都会超过这个规模。这点人,这点武器,平时扛着武器出来吓唬吓唬那些平日不敢惹事的老百姓还差不多。如果真的碰上不要命的造反者,根本不顶用。
这些守城的军士,并不是清朝的经制军队绿营军。在这里找到一份当时河南绿营军兵力布防情况说明:河南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25人左右,分防汛弁后,小汛只有1—6人,守城兵少的不到10人。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守城的军士官只是地方负责民政工作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守城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临时抽调的丁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民兵,在当时称之为“勇”。
守城当然需要士兵和武器,更少不了粮饷的支持。当时的军队给养,通常是以每人每年食米3石5斗计,一支1000人的部队至少需要3500石。这些粮饷基本上都是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全部取自于民,用之于兵。非但如此,就连那些用来打硬仗的正规军所需要的粮饷也是依靠底层社会的捐输。而基层统治构成的诸多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地方乡绅就成了上层权力系统的依赖对象,州县以下皆自治,这里的自治就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作用力。
这些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在非常时期为朝廷卖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们担负起地方的防御职责,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一方面结寨自保,另一方面也真刀真枪地攻防。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河南省境内,不光一个禹州城的武装力量薄弱,其它各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装备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那些锈迹斑斑的枪炮只是政治走秀时用的道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没来得及渡过黄河的太平天国小股部队,在河南境内能够长驱直入的最根本原因。
河南巡抚陆应谷就是因为剿防不力被朝廷革职,而接任巡抚一职的是满洲正蓝旗人英桂。英桂为了避免重走前任的老路,他在就任河南巡抚之后,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之后,传檄河南各地,着令地方乡绅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
联庄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简单说,也就是联合各村庄武装力量的民团组织,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兵预备役。这种民团组织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有突发性事件,会互相照应、互相支援,进行自卫还击。
既然朝廷的正规军无法担当起抵御流寇侵扰的重任,那么地方官府索性就发动民间武装力量,通过开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经过实践证明,这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既不需要朝廷资粮助饷,更不需要地方官府劳心费力;在化解朝廷眼前困境的同时,又能够让权力集团打着保护老百姓私人利益的旗号将民间力量都争取到自己身边,为己所用。
正是基于以上目的,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河南巡抚英桂才会做出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的决定。
建立联庄会固然是非常时期的一种无奈之举,可也的确能够起到御敌保境的作用,算是纷乱时局下的上选之策。官府号召乡民们拿起武器保护私人财产和自己的家园,在这里地方官府没有提到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只是说保护好老百姓自己的私有财产。
对于乡民们来说,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家资才是最为现实的眼前利益。相对于乡民的私产,而官府更为看重的是地方的稳定。建立联庄会,既可以孤立那些举旗造反的“暴民”,又能够起到节约兵力的目的。
有了官府的支持,乡民“剿匪”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高涨。等到太平军或捻子队伍再次奔袭而来时,他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四散逃命的官兵和老百姓,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乡团举着武器向自己迎面扑来。
这些占据乡土,在自己家门口抵御外敌的联庄会让那些流动作战,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流寇们伤透了脑筋。联庄会的会众是以逸待劳,通常是整乡整族总动员,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可想而知。另外直接参与组建联庄会的,都是那些地方上的乡绅和大户,在地方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实权人物。
联庄会这种民间组织之所以能够以滚雪球的态势发展起来,除了有乡民自保的成分在里面,还有民间社会抱团自肥的谋利行为在其中。在利益的双轮驱动下,其发展势头焉有不快之理。
中国的社会形态其实就是一张庞大的“家国网络图”,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被置于“国”与“家”的大网络体系中。我们习惯了只见国家行使权力,不见社会争取权利。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言,那些寄生于“国”的概念下的权力结构其实是较为粗放的形态;而“家”的概念下基层社会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更多体现于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权力结构末端的补充。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与“国”双线调整下的波浪式推进。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绵延不断,没完没了的匪患和兵祸,使得这种双重权力格局更加凸显无遗,并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由于晚清官场腐败导致上层统治对国家权力逐渐失去掌控力,使其在双重权力格局中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洪秀全的太平军所过之处,各地方政权、绿营军望风而逃。太平军经常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在各府州县城如入无人之境。清廷花大钱打造的绿营军毫无战斗力,进不能战,退不能守。
古代官家制度的权力设置始终处于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悬浮状态,皇权只是高高端坐于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即使有着光芒万丈的辐射力也不能做到通透彻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县衙,县级以下则属于权力自治的范畴。在上层权力格局失去主动权的同时,县以下基层社会统治在双重权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下层权力格局并不需要正式权力的过多介入,它通常是在民约乡规和宗族制度的规范下运行的。这里临时组建起来的民间乡团组织往往会推举那些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乡绅作领袖,承担起维持乡土秩序的责任。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当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绅士代表,完全做到了以乡政取代县政,他们将民间社会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
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其绅士代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试图摆脱这种双重权力格局的束缚,不再尽心竭力地支持上层政权。
在纷乱的社会时局下,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就这样被生生打破,或者说是被撕扯得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中的上层统治也开始渐行渐弱,与之相对应的是下层统治逐渐走强的状况也开始变得日趋明朗化。官府要求地方建立联庄会,他们指定由那些地方的强势人物牵头组建。这些地方强势人物大多是大户出身,家里田产众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要优于普通民众。但是话又说回来,当太平军、捻军或其他匪寇到来时,最先受到冲击的也正是这样一拨手里有钱,地里有田的人。无论是分田,还是分资产,作为有产阶级的他们都要首当其冲。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权力集团无从指望的时候,这些地方大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于筹建地方自卫武装将会变得非常卖力。而在官府之外,也只有这些大户和乡绅们,才有充分的财力和地方影响力,去动员整个乡土社会,联合起来建立联庄会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
当联庄会建立起来之后,这帮人也自然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地联庄会的带头大哥,有钱有田才好说话。
接到现任巡抚英桂的檄令后,禹州城率先行动起来。当然这时候不行动起来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环境可以让那些地方上的脸面人物捞到实在好处,以巩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因为太平军的骑兵曾经一度抵达禹州城下,形成围城之势。禹州城的守城负责人没废多少周折,就在最短的时间里于各里甲建起了联庄会。
在这件事上,官府与民间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短暂的共识。为什么说是短暂的共识,因为在官府、民间力量和太平军三方力量处于利益博弈状态时,这种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识是存在的;可是当其中一方的利益伤害值逐步缩小,他就有可能不再去冒险,甚至撤离利益博弈的困局,那么以利益为纽带的共识也就自然消解。
这时候禹州城内的三方博弈还处于胶着状态,可偏偏节外又横生枝节。禹州城辖区内有一处叫紫金里的地方,当地有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因为某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闹到要告官的程度。在告官之前,双方就找到了紫金里的联庄会首领来主持公道,不出意料的是接到申述的联庄会首领早就被富人花钱买通了。收到好处的首领完全弃公平公正于不顾,在仲裁时明目张胆地偏袒富人。
联庄会首领本身就是地方大户,属于地方上的富人群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这么做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以群分,其实分离的界限往往就是现实利益的界限。另外作为地方大户,他们与那些穷老百姓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隔阂。事情发生之后,地方上下舆论哗然。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紫金里一个叫做刘化镇的人耳朵里。此人是个有侠义心肠,爱打抱不平的人。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出面替这个被欺负的穷人说话,当众指责联庄会首领这么做太不地道,有点欺负穷人的意思。
这个刘化镇并不是普通的乡民,他是一个开过杂货铺的小商人,也有人说他开的是铁匠铺。这种人在民间社会虽然不能与那些财势双全的地方大户相提并论,但也算是乡民中的能人,在民间社会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化镇是个为人仗义,急人所难,有意于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人。其实在底层权力结构中,这种民间能人往往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地方官府当初要求组建联庄会时,像刘化镇这种人也应该是积极分额中一员,甚至还考虑过谋取个首领位置。
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与老实巴交的乡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生存根基并不是完全扎根于土地,他们往往有个一技之长或者脑子比较活泛,会做点小本生意。如果说底层社会的大部分人赚取的是活命之资,那么乡间能人走的就是富裕之路。他们的生存收益介于大户与普通乡民之间,比大户底子薄一些,比普通乡民底子厚一些。可是在注重门阀资历的乡土宗法社会里,像刘化镇这样的社会能人的社会地位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始终不上不下,上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够,下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确还有一些实力。
这种上下不得的状态又让他们心有不甘,始终在寻找利益突围的机会。
恰恰就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这场发生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刘化镇也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才上演了这样一幕,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发并驳斥联庄会首领违背公义,不配做乡民的领头人。
联庄会首领面对刘化镇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感觉到理屈,只好辞去了首领一职。
造成这种局面,至少可以表明两层意思:一是这个辞职的地方大户尚有羞耻之心,还算是个明白之人;二是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刘化镇与普通乡民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在民间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要高于普通乡民。
如若不然,心黑脸皮厚的地方大户绝对不会因为他的两句指责就将首领之位拱手相让。
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他们并不甘心长期居于乡绅大户之下。他们热衷于公众事务并不是学雷锋,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自己民间话语权的最大化,当然并不排除他对于联庄会首领一职的向往。
联庄会首领虽然算不上正式权力系统的官衔,但至少是民间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
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相比,那些大户对于担任联庄会这种武装组织首领却表现得很是纠结。首先拥有乡绅的社会身份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这个身份也让他们成为沟通民间与官方的中介人。危急存亡之际,官府让他们挺身而出成立联庄会,以保家的名义保卫国家现有的权力机制。对此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只要是动刀动枪的事都会有风险,而且是随时会要人命的大风险。那些“流寇”杀来的时候,做为抵抗武装力量的带头大哥,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来自于政治与人身安全两方面,前者的风险性要大于后者。一旦己方在战斗中溃败,那么就会受到对方的惩罚。就算战争结束后找替罪羊,只清算一个人,作为落败方的领头人必然首当其冲。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乡绅大户支持官府在民间设立联庄会,并不代表他们就想站出来当这个带头大哥。
他们对联庄会的热心还是源于利益上的考量,对于出任联庄会首领一职,他们内心的纠结也同样源于利益。
当刘化镇在乡民前面斥责大户不公时,大户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驳,就势辞职。
当这件事传播开来,其他里甲大户好像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路经,也跟着纷纷辞职。
由刘化镇事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很快在禹州以及周边地区的乡绅大户中掀起一股辞职风潮。有人说这是大户之间抱团博利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说这是富人之间讲究“圈子”义气。但是问题是,这种由大户“圈子”所表现出来的援助方式,不是联合,不是抱团对抗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采取了一种决绝的方式——辞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富人“圈子”走的是抱团博利的路子,或者结有政治和利益联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是以退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而是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死磕到底。
为了保护个人丰足的家资,这些大户们对于建立地方武装以自卫的积极性是有的。但是他们对于担任地方武装的带头大哥这件事还是很纠结的,毕竟当带头大哥的风险性在那里摆着。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押在利益博弈的台面上,自己宁愿守着既得利益苟安于世。黄金虽值钱,生命价更高。这是一项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与选择。
地方的乡绅大户以刘化镇事件作为借口,纷纷辞职。没有办法,官府只好将刘化镇这样经济实力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具有公道和侠义之心的人推向前台,更主要的是这帮人有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当时有一大批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成为各地联庄会的新带头大哥,比如岳三教、武宣文、李贤、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纯等等。这些人共同推举刘化镇为会首,并且将联庄会的总部设在了紫金里的高庙。
刘化镇等人就这样由乡间能人转型为乡间强人,而联庄会也由乡绅大户领导的地方团练,转型为普通民众为骨干的地方武装组织。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刘化镇事件的发生,联庄会的转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其实这种转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身份转换。从表面上看,乡间能人接过了联庄会的权柄就有成为乡间强人的可能。可现实却并不是这么简单,作为底层权力结构中的博弈三方,无论是普通民众、乡绅大户,还是地方官府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型带来的祸患。
联庄会的发端是由官方发起的,官方的本意是想借着民间力量来制衡民间力量,以达到利益自保的目的。可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与民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官员可以动用公权力和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可以让公权力成为自己掠夺民间利益的工具。而普通乡民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现实,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们好像永远是弱势的一方。
就算有人并不甘心在现实面前低头弯腰,可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官员在公权力的庇护下,向民间索利的手段更加花样百出,也更加酷烈。食权者恨不得脚下踩的这片土地是中东地区,随便刮地三尺都能见到油水冒出来。此时禹州知县程佶就是这样的官员,他将盘剥乡民的手段用到了极致。
清朝中后期,天下兵祸不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光老百姓会失去生存的安全感,就连那些朝廷官员也同样会迷失于纷乱的时局中。老百姓担心形势的恶化会让他们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将失去,时代洪流不知要将他们这些命运的浮萍卷向哪里?而像禹州知县程佶这样的朝廷官员最担心的两件事,一是现有的权力格局被生生打破,让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或者被完全颠覆;二是像联庄会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正在发展壮大,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前者只会让他陷入更加疯狂的贪婪境地,后者又会让他陷入权力和财富的双重不安之中,他担心正在发展壮大的民间力量一旦拥有和自己坐下来谈条件的资格,结果将会不堪设想。
程佶决定采取行动,既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要扩大自己的利益外延。在当时,一个知府的利益外延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他所能够拥有的正式权力指数,也就是官员的品级;二是他的非正式权力范畴究竟有多宽泛以及他对老百姓的伤害程度有多深。作为一县之长的程佶要保护自己的灰色收入,只能从普通乡民身上下手,通过损害地方乡民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对于一个知县而言,捞取灰色收入的通道主要是来自于赋税,准确地说是正税之外的附加部分。其实纷乱的时局对于官员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国内战争的爆发,让地方官员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当官都愿意当太平官,没有人愿意当一个灭火队员,代价太高,风险性也太大。可乱世有乱世的好处,比如说纷乱的时局能够为他们提供乱中取利的一方舞台,同时也为他们增加赋税捞取私利提供堂而皇之的借口。
禹州知县程佶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于乱世取利的官员,他以地方军费为名,每两银税又加收了340文钱,每斗米则在650文钱之外加收200文。按照《禹县志》记载,当时禹州城的正供赋税为40000余两银子。如果这套方案能够得以顺利推行的话,按照上面的标准推算,禹州地方官府将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每年要多收1000多万文铜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禹州地界的老百姓刚刚经历过蝗灾、旱灾和兵灾的“三灾”洗礼。
当时禹州地界大约有30万人口,官府增收的1000多万文的赋税虽然不是小数目,但是要平摊到30万人的头上,也成不了压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身上都具有很强的生存弹性,松一松,他能够活下去;紧一紧,他同样能够活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官府强加于他们的那一套又一套灰色章程。无非是穷一点,再穷一点。虽然他们清楚,官府这么做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朝廷法度。可没有触及到他们生存的底线,他们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大不了背地里放声骂骂娘也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要了解普通乡民在在缴纳税赋时需要经过多少道程序的盘剥,首先要搞清楚“火耗”究竟是怎么回事。
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老百姓基本上是以银子来抵赋税,也就是由征粮变为征银。老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有多少之分,为了图方便,征银大多是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可是各州县衙府在汇总上缴国库的时候,也为了方便起见,又将老百姓上交的碎银熔炼成大块,然后再上缴。
火耗,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火中耗去的那部分银钱。也就是碎银在火中熔炼过程中会发生损耗,损耗部分总要有人来补足,比猴还精的州县官吏不会认这个账,最后只有将损耗部分摊派给老百姓。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就要多缴纳,多缴的部分也就是“火耗”。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的官方标准,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可是由老百姓认下的“火耗”却要远远大于这个数,据资料显示,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每两银子加耗三四钱,最高的竟然要高达七八钱。当然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的原因,除了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夺外,还与当时官员实行低薪制,朝廷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来变相提高自己的收入有关。清朝建立之初,一个知县的年俸仅有45两,远远不够养家糊口、聘用师爷、贿赂上司、迎来送往的诸多开销。当时像禹州知县程佶的俸银是每年80两银子,但是实际上拿到手只有24两左右。这点钱恐怕连家都养不起,更不用说升官发财了,这显然不符合程佶这样的功利主义文人进入官场谋私利的初衷。
作为知县,程佶只好从火耗征收上来打主意。在征收银钱之外,朝廷也需要大量的粮米,用以皇室和大批京官的利益吞吐。粮米在运送的过程中,是需要运输成本的。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不发达,运输成本也相对较高。而这个运输成本,朝廷将其压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又毫无例外地加摊到了纳税人(农民)身上。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官民利益的二次博弈。很多时候,拥有权力工具的官府衙门和官员也就有了二次侵害纳税人的机会,作为纳税人的乡民也只有接受二次伤害的命运。官府衙门也趁此机会大肆加派,以至到了在一石粮米的正税之外,再加一石米的额外损耗,甚至更多。而这多余的部分,不用说也都中饱了各级官吏的私囊。-
如果说征收银钱是利益集团的供血管道,那么在这条供血的主管道上又分出了若干条支管道。要了解这些利益管道,我们就要先弄清楚几个简单概念。比如说在银钱征收过程中出现的火耗银子、依靠汇率而多收的那些铜钱、以及额外加征的粮米,叫做“羡余”,又叫“平余”。这些所谓的平余银钱,就是地方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州县官吏对多征的火耗也不敢一个人装进腰包,在这条权力生态链上,每个食权者都有分肥的资格。帝国的权力底层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中心血站,知县是这个血站上游的第一节管道,这条管道沿途要先后经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中央衙门和大臣。除了主管道需要奔腾不息的血源,次管道同样需要底层血库的供血,毕竟维系一个官员的权力运转,并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兵作战。但凡有些权力的朝廷命官,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壮大自己的权力产业,毕竟他还要通过自己的权力收入来豢养管家、门客、师爷等等。
道光年间,河南禹州乡民的赋税额目是每两正供税银,加上火耗之后,折算征收制钱2600文;漕米的成本损耗,则是每斗加收650文。到了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朝廷的军费开支也徒然升级,国家可供利用的库银也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银价跟着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还按照原来的额度来征收铜钱,那么将其折换成银子之后,除去应该上缴国库的那部分,地方官员能够获取的灰色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
混迹官场多年的程佶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是促使程佶伸手向老百姓刮地皮的根本原因。作为知县程佶的政治经验还是很有一套的,但是他信奉的那套顺民可欺的定律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成立。比如说当乡民抱团与官争利时,这个定律就会失去作用。
这时候的禹州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以程佶为首的官府与民争利;一面是以刘化镇为首的联庄会与官府争利。当然这里的两个“利”,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灰色收入,后者是自己的应得之利。
禹州还是那个禹州,乡民也还是那些乡民。不同的是,作为个体的乡民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乡民组织——联庄会。当官府派出的胥吏拿着鸡毛当令箭踢开门催粮时,乡民们去寻求组织的庇护。联庄会本来就是乡民组织,随着那些乡绅大户从领导层退出,联庄会比以往更具有平民化。尤其是刘化镇、岳三教这样的带头大哥成功上位后,完全是以民间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乡民面前。只要乡民有难,就会激发他们身上那股江湖儿女的侠义热情,路见不平一声吼。做为带头大哥,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乡民伸张正义。当然这也是乡间能人成为乡间强人所必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然他们拿什么让乡民信服。
如此一来,联庄会就成了乡民维护个体利益不受侵害的民间组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基层工会。乡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必然要动用力量与侵害者对抗,也就是抗粮。这也是清朝建制以来,禹州农民第一次以民间组织的形式与官府直接对抗,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帮人的抗争,这是底层社会权力形式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这种变化是禹州知县程佶始料未及的,他遇上了超出自己政治经验之外的权力困境。
那些准备动用暴力机器的胥吏,在面对一个民间组织时,就像是一条狗围着一个刺猬打转,却不知道从何处下嘴。这种局面如果打破不了,最后的结局不是狗疯狂了,就是狗与刺猬两败俱伤。
无所适从的程知县就这样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来改变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话,民众沸腾的情绪将有可能酿出更大的祸端。这是程佶最为担心的事,当务之急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捞取灰色收入,结果却激起了民愤,酿出了民变。禹州城外,太平军虎视眈眈;禹州城内,官民碰撞对抗。对于程知县来说,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要想真正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修改征粮方案,尤其是降低强加于老百姓的赋税标准。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地方官员在这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动权正在逐步丧失。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那就是以官府的暴力机器作为制度的开道手段,继续向乡民施加压力,强制征赋,为此不惜激起民变,然后再用一场血腥的杀人游戏来镇压那些抗粮到底的乡民。
虽然程知县是个财迷加官迷,可是他此时却没有继续再走下去的勇气和胆量。对于程知县来说,他既不想重新修改已经颁布的规章制度,免得世人以为官家制度是闹着玩的儿戏。更重要的是,一旦他废除或者降低修改标准,那么他就等于是破坏了官员生存游戏的潜规则,等待着他的还有来自于权力系统上游的惩罚。这真是一道让人纠结的选择题,可他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时此刻,知县程佶必然会为当初加派浮收的举动追悔不已。经过内心的百般纠结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辞官。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索性撂挑子不干,至少在现实世界里可以做到明哲保身。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