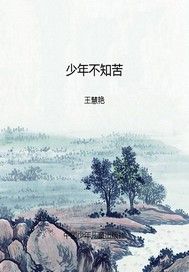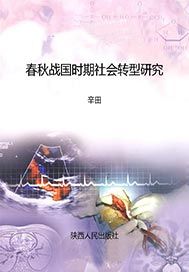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七章 皇权的亲密敌人
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刚刚登上帝位不久的朱元璋接见了江南首富沈万三,在这次会面中,国家之主与财富之王有过一次非常精彩的对话。能够得到帝国新主人的召见,沈万三的内心自然有着极大的满足和得意。这时候的沈万三,还无法预见十年后自己的人生结局。在他的观念里,一个拥有财富的男人,和一个拥有权力的男人,就算不是平等的,最起码也是利益伙伴。帝国首富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拥有的财富有一天会被权力血盆大口吞噬,而自己也就此沦陷于万劫不复的泥沼。
中国有句老话“富贵险中求”,也就是说商人是一群风险偏好者,他们的富贵往往伴随着风险。在古代的商业环境中,商人们险中求来的并不是大富贵,只是赚些活命之资罢了,大的富贵只能在权力系统中寻求。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官商这个共同体。官商,一半是权力,另一半是经济势力,是权力与经济的畸形结合。买卖关系是官商结合的基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是权力集团的社会效益,与市场经济的平等契约精神没有多大的关系。官商的出现,使社会商业完全成为一种特权者的游戏,生产经营并没有按照商业定律在运行。古代政治制度放大了这种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行为,这样就等于打破了正常的市场规则。
在秦朝统一之前,商业虽然不是社会结构中的主流,但还是足够发达的,所谓的商业网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商业活动受到了权力集团的抑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代,这一倾向也是反反复复。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抑商政策达到了巅峰,在当时但凡能够盈利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权力集团所控制。
中国封建时代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权力集团作为国家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手中掌握着对老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选择将权力直接兑换成财富。商人地位处于“四民之末”,由于其社会地位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不稳定性,使得自己的利益无从保证。他们既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承担买卖亏本的风险,另外还有各级官府的盘剥,地方黑势力的敲诈和掠夺。为了乱世求得生存,他们就要在权力集团中寻求庇护。因为只有权力才能超越经济力量。而这种庇护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我出钱你出权,然后谋取利益再共同分割。这样就造成了官商勾结的恶性关系,在商人们看来,要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奉行“是官当敬”游戏规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口袋鼓鼓的富商大贾就有“游诸侯”、“交将相”的光荣传统。一个商人要想立足于规则大于法制的时代,肯定要用手中财富打开权力的通道。
有了权力的保驾护航,商业在盛唐和南宋时期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到了明正德、嘉靖以后,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改观,国家允许商人子弟进入官家的权力系统,这样就打破了长久以来不许商人子弟入仕为官的禁锢。随着商人子弟不断进入官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抬高。而这些进入权力系统的商人子弟,又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反哺商业。这样就使得官商一体化愈演愈烈,权力与财富一起水涨船高。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影响力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时候,与很多商人一样,对于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远离,也不亲近的态度,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市场调节”。相邻吴江县的巨富陆老先生一句话点醒沈万三:“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巨富,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动”规则或者说是官商博弈之术。沈万三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机遇、时势和个人的投资眼光。
一是粮食生产与土地兼并成为沈万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记载“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资料显示,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在财富的累计与权力的递增之路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机遇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动荡的乱世里博取生存之资。沈万三在发展的路上,还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
二是依托时势,让沈万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条捷径,沈万三的财富王国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元朝末年,各地农民军风起云涌。沈万三抓住机会,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地区,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然后再依靠张士诚的武装保护将其提供的私盐倒卖出去(张士诚的队伍大多具备盐民身份)。可以说沈万三发的是战争财,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单生意做下来,沈万三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他以跳楼价买下大半个苏州的商业,投入数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以躲避战祸。沈万三和张士诚很熟,凭着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士诚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同行们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凭此一战,沈万三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商,成为天下首富。
三是借助皇家权力管道实现财富累积。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不利条件下,沈万三居然可以打着皇家的龙旗,开着十几条船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大肆走私。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张士诚曾经降元,元政府令他从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于是张士诚则将这件事交予沈万三具体操办。沈万三知道,政府长期禁海,出海贸易必定是一场暴利之旅。于是,沈万三在朝廷的船里,一半装上粮食,另一半装上自己的私货,皇船打着龙旗,大摇大摆,一路畅通无阻。出了长江,沈万三便兵分两路,装皇粮的北上复命,而承载私货的船则扬帆南下直接开往东南亚去发财。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货物,卖到东南亚,都是数十数百倍的暴利。沈万三船队随行人员中,有人带了一些成本只有5两银子一筐的桔子,居然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可以卖到几两银子一个,一筐桔子,卖到了1000两银子。从南洋回来,沈万三的财富已经滚雪球似的达到十几亿两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沈万三的财富之路,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有勇气和造反者张士诚合伙做走私生意,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其关键所在。这样的生意,做早了风险性太高,随时都会有掉脑袋的可能性,而做晚了就有可能丧失机会。
沈万三敢于在张士诚打苏州前,倾其所有,买下大半个苏州商业,靠的是他的政治敏锐性。他在社会的恶风大浪中,准确判断了形势的走向。至于走私南洋大发洋财,则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资源,特别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证这样的政策资源。财富和政治资源给沈万三的人生带来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最后也让他输的很惨。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于这些豪族巨富们来说,这无疑于是一场财富的轮盘赌。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助他购粮扩军。后来,沈万三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进入权力系统,甚至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有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经结拜为异姓兄弟。
南京城原有十三道城门,南门又被称作聚宝门,据说这段城墙是由沈万三所筑。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初,国库空虚,就让沈万三资筑东南诸城。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欢心,沈万三不惜花重金买宠。结果皇家出资建造的西北城还没有建造成形,沈万三的东南城就已经提前竣工了。筑城还不够表达自己的忠心,沈万三又献出白金2 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帝国上下对沈万三此举无不称颂不已。可是沈万三这么做,却大大触痛了一个人的敏感神经,那个人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这个出身于草根的皇帝,似乎与权贵有着天生的敌意。
明末《云焦馆纪谈》说得更加具体,朱元璋和沈万三约好同时开工,结果被沈万三抢先三天完工。在庆功会上,朱元璋举着酒杯对沈万三说:“古有白衣天子一说,号称素封,你就是个白衣天子。”这句话表面上听着像是夸奖,可话里已经隐隐透出了杀机,大明江山岂能容许两个天子并存于世?
有一天,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发奇想,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帝国军队。
朱元璋听后。脸色十分难看,冷冷地说道:“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拍着胸脯说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万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种志得意满的表情。自己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犒劳帝国军队,既可取悦皇帝,又可以炫耀财富。可是他并没注意到朱元璋变幻莫测的脸色下藏着深重的忧虑。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对话:朱元璋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这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马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家天下”的皇权年代,家国一体,这天下的一切都是我皇家的,一个不自量力的商人居然要犒劳皇家军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皇后的意思是告诉朱元璋,现在还远没有到杀了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在开国之初都会呈现出貌似宏大宽松的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朱元璋的时代也同样不例外。洪武初年,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可是等到政权稍有稳定,朱元璋对工商的态度立即发生微妙的变化。
每次王朝更迭,旧词翻新阙的建政者都会吸取前朝败亡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对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败亡的历史现实也同样做出总结:“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蒙元帝国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权涣散的境地,是因为民间的势力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天下祸乱。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个商人居然想要犒劳三军,这让自己这个皇帝的脸该往哪里搁?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打拼上来,吃了太多的苦,更见识过太多的社会黑暗面,这或许成为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决心所在。作为来自民间草根阶层,朱元璋对商人有着天生的敌意。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没有之一。
朱元璋不仅没有赋予商人某种特权,甚至通过一些不合常理的制度来限制和束缚他们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面,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可是他并有考虑到,无利可图的农民即使有权利穿高档服装,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够穿得起,却没有穿的权利,他们也只好将绫罗绸缎烂在自家的箱底。不仅如此,商人在科举和仕途上,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而那些商人们整天只知道耍些坑蒙拐骗的卑劣手段去谋取暴利,却从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生产任何产品。他们依靠财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所在,是社会稳压器上最危险的隐患所在。
朱元璋的逻辑来自于小农的利益计算方式,简单而现实,他认为:沈万三既然有养活军队的庞大财力,那么他就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叛乱的现实行为,也应该将其列为打击的对象或者平灭的乱民。
如果我们把朱元璋的帝国战略分为左右手,那么他在运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右手则用来打击富商和地主。朱元璋并不建立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可是他也不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将会被财富者赶出土地,农民则会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颠沛于江湖之上的朱元璋就是一个流民,对此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将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地方的富商地主。史料记载,三吴地区的豪族大姓在离开故土后就成了离水之鱼,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资产也流失殆尽。在数年之内,这些离乡背井之人或死或迁,无一存者。他们留恋曾经的富足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乡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又先后两次,将天下将近7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又一次伤筋动骨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做出评论:“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对于商人阶层采取“先用之,后弃之”的使用策略,朱元璋并不是历史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这种对待商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通之处。朱元璋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为帝国的财富战略之后,沈万三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朱元璋的一系列铁血政策嗅到了扑面而来的风险气息。为免树大招风,沈万三主动将偌大的家族资产分割为四户。沈家有人被举荐到京师为官,沈万三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辞:“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沈万三希望用财富为当权者分忧解难,也借此利用皇权为自己的财富之路保驾护航。可是他哪里晓得,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博得朱元璋的欢心,反而适得其反。当沈万三进一步进贡龙角、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马十匹,并在南京城内投资兴建廊庑酒楼时,朱元璋彻底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财富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朱元璋这个帝国的当权者无法容忍的,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权力的垄断,还是财富的垄断,高利润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沈家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沈万三的倒下,而全盘尽墨。
《弘治吴江志》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亲、户部左侍郎的莫礼回乡省亲,特地到周庄沈家拜访,见到“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莫礼看到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自己,已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风险。“呜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莫礼返乡探亲时的历史背景。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蓝党案”的高潮,三月间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朱梓和王妃于氏竟然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被朱元璋称为“朕之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也被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背景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乡期间写下《归吴江省亲》一诗,诗云:“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在朱元璋的时代里为官是一件高风险的事,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礼一道回家的侄儿莫辕也写下一副对联:“世路风波今暂息,惊心犹觉骨毛寒。”
沈家姻亲如此如此高规格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让莫氏叔侄回乡之旅惊心不已。沈万三的后人并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还是希望能够用财富沟通权力。可是官员的处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财富于他们而言,只能是让他们心惊肉跳的麻烦与负担而已。
在家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财富。财富通常是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与之相反,如果财富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会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农耕社会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制度为每个人设计好了财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制度,通过非农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会被视为异类。
事实上,古代官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那些贴金挂银的所谓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贫困的。于是才有了元朝诗人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声叹息。
沈万三成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官家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永远不会结束。《明史·纪纲传》中记载:朱元璋驾崩后,燕王朱棣从北京举兵一直打到南京,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的心腹官员,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这个人非常善于敛财,曾经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家财富已经被朱元璋抄没,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万三的儿子沈文度匍匐于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分账。
尽管如此,沈万三的后人依然难以逃脱财富带来的命运之劫,两个孙子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那就是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那么商人和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话“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作为权力最亲密的战友和宠儿,沈万三的财富来自于权力的庇护,同样又失之于权力的毁灭性打击。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竟然会“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官家对商业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成为晚明时期的关键词,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商业社会的崛起,使得千年传承的“士农工商”阶层排序被打破,向来被鄙视的“逐利之徒”华丽转型成为社会生活的掌控者,他们消费着最奢侈的物品,赚取着最丰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洗刷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中国有句老话“富贵险中求”,也就是说商人是一群风险偏好者,他们的富贵往往伴随着风险。在古代的商业环境中,商人们险中求来的并不是大富贵,只是赚些活命之资罢了,大的富贵只能在权力系统中寻求。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官商这个共同体。官商,一半是权力,另一半是经济势力,是权力与经济的畸形结合。买卖关系是官商结合的基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是权力集团的社会效益,与市场经济的平等契约精神没有多大的关系。官商的出现,使社会商业完全成为一种特权者的游戏,生产经营并没有按照商业定律在运行。古代政治制度放大了这种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行为,这样就等于打破了正常的市场规则。
在秦朝统一之前,商业虽然不是社会结构中的主流,但还是足够发达的,所谓的商业网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商业活动受到了权力集团的抑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代,这一倾向也是反反复复。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抑商政策达到了巅峰,在当时但凡能够盈利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权力集团所控制。
中国封建时代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权力集团作为国家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手中掌握着对老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选择将权力直接兑换成财富。商人地位处于“四民之末”,由于其社会地位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不稳定性,使得自己的利益无从保证。他们既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承担买卖亏本的风险,另外还有各级官府的盘剥,地方黑势力的敲诈和掠夺。为了乱世求得生存,他们就要在权力集团中寻求庇护。因为只有权力才能超越经济力量。而这种庇护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我出钱你出权,然后谋取利益再共同分割。这样就造成了官商勾结的恶性关系,在商人们看来,要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奉行“是官当敬”游戏规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口袋鼓鼓的富商大贾就有“游诸侯”、“交将相”的光荣传统。一个商人要想立足于规则大于法制的时代,肯定要用手中财富打开权力的通道。
有了权力的保驾护航,商业在盛唐和南宋时期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到了明正德、嘉靖以后,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改观,国家允许商人子弟进入官家的权力系统,这样就打破了长久以来不许商人子弟入仕为官的禁锢。随着商人子弟不断进入官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抬高。而这些进入权力系统的商人子弟,又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反哺商业。这样就使得官商一体化愈演愈烈,权力与财富一起水涨船高。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影响力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时候,与很多商人一样,对于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远离,也不亲近的态度,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市场调节”。相邻吴江县的巨富陆老先生一句话点醒沈万三:“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巨富,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动”规则或者说是官商博弈之术。沈万三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机遇、时势和个人的投资眼光。
一是粮食生产与土地兼并成为沈万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记载“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资料显示,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在财富的累计与权力的递增之路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机遇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动荡的乱世里博取生存之资。沈万三在发展的路上,还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
二是依托时势,让沈万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条捷径,沈万三的财富王国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元朝末年,各地农民军风起云涌。沈万三抓住机会,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地区,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然后再依靠张士诚的武装保护将其提供的私盐倒卖出去(张士诚的队伍大多具备盐民身份)。可以说沈万三发的是战争财,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单生意做下来,沈万三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他以跳楼价买下大半个苏州的商业,投入数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以躲避战祸。沈万三和张士诚很熟,凭着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士诚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同行们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凭此一战,沈万三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商,成为天下首富。
三是借助皇家权力管道实现财富累积。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不利条件下,沈万三居然可以打着皇家的龙旗,开着十几条船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大肆走私。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张士诚曾经降元,元政府令他从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于是张士诚则将这件事交予沈万三具体操办。沈万三知道,政府长期禁海,出海贸易必定是一场暴利之旅。于是,沈万三在朝廷的船里,一半装上粮食,另一半装上自己的私货,皇船打着龙旗,大摇大摆,一路畅通无阻。出了长江,沈万三便兵分两路,装皇粮的北上复命,而承载私货的船则扬帆南下直接开往东南亚去发财。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货物,卖到东南亚,都是数十数百倍的暴利。沈万三船队随行人员中,有人带了一些成本只有5两银子一筐的桔子,居然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可以卖到几两银子一个,一筐桔子,卖到了1000两银子。从南洋回来,沈万三的财富已经滚雪球似的达到十几亿两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沈万三的财富之路,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有勇气和造反者张士诚合伙做走私生意,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其关键所在。这样的生意,做早了风险性太高,随时都会有掉脑袋的可能性,而做晚了就有可能丧失机会。
沈万三敢于在张士诚打苏州前,倾其所有,买下大半个苏州商业,靠的是他的政治敏锐性。他在社会的恶风大浪中,准确判断了形势的走向。至于走私南洋大发洋财,则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资源,特别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证这样的政策资源。财富和政治资源给沈万三的人生带来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最后也让他输的很惨。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于这些豪族巨富们来说,这无疑于是一场财富的轮盘赌。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助他购粮扩军。后来,沈万三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进入权力系统,甚至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有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经结拜为异姓兄弟。
南京城原有十三道城门,南门又被称作聚宝门,据说这段城墙是由沈万三所筑。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初,国库空虚,就让沈万三资筑东南诸城。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欢心,沈万三不惜花重金买宠。结果皇家出资建造的西北城还没有建造成形,沈万三的东南城就已经提前竣工了。筑城还不够表达自己的忠心,沈万三又献出白金2 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帝国上下对沈万三此举无不称颂不已。可是沈万三这么做,却大大触痛了一个人的敏感神经,那个人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这个出身于草根的皇帝,似乎与权贵有着天生的敌意。
明末《云焦馆纪谈》说得更加具体,朱元璋和沈万三约好同时开工,结果被沈万三抢先三天完工。在庆功会上,朱元璋举着酒杯对沈万三说:“古有白衣天子一说,号称素封,你就是个白衣天子。”这句话表面上听着像是夸奖,可话里已经隐隐透出了杀机,大明江山岂能容许两个天子并存于世?
有一天,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发奇想,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帝国军队。
朱元璋听后。脸色十分难看,冷冷地说道:“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拍着胸脯说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万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一种志得意满的表情。自己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犒劳帝国军队,既可取悦皇帝,又可以炫耀财富。可是他并没注意到朱元璋变幻莫测的脸色下藏着深重的忧虑。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对话:朱元璋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这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马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家天下”的皇权年代,家国一体,这天下的一切都是我皇家的,一个不自量力的商人居然要犒劳皇家军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皇后的意思是告诉朱元璋,现在还远没有到杀了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在开国之初都会呈现出貌似宏大宽松的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朱元璋的时代也同样不例外。洪武初年,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可是等到政权稍有稳定,朱元璋对工商的态度立即发生微妙的变化。
每次王朝更迭,旧词翻新阙的建政者都会吸取前朝败亡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对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败亡的历史现实也同样做出总结:“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蒙元帝国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权涣散的境地,是因为民间的势力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天下祸乱。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个商人居然想要犒劳三军,这让自己这个皇帝的脸该往哪里搁?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打拼上来,吃了太多的苦,更见识过太多的社会黑暗面,这或许成为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决心所在。作为来自民间草根阶层,朱元璋对商人有着天生的敌意。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没有之一。
朱元璋不仅没有赋予商人某种特权,甚至通过一些不合常理的制度来限制和束缚他们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面,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可是他并有考虑到,无利可图的农民即使有权利穿高档服装,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够穿得起,却没有穿的权利,他们也只好将绫罗绸缎烂在自家的箱底。不仅如此,商人在科举和仕途上,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而那些商人们整天只知道耍些坑蒙拐骗的卑劣手段去谋取暴利,却从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生产任何产品。他们依靠财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所在,是社会稳压器上最危险的隐患所在。
朱元璋的逻辑来自于小农的利益计算方式,简单而现实,他认为:沈万三既然有养活军队的庞大财力,那么他就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叛乱的现实行为,也应该将其列为打击的对象或者平灭的乱民。
如果我们把朱元璋的帝国战略分为左右手,那么他在运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右手则用来打击富商和地主。朱元璋并不建立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可是他也不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将会被财富者赶出土地,农民则会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颠沛于江湖之上的朱元璋就是一个流民,对此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将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地方的富商地主。史料记载,三吴地区的豪族大姓在离开故土后就成了离水之鱼,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资产也流失殆尽。在数年之内,这些离乡背井之人或死或迁,无一存者。他们留恋曾经的富足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乡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又先后两次,将天下将近7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又一次伤筋动骨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做出评论:“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对于商人阶层采取“先用之,后弃之”的使用策略,朱元璋并不是历史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这种对待商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通之处。朱元璋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为帝国的财富战略之后,沈万三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朱元璋的一系列铁血政策嗅到了扑面而来的风险气息。为免树大招风,沈万三主动将偌大的家族资产分割为四户。沈家有人被举荐到京师为官,沈万三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辞:“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沈万三希望用财富为当权者分忧解难,也借此利用皇权为自己的财富之路保驾护航。可是他哪里晓得,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博得朱元璋的欢心,反而适得其反。当沈万三进一步进贡龙角、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马十匹,并在南京城内投资兴建廊庑酒楼时,朱元璋彻底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财富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朱元璋这个帝国的当权者无法容忍的,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权力的垄断,还是财富的垄断,高利润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沈家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沈万三的倒下,而全盘尽墨。
《弘治吴江志》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亲、户部左侍郎的莫礼回乡省亲,特地到周庄沈家拜访,见到“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莫礼看到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自己,已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风险。“呜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莫礼返乡探亲时的历史背景。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蓝党案”的高潮,三月间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朱梓和王妃于氏竟然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被朱元璋称为“朕之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也被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背景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乡期间写下《归吴江省亲》一诗,诗云:“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在朱元璋的时代里为官是一件高风险的事,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礼一道回家的侄儿莫辕也写下一副对联:“世路风波今暂息,惊心犹觉骨毛寒。”
沈家姻亲如此如此高规格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让莫氏叔侄回乡之旅惊心不已。沈万三的后人并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还是希望能够用财富沟通权力。可是官员的处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财富于他们而言,只能是让他们心惊肉跳的麻烦与负担而已。
在家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财富。财富通常是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与之相反,如果财富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会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农耕社会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制度为每个人设计好了财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制度,通过非农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会被视为异类。
事实上,古代官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那些贴金挂银的所谓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贫困的。于是才有了元朝诗人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声叹息。
沈万三成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官家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永远不会结束。《明史·纪纲传》中记载:朱元璋驾崩后,燕王朱棣从北京举兵一直打到南京,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的心腹官员,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这个人非常善于敛财,曾经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家财富已经被朱元璋抄没,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万三的儿子沈文度匍匐于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分账。
尽管如此,沈万三的后人依然难以逃脱财富带来的命运之劫,两个孙子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那就是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那么商人和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话“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作为权力最亲密的战友和宠儿,沈万三的财富来自于权力的庇护,同样又失之于权力的毁灭性打击。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竟然会“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官家对商业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成为晚明时期的关键词,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商业社会的崛起,使得千年传承的“士农工商”阶层排序被打破,向来被鄙视的“逐利之徒”华丽转型成为社会生活的掌控者,他们消费着最奢侈的物品,赚取着最丰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洗刷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