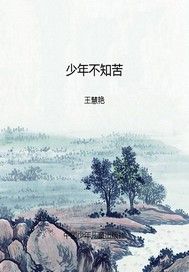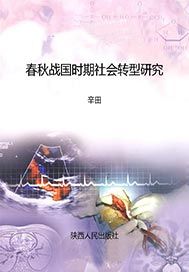挥泪斩马谡
古人有诗云: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
孔明第一次出祁山伐魏,派马谡守街亭,结果因马谡违反指示、恃才刚愎自用,不听部属劝告将大军驻守山上导致全军大败,使孔明大军撤守。虽然孔明对马谡视如己出,但仍依军令将他处斩,这也是三国中极有名的一段——挥泪斩马谡:
孔明回到汉中,计点军士,只少赵云、邓芝,心中非常担心,但命关兴、张苞,各引一军前去接应。二人正欲起身,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向道:“我命你同马谡守街亭,你为什么不谏阻他,致使失事?”王平道:“我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参军大怒不从,我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我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我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我奋死杀出。回到营寨,早被魏兵占了。想去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收回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军,以此心疑。登高一看,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我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兵合一处。我恐失掉阳平关,因此急来回守。不是我没有谏阻。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
马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道:“你自幼饱读兵书,熟谙兵法。我累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军的根本。你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你若早听王平之言,怎么会有这场灾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都是你的过错!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你现在犯了军法,就不要怨我了。你死之后,你的家小,我按月给与禄粮,你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首。马谡泣道:“丞相视我如子,我以丞相为父。我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我虽死也无恨于九泉!”说完大哭不止。孔明挥泪道:“我与你义同兄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参军蒋琬自成都来到这儿,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道:“昔日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吗?”孔明流涕而答道:“昔日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执法严明。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合当斩之。”一会儿,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道:“今幼常获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痛哭?”孔明道:“我不是为马谡而哭。我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我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的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马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亮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故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感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派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诸葛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谁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置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任何组织要良性运行,都必须有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落实到措施上,就是赏和罚,说通俗了,就是胡萝卜和大棒。胡萝卜和大棒这两种工具用好了,能起到很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用不好,则适得其反,不仅人们不欢迎的大棒如此,就是人人愿意得到的胡萝卜也是如此。这就要求胡萝卜和大棒的使用要有些原则,那就是信赏必罚、赏罚分明、赏罚得当。
信赏必罚,是说赏罚要言出必行,说过的就要做到。如果事前许诺的奖赏不能兑现,或者规定的惩罚未能执行,就必然影响赏罚制度的信用,损害企业和领导人的形象,不仅不能起到激励、警示作用,消极影响也将会十分明显——该奖未奖的将不再努力,甚至甩手不干;该罚未罚的将心存侥幸,甚至肆无忌惮。
赏罚分明,是说无论是赏是罚,都要旗帜鲜明,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赏罚都要放到桌面上来,结果要明确公布,对于同一个团队或同一个人,不能搞什么将功补过,功是功、过是过。功要奖,过还是要罚。只有赏罚分明,才能起到示范作用。
赏罚得当,是指尺度问题。赏罚固然是对当事人功过的报偿和惩罚,但作用绝不仅止于此。就组织而言,都期望赏罚成为一种机制。除了作用于已然的事实,也作用于未然的行为,也就是对当事者本人和其他人都能起到激励或警示作用。有没有作用,就是一个衡量当与不当的尺度。这个尺度的把握是比较微妙的,但这种微妙却不能成为随意行事的借口。一般来说,得当与否,应该是制度、规定说了算,应当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如果有问题,也应该是修订制度或规定,而不是修改具体的赏罚措施。
前车之鉴,冷冻姜维
马谡虽然死了,诸葛亮在首次北伐时,却有意外的收获,即姜维来归。姜维当时二十七岁,会来投降蜀军,实在有点阴错阳差。前面说过,诸葛亮初次北伐时,吓坏了魏国上下,魏国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自动起兵响应。姜维是天水冀县人,当时在天水郡做小官,随太守马遵出巡。马遵听说自己的辖区反了,便疑神疑鬼,觉得姜维可能也是蜀国的奸细,于是丢下姜维,自己趁夜溜到上邽。姜维追去,被上邽守军拒绝,他只好回冀县。没想到冀县也不让他进城,他走投无路,最后投奔诸葛亮。诸葛亮对姜维做过一番调查和测试后,大感兴奋,写信给人在成都的蒋琬和张裔,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伯约是姜维的字,永南是李邵的字,季常是马良的字。李邵是何等人物,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诸葛亮曾聘用他为西曹掾,大概也是诸葛亮极为赏识的人,否则也不会与马良并列。诸葛亮称赞姜维的能力在马良之上,这可是极高的赞誉。此外,在信中还吩咐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显然想有计划地栽培他成为蜀国大将。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不但充分肯定了姜维的军事才能与潜力,而且已分析出他的忠诚度没问题,栽培成功后,可推荐给刘禅任用。诸葛亮才与姜维相处不久,就得出这么多正面的结论。他刚忍痛杀了旧徒弟马谡,又收了新徒弟姜维,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埃
有了马谡的前车之鉴,收了新徒弟的诸葛亮不敢大意,决定慢慢栽培姜维,急不得。除了先教他兵法之外,只让他当“仓曹掾”的小官兼空头衔“奉义将军”,跟在自己身边见习。往后的六年之中,姜维虽然升任中监军征西将军,诸葛亮仍不轻易让他抛头露面、独当一面,这都是因为挥泪斩马谡的过往造成的投鼠忌器效应。姜维很听话,默默跟在诸葛亮身边学习,没有任何怨言。
公元234年,诸葛亮五十四岁,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而姜维三十三岁,当然也跟去。诸葛亮常对姜维有机会就教育,让他快速成长。这一次途中,诸葛亮见对手司马懿死守不出,便派人拿女人的衣服去嘲笑司马懿,司马懿不予理会,但他底下的人愤恨不平,急着出战。司马懿见压不住了,于是飞书请示皇帝,皇帝派辛毗来宣示不准出战的旨意。诸葛亮问姜维的看法,姜维说:“辛毗一来,司马懿就不会出来应战。”诸葛亮说:“你搞错了,司马懿原本就不想出战,他只是想借皇帝的命令来压制手下出战的意念罢了。”姜维这时还正年轻,对于许多人性的尔虞我诈还不清楚,需要诸葛亮不时加以点破。
诸葛亮虽然如此器重姜维,但临终前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反而对刘禅的使者李福提示蒋琬,蒋琬之后则是费祎。费祎之后呢?诸葛亮竟然笑而不答!这太奇怪了,对姜维而言,他二十七岁时遇到诸葛亮,尽得孔明真传,照理说是少年得志,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临死前做了许多交代,却没有把姜维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反而是看中蒋琬和费祎的治国守城的能力,把今后国家大权都交给了两位稳重的大臣,实在令人困惑。诸葛亮毕生的志业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北伐中原,恢复汉室,以报刘备知遇之恩。从他的两篇《出师表》和他晚年连年用兵的情况来看,便知道他对心中这个久悬的梦想,有着多么急切的盼望,深恐时不我与。他在《前出师表》一文说: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在《后出师表》中又说: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清楚看到诸葛亮的内心世界:他当然知道以他的能力,以蜀国的国力,是很难北伐成功的,但他还是要做,为什么?为了使命感,为了复兴汉室,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坚定反对偏安的局面!他的意思这么明显了,在他死后,还有谁能继承这个遗志呢?环顾当时的蜀汉,老将凋零,新枝青黄未接,除了姜维,还有谁能担负如此重任?而诸葛亮心中的名单只有蒋琬和费祎,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除非,我们从诸葛亮的个性来考虑。他生平处事慎重,不打没把握的仗,因此,在临终之前,内心必定经过一番挣扎:一方面思索姜维当他接班人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姜维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但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姜维只是个三十三岁的毛头小子,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会不会干下什么冲动的事情来,反而坏了大事,那就功亏一篑了。马谡的教训,一定不时浮现在他脑海,要他谨慎!基于慎重其事的个人行事风格,诸葛亮最后还是决定:让姜维多磨练几年,多沉寂一段时日。唯有这样解释,才能对诸葛亮的决定有一些体会。换成是你我或任何人,这也会是个很大的难题吧。
诸葛亮死前,对撤军的事情做了一番交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让魏延压阵,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听调度,则由姜维压阵。蜀军当时面对的敌人已经不是张郃,而是比张郃强上数倍的司马懿。司马懿的智谋与诸葛亮相当,诸葛亮居然派出三十三岁的姜维压阵,要与司马懿的追兵斗智!这也是很大胆的调度吧,如果姜维没搞好,蜀国全军覆没不说,还有可能让司马懿长驱直入,蜀国不就亡国在即了?
这个决定是很矛盾的。如果诸葛亮真的信任姜维能够抗衡司马懿,为何不将蜀国军政大权分一些给姜维?如果诸葛亮因为疑虑姜维能力、经验不足,会将蜀国弄垮,又为何要让他压阵呢?当时蜀军中仍有充满经验的老将,如王平等人,也足以托付压阵的重责大任埃
这种错乱、矛盾的做法,似乎更可看出诸葛亮心中的煎熬、挣扎。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前提必须是在思虑清楚的时候。如果回光返照、脑袋不清,做出来的决定往往会有害大局,不知道诸葛亮在临终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孔明第一次出祁山伐魏,派马谡守街亭,结果因马谡违反指示、恃才刚愎自用,不听部属劝告将大军驻守山上导致全军大败,使孔明大军撤守。虽然孔明对马谡视如己出,但仍依军令将他处斩,这也是三国中极有名的一段——挥泪斩马谡:
孔明回到汉中,计点军士,只少赵云、邓芝,心中非常担心,但命关兴、张苞,各引一军前去接应。二人正欲起身,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向道:“我命你同马谡守街亭,你为什么不谏阻他,致使失事?”王平道:“我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参军大怒不从,我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我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我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我奋死杀出。回到营寨,早被魏兵占了。想去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收回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军,以此心疑。登高一看,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我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兵合一处。我恐失掉阳平关,因此急来回守。不是我没有谏阻。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
马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道:“你自幼饱读兵书,熟谙兵法。我累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军的根本。你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你若早听王平之言,怎么会有这场灾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都是你的过错!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你现在犯了军法,就不要怨我了。你死之后,你的家小,我按月给与禄粮,你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首。马谡泣道:“丞相视我如子,我以丞相为父。我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我虽死也无恨于九泉!”说完大哭不止。孔明挥泪道:“我与你义同兄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参军蒋琬自成都来到这儿,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道:“昔日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吗?”孔明流涕而答道:“昔日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执法严明。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合当斩之。”一会儿,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道:“今幼常获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痛哭?”孔明道:“我不是为马谡而哭。我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我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的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马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亮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故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感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派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诸葛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谁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置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任何组织要良性运行,都必须有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落实到措施上,就是赏和罚,说通俗了,就是胡萝卜和大棒。胡萝卜和大棒这两种工具用好了,能起到很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用不好,则适得其反,不仅人们不欢迎的大棒如此,就是人人愿意得到的胡萝卜也是如此。这就要求胡萝卜和大棒的使用要有些原则,那就是信赏必罚、赏罚分明、赏罚得当。
信赏必罚,是说赏罚要言出必行,说过的就要做到。如果事前许诺的奖赏不能兑现,或者规定的惩罚未能执行,就必然影响赏罚制度的信用,损害企业和领导人的形象,不仅不能起到激励、警示作用,消极影响也将会十分明显——该奖未奖的将不再努力,甚至甩手不干;该罚未罚的将心存侥幸,甚至肆无忌惮。
赏罚分明,是说无论是赏是罚,都要旗帜鲜明,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赏罚都要放到桌面上来,结果要明确公布,对于同一个团队或同一个人,不能搞什么将功补过,功是功、过是过。功要奖,过还是要罚。只有赏罚分明,才能起到示范作用。
赏罚得当,是指尺度问题。赏罚固然是对当事人功过的报偿和惩罚,但作用绝不仅止于此。就组织而言,都期望赏罚成为一种机制。除了作用于已然的事实,也作用于未然的行为,也就是对当事者本人和其他人都能起到激励或警示作用。有没有作用,就是一个衡量当与不当的尺度。这个尺度的把握是比较微妙的,但这种微妙却不能成为随意行事的借口。一般来说,得当与否,应该是制度、规定说了算,应当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如果有问题,也应该是修订制度或规定,而不是修改具体的赏罚措施。
前车之鉴,冷冻姜维
马谡虽然死了,诸葛亮在首次北伐时,却有意外的收获,即姜维来归。姜维当时二十七岁,会来投降蜀军,实在有点阴错阳差。前面说过,诸葛亮初次北伐时,吓坏了魏国上下,魏国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自动起兵响应。姜维是天水冀县人,当时在天水郡做小官,随太守马遵出巡。马遵听说自己的辖区反了,便疑神疑鬼,觉得姜维可能也是蜀国的奸细,于是丢下姜维,自己趁夜溜到上邽。姜维追去,被上邽守军拒绝,他只好回冀县。没想到冀县也不让他进城,他走投无路,最后投奔诸葛亮。诸葛亮对姜维做过一番调查和测试后,大感兴奋,写信给人在成都的蒋琬和张裔,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伯约是姜维的字,永南是李邵的字,季常是马良的字。李邵是何等人物,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诸葛亮曾聘用他为西曹掾,大概也是诸葛亮极为赏识的人,否则也不会与马良并列。诸葛亮称赞姜维的能力在马良之上,这可是极高的赞誉。此外,在信中还吩咐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显然想有计划地栽培他成为蜀国大将。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不但充分肯定了姜维的军事才能与潜力,而且已分析出他的忠诚度没问题,栽培成功后,可推荐给刘禅任用。诸葛亮才与姜维相处不久,就得出这么多正面的结论。他刚忍痛杀了旧徒弟马谡,又收了新徒弟姜维,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埃
有了马谡的前车之鉴,收了新徒弟的诸葛亮不敢大意,决定慢慢栽培姜维,急不得。除了先教他兵法之外,只让他当“仓曹掾”的小官兼空头衔“奉义将军”,跟在自己身边见习。往后的六年之中,姜维虽然升任中监军征西将军,诸葛亮仍不轻易让他抛头露面、独当一面,这都是因为挥泪斩马谡的过往造成的投鼠忌器效应。姜维很听话,默默跟在诸葛亮身边学习,没有任何怨言。
公元234年,诸葛亮五十四岁,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而姜维三十三岁,当然也跟去。诸葛亮常对姜维有机会就教育,让他快速成长。这一次途中,诸葛亮见对手司马懿死守不出,便派人拿女人的衣服去嘲笑司马懿,司马懿不予理会,但他底下的人愤恨不平,急着出战。司马懿见压不住了,于是飞书请示皇帝,皇帝派辛毗来宣示不准出战的旨意。诸葛亮问姜维的看法,姜维说:“辛毗一来,司马懿就不会出来应战。”诸葛亮说:“你搞错了,司马懿原本就不想出战,他只是想借皇帝的命令来压制手下出战的意念罢了。”姜维这时还正年轻,对于许多人性的尔虞我诈还不清楚,需要诸葛亮不时加以点破。
诸葛亮虽然如此器重姜维,但临终前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反而对刘禅的使者李福提示蒋琬,蒋琬之后则是费祎。费祎之后呢?诸葛亮竟然笑而不答!这太奇怪了,对姜维而言,他二十七岁时遇到诸葛亮,尽得孔明真传,照理说是少年得志,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临死前做了许多交代,却没有把姜维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反而是看中蒋琬和费祎的治国守城的能力,把今后国家大权都交给了两位稳重的大臣,实在令人困惑。诸葛亮毕生的志业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北伐中原,恢复汉室,以报刘备知遇之恩。从他的两篇《出师表》和他晚年连年用兵的情况来看,便知道他对心中这个久悬的梦想,有着多么急切的盼望,深恐时不我与。他在《前出师表》一文说: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在《后出师表》中又说: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清楚看到诸葛亮的内心世界:他当然知道以他的能力,以蜀国的国力,是很难北伐成功的,但他还是要做,为什么?为了使命感,为了复兴汉室,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坚定反对偏安的局面!他的意思这么明显了,在他死后,还有谁能继承这个遗志呢?环顾当时的蜀汉,老将凋零,新枝青黄未接,除了姜维,还有谁能担负如此重任?而诸葛亮心中的名单只有蒋琬和费祎,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除非,我们从诸葛亮的个性来考虑。他生平处事慎重,不打没把握的仗,因此,在临终之前,内心必定经过一番挣扎:一方面思索姜维当他接班人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姜维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但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姜维只是个三十三岁的毛头小子,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会不会干下什么冲动的事情来,反而坏了大事,那就功亏一篑了。马谡的教训,一定不时浮现在他脑海,要他谨慎!基于慎重其事的个人行事风格,诸葛亮最后还是决定:让姜维多磨练几年,多沉寂一段时日。唯有这样解释,才能对诸葛亮的决定有一些体会。换成是你我或任何人,这也会是个很大的难题吧。
诸葛亮死前,对撤军的事情做了一番交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让魏延压阵,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听调度,则由姜维压阵。蜀军当时面对的敌人已经不是张郃,而是比张郃强上数倍的司马懿。司马懿的智谋与诸葛亮相当,诸葛亮居然派出三十三岁的姜维压阵,要与司马懿的追兵斗智!这也是很大胆的调度吧,如果姜维没搞好,蜀国全军覆没不说,还有可能让司马懿长驱直入,蜀国不就亡国在即了?
这个决定是很矛盾的。如果诸葛亮真的信任姜维能够抗衡司马懿,为何不将蜀国军政大权分一些给姜维?如果诸葛亮因为疑虑姜维能力、经验不足,会将蜀国弄垮,又为何要让他压阵呢?当时蜀军中仍有充满经验的老将,如王平等人,也足以托付压阵的重责大任埃
这种错乱、矛盾的做法,似乎更可看出诸葛亮心中的煎熬、挣扎。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前提必须是在思虑清楚的时候。如果回光返照、脑袋不清,做出来的决定往往会有害大局,不知道诸葛亮在临终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