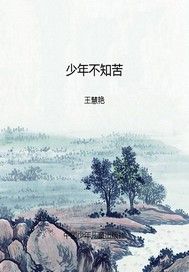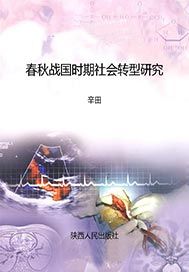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曹植是盗我是贼
曹植是盗我是贼
1
你——曹植——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峰巅,在你离开邺城一千七百年后的1996年深秋,一个偶然的事情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让我有了攀附你老人家的理由。
恕我匹夫无知,不该称你为盗,虽然你天生就不是做盗贼的料,可我猜想,你的基因里应该有盗的遗传。你父亲曹操置汉献帝于股掌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盗吗?大盗窃国,这个用无数鲜血过滤出来的道理,已被无数史实所证明。可偏偏在你的基因里,文人的放荡不羁把“盗”稀释成了一泓秋水,而你的政治生命就毙溺在自己秋水一样散淡的性格里。所以,乃父“盗”的遗传就集中在了你的兄长曹丕身上。你与曹丕可是一母同胞啊,同样的爹精娘血怎么就让你定格在文人的悲剧上了呢?你应该记得,金碧辉煌的铜雀台刚刚落成的时候,你便和所有弟兄簇拥着父亲曹操在阁道上信步欢游。一向习惯临景吟诗的父亲这次把诗兴分发给了你们弟兄,新落成的铜雀台就是你们作赋的考题。由此也拉开了竞争的序幕。
西望太行山,南俯漳河水,太行山的葱郁和漳河水的波光都汇入了你灵性的笔,于是沉吟片刻,援笔而成,众弟兄正在搜肠刮肚之时,你文质俱佳的《登台赋》就已呈在了父亲面前。
父亲那双识过无数英材的慧眼不仅为之一亮,原来对你十岁即能吟诗赋文的疑虑终于化作了大喜过望的欣慰。他一直惟才是举,对流淌自己血脉的儿子的如此才情能不欢喜吗?于是,你的《登台赋》就奠定了你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这可不仅仅是一篇辞赋,是登上太子之位的一个重要台阶,甚至是你父亲百年身后的一国之君。
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和机遇你竟没有把握住,是不是文人的风流倜傥的潇洒害了你?可你的哥哥曹丕却嗅到了蛛丝马迹。他从父亲脸上读出了你的分量,也读出了自己的恐慌。所以你骤然就成了压在曹丕心头或阻挡在曹丕面前的一座大山,把你搬掉或踩在脚下,他才能接近太子的宝座。
公平地讲,要论才情,曹丕真的不如你,虽然他是七言诗的开创者和文学理论的里程碑。尽管他有《燕歌行》和《典论》传世,可他没有你汪洋恣肆的才华,没有你纵横捭阖的自如。可他有立长不立幼这一传统的优势筹码。况且他比你工于心计狡黯世故,他把自己的野心化作笑脸,使许多人都在父亲面前为他美言。
可曹植你呢?虽然贵为豪门公子,身上没有多少纨绔气息,可你文人那任性而为的张扬个性却始终未曾收敛。在父亲离开邺城后,你竟然毫无顾忌地私自打开王宫大门,乘车在不该你行驶的禁道上跑了一圈,那是只有你父亲一人才能行驶的禁道呀,你竟为了一个无名侍从的怂恿而胆敢冒犯父亲。大军出征在即,父亲本来想让你建功立业,你却喝得酩酊大醉,使父亲不得不临阵换将。
本来杨修丁仪一帮铁哥儿们都是为了你好,在父亲每次召见前总是为你出谋划策。可你不该在父亲尚未讲完问题,就急不可耐按杨修的事先准备抢先作了回答,弄巧成拙,可你又不会圆滑隐瞒,结果害苦了杨修,也害苦了自己。终于,你的种种迂腐和任性,使你本来在父亲心目中一直被看好的上涨行情,一跌再跌。而你的兄长曹丕一边玩权术赢得父亲的信任,一边拨弄是非降低你的威信,终于窃国成功。
从此,你由春风得意走上了秋风萧瑟。
由此,你由一个“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翩翩少年变成了曹丕重压之下的一个精神囚徒。你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凌云壮志变成了动辄得咎的秋后寒蝉。你曾心高气盛,视诗文为雕虫小技,此时又不得不在四处冷漠中以诗文哀鸣。从乐观开朗风流自赏到深沉悲凉暇不自顾,从直抒胸怀到隐喻曲意,你不得不转变诗风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可即使如此,你仍想“愿得展勤功,输力于明君,”尽管直抒胸臆的《求自试表》表明你雄心犹在,尽管凄美的《洛神赋》呻吟着有志难酬的痛苦,可在曹丕眼里都不过是秋后虫鸣,只要他脚尖轻轻一拧,你便会成为一个血红的绝句。
曾经,你一个有天赋的文人反而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而你的兄长曹丕这个政客反而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是莫大的讽刺,无权而善为文者不愿以文为业,有权而不为文者却视文为宝。看来,文章的概念和功用是文人与政客之间永远难以苟同的话题,历史的反差总是让人啼笑皆非。
三十多岁本是蒸蒸日上的人生夏季,可你却过早地踏上了悲秋之旅,踽踽独行,郁郁寡欢,边走边唱,一路悲歌。自父亲驾崩,你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遮风挡雨的屏障。兄长曹丕的残忍,使你这座才情坚实的大山,变成了烈日炙烤的雪峰。客观环境的剥蚀和主观内心的沮丧,使你一点点夷为平地。在这场不对称的交锋中,在曹丕志满意得冷笑中,你变成了枝杈上岌岌可危的枯叶。
六次变更爵位,三次迁徙封地,境遇每况愈下,直至衣食不继。如此,仍不解曹丕对你的恐惧和心头之恨,宫殿上你的七步诗也曾激起曹丕良知的一点涟漪,你的哀鸣也曾让曹丕潸然泪下,可泪痕未干便又要置你于死地,若非母亲卞后的干预,你的人头恐怕早已成了蚂蚁的食物。
我想你肯定后悔。后悔自己的散漫,后悔自己心慈手软,后悔自己书生意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你骨子里是一个文人,你还没来得及从文人到政客的蜕变,就已霜雪压身。所以我就常常为你悲哀。可是当你的悲哀透过一千七百年的烟尘传导在我身上时,我才知道,文人悲哀是有传承性的,你的悲哀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
2
我真正认识这种悲哀是1996年的深秋。那是我作为一个刀笔侍从跟随新任市长在检查完工作后到铜雀台观光的时候,在陈列室欣赏了出土不久的大量的汉代陶俑,每个陶俑高不过尺半,做工算不上精制,可管理人员说,一个陶俑在日本可换一辆汽车。
如果站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角度,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当时你们随便埋下的高不过一尺的陶俑,如今在东边邻国一个即可换来一辆汽车。因是珍贵文物,一饱眼福后我便随众人离开了铜雀台。完成报道任务后,市长还当人家的市长,我仍做我的新闻记者。然而半年后竟有人举报我偷了人家的陶俑,而且是直接给新任市长写的信。不明就里的台长欢天喜地的把市长的电话号码送给我时,掩饰不住对我即将飞黄腾达的羡慕,嘱咐我苟富贵勿相忘。我却忐忑不安,不是我心虚,而是觉得一个市长要我一个普通记者直接与他通话,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当新任市长那和蔼可亲的声音把这个消息传给我时,我的嘴和手都颤抖成了一团。市长是爱护我,说拿了人家陶俑送回去即可,这件事我就不往外扩大了,年轻人嘛,改正就好。我的声音近乎哭腔,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让公安立案侦查。
后来几经询问查证,陶俑根本就没有丢失,我才松了一口气。可为什么有人要写信诬告我呢?是我平时文理不通的豆腐块文章戳到了谁的痛处?是我在铜雀台为市长讲说了关公点曹兵故事引起别人不满?还是我直率的脾气得罪了谁?我百思不解。就这样,平白无故戴上了“贼”的帽子。
大盗窃国,小盗窃钩。我虽出身贫寒,没有曹植窃国最基本的条件,可自幼严格的家教、人格的尊严以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使我不屑于窃钩的勾当。后来又想,是不是我成了谁人上进的绊脚石?其实,我也是自作多情,与曹植相比,我连小盗的称谓都够不上,充其量一个小蟊贼而已。
尽管受了冤枉,没有成为盗贼,可我仍觉得沾了曹植的光,因为这件事让我有了攀附他老人家的由头。不同的是,曹植和曹丕的争斗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曹植有身份和才华,有多层保护桑而我却是一介平民,我在明处,别人在暗处,连叫阵的对手都找不到,随时都有让别人推上祭坛的可能。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曹丕的名言。至今,文人相轻像历史杂草污秽处营营嗡嗡的苍蝇,它的生命力足以穿过季节的冷暖,而让人震惊。曹植与曹丕的骨肉相残,仅用文人相轻或兄弟阋墙来概括,未免有些牵强和单薄,至少是人性与权力专制碰撞的必然。
由此,我从建安文学辉煌的背后,多少也悟出了一些文人与政治的血腥缘源。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主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尤其是给一点阳光就想灿烂的穷酸文人,施舍的当权者是为了让你折射他的光环,如果你连自身的工具性都不明白,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顺着阳光去捅当权者的黑洞,甚至自己也要成为普照天下的发光体,那阳光的温暖就会变成大棒的冷压,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落叶悲秋文人心,曹植这片枯叶至今还飘泊在历史的烟尘中。我无语独立,残阳溅我一身血色。
你——曹植——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峰巅,在你离开邺城一千七百年后的1996年深秋,一个偶然的事情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让我有了攀附你老人家的理由。
恕我匹夫无知,不该称你为盗,虽然你天生就不是做盗贼的料,可我猜想,你的基因里应该有盗的遗传。你父亲曹操置汉献帝于股掌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盗吗?大盗窃国,这个用无数鲜血过滤出来的道理,已被无数史实所证明。可偏偏在你的基因里,文人的放荡不羁把“盗”稀释成了一泓秋水,而你的政治生命就毙溺在自己秋水一样散淡的性格里。所以,乃父“盗”的遗传就集中在了你的兄长曹丕身上。你与曹丕可是一母同胞啊,同样的爹精娘血怎么就让你定格在文人的悲剧上了呢?你应该记得,金碧辉煌的铜雀台刚刚落成的时候,你便和所有弟兄簇拥着父亲曹操在阁道上信步欢游。一向习惯临景吟诗的父亲这次把诗兴分发给了你们弟兄,新落成的铜雀台就是你们作赋的考题。由此也拉开了竞争的序幕。
西望太行山,南俯漳河水,太行山的葱郁和漳河水的波光都汇入了你灵性的笔,于是沉吟片刻,援笔而成,众弟兄正在搜肠刮肚之时,你文质俱佳的《登台赋》就已呈在了父亲面前。
父亲那双识过无数英材的慧眼不仅为之一亮,原来对你十岁即能吟诗赋文的疑虑终于化作了大喜过望的欣慰。他一直惟才是举,对流淌自己血脉的儿子的如此才情能不欢喜吗?于是,你的《登台赋》就奠定了你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这可不仅仅是一篇辞赋,是登上太子之位的一个重要台阶,甚至是你父亲百年身后的一国之君。
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和机遇你竟没有把握住,是不是文人的风流倜傥的潇洒害了你?可你的哥哥曹丕却嗅到了蛛丝马迹。他从父亲脸上读出了你的分量,也读出了自己的恐慌。所以你骤然就成了压在曹丕心头或阻挡在曹丕面前的一座大山,把你搬掉或踩在脚下,他才能接近太子的宝座。
公平地讲,要论才情,曹丕真的不如你,虽然他是七言诗的开创者和文学理论的里程碑。尽管他有《燕歌行》和《典论》传世,可他没有你汪洋恣肆的才华,没有你纵横捭阖的自如。可他有立长不立幼这一传统的优势筹码。况且他比你工于心计狡黯世故,他把自己的野心化作笑脸,使许多人都在父亲面前为他美言。
可曹植你呢?虽然贵为豪门公子,身上没有多少纨绔气息,可你文人那任性而为的张扬个性却始终未曾收敛。在父亲离开邺城后,你竟然毫无顾忌地私自打开王宫大门,乘车在不该你行驶的禁道上跑了一圈,那是只有你父亲一人才能行驶的禁道呀,你竟为了一个无名侍从的怂恿而胆敢冒犯父亲。大军出征在即,父亲本来想让你建功立业,你却喝得酩酊大醉,使父亲不得不临阵换将。
本来杨修丁仪一帮铁哥儿们都是为了你好,在父亲每次召见前总是为你出谋划策。可你不该在父亲尚未讲完问题,就急不可耐按杨修的事先准备抢先作了回答,弄巧成拙,可你又不会圆滑隐瞒,结果害苦了杨修,也害苦了自己。终于,你的种种迂腐和任性,使你本来在父亲心目中一直被看好的上涨行情,一跌再跌。而你的兄长曹丕一边玩权术赢得父亲的信任,一边拨弄是非降低你的威信,终于窃国成功。
从此,你由春风得意走上了秋风萧瑟。
由此,你由一个“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翩翩少年变成了曹丕重压之下的一个精神囚徒。你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凌云壮志变成了动辄得咎的秋后寒蝉。你曾心高气盛,视诗文为雕虫小技,此时又不得不在四处冷漠中以诗文哀鸣。从乐观开朗风流自赏到深沉悲凉暇不自顾,从直抒胸怀到隐喻曲意,你不得不转变诗风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可即使如此,你仍想“愿得展勤功,输力于明君,”尽管直抒胸臆的《求自试表》表明你雄心犹在,尽管凄美的《洛神赋》呻吟着有志难酬的痛苦,可在曹丕眼里都不过是秋后虫鸣,只要他脚尖轻轻一拧,你便会成为一个血红的绝句。
曾经,你一个有天赋的文人反而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而你的兄长曹丕这个政客反而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是莫大的讽刺,无权而善为文者不愿以文为业,有权而不为文者却视文为宝。看来,文章的概念和功用是文人与政客之间永远难以苟同的话题,历史的反差总是让人啼笑皆非。
三十多岁本是蒸蒸日上的人生夏季,可你却过早地踏上了悲秋之旅,踽踽独行,郁郁寡欢,边走边唱,一路悲歌。自父亲驾崩,你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遮风挡雨的屏障。兄长曹丕的残忍,使你这座才情坚实的大山,变成了烈日炙烤的雪峰。客观环境的剥蚀和主观内心的沮丧,使你一点点夷为平地。在这场不对称的交锋中,在曹丕志满意得冷笑中,你变成了枝杈上岌岌可危的枯叶。
六次变更爵位,三次迁徙封地,境遇每况愈下,直至衣食不继。如此,仍不解曹丕对你的恐惧和心头之恨,宫殿上你的七步诗也曾激起曹丕良知的一点涟漪,你的哀鸣也曾让曹丕潸然泪下,可泪痕未干便又要置你于死地,若非母亲卞后的干预,你的人头恐怕早已成了蚂蚁的食物。
我想你肯定后悔。后悔自己的散漫,后悔自己心慈手软,后悔自己书生意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你骨子里是一个文人,你还没来得及从文人到政客的蜕变,就已霜雪压身。所以我就常常为你悲哀。可是当你的悲哀透过一千七百年的烟尘传导在我身上时,我才知道,文人悲哀是有传承性的,你的悲哀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
2
我真正认识这种悲哀是1996年的深秋。那是我作为一个刀笔侍从跟随新任市长在检查完工作后到铜雀台观光的时候,在陈列室欣赏了出土不久的大量的汉代陶俑,每个陶俑高不过尺半,做工算不上精制,可管理人员说,一个陶俑在日本可换一辆汽车。
如果站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角度,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当时你们随便埋下的高不过一尺的陶俑,如今在东边邻国一个即可换来一辆汽车。因是珍贵文物,一饱眼福后我便随众人离开了铜雀台。完成报道任务后,市长还当人家的市长,我仍做我的新闻记者。然而半年后竟有人举报我偷了人家的陶俑,而且是直接给新任市长写的信。不明就里的台长欢天喜地的把市长的电话号码送给我时,掩饰不住对我即将飞黄腾达的羡慕,嘱咐我苟富贵勿相忘。我却忐忑不安,不是我心虚,而是觉得一个市长要我一个普通记者直接与他通话,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当新任市长那和蔼可亲的声音把这个消息传给我时,我的嘴和手都颤抖成了一团。市长是爱护我,说拿了人家陶俑送回去即可,这件事我就不往外扩大了,年轻人嘛,改正就好。我的声音近乎哭腔,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让公安立案侦查。
后来几经询问查证,陶俑根本就没有丢失,我才松了一口气。可为什么有人要写信诬告我呢?是我平时文理不通的豆腐块文章戳到了谁的痛处?是我在铜雀台为市长讲说了关公点曹兵故事引起别人不满?还是我直率的脾气得罪了谁?我百思不解。就这样,平白无故戴上了“贼”的帽子。
大盗窃国,小盗窃钩。我虽出身贫寒,没有曹植窃国最基本的条件,可自幼严格的家教、人格的尊严以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使我不屑于窃钩的勾当。后来又想,是不是我成了谁人上进的绊脚石?其实,我也是自作多情,与曹植相比,我连小盗的称谓都够不上,充其量一个小蟊贼而已。
尽管受了冤枉,没有成为盗贼,可我仍觉得沾了曹植的光,因为这件事让我有了攀附他老人家的由头。不同的是,曹植和曹丕的争斗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曹植有身份和才华,有多层保护桑而我却是一介平民,我在明处,别人在暗处,连叫阵的对手都找不到,随时都有让别人推上祭坛的可能。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曹丕的名言。至今,文人相轻像历史杂草污秽处营营嗡嗡的苍蝇,它的生命力足以穿过季节的冷暖,而让人震惊。曹植与曹丕的骨肉相残,仅用文人相轻或兄弟阋墙来概括,未免有些牵强和单薄,至少是人性与权力专制碰撞的必然。
由此,我从建安文学辉煌的背后,多少也悟出了一些文人与政治的血腥缘源。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主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尤其是给一点阳光就想灿烂的穷酸文人,施舍的当权者是为了让你折射他的光环,如果你连自身的工具性都不明白,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顺着阳光去捅当权者的黑洞,甚至自己也要成为普照天下的发光体,那阳光的温暖就会变成大棒的冷压,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落叶悲秋文人心,曹植这片枯叶至今还飘泊在历史的烟尘中。我无语独立,残阳溅我一身血色。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