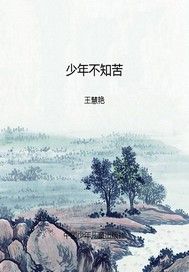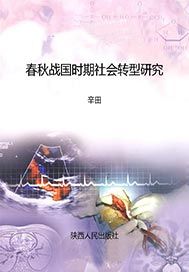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脂粉狼烟
脂粉狼烟
有一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似乎战争就是男人之间的事情。其实,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过。
原以为“花姑娘的有”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发明,翻开史书一瞧,早在两千年前咱中国人刘敬就有了这个创意。
河西走廊的苍凉掩遮不住红蓝花诱人的艳丽。红花蓝叶是匈奴人眼中的至美,他们把这种植物制成染料,让衣裳的亮色成为大漠中飞动的彩虹;把这种植物制成胭脂,让女人成为草原上奔跑的花朵。
红蓝花寄托了匈奴人对美的渴望,胭脂在匈奴人心中是美的代名词。他们把生长红蓝花的山称为胭脂山,把他们头领单于的妻子——部族最美的女人称为阏氏(胭脂的谐音)。
冒顿是爱美的匈奴人中的一个,他是匈奴单于头曼的儿子。
冒顿有资格爱美,因为他就是将来部族的单于,是大漠和草原未来的最高主宰。冒顿和他的美人在草原上嬉戏追逐时的那份恩爱,衣食男女们羡慕得眼珠子发红,青草都羡慕地抻着脖子,野风想按都按不住,牛羊都不忍心啃带花的青草,坚硬的阳光像激动的火苗一样跳着,粗犷的歌声也缠绵得跑了调儿。微风春色,羊群白云,冒顿憧憬在与自己一样年轻气盛的部族的未来;爱河畅游,女人陶醉在冒顿雄性勃勃的男儿柔情之中。
北风卷地,八月飞雪,塞北的天是多变的。乌云划碎了如血的残阳,也让冒顿的单于梦阴云密布。他被父亲和后母逼上了绝路,如同被猎人追赶的狼一样红着眼在悬崖边寻找着退路和反扑的办法。
反扑就要有反扑的资本,在父亲的眼皮下,他忍气吞声,不动声色地悄悄蓄积力量。为训练一支绝对忠诚自己的队伍,他发明了一种带响的箭——鸣镝,并向部下宣布“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此来检视部下对自己忠诚程度。
打猎时冒顿以鸣镝射猎物,凡不跟随他一起射的一律斩首。在训练中他以鸣镝射向自己心爱的战马,凡不射战马者一律斩首。后来他把鸣镝射向自己宠爱的妻子时,部下都惊呆了,他们犹豫着,弓箭在手中颤抖,他们不明白:这女人究竟有什么过错,刚才俩人还亲亲热热,怎么一转身妻子就成了丈夫射杀的目标?可是女人的痛苦挣扎并没有从冒顿阴冷的眼光里得到半点怜惜,因为此时冒顿眼中只有血红的两个字:权力。在冒顿刀一样的目光逼视下,大多数部下的盲从战胜了人性的理智,箭软绵绵地射向了那至死都不知为什么成为丈夫靶子的女人,而那几个良知未泯没有动手的也同那女人一样成了冒顿的刀下鬼。青草和牛羊都惊恐地低下了头;草丛里远远观望的狼,吓得一溜烟窜了。
滴血的忠诚带来的是狼性的残忍,当冒顿把鸣镝射向他父亲心爱的战马时,部下都毫不犹豫地随之一齐发射。最终,冒顿的鸣镝射向了自己的父亲。他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向了单于的位子。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权力是政客们的终极目标,在不能用和平手段获取的情况下,流血和战争便是最基本的手段,即使最心爱的女人也是他们手中摧毁目标的武器。
冒顿毕竟是一个有头脑的部族首领,面对东西两边强敌的夹击,匈奴这匹夹在中间的瘦狼随时都有可能被吃掉,他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成熟。东胡不断挑衅,先派使者索取头曼时的千里马,接着又派使提出欲得单于一阏氏,对侮辱性的无理要求,群臣皆怒,要求出击,冒顿却理智地说服了大家,向东胡送“千里马”,接着又送“阏氏”,以此麻痹敌人,赢得了养生休息的机会。
当大漠的风沙和草原的水草磨砺强壮了筋骨之后,这匹北方狼便不再满足于现状的盘踞,按捺不住欲望的冲动,从大漠深处一跃而起,挟着飕飕冷风,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兰,北服丁令。一时马蹄声碎,狼烟四起,东边的辽河冲刷着匈奴的战刀,西边的葱岭烙上了匈奴的跌蹄,北边的贝加尔湖有匈奴战马的倒影,南边的长城响起匈奴的阵阵马嘶。
在征服中体味着血腥的快感,在杀戮中流连着刀光剑影的乐趣,他们掠夺自然,掠夺财物,掠夺女人,掠夺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心思坐下来琢磨用于教化臣民的文字,除了胡笳,鲜血成了他们装扮内心世界的精神胭脂。大漠草原的广袤助长了野性,寒风冷月刺激了双眼永远饥饿的贼光,柔弱的汉家美女和区区长城又怎能融化和阻挡那已肆虐的心?
这是遍地狼烟弱肉强食的时代,贪婪和野性成了人和狼的共性。至少这个时代的争霸者们是这样。
战国七雄由诸侯而称王称霸,哪个不是靠别人的血肉来扩张自己的胃口?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唇边的鲜血还未擦去,北边的匈奴就虎视眈眈地盯上了他那还没有消化下去的肚子。
长城阻挡了匈奴的一时骚扰,却没能阻挡住秦始皇子孙江山梦的破灭。秦朝的暴政把人逼成了狼,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呐喊,为刘邦项羽吹响了汉楚争雄的前奏。刘邦用狼性的狡黠,战胜了项羽狼性的野蛮。可当刘邦踌躇满志地挥师北上时,才真正知道了匈奴这匹北方狼的剽悍。
匈奴铁骑个个膘肥体壮,四十万大军按马的毛色一队队分列排开,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而刘邦这个堂堂的汉朝皇帝,却没有力量为自己配备四匹一色的四驾车,他的将相大臣只能乘坐牛车。三十万汉军在白登山被围困了七天,刘邦一举踏平胡马的信心一下子变成了胆战心惊的阵阵冷汗。实力的悬殊,使刘邦不得不另谋退兵之计,派人暗中以厚礼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女人的枕边风才使刘邦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于是大臣刘敬的和亲政策便成了汉朝对匈奴强盛的一种柔性杀伤。刘敬的如意算盘是:汉皇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公主生了孩子就是匈奴将来的单于,这样汉匈一家亲,当单于的外甥就不会给汉皇帝的姥爷找事儿。
国力凋蔽也真为难了刘敬的一片苦心。于是,女人就成了冷器时代的热兵器。
长城默默注视着人间的纷争,大雁默默穿梭着季节的冷暖。长城内外的汉匈也在岁月轮回中此消彼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韬光养晦十三年后,汉朝的金戈铁马终于理直气壮地越过了长城,卫青和霍去病像两把尖刀在匈奴盘踞的大漠和草原上所向披靡,封礼狼居胥山,禅礼姑衍山,汉军大旗在大漠和草原的深处猎猎飞扬。遁逃的匈奴在风雪中长吁短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是一个思想和行为极其矛盾的部族:一方面追求生活追求美,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活破坏美。然而,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女人总是绕不开的话题,南弱北强时,汉廷主动以和亲作为退敌的手段;南强北弱时,匈奴被动地请求和亲作为向汉廷妥协的筹码。双方都明白,血缘往往比地缘更能让人心靠近,女人是天然的溶和剂。
于是,在汉将李陵战败被俘后,匈奴单于将自己女儿的美丽青春编成一道金箍咒,使这个曾令匈奴人闻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乖乖成了匈奴进攻汉军的急先锋,如果李陵听了后来唐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不知该如何面对他英雄一世的爷爷。后来汉将李广利也战败被俘,匈奴单于亦以女妻之,官之以位,以同样的手段化解了刀兵相见的敌视。
石榴裙裹碎英雄心,女人胜过刀枪箭。在这一手上,汉廷和匈奴都运用得技法娴熟。然而,并非英雄都过不去美人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两次被匈奴拘押,第二次长达十三年之久,即使已在匈奴娶妻生子,可他仍不忘自己的使命。苏武出使匈奴被拘押,严辞美女官禄利诱,十九年受尽折磨,可他矢志不渝,即使风雪中牧羊北海,仍持节望归。可见,女人并非万能武器,摧毁气节和信念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和亲是政治联姻,形式往往大于内容。汉高祖刘邦为赢得喘息机会,曾依刘敬的建议,打算把长女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可遭到吕后的阻拦,说为什么把我的女儿弃之匈奴?最后只好找了个皇室女子冒名顶替了事。在汉朝与异族和亲的十三个女子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皇帝公主。
王昭君虽然身为宫女,可她在十三个和亲的女子中是很另类的一个。说她另类,是因为其他十二位都是极不情愿地走上了和亲之路,而她是主动提出来到匈奴和亲。再则,这次和亲双方重视程度都超过了以往。
作为众多美女中的一个,王昭君原本也是汉皇金笼中的一个玩偶。然而,宫庭幽深,美女如云,王昭君别说享受做女人的权利,就连当玩偶的机会都没有,仅是深宫中一个寂寞的花瓶。是呼韩邪给她带来了机会。
因争单于之位,呼韩邪与其兄反目为仇,他明智地臣服在了汉元帝面前,自然,请求和亲成为呼韩邪攀附汉廷一个重要条件。王昭君抓住了机会。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和亲,是匈奴主动归附后真正意义上的和亲,虽然和亲的女子不是公主,汉元帝也极为重视。也许在他眼里,走掉一个宫女如丢掉一件衣裳无足轻重,他重视的是和亲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带来的政治利益。再说汉元帝以前从没注意过王昭君的存在。可当王昭君泪面悲戚地向他告别时,汉元帝还是惊呆了,他后悔不该让如此姣美的女人离开自己,去伺候一个已臣服自己的男人,可这已是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
钟鼓阵阵,琴笛悠扬。在虚掷青春的宫门,王昭君顾影徘徊;在呼韩邪热辣辣的目光中,王昭君告别了生她养她的故土,款款走向迎亲的车队;在汉元帝懊悔贪恋的目光中,王昭君随辚辚车队把长安街头的繁华喧嚣稀释在了塞北天高云淡的苍凉之中。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在泪眼模糊中渐渐远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空旷忐忑着王昭君的心。自此,深宫的寂寞变成了草原穹庐的孤独,锦服鼎食变成了裘衣畜肉。
月光下,南飞的大雁常常捎去王昭君无奈的乡思;长城南,北飘的云朵常常在草原上落下父母和亲人的相思泪。草原、长城、父母,这是王昭君思绪的轨迹;汉廷、长城、单于,这是王昭君所处的现实。她既是汉家女儿,又是匈奴单于的妻子,她把汉朝的农耕文明与匈奴的游牧文化融合成了一道桥梁,使长城南北分庭抗礼的风雨雪霜化作了祥和的宁静彩云,所以千百年来,王昭君的那座青冢是草原上最灿烂的花朵。
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代,到公元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那个以胭脂血红为主色调的部族消失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八百年的狼烟也早已消散。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交融,到公元505年以后,冒顿单于的后代、匈奴人刘渊宣布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建国号为汉,八百年的分分合合,给历史留下了沉重丰厚的一页,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和感叹。
蓝天白云、羊群奔马、牧歌炊烟、大漠落日,本是诗情的意象组合,可历史偏偏在这里搞了一个小把戏,导演了一场兄弟恩怨纠葛的片断。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历史把这八百年的人间活剧收起来的时候,长城依然巍立,大漠依然雄浑,草原依然辽阔,红蓝花仍然艳丽,人们依然记得秦始皇、汉武帝、霍去并苏武,依然记得冒顿、呼韩邪。可对于女人,除了昭君出塞、文姬归汉之外,那些有名的或无名的女人,那些有幸的或无辜的女人,无论是汉朝的还是匈奴的,无论是内部争斗的牺牲品,还是部族间的政治联姻,她们为世间流血纷争所付出的一切,有谁还记得?
狼烟和胡笳声都已远去,胭脂是否还是那抹血红的单调?
原以为“花姑娘的有”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发明,翻开史书一瞧,早在两千年前咱中国人刘敬就有了这个创意。
河西走廊的苍凉掩遮不住红蓝花诱人的艳丽。红花蓝叶是匈奴人眼中的至美,他们把这种植物制成染料,让衣裳的亮色成为大漠中飞动的彩虹;把这种植物制成胭脂,让女人成为草原上奔跑的花朵。
红蓝花寄托了匈奴人对美的渴望,胭脂在匈奴人心中是美的代名词。他们把生长红蓝花的山称为胭脂山,把他们头领单于的妻子——部族最美的女人称为阏氏(胭脂的谐音)。
冒顿是爱美的匈奴人中的一个,他是匈奴单于头曼的儿子。
冒顿有资格爱美,因为他就是将来部族的单于,是大漠和草原未来的最高主宰。冒顿和他的美人在草原上嬉戏追逐时的那份恩爱,衣食男女们羡慕得眼珠子发红,青草都羡慕地抻着脖子,野风想按都按不住,牛羊都不忍心啃带花的青草,坚硬的阳光像激动的火苗一样跳着,粗犷的歌声也缠绵得跑了调儿。微风春色,羊群白云,冒顿憧憬在与自己一样年轻气盛的部族的未来;爱河畅游,女人陶醉在冒顿雄性勃勃的男儿柔情之中。
北风卷地,八月飞雪,塞北的天是多变的。乌云划碎了如血的残阳,也让冒顿的单于梦阴云密布。他被父亲和后母逼上了绝路,如同被猎人追赶的狼一样红着眼在悬崖边寻找着退路和反扑的办法。
反扑就要有反扑的资本,在父亲的眼皮下,他忍气吞声,不动声色地悄悄蓄积力量。为训练一支绝对忠诚自己的队伍,他发明了一种带响的箭——鸣镝,并向部下宣布“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此来检视部下对自己忠诚程度。
打猎时冒顿以鸣镝射猎物,凡不跟随他一起射的一律斩首。在训练中他以鸣镝射向自己心爱的战马,凡不射战马者一律斩首。后来他把鸣镝射向自己宠爱的妻子时,部下都惊呆了,他们犹豫着,弓箭在手中颤抖,他们不明白:这女人究竟有什么过错,刚才俩人还亲亲热热,怎么一转身妻子就成了丈夫射杀的目标?可是女人的痛苦挣扎并没有从冒顿阴冷的眼光里得到半点怜惜,因为此时冒顿眼中只有血红的两个字:权力。在冒顿刀一样的目光逼视下,大多数部下的盲从战胜了人性的理智,箭软绵绵地射向了那至死都不知为什么成为丈夫靶子的女人,而那几个良知未泯没有动手的也同那女人一样成了冒顿的刀下鬼。青草和牛羊都惊恐地低下了头;草丛里远远观望的狼,吓得一溜烟窜了。
滴血的忠诚带来的是狼性的残忍,当冒顿把鸣镝射向他父亲心爱的战马时,部下都毫不犹豫地随之一齐发射。最终,冒顿的鸣镝射向了自己的父亲。他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向了单于的位子。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权力是政客们的终极目标,在不能用和平手段获取的情况下,流血和战争便是最基本的手段,即使最心爱的女人也是他们手中摧毁目标的武器。
冒顿毕竟是一个有头脑的部族首领,面对东西两边强敌的夹击,匈奴这匹夹在中间的瘦狼随时都有可能被吃掉,他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成熟。东胡不断挑衅,先派使者索取头曼时的千里马,接着又派使提出欲得单于一阏氏,对侮辱性的无理要求,群臣皆怒,要求出击,冒顿却理智地说服了大家,向东胡送“千里马”,接着又送“阏氏”,以此麻痹敌人,赢得了养生休息的机会。
当大漠的风沙和草原的水草磨砺强壮了筋骨之后,这匹北方狼便不再满足于现状的盘踞,按捺不住欲望的冲动,从大漠深处一跃而起,挟着飕飕冷风,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兰,北服丁令。一时马蹄声碎,狼烟四起,东边的辽河冲刷着匈奴的战刀,西边的葱岭烙上了匈奴的跌蹄,北边的贝加尔湖有匈奴战马的倒影,南边的长城响起匈奴的阵阵马嘶。
在征服中体味着血腥的快感,在杀戮中流连着刀光剑影的乐趣,他们掠夺自然,掠夺财物,掠夺女人,掠夺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心思坐下来琢磨用于教化臣民的文字,除了胡笳,鲜血成了他们装扮内心世界的精神胭脂。大漠草原的广袤助长了野性,寒风冷月刺激了双眼永远饥饿的贼光,柔弱的汉家美女和区区长城又怎能融化和阻挡那已肆虐的心?
这是遍地狼烟弱肉强食的时代,贪婪和野性成了人和狼的共性。至少这个时代的争霸者们是这样。
战国七雄由诸侯而称王称霸,哪个不是靠别人的血肉来扩张自己的胃口?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唇边的鲜血还未擦去,北边的匈奴就虎视眈眈地盯上了他那还没有消化下去的肚子。
长城阻挡了匈奴的一时骚扰,却没能阻挡住秦始皇子孙江山梦的破灭。秦朝的暴政把人逼成了狼,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呐喊,为刘邦项羽吹响了汉楚争雄的前奏。刘邦用狼性的狡黠,战胜了项羽狼性的野蛮。可当刘邦踌躇满志地挥师北上时,才真正知道了匈奴这匹北方狼的剽悍。
匈奴铁骑个个膘肥体壮,四十万大军按马的毛色一队队分列排开,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而刘邦这个堂堂的汉朝皇帝,却没有力量为自己配备四匹一色的四驾车,他的将相大臣只能乘坐牛车。三十万汉军在白登山被围困了七天,刘邦一举踏平胡马的信心一下子变成了胆战心惊的阵阵冷汗。实力的悬殊,使刘邦不得不另谋退兵之计,派人暗中以厚礼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女人的枕边风才使刘邦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于是大臣刘敬的和亲政策便成了汉朝对匈奴强盛的一种柔性杀伤。刘敬的如意算盘是:汉皇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公主生了孩子就是匈奴将来的单于,这样汉匈一家亲,当单于的外甥就不会给汉皇帝的姥爷找事儿。
国力凋蔽也真为难了刘敬的一片苦心。于是,女人就成了冷器时代的热兵器。
长城默默注视着人间的纷争,大雁默默穿梭着季节的冷暖。长城内外的汉匈也在岁月轮回中此消彼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韬光养晦十三年后,汉朝的金戈铁马终于理直气壮地越过了长城,卫青和霍去病像两把尖刀在匈奴盘踞的大漠和草原上所向披靡,封礼狼居胥山,禅礼姑衍山,汉军大旗在大漠和草原的深处猎猎飞扬。遁逃的匈奴在风雪中长吁短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是一个思想和行为极其矛盾的部族:一方面追求生活追求美,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活破坏美。然而,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女人总是绕不开的话题,南弱北强时,汉廷主动以和亲作为退敌的手段;南强北弱时,匈奴被动地请求和亲作为向汉廷妥协的筹码。双方都明白,血缘往往比地缘更能让人心靠近,女人是天然的溶和剂。
于是,在汉将李陵战败被俘后,匈奴单于将自己女儿的美丽青春编成一道金箍咒,使这个曾令匈奴人闻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乖乖成了匈奴进攻汉军的急先锋,如果李陵听了后来唐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不知该如何面对他英雄一世的爷爷。后来汉将李广利也战败被俘,匈奴单于亦以女妻之,官之以位,以同样的手段化解了刀兵相见的敌视。
石榴裙裹碎英雄心,女人胜过刀枪箭。在这一手上,汉廷和匈奴都运用得技法娴熟。然而,并非英雄都过不去美人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两次被匈奴拘押,第二次长达十三年之久,即使已在匈奴娶妻生子,可他仍不忘自己的使命。苏武出使匈奴被拘押,严辞美女官禄利诱,十九年受尽折磨,可他矢志不渝,即使风雪中牧羊北海,仍持节望归。可见,女人并非万能武器,摧毁气节和信念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和亲是政治联姻,形式往往大于内容。汉高祖刘邦为赢得喘息机会,曾依刘敬的建议,打算把长女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可遭到吕后的阻拦,说为什么把我的女儿弃之匈奴?最后只好找了个皇室女子冒名顶替了事。在汉朝与异族和亲的十三个女子中,没有几个是真正的皇帝公主。
王昭君虽然身为宫女,可她在十三个和亲的女子中是很另类的一个。说她另类,是因为其他十二位都是极不情愿地走上了和亲之路,而她是主动提出来到匈奴和亲。再则,这次和亲双方重视程度都超过了以往。
作为众多美女中的一个,王昭君原本也是汉皇金笼中的一个玩偶。然而,宫庭幽深,美女如云,王昭君别说享受做女人的权利,就连当玩偶的机会都没有,仅是深宫中一个寂寞的花瓶。是呼韩邪给她带来了机会。
因争单于之位,呼韩邪与其兄反目为仇,他明智地臣服在了汉元帝面前,自然,请求和亲成为呼韩邪攀附汉廷一个重要条件。王昭君抓住了机会。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和亲,是匈奴主动归附后真正意义上的和亲,虽然和亲的女子不是公主,汉元帝也极为重视。也许在他眼里,走掉一个宫女如丢掉一件衣裳无足轻重,他重视的是和亲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带来的政治利益。再说汉元帝以前从没注意过王昭君的存在。可当王昭君泪面悲戚地向他告别时,汉元帝还是惊呆了,他后悔不该让如此姣美的女人离开自己,去伺候一个已臣服自己的男人,可这已是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
钟鼓阵阵,琴笛悠扬。在虚掷青春的宫门,王昭君顾影徘徊;在呼韩邪热辣辣的目光中,王昭君告别了生她养她的故土,款款走向迎亲的车队;在汉元帝懊悔贪恋的目光中,王昭君随辚辚车队把长安街头的繁华喧嚣稀释在了塞北天高云淡的苍凉之中。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在泪眼模糊中渐渐远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空旷忐忑着王昭君的心。自此,深宫的寂寞变成了草原穹庐的孤独,锦服鼎食变成了裘衣畜肉。
月光下,南飞的大雁常常捎去王昭君无奈的乡思;长城南,北飘的云朵常常在草原上落下父母和亲人的相思泪。草原、长城、父母,这是王昭君思绪的轨迹;汉廷、长城、单于,这是王昭君所处的现实。她既是汉家女儿,又是匈奴单于的妻子,她把汉朝的农耕文明与匈奴的游牧文化融合成了一道桥梁,使长城南北分庭抗礼的风雨雪霜化作了祥和的宁静彩云,所以千百年来,王昭君的那座青冢是草原上最灿烂的花朵。
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代,到公元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那个以胭脂血红为主色调的部族消失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八百年的狼烟也早已消散。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交融,到公元505年以后,冒顿单于的后代、匈奴人刘渊宣布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建国号为汉,八百年的分分合合,给历史留下了沉重丰厚的一页,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和感叹。
蓝天白云、羊群奔马、牧歌炊烟、大漠落日,本是诗情的意象组合,可历史偏偏在这里搞了一个小把戏,导演了一场兄弟恩怨纠葛的片断。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历史把这八百年的人间活剧收起来的时候,长城依然巍立,大漠依然雄浑,草原依然辽阔,红蓝花仍然艳丽,人们依然记得秦始皇、汉武帝、霍去并苏武,依然记得冒顿、呼韩邪。可对于女人,除了昭君出塞、文姬归汉之外,那些有名的或无名的女人,那些有幸的或无辜的女人,无论是汉朝的还是匈奴的,无论是内部争斗的牺牲品,还是部族间的政治联姻,她们为世间流血纷争所付出的一切,有谁还记得?
狼烟和胡笳声都已远去,胭脂是否还是那抹血红的单调?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