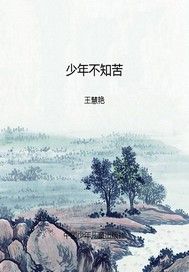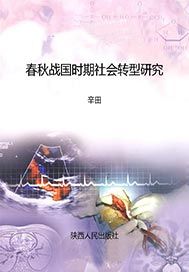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我哥
我哥
可以称兄道弟的人不少,而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就一人,他是我哥。我哥比我大12岁,都属兔。
本来命里注定要生活在那个叫杜寨小村的两个农民,如今都生活在了城市。虽然我也是整日为生计奔波,可相比较,哥哥绕的圈子更大,路也曲折。
如果年份正常,哥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成,因为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他赶上了不正常的年代,高小毕业,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哥哥就不得不回家劳动挣工分。哥哥辍学后,老师两次到我家做我父母工作,老师说这孩子不读书实在可惜。可我父母没有办法。哥这棵苗从小就营养不良,这也给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后来父亲对我说,你哥哥要是有你这个文化,可比你有出息。父亲说得是实话,直到现在哥仍保持爱看书的习惯,他会背诵许多唐诗宋词,字写得也很周正有力,全不像一个高小毕业生,如果他有条件读书,肯定会考上大学。可哥没有我幸运。
几乎所有的农活重活哥哥都干过,比如挖海河。第一年去挖海河时,身体单薄的哥哥连带工的看了都皱眉头,认为他顶不住,可哥哥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那年哥哥也就十六七岁,还不到成年。可哥硬是与那些成年人一样在数九寒冬里挖泥拉土挥汗如雨。因为挖海河的活儿虽然很累,可挣工分多,还能填饱肚子。回来后哥哥就成了民兵排长,那些比他年龄大的都乖乖听他的话。
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可哥又不甘心就这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浪费自己。一个从未来往的我们称呼大姨的丈夫在外地搞副业,哥听说后,大雪天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二姐坐在车子后座,趁春节带着我们去给人家拜年,拜年是借口,哥的目的是想跟着人家到外地挣钱。他骑车技术不行,路上摔了几次,十几里路赶到人家村子时,人家竟然不认识我们这三个“亲戚”。哥在回来路上掉了泪。
机会终于来临。那时煤矿在农村大批招工,我们村也分到一个指标。但这个指标原来不是哥哥的,支书给了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人家体检填表准备走时,他的父母却不让去,怕儿子到煤矿出事故,因为我们附近村子刚有一个在煤窑砸死的人。正在支书犹豫把指标给谁的时候,哥哥三番五次去找支书,加上我本家一个在村子当治保主任堂哥的说和,哥终于如愿。他到煤矿上班不到半月内,一个同去的邻村老乡就把性命丢在了几百米的地下,一个老乡偷跑回家,有几个也准备伺机开溜,煤矿不得不派人监督他们这些新到的工人。可哥没有动摇,这并不是他有多高政治觉悟要为我国煤炭事业做贡献,而是他不愿再回到一天工值还不到一毛钱的穷村。哥后来对我说,就咱家那个困难情况,我要是回去,恐怕成家都难。
不久哥也出了事故,他左手中指被机器咬掉半截,担惊受怕之际,哥动了要调换工作的心思。可他两眼一抹黑没有可利用的关系,腰包紧张没有可送礼的资金,他就用笨办法,经常跟劳资科长套近乎,有事没事到科长家走走,帮助干些家务活儿。这招还真感动了科长,加上他手指受伤的原因,哥终于调到井上开卷车。
环境造就人,哥哥就是很好的例证。按说在煤矿开卷车也算不错的工种了,只要把矿工安全提上来和送下去,就不会有问题。可哥后来还是离开了这里。那年我们家正是多事之秋,我第一次高考落榜,秋天母亲病重住进了地区医院,不由得哥哥不担心。他下班后骑车六七十里路到邯郸伺候母亲,还要第二天天不亮赶回峰峰煤矿上班,当时家里相当拮据,他不得不奔忙挣钱给母亲治玻过度的忧虑和劳累使他在工作上出现疏忽,一次往井下送人时,卷车开过了头,几个矿工被蹾伤,幸好没出人命,否则事儿就大了。
一边受批评做检查扣工资,一边惦念母亲的病情和落榜弟弟的前途,本来就消瘦的哥更加憔悴。他说,那一阵子,我哭都没有地方。这次事故也坚定了他离开煤矿的决心。可这又谈何容易?远比他从井下调井上复杂得多。可哥有毅力,他打听到煤矿附近村庄一个在邯郸粮店工作的李哥想回老家工作。他准备与李哥对调,对调在八十年代初很流行,就是双方协商后,单位办手续,甲到乙单位工作,乙到甲单位工作,请客送礼等中间费用几乎没有。可李哥仅仅有此想法,并不着急,人家毕竟在城市工作,工种也好,那时粮本还没取消,想多吃细粮多吃油就得求售粮员通融。哥着急,怕夜长梦多,就一趟一趟到李哥家里做工作,讲李哥回来本地工作的种种好处,终于在1980年底调进了城市粮店,那年秋我考进师专。哥俩终于在城市会面。
哥并不是机会主义者,可哥能抓住机会。当粮食供应基本放开,粮店渐露颓势时,哥又调进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商场,当时这个商场是邯郸最大的,货全,生意很火。这个商场成了哥哥人生高潮和低谷的分水岭。
有在粮店几年从商的积累,哥哥肯吃苦,再加上商场大多是新手,哥很快从站柜台售货员变为部门经理,由部门经理变为楼层副经理。至此,哥哥的人生达到最高度,那几年市场经济还没有全面铺开,一些物资供应相对紧缺,求哥哥购买东西的人也多。哥哥通过关系把嫂子和我侄女侄子的户口农转非,他也不再春种秋收时风尘仆仆回家劳作。
可是好景不长,市场经济大潮把哥哥供职的商场吹打的风雨飘摇,嫂子失去了在商场打扫卫生的差使,第三年,哥哥也在无奈中下岗。失去固定收入,失去了原本打算依靠一生的工作单位,哥哥心理一直难以调整,他不断到单位找我,让我帮忙找工作,有时也不说话,就坐在我办公室看半天报纸。在家里嫂子嘟囔,他心里烦,有时骑一辆破自行车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转悠,有一次我到旧书刊市场转,发现哥哥蹲在一个摊贩前戴着花镜看一本过期杂志。我心里一酸,没敢打扰他就离开了。我能力有限,终究没能给哥哥找到工作,只是牵线让嫂子找到了看自行车的差使,因为嫂子没文化,只有干这个不需要文化的工作。后来哥哥自己找关系在贸易街边开了一个烟酒小卖部,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可不到一年,因为马路扩建,哥哥的小卖部被取消。他又在陵西路找了一个地方,还是烟酒小卖部。开始还可以,一年多后,就有地痞流氓总是去他那里“借钱”,自然是有借无还,说是保护哥哥在这一片没人敢欺负。其实哥哥根本不用那个地痞保护,因为哥哥与周围邻居和商贩搞的关系很好。这个事情哥哥一直不给我说,怕我脾气不好,跟那个地痞干架,或找人收拾地痞,更怕地痞报复。直到停业,在闲谈中哥哥透露了原因,就这样哥哥还说破财免灾。他这个人有时很有主张,有时很软弱,总是与人为善,受屈后自己安慰自己,自我解脱。这可能与他多年靠自己奋斗有关,没有靠山,没有经济力量,只能委曲求全,回家还不愿跟嫂子说,怕嫂子生气。跟我有时偶尔透露一点,但往往是欲言又止,怕我替他操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弟弟心目中的重量。
可以说我是哥哥看着长大的,他对我操的心并不比对他的子女的少。我记得他到煤矿上班第一次回家探亲给我买的礼物是高尔基《童年》小人书。就是“开门办学”不学文化那年月,哥回家总是翻开我的作业本看看,要我把字写好。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又逢母亲病重,家里是一贫如洗,在是让我复读再考,还是尽快回家劳动补贴家用的选择上,有许多亲戚邻居建议我父亲让我尽快去挣钱,哥哥却毫不犹豫支持我复读再考,他对父亲说:我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不能让东汇再走我的老路,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上学。1980年春,病入膏肓的母亲不得不回到老家打发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回家时哥哥除了详尽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还问我有啥困难,我告诉哥哥我的眼近视了,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也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迹。下午哥哥就用自行车带着我到十几里外的一个个人眼科门诊去看。他回煤矿时专门到邯郸的眼镜门市给我配眼镜,找人钉一个小木箱把眼镜邮寄到学校。我读师专时候哥也从煤矿调进粮店工作,他自己起火做饭,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带我到他那里吃饭。我师专毕业分配到县里工作,尤其结婚后就打算在本乡本土工作一辈子,哥从报纸上看到地区广电局招聘编辑记者消息后赶忙打电话鼓励参加考试,他用自行车带着我报名,参加考试,办调动手续。去年父亲病重,坚持自己伺候父亲,不让我工作分心,他说,你忙吧,我自己能伺候。今年我获奖的消息在本地报纸刊登,哥哥剪下来,装在衣兜,见面高兴地说,这不,我知道你得奖了。有了不顺心的事也总是找哥哥诉说,他安慰我,给我出主意想办法。
哥是我心灵的依靠,哥也尽自己所能为我铺路搭桥,他想法很单纯,就是尽可能让弟弟生活的顺一些。而他自己却屡遭挫折。第二次小卖部停业后,哥哥还是不甘心,总想干点什么,一是他觉得自己年龄还不算大,二是生活压力所迫使。后来市政府为大龄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哥哥才放弃了自己做生意的念头。岗位是免费提供的,可要就业就必须参加考试,我在有关部门找了一个朋友询问是否可以对哥哥关照一下。朋友说,现在透明度高,不敢。我给打气,鼓励他参加考试。考试前哥哥认真进行了准备。我原担心他学历低,怕不行。可哥真是沾了他爱读书看报的光,在二百多人中他的成绩名列第四,这个结果让我兴奋万分,因为这二百人中大专中专文化的多的是。到城管队上临时班,工资五百元,可哥没嫌少,他很珍惜这次机会。由于他肯干,不久就升职为小队长,管几十号人。
前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听后面有人喊我,哥从后面赶来,对我说他现在虽然工资低一点,可很舒心,因为领导和同事都很信任他,国庆节举办系统内歌咏比赛,单位专门让他参加,从来没人嫌弃他这个临时工。哥哥说,到这儿上班是我这几年心情最舒畅的时候。
尽管挪了不少地方,可哥这人很容易满足。没有就业那阵子,哥的情绪相当低落,对我说,如果没有工作他就打算与嫂子一起回老家过日子,把老家的房子收拾一下,把转给别人的地要回来,这样可以自食其力。而现在哥哥完全没有了工作没有着落时的愁容,尽管他现在依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奔波,可他的心情却大为转变。他的儿女都已成家,他也当上了爷爷,可按目前情况看,哥哥是不会安于在家照看孙子的。
这几年我忙于生计,与哥哥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前年,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哥却记得,晚上哥让儿子给我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让我当时就热泪盈眶。而我却没有记着他的生日。今天在大街遇见哥哥后,晚上回家我想起哥哥的生日应该就在这几天,就给侄子打电话询问,侄子说都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是农历十月初四。
农历十月初四,我记住了哥哥的生日。明年我一定祝福他。
本来命里注定要生活在那个叫杜寨小村的两个农民,如今都生活在了城市。虽然我也是整日为生计奔波,可相比较,哥哥绕的圈子更大,路也曲折。
如果年份正常,哥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收成,因为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他赶上了不正常的年代,高小毕业,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哥哥就不得不回家劳动挣工分。哥哥辍学后,老师两次到我家做我父母工作,老师说这孩子不读书实在可惜。可我父母没有办法。哥这棵苗从小就营养不良,这也给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后来父亲对我说,你哥哥要是有你这个文化,可比你有出息。父亲说得是实话,直到现在哥仍保持爱看书的习惯,他会背诵许多唐诗宋词,字写得也很周正有力,全不像一个高小毕业生,如果他有条件读书,肯定会考上大学。可哥没有我幸运。
几乎所有的农活重活哥哥都干过,比如挖海河。第一年去挖海河时,身体单薄的哥哥连带工的看了都皱眉头,认为他顶不住,可哥哥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那年哥哥也就十六七岁,还不到成年。可哥硬是与那些成年人一样在数九寒冬里挖泥拉土挥汗如雨。因为挖海河的活儿虽然很累,可挣工分多,还能填饱肚子。回来后哥哥就成了民兵排长,那些比他年龄大的都乖乖听他的话。
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可哥又不甘心就这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浪费自己。一个从未来往的我们称呼大姨的丈夫在外地搞副业,哥听说后,大雪天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二姐坐在车子后座,趁春节带着我们去给人家拜年,拜年是借口,哥的目的是想跟着人家到外地挣钱。他骑车技术不行,路上摔了几次,十几里路赶到人家村子时,人家竟然不认识我们这三个“亲戚”。哥在回来路上掉了泪。
机会终于来临。那时煤矿在农村大批招工,我们村也分到一个指标。但这个指标原来不是哥哥的,支书给了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人家体检填表准备走时,他的父母却不让去,怕儿子到煤矿出事故,因为我们附近村子刚有一个在煤窑砸死的人。正在支书犹豫把指标给谁的时候,哥哥三番五次去找支书,加上我本家一个在村子当治保主任堂哥的说和,哥终于如愿。他到煤矿上班不到半月内,一个同去的邻村老乡就把性命丢在了几百米的地下,一个老乡偷跑回家,有几个也准备伺机开溜,煤矿不得不派人监督他们这些新到的工人。可哥没有动摇,这并不是他有多高政治觉悟要为我国煤炭事业做贡献,而是他不愿再回到一天工值还不到一毛钱的穷村。哥后来对我说,就咱家那个困难情况,我要是回去,恐怕成家都难。
不久哥也出了事故,他左手中指被机器咬掉半截,担惊受怕之际,哥动了要调换工作的心思。可他两眼一抹黑没有可利用的关系,腰包紧张没有可送礼的资金,他就用笨办法,经常跟劳资科长套近乎,有事没事到科长家走走,帮助干些家务活儿。这招还真感动了科长,加上他手指受伤的原因,哥终于调到井上开卷车。
环境造就人,哥哥就是很好的例证。按说在煤矿开卷车也算不错的工种了,只要把矿工安全提上来和送下去,就不会有问题。可哥后来还是离开了这里。那年我们家正是多事之秋,我第一次高考落榜,秋天母亲病重住进了地区医院,不由得哥哥不担心。他下班后骑车六七十里路到邯郸伺候母亲,还要第二天天不亮赶回峰峰煤矿上班,当时家里相当拮据,他不得不奔忙挣钱给母亲治玻过度的忧虑和劳累使他在工作上出现疏忽,一次往井下送人时,卷车开过了头,几个矿工被蹾伤,幸好没出人命,否则事儿就大了。
一边受批评做检查扣工资,一边惦念母亲的病情和落榜弟弟的前途,本来就消瘦的哥更加憔悴。他说,那一阵子,我哭都没有地方。这次事故也坚定了他离开煤矿的决心。可这又谈何容易?远比他从井下调井上复杂得多。可哥有毅力,他打听到煤矿附近村庄一个在邯郸粮店工作的李哥想回老家工作。他准备与李哥对调,对调在八十年代初很流行,就是双方协商后,单位办手续,甲到乙单位工作,乙到甲单位工作,请客送礼等中间费用几乎没有。可李哥仅仅有此想法,并不着急,人家毕竟在城市工作,工种也好,那时粮本还没取消,想多吃细粮多吃油就得求售粮员通融。哥着急,怕夜长梦多,就一趟一趟到李哥家里做工作,讲李哥回来本地工作的种种好处,终于在1980年底调进了城市粮店,那年秋我考进师专。哥俩终于在城市会面。
哥并不是机会主义者,可哥能抓住机会。当粮食供应基本放开,粮店渐露颓势时,哥又调进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商场,当时这个商场是邯郸最大的,货全,生意很火。这个商场成了哥哥人生高潮和低谷的分水岭。
有在粮店几年从商的积累,哥哥肯吃苦,再加上商场大多是新手,哥很快从站柜台售货员变为部门经理,由部门经理变为楼层副经理。至此,哥哥的人生达到最高度,那几年市场经济还没有全面铺开,一些物资供应相对紧缺,求哥哥购买东西的人也多。哥哥通过关系把嫂子和我侄女侄子的户口农转非,他也不再春种秋收时风尘仆仆回家劳作。
可是好景不长,市场经济大潮把哥哥供职的商场吹打的风雨飘摇,嫂子失去了在商场打扫卫生的差使,第三年,哥哥也在无奈中下岗。失去固定收入,失去了原本打算依靠一生的工作单位,哥哥心理一直难以调整,他不断到单位找我,让我帮忙找工作,有时也不说话,就坐在我办公室看半天报纸。在家里嫂子嘟囔,他心里烦,有时骑一辆破自行车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转悠,有一次我到旧书刊市场转,发现哥哥蹲在一个摊贩前戴着花镜看一本过期杂志。我心里一酸,没敢打扰他就离开了。我能力有限,终究没能给哥哥找到工作,只是牵线让嫂子找到了看自行车的差使,因为嫂子没文化,只有干这个不需要文化的工作。后来哥哥自己找关系在贸易街边开了一个烟酒小卖部,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可不到一年,因为马路扩建,哥哥的小卖部被取消。他又在陵西路找了一个地方,还是烟酒小卖部。开始还可以,一年多后,就有地痞流氓总是去他那里“借钱”,自然是有借无还,说是保护哥哥在这一片没人敢欺负。其实哥哥根本不用那个地痞保护,因为哥哥与周围邻居和商贩搞的关系很好。这个事情哥哥一直不给我说,怕我脾气不好,跟那个地痞干架,或找人收拾地痞,更怕地痞报复。直到停业,在闲谈中哥哥透露了原因,就这样哥哥还说破财免灾。他这个人有时很有主张,有时很软弱,总是与人为善,受屈后自己安慰自己,自我解脱。这可能与他多年靠自己奋斗有关,没有靠山,没有经济力量,只能委曲求全,回家还不愿跟嫂子说,怕嫂子生气。跟我有时偶尔透露一点,但往往是欲言又止,怕我替他操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弟弟心目中的重量。
可以说我是哥哥看着长大的,他对我操的心并不比对他的子女的少。我记得他到煤矿上班第一次回家探亲给我买的礼物是高尔基《童年》小人书。就是“开门办学”不学文化那年月,哥回家总是翻开我的作业本看看,要我把字写好。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又逢母亲病重,家里是一贫如洗,在是让我复读再考,还是尽快回家劳动补贴家用的选择上,有许多亲戚邻居建议我父亲让我尽快去挣钱,哥哥却毫不犹豫支持我复读再考,他对父亲说:我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不能让东汇再走我的老路,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上学。1980年春,病入膏肓的母亲不得不回到老家打发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回家时哥哥除了详尽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还问我有啥困难,我告诉哥哥我的眼近视了,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也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迹。下午哥哥就用自行车带着我到十几里外的一个个人眼科门诊去看。他回煤矿时专门到邯郸的眼镜门市给我配眼镜,找人钉一个小木箱把眼镜邮寄到学校。我读师专时候哥也从煤矿调进粮店工作,他自己起火做饭,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带我到他那里吃饭。我师专毕业分配到县里工作,尤其结婚后就打算在本乡本土工作一辈子,哥从报纸上看到地区广电局招聘编辑记者消息后赶忙打电话鼓励参加考试,他用自行车带着我报名,参加考试,办调动手续。去年父亲病重,坚持自己伺候父亲,不让我工作分心,他说,你忙吧,我自己能伺候。今年我获奖的消息在本地报纸刊登,哥哥剪下来,装在衣兜,见面高兴地说,这不,我知道你得奖了。有了不顺心的事也总是找哥哥诉说,他安慰我,给我出主意想办法。
哥是我心灵的依靠,哥也尽自己所能为我铺路搭桥,他想法很单纯,就是尽可能让弟弟生活的顺一些。而他自己却屡遭挫折。第二次小卖部停业后,哥哥还是不甘心,总想干点什么,一是他觉得自己年龄还不算大,二是生活压力所迫使。后来市政府为大龄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哥哥才放弃了自己做生意的念头。岗位是免费提供的,可要就业就必须参加考试,我在有关部门找了一个朋友询问是否可以对哥哥关照一下。朋友说,现在透明度高,不敢。我给打气,鼓励他参加考试。考试前哥哥认真进行了准备。我原担心他学历低,怕不行。可哥真是沾了他爱读书看报的光,在二百多人中他的成绩名列第四,这个结果让我兴奋万分,因为这二百人中大专中专文化的多的是。到城管队上临时班,工资五百元,可哥没嫌少,他很珍惜这次机会。由于他肯干,不久就升职为小队长,管几十号人。
前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听后面有人喊我,哥从后面赶来,对我说他现在虽然工资低一点,可很舒心,因为领导和同事都很信任他,国庆节举办系统内歌咏比赛,单位专门让他参加,从来没人嫌弃他这个临时工。哥哥说,到这儿上班是我这几年心情最舒畅的时候。
尽管挪了不少地方,可哥这人很容易满足。没有就业那阵子,哥的情绪相当低落,对我说,如果没有工作他就打算与嫂子一起回老家过日子,把老家的房子收拾一下,把转给别人的地要回来,这样可以自食其力。而现在哥哥完全没有了工作没有着落时的愁容,尽管他现在依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奔波,可他的心情却大为转变。他的儿女都已成家,他也当上了爷爷,可按目前情况看,哥哥是不会安于在家照看孙子的。
这几年我忙于生计,与哥哥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前年,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哥却记得,晚上哥让儿子给我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让我当时就热泪盈眶。而我却没有记着他的生日。今天在大街遇见哥哥后,晚上回家我想起哥哥的生日应该就在这几天,就给侄子打电话询问,侄子说都过去一个多星期了,是农历十月初四。
农历十月初四,我记住了哥哥的生日。明年我一定祝福他。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