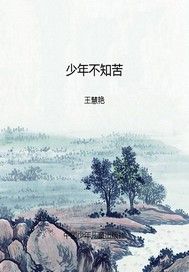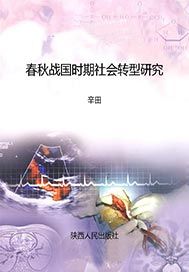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这个生死相拥的节日
这个生死相拥的节日
清明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一个活人与死人共有的节日。
关于清明有多种解释和比喻:清明是一个故事。名臣介子推的耿忠逸卷狷和晋文公重耳的厚情眷念,肇始了一段阴差阳错生死别离的千古传说。
清明是一首诗。细雨霏霏,行人断魂,循着血脉之路且行且吟,从汉唐走到了今。
清明是一幅画。小桥流水,熙熙攘攘,张择端的妙手把生命中的喧闹从宋捧到了今。
而我说,清明是一棵树。氤氲世事,沧桑生命,枝干和根须轮回着生与死、灵与肉。
天亦有情,依然是春雨拉开了清明的序幕。于是,对故乡的牵念就化作了匆匆而归的脚步。
雨润万物,田地的面色由此浓重厚实,麦苗亦秀丽生动,如初潮少女,欣欣然心事多彩的样子。清晰的脚印丈量着久违的乡情。
春雨之于清明并无必然的前提条件和因果关系,都是大自然的派生物,当二者成为人文载体时,人们蓦然觉得二者逻辑上的对应是那么相得益彰。于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成了一种宿命定式,雨是后人的泪滴,清明是故去先人们的显影剂。
村边的杨柳依然精神抖擞,几棵年轮清晰的树桩剖露出生命的横断面。它的躯干已变成棺材随村里的某个老人一起寿终正寝在田地。新增了几棵树桩,便知道村里走了几位老人。在此,人与树是对应的。
树和人一样,都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生命过程。树记载着庄稼人的日子,一圈圈年轮荡漾着庄稼人的喜怒哀乐。渐渐,人老了,树也老了,其中的某一棵与某个老人一同走入土地深层,其余的全成了子孙头上的绿荫,树是村庄的一部分,也是人的一部分。
老树的躯干和老人的躯体携手走后,树桩的周围又衍生出许多小树,纤柔的小树与老人遗留在世间的子孙就成了伙伴,根的延伸和生命的循环又是一个开始。
生命在时间的直线上滑行,田野是它纵横驰骋的平台,人、鸟兽、村庄、庄稼、树木花草是它的轨迹。
树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速度,年轮在一定的时候变得迟缓起来,不如年幼时的迅速,去年还是细细的一条胳膊,今年却变成了小腿一般。这与人一样的道理,原来一个小不点在你眼皮下晃来晃去,一年或几年不见,猛不丁站在了你面前,让你逼视或仰视生命的朝气。所以,面对那些一脸狐疑的孩子,我又一次感到了对土地的陌生。一一询问着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的名字,然后按照他们的答复,快速搜寻筛选自己的记忆,并按照自己原有的印象储存,从眼前稚气的脸上一一验证他们长辈的痕迹,比如脸型、嘴、眼。然而扭转身我却难再将他们认出。这种无意识的遗忘,和孩子们“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是对应的。生命在某种程度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因亲近而繁衍,因遗忘而更迭。若干年后我的记忆消失,那时收留我灵魂的是城市的钢筋水泥,还是乡间田野?我不敢贸然揣测。
春雨后的阳光妩媚着田野,灿烂如火的油菜花和炽白如雪的梨花都忘情恣肆地随风舞蹈,如故去的先人们的张张笑脸,在坟头欢天喜地迎接着亲人的团聚。
田野上的坟是村的根,村庄是坟的躯干;故去的先人是活人的根,活人是先人的躯干;如树一样的道理。祭奠先人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苍烟落照,人神相拥,这是世间最热闹最混沌的一天,活人与死人会晤,死人与活人共享。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庄稼人,最后化作一粒种子植入泥土,沉入历史的厚层,延伸着生命的根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言之谆谆。
我跪在母亲坟前,点燃世俗的纸箔,这是我报答生命之恩的唯一直接的方式。冥冥中我看到了母亲沧桑的脸。祭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思念是我一生的情结。
母亲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知道,是贫穷让母亲不敢有照一张相的奢望,当然亲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母亲会走的那样匆忙。于是我就在记忆里寻觅。院中的枣树应该记得母亲在初春月光下纺车摇出的叹息,干枯的砖井应该记得母亲冬天洗菜时皲裂的双手,风应该记得母亲为生活奔波的斑白霜发,田地应该记得母亲躬耕的弯腰。这些都刻在她52岁的年轮中,也定格在我17岁的记忆里。
至今,24个春天,24个清明,每圈年轮都有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操劳的身影。我知道,我是母亲栽植在田野上的一棵树,我延续着她老人家的生命。
树杈上的窝巢依旧在等待着候鸟的归来。我就是家乡的一只候鸟,可我只有一年一度的清明才能归来。又是来去匆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为生计役使。在这点,我不如候鸟对家乡的倾情。我知道,只要安有亲人的灵魂,即使最荒凉的地方,也是后人眼中诗意盎然的杏花村。
可回望村庄我又怅然若失,因为在那茂密的树木中却没有一棵属于我。虽然我的根在这里,可我的躯干却成了城市世俗中的一个摆设。我觉得自己愧对母亲,愧对土地。回城的路上不时有酒家闪过,我却不敢把目光停留,因为城市的灯红酒绿扎不下我精神的根须,不能茂盛我的躯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沉甸甸的心思又在明年的日历打了一个结:清明。
关于清明有多种解释和比喻:清明是一个故事。名臣介子推的耿忠逸卷狷和晋文公重耳的厚情眷念,肇始了一段阴差阳错生死别离的千古传说。
清明是一首诗。细雨霏霏,行人断魂,循着血脉之路且行且吟,从汉唐走到了今。
清明是一幅画。小桥流水,熙熙攘攘,张择端的妙手把生命中的喧闹从宋捧到了今。
而我说,清明是一棵树。氤氲世事,沧桑生命,枝干和根须轮回着生与死、灵与肉。
天亦有情,依然是春雨拉开了清明的序幕。于是,对故乡的牵念就化作了匆匆而归的脚步。
雨润万物,田地的面色由此浓重厚实,麦苗亦秀丽生动,如初潮少女,欣欣然心事多彩的样子。清晰的脚印丈量着久违的乡情。
春雨之于清明并无必然的前提条件和因果关系,都是大自然的派生物,当二者成为人文载体时,人们蓦然觉得二者逻辑上的对应是那么相得益彰。于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成了一种宿命定式,雨是后人的泪滴,清明是故去先人们的显影剂。
村边的杨柳依然精神抖擞,几棵年轮清晰的树桩剖露出生命的横断面。它的躯干已变成棺材随村里的某个老人一起寿终正寝在田地。新增了几棵树桩,便知道村里走了几位老人。在此,人与树是对应的。
树和人一样,都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生命过程。树记载着庄稼人的日子,一圈圈年轮荡漾着庄稼人的喜怒哀乐。渐渐,人老了,树也老了,其中的某一棵与某个老人一同走入土地深层,其余的全成了子孙头上的绿荫,树是村庄的一部分,也是人的一部分。
老树的躯干和老人的躯体携手走后,树桩的周围又衍生出许多小树,纤柔的小树与老人遗留在世间的子孙就成了伙伴,根的延伸和生命的循环又是一个开始。
生命在时间的直线上滑行,田野是它纵横驰骋的平台,人、鸟兽、村庄、庄稼、树木花草是它的轨迹。
树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速度,年轮在一定的时候变得迟缓起来,不如年幼时的迅速,去年还是细细的一条胳膊,今年却变成了小腿一般。这与人一样的道理,原来一个小不点在你眼皮下晃来晃去,一年或几年不见,猛不丁站在了你面前,让你逼视或仰视生命的朝气。所以,面对那些一脸狐疑的孩子,我又一次感到了对土地的陌生。一一询问着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的名字,然后按照他们的答复,快速搜寻筛选自己的记忆,并按照自己原有的印象储存,从眼前稚气的脸上一一验证他们长辈的痕迹,比如脸型、嘴、眼。然而扭转身我却难再将他们认出。这种无意识的遗忘,和孩子们“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是对应的。生命在某种程度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因亲近而繁衍,因遗忘而更迭。若干年后我的记忆消失,那时收留我灵魂的是城市的钢筋水泥,还是乡间田野?我不敢贸然揣测。
春雨后的阳光妩媚着田野,灿烂如火的油菜花和炽白如雪的梨花都忘情恣肆地随风舞蹈,如故去的先人们的张张笑脸,在坟头欢天喜地迎接着亲人的团聚。
田野上的坟是村的根,村庄是坟的躯干;故去的先人是活人的根,活人是先人的躯干;如树一样的道理。祭奠先人是绿叶对根的情谊。
苍烟落照,人神相拥,这是世间最热闹最混沌的一天,活人与死人会晤,死人与活人共享。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庄稼人,最后化作一粒种子植入泥土,沉入历史的厚层,延伸着生命的根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言之谆谆。
我跪在母亲坟前,点燃世俗的纸箔,这是我报答生命之恩的唯一直接的方式。冥冥中我看到了母亲沧桑的脸。祭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思念是我一生的情结。
母亲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知道,是贫穷让母亲不敢有照一张相的奢望,当然亲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母亲会走的那样匆忙。于是我就在记忆里寻觅。院中的枣树应该记得母亲在初春月光下纺车摇出的叹息,干枯的砖井应该记得母亲冬天洗菜时皲裂的双手,风应该记得母亲为生活奔波的斑白霜发,田地应该记得母亲躬耕的弯腰。这些都刻在她52岁的年轮中,也定格在我17岁的记忆里。
至今,24个春天,24个清明,每圈年轮都有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操劳的身影。我知道,我是母亲栽植在田野上的一棵树,我延续着她老人家的生命。
树杈上的窝巢依旧在等待着候鸟的归来。我就是家乡的一只候鸟,可我只有一年一度的清明才能归来。又是来去匆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为生计役使。在这点,我不如候鸟对家乡的倾情。我知道,只要安有亲人的灵魂,即使最荒凉的地方,也是后人眼中诗意盎然的杏花村。
可回望村庄我又怅然若失,因为在那茂密的树木中却没有一棵属于我。虽然我的根在这里,可我的躯干却成了城市世俗中的一个摆设。我觉得自己愧对母亲,愧对土地。回城的路上不时有酒家闪过,我却不敢把目光停留,因为城市的灯红酒绿扎不下我精神的根须,不能茂盛我的躯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沉甸甸的心思又在明年的日历打了一个结:清明。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