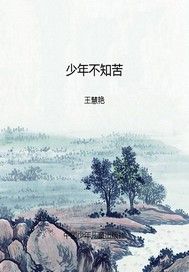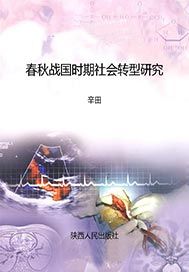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那个失踪的女人
那个失踪的女人
偶然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碰见了多年前的朋友洪,就再次证实那个叫英的女人失踪了。望着洪远去的背影我在街道树下呆立着,那纷纷坠落的枯叶无声地敲打着我的记忆。
现在想来我与英是有缘分的,有缘分不是说我与她有多少瓜葛,而是与她生活有关的两个男人都是我的朋友。
刚认识英时她还是一个水灵灵的女孩。那时我也年轻,懵懂的我刚从师专毕业就到家乡中学成了一名教师。尽管地处偏僻,校园破败,可对于我这个刚跳出农门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知足的,上课、批改作业、与学生做游戏、在操场来回奔跑,都乐此不彼。要不是英的出现,一向易于满足的我很可能现在还是一名教师。
英的出现与我的一个同事有关,这个同事叫阿木。阿木是我同届但不同专业的同学,他人高马大,会二郎拳。那会儿《霍元甲》正如火如荼迷惑着我年轻的心,阿木就成了我的偶像,晚上自习学生睡觉后我和几个年轻教师就跟着阿木在操场上蹲马步、扒单杠、练劈脚,以此来消磨过剩的荷尔蒙。一身臭汗躺在单人床上常常辗转反侧,总有一种冲动的东西在体内冲撞,后来想,那应该是对爱情渴望的缘故吧。
阿木是我们这一拨中最早搞对象的,他的第一个对象是英。那时找对象首要条件是非农业户口,我们这些农村考学出来的,都清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都不愿意再与土地打交道。英那时在一个距离我们四十多里路的乡里工作,长得小巧玲珑,她来我们学校时穿一身豆青色衣裳,站在校园西北角我们单身教师宿舍门前的柳树下,让众多老师学生都忍不住西北望。年轻好奇,阿木和英在宿舍里面说话,我们在外面鬼转,总想着自己能搀乎进去,不时进去装作找东西打探一下,有一个就蹲在窗户下偷听。
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从阿木情况看,爱情至少是长精神的。那一阵子阿木脸上总是挂着太阳,走路一跳一跳地弹性十足,就连上厕所都哼着邓丽君的《何时君再来》。后来阿木几乎每天都要骑车风尘仆仆地赶去与英约会。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尝到爱情的滋味。阿木回来后我们穷追不舍地打听他们的每一个细节,是否拥抱接吻,说了哪些话。然而阿木的这种兴奋心情只保持了三个月。失恋后的阿木像神经了一样,课也不上,整天阴着脸,走路耷拉着头,有时自言自语。失恋的原因是英嫌他是教师,没前途。所以,阿木就发誓一定要离开这个破学校,他首要目标是转行不再当老师,如果转行不成,其次是调进县城的学校。阿木是骨干教师,学校当然不放。他就告病假,不上班。软磨硬泡,学校只得放人。临走,阿木颇为伤感地对我说,想办法离开这儿吧,社会上谁看得起你一个没权没势的穷教师呢?阿木提醒和带动了我们,后来我们一起分来的几个年轻教师都先后离开了这里。当然,离开教师队伍的阿木也没有挽回他与英的爱情。
三年后再见到英时我已经调入县城工作。一次随同事去他的同学家,也就是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洪家串门。进门后就觉得洪的老婆面熟,仔细一看是英。她当然也认出了我,脸微微一红,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让座倒水。同事向洪和英介绍我。我也装作不认识似的点头问好,以避免尴尬。不咸不淡地坐了一会儿就拔腿走人。
虽然英没能与阿木结合,但她选择洪是没有错的。洪是干部子弟,家庭条件相当优越,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后来通过洪的父母关系英在结婚后调进了县城的一个金融部门工作。调入县城工作的英很快就成为领导时尚的主儿,总是见她时髦地骑着崭新的坤车在街上优雅地慢行,后来她的坤车变成了时兴的小摩托。再后来洪的父母相继离开领导岗位,洪还是平平淡淡守着死工资按部就班地上班。县城不断传言英与洪经常吵架,嫌洪窝囊,还听说她与一些经常打交道的大款们的风流韵事。没有父母作靠山的洪自然惹不起越来越生猛的英,经常借酒浇愁。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不知道是生理原因,还是另有企图。现在想来,英似乎早有预谋。
我到市里工作后与洪见面较少,在两年前我就从过去的同事那里听说英跟一个深圳的老板私奔,至今杳无音信。这次见了憔悴的洪,知道他还是独身,其他我也不便打听。
望着洪惴惴而行的孤独背影,我的心就像渐寒的秋风一样凉巴巴的没个着落。显然我没有理由和资格去责怪英,因为这是她个人的私事。而对洪我只有同情,像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见了落叶就落泪一样,性格使然。因为枯叶和这世道一样是循环往复的,只是凑巧砸在了洪的身上,阿木就相对侥幸了一点。要是这事摊在自己头上又该如何?我也曾想过,但终无结果,因为人生没有假设。
现在想来我与英是有缘分的,有缘分不是说我与她有多少瓜葛,而是与她生活有关的两个男人都是我的朋友。
刚认识英时她还是一个水灵灵的女孩。那时我也年轻,懵懂的我刚从师专毕业就到家乡中学成了一名教师。尽管地处偏僻,校园破败,可对于我这个刚跳出农门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知足的,上课、批改作业、与学生做游戏、在操场来回奔跑,都乐此不彼。要不是英的出现,一向易于满足的我很可能现在还是一名教师。
英的出现与我的一个同事有关,这个同事叫阿木。阿木是我同届但不同专业的同学,他人高马大,会二郎拳。那会儿《霍元甲》正如火如荼迷惑着我年轻的心,阿木就成了我的偶像,晚上自习学生睡觉后我和几个年轻教师就跟着阿木在操场上蹲马步、扒单杠、练劈脚,以此来消磨过剩的荷尔蒙。一身臭汗躺在单人床上常常辗转反侧,总有一种冲动的东西在体内冲撞,后来想,那应该是对爱情渴望的缘故吧。
阿木是我们这一拨中最早搞对象的,他的第一个对象是英。那时找对象首要条件是非农业户口,我们这些农村考学出来的,都清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都不愿意再与土地打交道。英那时在一个距离我们四十多里路的乡里工作,长得小巧玲珑,她来我们学校时穿一身豆青色衣裳,站在校园西北角我们单身教师宿舍门前的柳树下,让众多老师学生都忍不住西北望。年轻好奇,阿木和英在宿舍里面说话,我们在外面鬼转,总想着自己能搀乎进去,不时进去装作找东西打探一下,有一个就蹲在窗户下偷听。
有人说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从阿木情况看,爱情至少是长精神的。那一阵子阿木脸上总是挂着太阳,走路一跳一跳地弹性十足,就连上厕所都哼着邓丽君的《何时君再来》。后来阿木几乎每天都要骑车风尘仆仆地赶去与英约会。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尝到爱情的滋味。阿木回来后我们穷追不舍地打听他们的每一个细节,是否拥抱接吻,说了哪些话。然而阿木的这种兴奋心情只保持了三个月。失恋后的阿木像神经了一样,课也不上,整天阴着脸,走路耷拉着头,有时自言自语。失恋的原因是英嫌他是教师,没前途。所以,阿木就发誓一定要离开这个破学校,他首要目标是转行不再当老师,如果转行不成,其次是调进县城的学校。阿木是骨干教师,学校当然不放。他就告病假,不上班。软磨硬泡,学校只得放人。临走,阿木颇为伤感地对我说,想办法离开这儿吧,社会上谁看得起你一个没权没势的穷教师呢?阿木提醒和带动了我们,后来我们一起分来的几个年轻教师都先后离开了这里。当然,离开教师队伍的阿木也没有挽回他与英的爱情。
三年后再见到英时我已经调入县城工作。一次随同事去他的同学家,也就是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洪家串门。进门后就觉得洪的老婆面熟,仔细一看是英。她当然也认出了我,脸微微一红,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让座倒水。同事向洪和英介绍我。我也装作不认识似的点头问好,以避免尴尬。不咸不淡地坐了一会儿就拔腿走人。
虽然英没能与阿木结合,但她选择洪是没有错的。洪是干部子弟,家庭条件相当优越,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后来通过洪的父母关系英在结婚后调进了县城的一个金融部门工作。调入县城工作的英很快就成为领导时尚的主儿,总是见她时髦地骑着崭新的坤车在街上优雅地慢行,后来她的坤车变成了时兴的小摩托。再后来洪的父母相继离开领导岗位,洪还是平平淡淡守着死工资按部就班地上班。县城不断传言英与洪经常吵架,嫌洪窝囊,还听说她与一些经常打交道的大款们的风流韵事。没有父母作靠山的洪自然惹不起越来越生猛的英,经常借酒浇愁。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不知道是生理原因,还是另有企图。现在想来,英似乎早有预谋。
我到市里工作后与洪见面较少,在两年前我就从过去的同事那里听说英跟一个深圳的老板私奔,至今杳无音信。这次见了憔悴的洪,知道他还是独身,其他我也不便打听。
望着洪惴惴而行的孤独背影,我的心就像渐寒的秋风一样凉巴巴的没个着落。显然我没有理由和资格去责怪英,因为这是她个人的私事。而对洪我只有同情,像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见了落叶就落泪一样,性格使然。因为枯叶和这世道一样是循环往复的,只是凑巧砸在了洪的身上,阿木就相对侥幸了一点。要是这事摊在自己头上又该如何?我也曾想过,但终无结果,因为人生没有假设。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