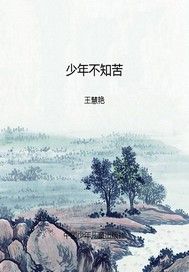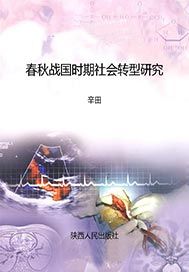当前位置:
经管励志
> 有一种境界叫孤独
> 像柳树一样活着
像柳树一样活着
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可惜当时并未仔细把玩脉脉此情。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达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植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都能用上了。
父亲还用耕种土地的思维方式来考量我的前程。因为,此时跟随了我十七年的农业户口终于随我迁往了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人生从此将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本该属于我的那份责任田也由国家转换成了令乡亲们羡慕不已的供应票证。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却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城市),柳树在那头(乡村)。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那时,柳树浩浩荡荡点缀着荒凉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气派。现在想来,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都接二连三地充斥到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城市出生的同龄人不属于柳树种类,他们是非农业户口,虽然与土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却有相对优越的生存土壤。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贵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难。于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除了老三届外,最拥挤的就是我们这一拨人了。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明知春风似刀,我们偏向刀丛涌挤。
受招生数量限制,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百分之四点三,这就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五点七的人在高考后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有的参军到部队考军校,搞曲线救国;更多的是屡败屡战。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这数十步却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却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因为他们考上考不上都无关紧要,反正高中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为此,我的同学张庆雨气愤而又无奈地对我说:我要是非农业户口,才不费这龟孙傻劲儿哩!其实在我看来,张庆雨在学习上就没费过什么力气。那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学校也是这个态度,连单独的文科班也没有,十多个学文科的同学混编在理科班里,上物理化学时他们就到教室外边背诵历史地理。张庆雨挟着课本东游西逛,没想到第一年他就考上了地区财校。这使我大受启发,我觉得他的文科基础比我还差些,所以第二年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那时的想法,只要能考上学成为非农业户口,学什么都是其次。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所以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青春的萌动不断在油灯上摇曳,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同学王静花就常常走到我们的梦中。但往往又是转瞬即逝,人家一个非农业户口就足以让我们自渐形秽白日做梦。于是,许多男同学的床单上都留下了青春幻觉的遗痕。心理显然抑制不住生理。王静花在夏天可以每天举着一根冰棍斜靠在门框上优雅地享受,羡慕得我们口干舌燥浑身冒汗。可我们不敢,因为五分钱几乎是我们两顿饭的菜票。所以,在可望不可即中,那熠熠闪光的檩梁椽木在我们眼里就成了面目狰狞的骷髅架,屋顶上片片蓝瓦也成了禁锢我们青春冲动的稠密的鳞甲。
师专破破烂烂的教室,让我有仍在县中学一样的感觉。陌生的面孔和多杂的口音以及许多经历大抵相似的同学,多多少少填补了一点好奇心。那年有两件事令我难忘,一是审判“四人帮”,一是学校所在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看到年龄大的同学拿着一张张选票招摇,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就忿忿不平地找班主任讨说法。班主任哑然失笑:你们不满十八周岁,还不是真正的公民,没有选举权。这才知道了公民和选举权这两个概念。
我们那届学生来源依然杂乱,年龄参差不齐,大小差距有七八岁之多。老宽在地方铁路开了五年小火车,被精减下来后胡子拉茬地同我们坐在了一个教室,看见他我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当过兵的、上过几年临时班的都有。这些同学在社会上见多识广,每天晚自习后,他们就抽着烟半躺在床被上神吹,话题大多是围绕女人,他们甚至把见到的男女肉体接触讲得绘声绘色,听得我们面红耳赤心惊肉跳。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知足,总是曾经沧海的样子。而我们这些从校门走进校门的同学,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总是兴趣盎然倾听他们的描述,可出了宿舍又一本正经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
潜移默化,我们这些人的故作清高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开始了偷偷摸摸的约会。在我上铺的S总是每天很晚才回宿舍,上床时铁架子吱吱咯咯地响,惊我好梦烦恼不堪,总是与之争吵。S却酸溜溜地说:孟子曰,食色,性也。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教室开夜车看书学习,他的鸿鹄之志使他的人生理想早已超过了社会为他既定的教师这个职业。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除了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后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S神色黯然地说:完了,这跟回村里当农民有啥区别?显然,现实冷酷了他的理想。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们那些年龄小的同学毕业时都以公民的身份步入了社会,而这个公民也仅是年龄层面上的,谁知道将来自己对社会和社会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样呢?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搭理它了,任其疯长,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了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而他能为我考虑的也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
我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认为脱离了稼穑劳累,眼前便是万里江山。当我离开村庄行将告别一年四季的臭汗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感到灰心,他说:毕业了当个老师也不懒,最起码好找媳妇。其实在我第一次落榜后,鉴于当时家庭条件和我本人的自然条件,父亲就私下与哥哥商量,一旦我再次落榜回村后成了老大难,就花钱从四川给我买个女人。为此,他甚至有意识地去讨好村里的人贩子王老拐,以期将来得到优惠。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那时母亲刚病逝,家里一贫如洗,我考不上学也只能走这一步。我那个考了六年的同学就是如此,考到第三年他就灰了心,准备偃旗罢兵,可家中弟兄多,媒人介绍他到外村倒插门,在人们的意识中,这是一种比买女人成家更让人轻视的婚姻,所谓“小子无能,改名换姓”,可就这样女方还嫌他家穷相貌差,所以才促使他横下心走过了独木桥。其实同学中和我一样困难的还很多,张庆雨就是一个。不过张庆雨自然条件好,人聪明,长得有模样。
所以我考上学后,父亲就长长松了一口气,总是自豪地向别人炫耀:好树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没管过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柳树经成了父亲多年的谈资。
而我在城市的种种经历证明父亲的那套柳树经是片面的,它只适用于柳树和我考学之前。因为城市不是乡村,一个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周末,我童心骤起,要为儿子拧一个柳笛,可走了许多大街小巷,竟没有找到一棵柳树,在经过公园门口时才发现几株柳树势单力薄地挤压在众多花木之间,而气势汹汹的法国梧桐臃肿地充塞着街道,那窈窕细柳的丝丝拂面已成了公园里的一个标本了。
一代又一代乡下人从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树的纯朴延续着城市的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树用自己的韧性丰富着城市的风景和人们的情感,折柳惜别、烟柳传情、柳丝寄意——柳树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
如今,城市的酥胸粉脸上已没了柳树的印痕。是因为城市的进步和无情,还是柳树种类的退化?
不管城市是否欢迎,我们都义务反顾地走进了城市。我们承袭着柳树纯朴的本性,带着柳树的失落在城市钢筋水泥间寻觅理想的高贵。与当年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第一代进城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疾风暴雨专政手段的强硬;与后来大批招工进城的第二代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侥幸后沾沾自喜的知足和驯服;我们凭的是自己的智力,没有颐指气使的资本,也不愿低眉顺眼任人摆布。
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学在四散蛰伏乡下后不久,许多又寻梦到了城市。那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腔豪情还在胸中澎湃,见了面总是相互鼓励,认为自己同样是城市八九点钟的太阳。然而,秃发耗尽了脑汁,皱纹沧桑了心理,短短十多年后,当年的相互鼓励竟变成了杯盏交错的相互安慰,渐渐学会了用酒精来抚平心中的沟壑了。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去年冬我和同学S让酒精浸泡得难以自恃的那次。这本该是庆贺他升迁的喜酒,他们处室提拔两个副处级,三个人中S各方面条件第一,考察和公示都没问题,然而宣布时他却名落孙山,提上去的一个是局长的儿子,一个是大企业厂长的儿子,就S一人没有后台。他明白自己的劣势在哪里,可又于心不甘。流出来的泪水比灌进肚的酒还多。他从洗手间呕吐回来时,一个我很面熟的人搀扶着S走了进来,此人也是一身酒气。坐下后才知道是师专同届物理系的,在某要害部门给领导当秘书,我这才想起,开会时曾见过面,怪不得面熟。我问这位秘书同学,这次大面积人事安排他升迁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还是老样子,和他一拨的秘书都已提拔,他大拇指搓着四指做点钱状,说:没这个不行。也许是同学缘故,或许他也喝高了,大声说:妈的,通过我给领导送钱跑官的都上去七八个了。后来我才知道,领导之所以让他当秘书,是因为他出身农家没有背景,老实忠厚能干,仅此而已。
那顿饭是那秘书同学埋单,一个经他牵线升迁的官人在隔壁雅间设宴答谢,不用他掏腰包。饭毕,他豪爽地说:走,上四楼,新来的俄罗斯小姐,全套服务。我明白这“全套”的意思,便借故避开,身后饭店门口的霓虹灯闪着凄迷暧昧的光。
淮南为桔,淮北为枳,水土之异让我们先天不足,囊中羞涩让我们的“金”绣前程黯然失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得不这样来安慰自己,纡解尴尬。窘迫的境况已使三个柳绵一样的同学随风而去,刚刚人到中年,生命之花便黯然凋谢,可附在枝上摇摆的我们的芳草依旧远在天涯,遥遥无期。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我们既未得道,又未成器,曾经舍我其谁的理想鲜馅像汤圆一样在空旷的世俗中滚荡,庸碌的尘埃一层层岁岁缠绕,渐渐变成了一个个适合社会口味的毫无个性的面球,成为他人的陪衬和祭品。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千年前风流词人的无奈难道真的要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吗?
在乡下人眼里,只要你是非农业户口,统统把你归纳到城市人的行列,不管你在哪里工作。他们认为,城市人总是欢游在幸福的海洋里。汝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被一张“城市人”的金纸包裹着,外表灿烂光亮,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除非这张金纸出现了破洞。张庆雨就是首先出现破洞的一个。所以他也常是我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之一。
张庆雨的破洞出现在婚姻上。
我的儿子开始上小学时,张庆雨的童子身还坚如磐石。不是他心理和生理上有问题,也不是工作单位差,是自己的承诺阻碍了他的婚姻。他下有两个挨肩的弟弟,父母都是老实巴交农民,为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发誓给两个弟弟成家后才考虑自己婚姻大事。与他对桌办公的女朋友也曾对他情意绵绵,可对他的家庭条件烦恼不堪,加上长年累月的爱情长跑和庆雨的升迁受阻,终于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局长的儿子。于是性格内向的张庆雨在家庭和婚姻重压下,精神出现了问题。当我再见到他时,他憔悴不堪地在精神病院呆若木鸡,身边是年迈的父母。他一个劲儿向我打听市场上钢筋水泥的价格,说要回家盖一座四层大楼,父母住一层,他和俩弟弟各住一层。我知道他是妄语,他现在也没这个能力,可那出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让我几乎落泪。
是啊,我们这些当初拼命跳出农门的乡下人,哪一个没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哪一个身后没有光宗耀祖殷殷期盼的目光?正是这刻骨铭心的责任感使我们游移在城乡之间,承受着双倍的压力。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的《杨柳枝词》常常与女同学王静花一块在我脑海浮动。
没有春江水暖的诗意,没有板桥遗踪的回味,只有青春朦胧中的美人和校园垂柳记忆的撩拨。然而,当二十年后在县城街头见到这位曾经的梦中情人时,美人的概念竟像柳树皮一样粗糙。厚厚的脂粉似是而非地应付着脸蛋对青春的乞求,皱纹流窜着岁月的狠毒,嘴唇涂着人为的血红,脑袋上跳跃的马尾辫已让时光磨消了锐气——一切征兆和现实都让我领略了岁月的无情。那曾诱着我们青春某个部位不由自主跃跃欲试的高耸弹性的胸脯也已平淡。最平淡的还是她的生活,当初令人羡艳的售货员与下岗连在了一起。时下,下岗一词是与非农业户口连在一起的,农民在土地上的岗位是相对恒定的。
世事无常,当初我们追求非农业户口的含金量现已大打折扣。正如柳树从城市视野中淡出一样,风水轮转,很难判定炕的哪头有持久的热力。
在见到王静花之前,有同学传言她下岗后靠一身过时的皮肉生活,我半信半疑,因为她当初高傲的神情一直贮存在我记忆中,那是一种对我们这些乡下同学不屑一顾的优越感。然而,此时传言得到了证实,那吃冰棍的自豪变成了抽烟的老练,一个个烟圈飘着两眼的迷茫。就在她拉开坤包找东西记录我的通讯地址时,我看到了几个粉红色的安全套在坦然地向外张望,我断定这就是她干活的工具。她凄然一笑,略带羞涩地把安全套压在卫生纸的下边。那个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号码,让我想象不出灯红酒绿中那曾经高傲的脸是一种什么神情。此时,我对残花败柳的尴尬也多了一份理解,甚至是同情,因为世道使然。道德本来就是束缚人们的一条精神腰带,宽松尺度只有自己把握,社会标准都是仅供参考。
改变不了自己命运,就要改变自己性格,我们像柳树一样努力适应着上苍的安排。受人颐指气使的琐碎一天天掩埋着曾经的壮志豪情。而对情义的珍重却一天天与日俱增,惺惺相惜也好,同病相怜也罢,我们毕竟在同样的境遇中挣扎。所以,当我从门岗登记簿上看到“张庆雨”三个字时,心里就陡然一阵发热,那个在大门外徘徊已久的肮脏的乡下人硬是让责任心极强的门岗给赶走了,只有我熟悉的那三个字可怜巴巴地趴在纸上,已失去了往昔神采飞扬的硬气。不知是他发病时潜意识里对我这个要好同学的惦念,还是清醒后专门从乡下老家来找我倾诉苦闷呢。
我在汽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寻觅那熟悉的身影,眼前总是晃动他那抽搐变异的表情。可一辆辆汽车碾碎了我急切的热情,此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奈和无能。更让我心痛的是,这竟是我和张庆雨最后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因为十多天后,老家传来他自缢的噩耗。
赶回老家,我久久打量着村外那棵歪斜的柳树,我想象不出两股细绳绞在脖颈时的痛苦。可我相信,庆雨走向柳树时一定是清醒的,他一定想到了自己活着的使命和无力改变命运的悲哀。他的自尊使他不愿成为亲人们的拖累。于是,在硕果累累的秋天,柳树收获了张庆雨。我失去了一个曾经推心置腹的好兄弟。
无心插柳柳成荫。乡间许多坟头前的柳树往往就是人们无心而天之有意的手笔。孝子的灵幡由柳枝糊制而成,待逝者下葬时灵幡埋在墓坑的一头,于是柳枝发芽生根,渐成树木。田地上一丛丛野柳往往是一个个生命的注解。而张庆雨的坟头光秃秃的一无所有,他没有后代,没有人为他打幡送魂,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天意的注解。其实那只是一种外在的符号,因为张庆雨本身就是柳树一种写意的注解。
后来我想,柳树退守乡野,并不能说明城市的冷漠无情,真正的悲哀在于柳树生不逢时的大众化和生存土壤的人为荒漠吧,正如我们这一拨挣扎在城市的乡下人,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福祸相倚,好在我们还有这赖以生存的乡野作后盾。可回到老家,当年父亲栽植在地头的那排柳树却在秋风中陌生地摇着头,显然,它把我当作城市人了。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可惜当时并未仔细把玩脉脉此情。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达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植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都能用上了。
父亲还用耕种土地的思维方式来考量我的前程。因为,此时跟随了我十七年的农业户口终于随我迁往了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人生从此将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本该属于我的那份责任田也由国家转换成了令乡亲们羡慕不已的供应票证。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却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城市),柳树在那头(乡村)。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那时,柳树浩浩荡荡点缀着荒凉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气派。现在想来,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都接二连三地充斥到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城市出生的同龄人不属于柳树种类,他们是非农业户口,虽然与土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却有相对优越的生存土壤。我一直这样认为。
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贵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难。于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除了老三届外,最拥挤的就是我们这一拨人了。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明知春风似刀,我们偏向刀丛涌挤。
受招生数量限制,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百分之四点三,这就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五点七的人在高考后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有的参军到部队考军校,搞曲线救国;更多的是屡败屡战。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这数十步却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却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因为他们考上考不上都无关紧要,反正高中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为此,我的同学张庆雨气愤而又无奈地对我说:我要是非农业户口,才不费这龟孙傻劲儿哩!其实在我看来,张庆雨在学习上就没费过什么力气。那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学校也是这个态度,连单独的文科班也没有,十多个学文科的同学混编在理科班里,上物理化学时他们就到教室外边背诵历史地理。张庆雨挟着课本东游西逛,没想到第一年他就考上了地区财校。这使我大受启发,我觉得他的文科基础比我还差些,所以第二年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那时的想法,只要能考上学成为非农业户口,学什么都是其次。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所以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青春的萌动不断在油灯上摇曳,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同学王静花就常常走到我们的梦中。但往往又是转瞬即逝,人家一个非农业户口就足以让我们自渐形秽白日做梦。于是,许多男同学的床单上都留下了青春幻觉的遗痕。心理显然抑制不住生理。王静花在夏天可以每天举着一根冰棍斜靠在门框上优雅地享受,羡慕得我们口干舌燥浑身冒汗。可我们不敢,因为五分钱几乎是我们两顿饭的菜票。所以,在可望不可即中,那熠熠闪光的檩梁椽木在我们眼里就成了面目狰狞的骷髅架,屋顶上片片蓝瓦也成了禁锢我们青春冲动的稠密的鳞甲。
师专破破烂烂的教室,让我有仍在县中学一样的感觉。陌生的面孔和多杂的口音以及许多经历大抵相似的同学,多多少少填补了一点好奇心。那年有两件事令我难忘,一是审判“四人帮”,一是学校所在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看到年龄大的同学拿着一张张选票招摇,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就忿忿不平地找班主任讨说法。班主任哑然失笑:你们不满十八周岁,还不是真正的公民,没有选举权。这才知道了公民和选举权这两个概念。
我们那届学生来源依然杂乱,年龄参差不齐,大小差距有七八岁之多。老宽在地方铁路开了五年小火车,被精减下来后胡子拉茬地同我们坐在了一个教室,看见他我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当过兵的、上过几年临时班的都有。这些同学在社会上见多识广,每天晚自习后,他们就抽着烟半躺在床被上神吹,话题大多是围绕女人,他们甚至把见到的男女肉体接触讲得绘声绘色,听得我们面红耳赤心惊肉跳。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知足,总是曾经沧海的样子。而我们这些从校门走进校门的同学,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总是兴趣盎然倾听他们的描述,可出了宿舍又一本正经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
潜移默化,我们这些人的故作清高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开始了偷偷摸摸的约会。在我上铺的S总是每天很晚才回宿舍,上床时铁架子吱吱咯咯地响,惊我好梦烦恼不堪,总是与之争吵。S却酸溜溜地说:孟子曰,食色,性也。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教室开夜车看书学习,他的鸿鹄之志使他的人生理想早已超过了社会为他既定的教师这个职业。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除了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后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S神色黯然地说:完了,这跟回村里当农民有啥区别?显然,现实冷酷了他的理想。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们那些年龄小的同学毕业时都以公民的身份步入了社会,而这个公民也仅是年龄层面上的,谁知道将来自己对社会和社会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样呢?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搭理它了,任其疯长,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了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而他能为我考虑的也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
我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认为脱离了稼穑劳累,眼前便是万里江山。当我离开村庄行将告别一年四季的臭汗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感到灰心,他说:毕业了当个老师也不懒,最起码好找媳妇。其实在我第一次落榜后,鉴于当时家庭条件和我本人的自然条件,父亲就私下与哥哥商量,一旦我再次落榜回村后成了老大难,就花钱从四川给我买个女人。为此,他甚至有意识地去讨好村里的人贩子王老拐,以期将来得到优惠。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那时母亲刚病逝,家里一贫如洗,我考不上学也只能走这一步。我那个考了六年的同学就是如此,考到第三年他就灰了心,准备偃旗罢兵,可家中弟兄多,媒人介绍他到外村倒插门,在人们的意识中,这是一种比买女人成家更让人轻视的婚姻,所谓“小子无能,改名换姓”,可就这样女方还嫌他家穷相貌差,所以才促使他横下心走过了独木桥。其实同学中和我一样困难的还很多,张庆雨就是一个。不过张庆雨自然条件好,人聪明,长得有模样。
所以我考上学后,父亲就长长松了一口气,总是自豪地向别人炫耀:好树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没管过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柳树经成了父亲多年的谈资。
而我在城市的种种经历证明父亲的那套柳树经是片面的,它只适用于柳树和我考学之前。因为城市不是乡村,一个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周末,我童心骤起,要为儿子拧一个柳笛,可走了许多大街小巷,竟没有找到一棵柳树,在经过公园门口时才发现几株柳树势单力薄地挤压在众多花木之间,而气势汹汹的法国梧桐臃肿地充塞着街道,那窈窕细柳的丝丝拂面已成了公园里的一个标本了。
一代又一代乡下人从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树的纯朴延续着城市的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树用自己的韧性丰富着城市的风景和人们的情感,折柳惜别、烟柳传情、柳丝寄意——柳树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
如今,城市的酥胸粉脸上已没了柳树的印痕。是因为城市的进步和无情,还是柳树种类的退化?
不管城市是否欢迎,我们都义务反顾地走进了城市。我们承袭着柳树纯朴的本性,带着柳树的失落在城市钢筋水泥间寻觅理想的高贵。与当年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第一代进城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疾风暴雨专政手段的强硬;与后来大批招工进城的第二代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侥幸后沾沾自喜的知足和驯服;我们凭的是自己的智力,没有颐指气使的资本,也不愿低眉顺眼任人摆布。
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学在四散蛰伏乡下后不久,许多又寻梦到了城市。那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腔豪情还在胸中澎湃,见了面总是相互鼓励,认为自己同样是城市八九点钟的太阳。然而,秃发耗尽了脑汁,皱纹沧桑了心理,短短十多年后,当年的相互鼓励竟变成了杯盏交错的相互安慰,渐渐学会了用酒精来抚平心中的沟壑了。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去年冬我和同学S让酒精浸泡得难以自恃的那次。这本该是庆贺他升迁的喜酒,他们处室提拔两个副处级,三个人中S各方面条件第一,考察和公示都没问题,然而宣布时他却名落孙山,提上去的一个是局长的儿子,一个是大企业厂长的儿子,就S一人没有后台。他明白自己的劣势在哪里,可又于心不甘。流出来的泪水比灌进肚的酒还多。他从洗手间呕吐回来时,一个我很面熟的人搀扶着S走了进来,此人也是一身酒气。坐下后才知道是师专同届物理系的,在某要害部门给领导当秘书,我这才想起,开会时曾见过面,怪不得面熟。我问这位秘书同学,这次大面积人事安排他升迁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还是老样子,和他一拨的秘书都已提拔,他大拇指搓着四指做点钱状,说:没这个不行。也许是同学缘故,或许他也喝高了,大声说:妈的,通过我给领导送钱跑官的都上去七八个了。后来我才知道,领导之所以让他当秘书,是因为他出身农家没有背景,老实忠厚能干,仅此而已。
那顿饭是那秘书同学埋单,一个经他牵线升迁的官人在隔壁雅间设宴答谢,不用他掏腰包。饭毕,他豪爽地说:走,上四楼,新来的俄罗斯小姐,全套服务。我明白这“全套”的意思,便借故避开,身后饭店门口的霓虹灯闪着凄迷暧昧的光。
淮南为桔,淮北为枳,水土之异让我们先天不足,囊中羞涩让我们的“金”绣前程黯然失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得不这样来安慰自己,纡解尴尬。窘迫的境况已使三个柳绵一样的同学随风而去,刚刚人到中年,生命之花便黯然凋谢,可附在枝上摇摆的我们的芳草依旧远在天涯,遥遥无期。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我们既未得道,又未成器,曾经舍我其谁的理想鲜馅像汤圆一样在空旷的世俗中滚荡,庸碌的尘埃一层层岁岁缠绕,渐渐变成了一个个适合社会口味的毫无个性的面球,成为他人的陪衬和祭品。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千年前风流词人的无奈难道真的要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吗?
在乡下人眼里,只要你是非农业户口,统统把你归纳到城市人的行列,不管你在哪里工作。他们认为,城市人总是欢游在幸福的海洋里。汝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被一张“城市人”的金纸包裹着,外表灿烂光亮,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除非这张金纸出现了破洞。张庆雨就是首先出现破洞的一个。所以他也常是我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之一。
张庆雨的破洞出现在婚姻上。
我的儿子开始上小学时,张庆雨的童子身还坚如磐石。不是他心理和生理上有问题,也不是工作单位差,是自己的承诺阻碍了他的婚姻。他下有两个挨肩的弟弟,父母都是老实巴交农民,为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发誓给两个弟弟成家后才考虑自己婚姻大事。与他对桌办公的女朋友也曾对他情意绵绵,可对他的家庭条件烦恼不堪,加上长年累月的爱情长跑和庆雨的升迁受阻,终于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局长的儿子。于是性格内向的张庆雨在家庭和婚姻重压下,精神出现了问题。当我再见到他时,他憔悴不堪地在精神病院呆若木鸡,身边是年迈的父母。他一个劲儿向我打听市场上钢筋水泥的价格,说要回家盖一座四层大楼,父母住一层,他和俩弟弟各住一层。我知道他是妄语,他现在也没这个能力,可那出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让我几乎落泪。
是啊,我们这些当初拼命跳出农门的乡下人,哪一个没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哪一个身后没有光宗耀祖殷殷期盼的目光?正是这刻骨铭心的责任感使我们游移在城乡之间,承受着双倍的压力。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的《杨柳枝词》常常与女同学王静花一块在我脑海浮动。
没有春江水暖的诗意,没有板桥遗踪的回味,只有青春朦胧中的美人和校园垂柳记忆的撩拨。然而,当二十年后在县城街头见到这位曾经的梦中情人时,美人的概念竟像柳树皮一样粗糙。厚厚的脂粉似是而非地应付着脸蛋对青春的乞求,皱纹流窜着岁月的狠毒,嘴唇涂着人为的血红,脑袋上跳跃的马尾辫已让时光磨消了锐气——一切征兆和现实都让我领略了岁月的无情。那曾诱着我们青春某个部位不由自主跃跃欲试的高耸弹性的胸脯也已平淡。最平淡的还是她的生活,当初令人羡艳的售货员与下岗连在了一起。时下,下岗一词是与非农业户口连在一起的,农民在土地上的岗位是相对恒定的。
世事无常,当初我们追求非农业户口的含金量现已大打折扣。正如柳树从城市视野中淡出一样,风水轮转,很难判定炕的哪头有持久的热力。
在见到王静花之前,有同学传言她下岗后靠一身过时的皮肉生活,我半信半疑,因为她当初高傲的神情一直贮存在我记忆中,那是一种对我们这些乡下同学不屑一顾的优越感。然而,此时传言得到了证实,那吃冰棍的自豪变成了抽烟的老练,一个个烟圈飘着两眼的迷茫。就在她拉开坤包找东西记录我的通讯地址时,我看到了几个粉红色的安全套在坦然地向外张望,我断定这就是她干活的工具。她凄然一笑,略带羞涩地把安全套压在卫生纸的下边。那个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号码,让我想象不出灯红酒绿中那曾经高傲的脸是一种什么神情。此时,我对残花败柳的尴尬也多了一份理解,甚至是同情,因为世道使然。道德本来就是束缚人们的一条精神腰带,宽松尺度只有自己把握,社会标准都是仅供参考。
改变不了自己命运,就要改变自己性格,我们像柳树一样努力适应着上苍的安排。受人颐指气使的琐碎一天天掩埋着曾经的壮志豪情。而对情义的珍重却一天天与日俱增,惺惺相惜也好,同病相怜也罢,我们毕竟在同样的境遇中挣扎。所以,当我从门岗登记簿上看到“张庆雨”三个字时,心里就陡然一阵发热,那个在大门外徘徊已久的肮脏的乡下人硬是让责任心极强的门岗给赶走了,只有我熟悉的那三个字可怜巴巴地趴在纸上,已失去了往昔神采飞扬的硬气。不知是他发病时潜意识里对我这个要好同学的惦念,还是清醒后专门从乡下老家来找我倾诉苦闷呢。
我在汽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寻觅那熟悉的身影,眼前总是晃动他那抽搐变异的表情。可一辆辆汽车碾碎了我急切的热情,此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奈和无能。更让我心痛的是,这竟是我和张庆雨最后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因为十多天后,老家传来他自缢的噩耗。
赶回老家,我久久打量着村外那棵歪斜的柳树,我想象不出两股细绳绞在脖颈时的痛苦。可我相信,庆雨走向柳树时一定是清醒的,他一定想到了自己活着的使命和无力改变命运的悲哀。他的自尊使他不愿成为亲人们的拖累。于是,在硕果累累的秋天,柳树收获了张庆雨。我失去了一个曾经推心置腹的好兄弟。
无心插柳柳成荫。乡间许多坟头前的柳树往往就是人们无心而天之有意的手笔。孝子的灵幡由柳枝糊制而成,待逝者下葬时灵幡埋在墓坑的一头,于是柳枝发芽生根,渐成树木。田地上一丛丛野柳往往是一个个生命的注解。而张庆雨的坟头光秃秃的一无所有,他没有后代,没有人为他打幡送魂,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天意的注解。其实那只是一种外在的符号,因为张庆雨本身就是柳树一种写意的注解。
后来我想,柳树退守乡野,并不能说明城市的冷漠无情,真正的悲哀在于柳树生不逢时的大众化和生存土壤的人为荒漠吧,正如我们这一拨挣扎在城市的乡下人,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福祸相倚,好在我们还有这赖以生存的乡野作后盾。可回到老家,当年父亲栽植在地头的那排柳树却在秋风中陌生地摇着头,显然,它把我当作城市人了。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