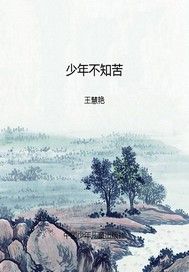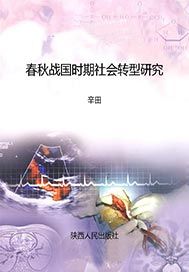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二十三 章远客让人人惊奇
1
槐树坡的多数乡亲,尽管在商品潮流中各干各的责任田已经二十来年年头,还丢不开传统的美德:“相互同情,相互关爱。不管李秀秀、猫头鹰等如何敲锣打鼓,朝韩美凤泼洒污水,韩美凤顺顺当当地将张欢欢送往火葬场火化完毕,乡亲们就不再为韩美凤揪心。时下,乡亲们最惦挂的是张金锁给予的史梅梅之苦。用一个不解拜金主义之凶残的老人的话说,一个虎虎势势的张金锁,一个会拨拉算盘的张金锁,一个家里日子不赖的张金锁,就是因为拿不到村里的两个梨木疙瘩(印章),就丢魂失魄,被送进医院,花干家里积蓄,让老婆苦得死不得死,活不得活,真是太那个了!”
史梅梅之苦,也确实值得人念叨,值得人同情。
太阳已经升出东山老高,史梅梅才让小儿子拴猫吃下早饭,让张金锁喝下中药。不能准时到达小学校上课的拴猫,跑往东厢房屋里向坐在沙发上的张金锁告别,叫声爸爸,说声我上学去了。张金锁睁着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睛,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笑出声来,吓得拴猫缩头缩脑的跑走,史梅梅将药锅刷洗干净,走到东厢房屋将张金锁扶到床铺上躺下,为张金锁盖好被子,慢步走向正房东屋里,在床边坐下来喘息。
张金锁从医院里回来那天是什么状态,现在还是什么状态:手可以伸出端碗,嘴可以细嚼烂咽的吃饭,腿脚可以走向厕所大便小便,却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狂笑不止,惊得拴猫缩头缩脑,吓得史梅梅提心吊胆。史梅梅从医院把张金锁接回家来,不管手里如何缺钱,仍天天为张金锁熬服中药,却看不到张金锁星星点点的好转。
史梅梅不仅消瘦得皮包骨头,腰背也已弯曲,脸色难看得不敢站到镜子前边去了。史梅梅是个刚强的女人,她的哥哥因贪污受贿包养情妇露馅跳河自杀,使她沉重的如头上压座大山,她没有消瘦多少,腰背题解没弯曲。张金锁给予她之苦,给予她之难,她再经受不了。她骂自己:你史梅梅百么不是,张金锁是他自寻自找,又不是你史梅梅人品不正把她害了,他到了阎王殿里去,你也要跟他往阎王殿里呀?她对自己火归火,骂归骂,总免不了为张金锁吃不足饭、睡不安稳,背转人一滴一滴的掉泪。
“拴虎妈在不在?”
喊声很高,被张金锁惊得提心吊胆的史梅梅不由得吸一口气才站起来应声:“我在,我在上房屋里。”是张石头的女人李秀秀。李秀秀手里托着米面做的两个黄亮亮的厚煎饼。李秀秀很快走来上房屋。“拴虎妈,原先拴虎爹希罕厚煎饼,我给你送来两个厚煎饼,请你让拴虎爹尝一尝。他要不希罕,你就和拴猫吃了。”李秀秀未敢提张石头,她清楚张金锁之倒下与张石头的关系,知道史梅梅对张石头恨之入骨。是张石头派李秀秀来给张金锁送厚煎饼,看一看张金锁是不是有了好转。史梅梅对张石头看不上眼,对张石头藏怒窝恨,与张石头掰得不能面对,碰见就免不了发怒撒恨。史梅梅对李秀秀的人品也无好感,远远地看着李秀秀的后影啐过唾液,骂过李秀秀破烂货儿。而她心里有着“都是自己家的,老人们埋在一个坟里,”没有同李秀秀翻脸,该得李秀秀说天长了说天长,该说天短了说天短,该说天热了说天热,该说天寒了说天寒。他与李秀秀说拴虎爹已吃过早饭,说着接过李秀秀送来的厚煎饼放下来,递给李秀秀一个凳子。
李秀秀坐下来,习惯地把左腿搬到右腿上问史梅梅:“拴虎爹有没有好转?”
史梅梅叹口气,丧着脸说:“一天一服中药,白吃。”
李秀秀叹口气问:“拴虎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史梅梅又叹口气说:“医院里大夫说是脑溢血后遗症。我弄不明白他是清楚还是糊涂,反正是丢了魂儿似的,腿脚不拐,能吃能拉;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啼哭;一句话不说,能把人烦死。不等他合眼,我累得就叫拴虎爹给我背了引魂幡了。”“拴虎妈呀,你可别这么说。”李秀秀神情和语气对史梅梅同情到底,可怜到家:双眉挤在一起,眉间鼓起杏核大的一个疙瘩,眼睛里几乎要流出热泪。她再叹口气,与史梅梅长篇大论,“你绝对不能这么悲观,你看看你瘦成一根柴了。你要再悲观,就是阎王不叫你去你也得去了。你别忘了拴猫还离不开你。我听说人的命长命短是有一定寿数的,你拴虎妈命虽苦但寿数不短。拴虎爹的病,带着邪气,这邪气出自白冰冰。拴虎爹是火命人,白冰冰的冰是水,水火不相容哩。可是邪气儿再邪,也压不倒正气儿。白冰冰的邪气是兔子的尾巴,邪不了多长时间。他的邪气只要散,拴虎爹的病就会好转。今儿个我把这话说在这儿,要由不了我李秀秀的嘴,你往我李秀秀嘴上摸屎。”李秀秀说得如朝铁板上钉钉。
史梅梅两耳伸直,听得很认真,而她不会把李秀秀的长篇大论听进心里,她认为李秀秀是瞎子算卦——胡诌八扯。她不顶不撞李秀秀,心口不一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就盼着拴虎爹尽快好转”。
李秀秀再劝慰了史梅梅几句,同史梅梅往东厢房屋里看望张金锁。
“拴虎爹,我看你来了。”
张金锁躺在床铺上睁着两只白多黑少的呆眼,紧紧地抿着发紫的嘴唇。一会儿。忽然打个挺响的喷嚏,上身晃动晃动,一会儿,又忽然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笑出声来。
李秀秀好似神仙要下凡似的微闭住眼睛,双手合在胸前三五分钟,再睁开眼睛,双手放开,一字一句的安慰张金锁道:“拴虎爹,你千万心宽,你走一步两脚印儿,没有亏待过人,没有黑唬过人,为你修下了庙,福气不浅,谁也夺不走你的。八路神仙都保佑你,你的病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就会好的。安!我来给你送来两个米面厚煎饼,香喷喷的,甜丝丝的,你中午记得吃了。我走啦,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张金锁仿佛耳里由了李秀秀的安慰,又放声狂笑,而且斜了李秀秀一眼。史梅梅认为张金锁的魂儿复归,满心地等待着张金锁开口说话,一等又等,锯倒大树捉老鸦——白费心思。
2
槐树坡乡亲们,特别是加入共同富裕合作社的乡亲们,心里不放心史梅梅,又免不了牵挂白冰冰,白冰冰外出已经六天。槐树坡东南角上,忽然有人喊:“白冰冰回来了!”是瞎子老人朝着正在猪圈边上翻弄圈肥的刘福福喊。刘福福将一锨圈肥扔开,转身面向瞎子老人:“瞎子哥,你看见白冰冰回来了?”瞎子老人笑笑说:“你这个老支书,我要看见白冰冰回来了,你还叫我瞎子哥吗?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他回来了。大家选举他挂了帅,就都把他当成财神了,我这个没眼儿的老家伙,更把他当成财神哩!”刘福福说:“你瞎子哥的梦也许是真的,他今儿个就回来了。”
瞎子老人梦得不错,刘福福也不是歪嘴和尚念经,白冰冰已经回到村里来了。
距戏楼不过百米远,挂着党支部、村委会两块牌匾,又挂着槐树坡共同富裕合作社牌匾的一个三分大的院子哩,坐南朝北破烂不堪的三间小平房,中间一间的二十平米大的屋子是村干部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仅有一张方桌,五六个长长短短高高矮矮的木凳。小院和三间小平房是村里唯一的共有财产。办公室里的桌凳火炉和其他用具等,全是干部们自带来的。小院和办公室里清扫得十分洁净,不见一片树叶,没有一根碎草。这些都是瞎子老人辛苦的结果。谁也不能将瞎子老人阻拦,谁也不能代瞎子老人辛苦。瞎子老人说这样的辛苦是他的福。
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是韩美凤。韩美凤安静的坐在方桌一侧的长凳上翻看着往天的报纸。她的眉眼又透出原有的媚气,她的面颊又显出固有的红润,好看得让女人们羡慕,让男人们心动。欢欢火化已经五天,她已放开欢欢给予她的痛苦,更不把张石头鼓动人寻衅闹事再搁在心里。欢欢妈也没有给她增添麻烦,真心实意的把她当成闺女,与她相依为命。
小院里并无声息,而韩美凤好像是听到院里有人呐喊她,她急忙推开报纸,嗖地站起来,紧走两步,爽快的拉开两扇院门,通通通地跑往院里,在院门口站立下来朝外暸望。转眼之间,仿佛暖心的春风朝暸吹来,她禁不住的心花怒放,眉目越发明媚,面颊愈加红润。白冰冰走过戏台一侧,大步流星地朝着办公室院门走来。白冰冰外出六天,心累身也乏。县委杨秋江书记答应为他设法办理采矿证,为他向蒋希文讨要百万欠款,又答应他帮助他解决抗日老民兵马大波的困难。而后,他的心回到村里南山上,琢磨又琢磨。挖掘铁矿石,修通山中道路,租赁铲土机、挖掘机、压道机、拖拉机,没有五十万,休想听一听“四机”的响声。村民们筹划不出三万四万,只有想法跑银行或跑信用社贷款。
站立在小院门口的韩美凤,只是瞅着白冰冰朝着小院走来,就嫣然一笑,急忙返回办公室,为白冰冰倒下一杯白开水,静等白冰冰往办公室里来坐下,把她淤积在心里的苦辣酸甜一锅端出。
白冰冰喊一声美凤,很快推开办公室的两扇屋门。
韩美凤不会想到,进屋的不只是白冰冰自己。杨大年、刘福福同两委班子的干部齐刷刷地跟在白冰冰身后。瞎子老人同十多位男女村民也随后而至,使二十平米大的办公室里再无插脚之地。人人喜气洋洋。最欢畅是杨大年。一个比杨大年年轻的后生为杨大年让座,杨大年双手把瞎子老人按在凳子上。杨大年今天才开始喘一口气。前几天,他估计白冰冰外出办理采矿证不会落实。他同两委班子的干部进一步翻山越岭,探测了铁矿准确的储量,距地面的厚度。勘测了机器进出的路线,算计出修宽道路用工数目,并做通了修路被占地户们的工作。
“拿回没拿回采矿证来?”村干部们与男女村民不约而同的急问白冰冰。白冰冰只顾接过韩美凤递他的水杯喝水没有立即回答。而且他的笑脸如常:既无一分乏力,又不显丝毫得意。难让人做出他外出白费了盘缠的结论。
“完啦,完啦!”叼旱烟袋的支部委员抢先大发牢骚,“冰冰哥必定是水中捞月——白扑腾了。我早猜到冰冰哥会水中捞月。山河好改,人的秉性难移,冰冰哥绝不会为拿到采矿证请客送礼。拿不到采矿证,咱槐树坡还得是槐树坡,谁也甭想多吃一口好的,多穿一件新的,生来是什么命就永远是什么命了。”
白冰冰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喝足水,耐心地等叼旱烟袋的支部委员牢骚完结,才慢腾腾地放下水杯,谦和地站立起来面向大家:“嘿嘿嘿,我没有把采矿证拿回来,我也不是水中捞月——白扑腾了。”他再喝一口水,将他跑县法院控告蒋希文碰壁,赴省国土资源厅办理采矿证生气窝火,后幸运地见到县委杨秋江书记,受到杨秋江书记非凡的热情关怀,绘影绘声、仔仔细细地汇报给大家,再畅快的笑笑说:“看来我这个二百五还有几分运气。”
人人喜气洋洋,人人兴高采烈。
“运气不错,运气不错!我早就想到冰冰哥外出的运气不会错了!”杨大年指手画脚,抢先感慨一番。“冰冰哥的运气,也是我们大家的运气。今后,我们更得实心饱力的干了!”
“哈哈哈,”瞎子老人喜兴得好像看到了亮光,由不得摇头晃脑,“看来,不管腐败的风气儿多么严重,总归还是共产党领导。”
“不错,总归还是共产党领导!”有人举着拳头呼应。
也还有人担心白冰冰的汇报不实。刘福福吞吞吐吐地问白冰冰:“冰冰,我……我想问你一句,我问得要不实际,你……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福福叔,你只管问你的。”白冰冰痛快的说。
“你……你同大家讲的全是实话?是不是害怕大家情绪低落,故……故意和大家吹……吹牛?”
“福福叔,”白冰冰憨厚的笑笑,推开身前的杨大年,朝刘福福走过一步,“我理解你的心思,我也很怕我向大家的汇报,是耕地用鞭子——吹(催)牛,给我往脸上抹黑。我二百五不二百五,脸皮并不是很厚。我看得不敢说绝对正确,可我看县委杨秋江书记对待我的态度,让你福福叔做不出我吹牛的结论。”白冰冰喘一口气再说:“福福叔,咱叔侄俩共事不是一年,你记得我冰冰什么时候说过一句大话,什么事上说过一句假话?大跃进、放卫星、当干部就得吹牛的时节,你当支书,我当大队长,我吹过一句牛没有?……”
“没有,没有,上岁数的都记得,你顶天立地,宁肯当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也不吹牛。你别往下说啦,你福福叔一句是不是吹牛,是有嘴无心,也实在是害怕现在当官儿的作风不实,胡弄咱平民百姓……”刘福福突然封口,有人在院里喊“冰冰大伯,有远客找你。”
3
“远客,谁呢?”办公室里人人张口,人人都感到惊奇。槐树坡人很少见到远客。人人争先恐后,一起跟白冰冰迎往院里。不认识远客的干部和村民吃惊,认识远客的白冰冰、杨大年、韩美凤同样吃惊。人人吃惊得直瞪瞪地瞧着从院门里走进院里的远客。白冰冰的一双眼睛瞪得最大。谁都看得出远客不是一位普通的客人。远客穿一身名牌深蓝色西服,外穿一件少见的时髦的呢子大衣,脚穿一双黑色皮鞋,大背头油光发亮。如此的气魄,不认识远客的村民们止不住的窃窃私语。而远客自己提一沉甸甸的提包,脚步不太自然,脸面干巴微黄,眉目欠爽欠展。
远客是凤凰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板——白冰冰心目中的骗子蒋希文。
蒋希文紧迈两步,干笑着用力与白冰冰握手,并谦恭地说:“进村就看到让我敬仰的白支书深感荣幸!”
白冰冰做梦也想不到在槐树坡见到蒋希文。他自然想起蒋希文欠他的百万,想起蒋希文高明的骗术;想起他在凤凰岭东边山岭下的水库边上,看到因为被蒋希文骗得没有活路跳水自尽的汉子;听到救汉子出水的山村教师对蒋希文的声讨。他止不住怒火中烧。他又想不到蒋希文对他恭而敬之,还有几分不得已的卑下。而他很快镇定下来,将火压下。他想:不管蒋希文来见他是做甚,他都没有必要简单粗暴。他坦然地与蒋希文握手,并客气地说:“我很高兴在我们村里见到你。”
“白支书,我想单独同您谈一谈,可以吗?”蒋希文继续与白冰冰握着手说。
“可以。”白冰冰答应的很痛快。
白冰冰说着带蒋希文走进办公室,干部和村民们都走开了。白冰冰等蒋希文将提包放在方桌上,在方桌左侧木凳上坐下来,为蒋希文斟杯白开水,他才在方桌右侧木凳上与蒋希文面对面地坐下来,瞪着一双眼睛等着蒋希文开口。他在院门里朝外看的清楚:蒋希文未带秘书,未带保镖,蒋希文是自己驾车而来。他嚼不透咬不烂蒋希文来见他之目的,而他能够想到,蒋希文孤家寡人来见他,必定与县委杨秋江书记有关。
白冰冰想的不错,蒋希文来见他,确确实实与杨秋江书记有关。
杨秋江书记接见白冰冰第二天早晨,杨秋江书记亲自给蒋希文打电话,通知蒋希文上午八点半,他在政府招待所一号楼三〇一房间等候蒋希文。蒋希文准时到达杨秋江书记指定的房间。杨秋江书记只是与蒋希文寒暄两句,就眼里闪烁出不快,抛出对蒋希文的不满:“蒋董事长,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向法院告你?”蒋希文装傻充愣:“哪一个告我?” 杨秋江书记对蒋希文更加不满,他精明的两只眼睛面对着蒋希文,闪射出难以遏制的怒火:搭在沙发扶手上的白白净净的两只手不停的颤动。他道一句“我简直不认识你蒋董事长是哪一个了!”再说,“蒋董事长,我对你十足的相信,相信你会把凤凰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干好,为金光县革命老区增添光彩,为你也为我争得荣誉。因此,我千方百计的对你支持!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对蒋希文不可重看,不必过分支持,要对他多加小心为好,我对人不加理睬。哪儿知道,人家把你看得千真万确!我杨秋江太无知!你同人签订施工合同,结果成了一张废纸。人催你履行合同,你花言巧语,拒不执行。你随意克扣朝凤凰岭打工工人们的工资,人去向你讨要欠款,你竟然变成了你哥哥蒋希武,说你蒋希文自杀身亡,随便的捉弄人家,我杨秋江怎么也想不到你的骗术如此不凡!你克扣了人的工资,建宾馆,盖别墅,养情妇,找三陪,肆意挥霍。” 杨秋江书记喘息,蒋希文接话:“是一个姓白叫冰冰的告了我?”
“不错,是槐树坡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白冰冰找我来反映了你目无党纪国法,严重损害党的声誉。”杨秋江书记的口气越来越严厉。
蒋希文不在乎,跷起二郎腿,背依沙发,掏出纸烟点着,慢慢悠悠的抽纸烟。
杨秋江书记怒气冲冲地斜蒋希文两眼,轻微地冷笑一声,忽然眼皮微合,抿着薄薄的嘴唇沉默片刻,让他的怒火沉到心底,面皮松松展展,语气平平和和:“希文,我告诉你,你切不要小看白冰冰这个庄稼汉子!” 杨秋江书记饮一口茶,将白冰冰与糊糊司令的关系详尽的讲给蒋希文,再严肃认真的说,“白冰冰已经向我申明,找见我再告不倒你,他就进京求见糊糊司令。糊糊司令绝不会不接见他!糊糊司令绝不会不为他说话!糊糊司令虽然早已离职,但他说句话可还顶句话哩!每到春节,中央领导同志都往他家里去看望他。” 杨秋江书记喘一口气,“我告诉你说,我已经得到消息,接替陈书记的正是从北京派下来的糊糊司令的老二。糊糊司令只要为白冰冰张一张口,你蒋希文就难不身败名裂,我杨秋江也难脱干系!”
蒋希文嘴唇抿成一条线,目珠凝滞,不言不语。
杨秋江书记压在心底的怒火猛然间爆发,他举手拍响桌面,大发雷霆:“姓蒋的,请你听着,我只警告你一句,你必须尽快去向白冰冰道歉,归还白冰冰的欠款,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姓蒋的负责!”
只是转眼之间,能装善变的蒋希文即变为另一副面孔:满脸披笑,急忙诚恳而又谦敬地发誓:“杨书记,请你息怒,我尽快去向白支书诚恳地道歉,如数归还对白支书的欠款。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到做到,你只管放心。”
只有鬼才知道蒋希文与杨秋江书记的发誓是虚是实。他驾车即将驶进槐树坡村口的时候,心里还朝白冰冰骂了一声他妈的!蒋希文在槐树坡村委会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白冰冰,如在杨秋江书记办公室里向杨秋江书记书记发誓那样,满脸披笑,诚恳而又谦敬:
“白支书,我今儿个找您来是向您道歉的,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跟您去凤凰岭打工的哥儿们兄弟,没有按时交还您百万工钱。更严重的,更不可宽恕的是,我还对您不择手段的欺骗,我败坏了革命老区金光县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党的威信。归根结底,或者说是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我受到拜金主义的严重影响,对三个代表学习的不透,领会的不深。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心胸宽广、忠厚老实的您,一定会不记小人之过,原谅我的失误。我向您发誓:今后,我一定学透吃透‘三个代表’的实质,完全彻底的改正我的错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绝对心口如一,说到做到!”
未道过一句假,未道一句空,对骗深恶痛绝的白冰冰,对蒋希文流畅的谈吐全神贯注,一字一句都不流失在耳外。
“白支书,请您允许我再同您解释两句。”蒋希文的语气愈加诚恳,神情越发显得真诚,“您听到的我克扣大家的工资,建宾馆,盖别墅,养情妇,找三陪什么的,全是对我的诬陷!这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地痞,去找我敲诈勒索,我没有使他得逞,他就四处对我栽赃陷害!你想想,我的失误再严重,我也还是个为革命教育基地做出了贡献的共产党员,我岂能如贪官污吏那样的无耻。”
蒋希文利索地刹住自己流利的谈吐,喘一口气,掏出手绢擦净两滴委屈的泪水,从提包里取出大捆钱票,推向白冰冰面前:“白支书,这是我给您送来的百万欠款,请您收下。”
白冰冰注意到蒋希文带来的提包,他却没有想到提包里装的欠他的百万欠款。他想蒋希文之“流畅”之“诚恳”,不过是耍一耍嘴皮子罢了。习惯见甜则乐的白冰冰,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实实在在的百万人民币——他与杨大年、韩美凤等困难户们的千辛万苦,难免不乐,而他的眉目中未透星星点点的笑意。他只是说:“谢谢你给我送来了欠款。”再搭一句:“中午,我请你喝盅红枣老酒。”一直对白冰冰目不转睛、诡计多端的蒋希文已经看出,白冰冰对他不会宽恕,白冰冰留他喝盅红枣老酒,只不过是和他客套。而他却瞎子牵驴——不松手:
槐树坡的多数乡亲,尽管在商品潮流中各干各的责任田已经二十来年年头,还丢不开传统的美德:“相互同情,相互关爱。不管李秀秀、猫头鹰等如何敲锣打鼓,朝韩美凤泼洒污水,韩美凤顺顺当当地将张欢欢送往火葬场火化完毕,乡亲们就不再为韩美凤揪心。时下,乡亲们最惦挂的是张金锁给予的史梅梅之苦。用一个不解拜金主义之凶残的老人的话说,一个虎虎势势的张金锁,一个会拨拉算盘的张金锁,一个家里日子不赖的张金锁,就是因为拿不到村里的两个梨木疙瘩(印章),就丢魂失魄,被送进医院,花干家里积蓄,让老婆苦得死不得死,活不得活,真是太那个了!”
史梅梅之苦,也确实值得人念叨,值得人同情。
太阳已经升出东山老高,史梅梅才让小儿子拴猫吃下早饭,让张金锁喝下中药。不能准时到达小学校上课的拴猫,跑往东厢房屋里向坐在沙发上的张金锁告别,叫声爸爸,说声我上学去了。张金锁睁着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睛,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笑出声来,吓得拴猫缩头缩脑的跑走,史梅梅将药锅刷洗干净,走到东厢房屋将张金锁扶到床铺上躺下,为张金锁盖好被子,慢步走向正房东屋里,在床边坐下来喘息。
张金锁从医院里回来那天是什么状态,现在还是什么状态:手可以伸出端碗,嘴可以细嚼烂咽的吃饭,腿脚可以走向厕所大便小便,却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狂笑不止,惊得拴猫缩头缩脑,吓得史梅梅提心吊胆。史梅梅从医院把张金锁接回家来,不管手里如何缺钱,仍天天为张金锁熬服中药,却看不到张金锁星星点点的好转。
史梅梅不仅消瘦得皮包骨头,腰背也已弯曲,脸色难看得不敢站到镜子前边去了。史梅梅是个刚强的女人,她的哥哥因贪污受贿包养情妇露馅跳河自杀,使她沉重的如头上压座大山,她没有消瘦多少,腰背题解没弯曲。张金锁给予她之苦,给予她之难,她再经受不了。她骂自己:你史梅梅百么不是,张金锁是他自寻自找,又不是你史梅梅人品不正把她害了,他到了阎王殿里去,你也要跟他往阎王殿里呀?她对自己火归火,骂归骂,总免不了为张金锁吃不足饭、睡不安稳,背转人一滴一滴的掉泪。
“拴虎妈在不在?”
喊声很高,被张金锁惊得提心吊胆的史梅梅不由得吸一口气才站起来应声:“我在,我在上房屋里。”是张石头的女人李秀秀。李秀秀手里托着米面做的两个黄亮亮的厚煎饼。李秀秀很快走来上房屋。“拴虎妈,原先拴虎爹希罕厚煎饼,我给你送来两个厚煎饼,请你让拴虎爹尝一尝。他要不希罕,你就和拴猫吃了。”李秀秀未敢提张石头,她清楚张金锁之倒下与张石头的关系,知道史梅梅对张石头恨之入骨。是张石头派李秀秀来给张金锁送厚煎饼,看一看张金锁是不是有了好转。史梅梅对张石头看不上眼,对张石头藏怒窝恨,与张石头掰得不能面对,碰见就免不了发怒撒恨。史梅梅对李秀秀的人品也无好感,远远地看着李秀秀的后影啐过唾液,骂过李秀秀破烂货儿。而她心里有着“都是自己家的,老人们埋在一个坟里,”没有同李秀秀翻脸,该得李秀秀说天长了说天长,该说天短了说天短,该说天热了说天热,该说天寒了说天寒。他与李秀秀说拴虎爹已吃过早饭,说着接过李秀秀送来的厚煎饼放下来,递给李秀秀一个凳子。
李秀秀坐下来,习惯地把左腿搬到右腿上问史梅梅:“拴虎爹有没有好转?”
史梅梅叹口气,丧着脸说:“一天一服中药,白吃。”
李秀秀叹口气问:“拴虎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史梅梅又叹口气说:“医院里大夫说是脑溢血后遗症。我弄不明白他是清楚还是糊涂,反正是丢了魂儿似的,腿脚不拐,能吃能拉;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啼哭;一句话不说,能把人烦死。不等他合眼,我累得就叫拴虎爹给我背了引魂幡了。”“拴虎妈呀,你可别这么说。”李秀秀神情和语气对史梅梅同情到底,可怜到家:双眉挤在一起,眉间鼓起杏核大的一个疙瘩,眼睛里几乎要流出热泪。她再叹口气,与史梅梅长篇大论,“你绝对不能这么悲观,你看看你瘦成一根柴了。你要再悲观,就是阎王不叫你去你也得去了。你别忘了拴猫还离不开你。我听说人的命长命短是有一定寿数的,你拴虎妈命虽苦但寿数不短。拴虎爹的病,带着邪气,这邪气出自白冰冰。拴虎爹是火命人,白冰冰的冰是水,水火不相容哩。可是邪气儿再邪,也压不倒正气儿。白冰冰的邪气是兔子的尾巴,邪不了多长时间。他的邪气只要散,拴虎爹的病就会好转。今儿个我把这话说在这儿,要由不了我李秀秀的嘴,你往我李秀秀嘴上摸屎。”李秀秀说得如朝铁板上钉钉。
史梅梅两耳伸直,听得很认真,而她不会把李秀秀的长篇大论听进心里,她认为李秀秀是瞎子算卦——胡诌八扯。她不顶不撞李秀秀,心口不一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就盼着拴虎爹尽快好转”。
李秀秀再劝慰了史梅梅几句,同史梅梅往东厢房屋里看望张金锁。
“拴虎爹,我看你来了。”
张金锁躺在床铺上睁着两只白多黑少的呆眼,紧紧地抿着发紫的嘴唇。一会儿。忽然打个挺响的喷嚏,上身晃动晃动,一会儿,又忽然如猫头鹰叫唤似的笑出声来。
李秀秀好似神仙要下凡似的微闭住眼睛,双手合在胸前三五分钟,再睁开眼睛,双手放开,一字一句的安慰张金锁道:“拴虎爹,你千万心宽,你走一步两脚印儿,没有亏待过人,没有黑唬过人,为你修下了庙,福气不浅,谁也夺不走你的。八路神仙都保佑你,你的病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就会好的。安!我来给你送来两个米面厚煎饼,香喷喷的,甜丝丝的,你中午记得吃了。我走啦,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张金锁仿佛耳里由了李秀秀的安慰,又放声狂笑,而且斜了李秀秀一眼。史梅梅认为张金锁的魂儿复归,满心地等待着张金锁开口说话,一等又等,锯倒大树捉老鸦——白费心思。
2
槐树坡乡亲们,特别是加入共同富裕合作社的乡亲们,心里不放心史梅梅,又免不了牵挂白冰冰,白冰冰外出已经六天。槐树坡东南角上,忽然有人喊:“白冰冰回来了!”是瞎子老人朝着正在猪圈边上翻弄圈肥的刘福福喊。刘福福将一锨圈肥扔开,转身面向瞎子老人:“瞎子哥,你看见白冰冰回来了?”瞎子老人笑笑说:“你这个老支书,我要看见白冰冰回来了,你还叫我瞎子哥吗?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他回来了。大家选举他挂了帅,就都把他当成财神了,我这个没眼儿的老家伙,更把他当成财神哩!”刘福福说:“你瞎子哥的梦也许是真的,他今儿个就回来了。”
瞎子老人梦得不错,刘福福也不是歪嘴和尚念经,白冰冰已经回到村里来了。
距戏楼不过百米远,挂着党支部、村委会两块牌匾,又挂着槐树坡共同富裕合作社牌匾的一个三分大的院子哩,坐南朝北破烂不堪的三间小平房,中间一间的二十平米大的屋子是村干部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仅有一张方桌,五六个长长短短高高矮矮的木凳。小院和三间小平房是村里唯一的共有财产。办公室里的桌凳火炉和其他用具等,全是干部们自带来的。小院和办公室里清扫得十分洁净,不见一片树叶,没有一根碎草。这些都是瞎子老人辛苦的结果。谁也不能将瞎子老人阻拦,谁也不能代瞎子老人辛苦。瞎子老人说这样的辛苦是他的福。
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是韩美凤。韩美凤安静的坐在方桌一侧的长凳上翻看着往天的报纸。她的眉眼又透出原有的媚气,她的面颊又显出固有的红润,好看得让女人们羡慕,让男人们心动。欢欢火化已经五天,她已放开欢欢给予她的痛苦,更不把张石头鼓动人寻衅闹事再搁在心里。欢欢妈也没有给她增添麻烦,真心实意的把她当成闺女,与她相依为命。
小院里并无声息,而韩美凤好像是听到院里有人呐喊她,她急忙推开报纸,嗖地站起来,紧走两步,爽快的拉开两扇院门,通通通地跑往院里,在院门口站立下来朝外暸望。转眼之间,仿佛暖心的春风朝暸吹来,她禁不住的心花怒放,眉目越发明媚,面颊愈加红润。白冰冰走过戏台一侧,大步流星地朝着办公室院门走来。白冰冰外出六天,心累身也乏。县委杨秋江书记答应为他设法办理采矿证,为他向蒋希文讨要百万欠款,又答应他帮助他解决抗日老民兵马大波的困难。而后,他的心回到村里南山上,琢磨又琢磨。挖掘铁矿石,修通山中道路,租赁铲土机、挖掘机、压道机、拖拉机,没有五十万,休想听一听“四机”的响声。村民们筹划不出三万四万,只有想法跑银行或跑信用社贷款。
站立在小院门口的韩美凤,只是瞅着白冰冰朝着小院走来,就嫣然一笑,急忙返回办公室,为白冰冰倒下一杯白开水,静等白冰冰往办公室里来坐下,把她淤积在心里的苦辣酸甜一锅端出。
白冰冰喊一声美凤,很快推开办公室的两扇屋门。
韩美凤不会想到,进屋的不只是白冰冰自己。杨大年、刘福福同两委班子的干部齐刷刷地跟在白冰冰身后。瞎子老人同十多位男女村民也随后而至,使二十平米大的办公室里再无插脚之地。人人喜气洋洋。最欢畅是杨大年。一个比杨大年年轻的后生为杨大年让座,杨大年双手把瞎子老人按在凳子上。杨大年今天才开始喘一口气。前几天,他估计白冰冰外出办理采矿证不会落实。他同两委班子的干部进一步翻山越岭,探测了铁矿准确的储量,距地面的厚度。勘测了机器进出的路线,算计出修宽道路用工数目,并做通了修路被占地户们的工作。
“拿回没拿回采矿证来?”村干部们与男女村民不约而同的急问白冰冰。白冰冰只顾接过韩美凤递他的水杯喝水没有立即回答。而且他的笑脸如常:既无一分乏力,又不显丝毫得意。难让人做出他外出白费了盘缠的结论。
“完啦,完啦!”叼旱烟袋的支部委员抢先大发牢骚,“冰冰哥必定是水中捞月——白扑腾了。我早猜到冰冰哥会水中捞月。山河好改,人的秉性难移,冰冰哥绝不会为拿到采矿证请客送礼。拿不到采矿证,咱槐树坡还得是槐树坡,谁也甭想多吃一口好的,多穿一件新的,生来是什么命就永远是什么命了。”
白冰冰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喝足水,耐心地等叼旱烟袋的支部委员牢骚完结,才慢腾腾地放下水杯,谦和地站立起来面向大家:“嘿嘿嘿,我没有把采矿证拿回来,我也不是水中捞月——白扑腾了。”他再喝一口水,将他跑县法院控告蒋希文碰壁,赴省国土资源厅办理采矿证生气窝火,后幸运地见到县委杨秋江书记,受到杨秋江书记非凡的热情关怀,绘影绘声、仔仔细细地汇报给大家,再畅快的笑笑说:“看来我这个二百五还有几分运气。”
人人喜气洋洋,人人兴高采烈。
“运气不错,运气不错!我早就想到冰冰哥外出的运气不会错了!”杨大年指手画脚,抢先感慨一番。“冰冰哥的运气,也是我们大家的运气。今后,我们更得实心饱力的干了!”
“哈哈哈,”瞎子老人喜兴得好像看到了亮光,由不得摇头晃脑,“看来,不管腐败的风气儿多么严重,总归还是共产党领导。”
“不错,总归还是共产党领导!”有人举着拳头呼应。
也还有人担心白冰冰的汇报不实。刘福福吞吞吐吐地问白冰冰:“冰冰,我……我想问你一句,我问得要不实际,你……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福福叔,你只管问你的。”白冰冰痛快的说。
“你……你同大家讲的全是实话?是不是害怕大家情绪低落,故……故意和大家吹……吹牛?”
“福福叔,”白冰冰憨厚的笑笑,推开身前的杨大年,朝刘福福走过一步,“我理解你的心思,我也很怕我向大家的汇报,是耕地用鞭子——吹(催)牛,给我往脸上抹黑。我二百五不二百五,脸皮并不是很厚。我看得不敢说绝对正确,可我看县委杨秋江书记对待我的态度,让你福福叔做不出我吹牛的结论。”白冰冰喘一口气再说:“福福叔,咱叔侄俩共事不是一年,你记得我冰冰什么时候说过一句大话,什么事上说过一句假话?大跃进、放卫星、当干部就得吹牛的时节,你当支书,我当大队长,我吹过一句牛没有?……”
“没有,没有,上岁数的都记得,你顶天立地,宁肯当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也不吹牛。你别往下说啦,你福福叔一句是不是吹牛,是有嘴无心,也实在是害怕现在当官儿的作风不实,胡弄咱平民百姓……”刘福福突然封口,有人在院里喊“冰冰大伯,有远客找你。”
3
“远客,谁呢?”办公室里人人张口,人人都感到惊奇。槐树坡人很少见到远客。人人争先恐后,一起跟白冰冰迎往院里。不认识远客的干部和村民吃惊,认识远客的白冰冰、杨大年、韩美凤同样吃惊。人人吃惊得直瞪瞪地瞧着从院门里走进院里的远客。白冰冰的一双眼睛瞪得最大。谁都看得出远客不是一位普通的客人。远客穿一身名牌深蓝色西服,外穿一件少见的时髦的呢子大衣,脚穿一双黑色皮鞋,大背头油光发亮。如此的气魄,不认识远客的村民们止不住的窃窃私语。而远客自己提一沉甸甸的提包,脚步不太自然,脸面干巴微黄,眉目欠爽欠展。
远客是凤凰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板——白冰冰心目中的骗子蒋希文。
蒋希文紧迈两步,干笑着用力与白冰冰握手,并谦恭地说:“进村就看到让我敬仰的白支书深感荣幸!”
白冰冰做梦也想不到在槐树坡见到蒋希文。他自然想起蒋希文欠他的百万,想起蒋希文高明的骗术;想起他在凤凰岭东边山岭下的水库边上,看到因为被蒋希文骗得没有活路跳水自尽的汉子;听到救汉子出水的山村教师对蒋希文的声讨。他止不住怒火中烧。他又想不到蒋希文对他恭而敬之,还有几分不得已的卑下。而他很快镇定下来,将火压下。他想:不管蒋希文来见他是做甚,他都没有必要简单粗暴。他坦然地与蒋希文握手,并客气地说:“我很高兴在我们村里见到你。”
“白支书,我想单独同您谈一谈,可以吗?”蒋希文继续与白冰冰握着手说。
“可以。”白冰冰答应的很痛快。
白冰冰说着带蒋希文走进办公室,干部和村民们都走开了。白冰冰等蒋希文将提包放在方桌上,在方桌左侧木凳上坐下来,为蒋希文斟杯白开水,他才在方桌右侧木凳上与蒋希文面对面地坐下来,瞪着一双眼睛等着蒋希文开口。他在院门里朝外看的清楚:蒋希文未带秘书,未带保镖,蒋希文是自己驾车而来。他嚼不透咬不烂蒋希文来见他之目的,而他能够想到,蒋希文孤家寡人来见他,必定与县委杨秋江书记有关。
白冰冰想的不错,蒋希文来见他,确确实实与杨秋江书记有关。
杨秋江书记接见白冰冰第二天早晨,杨秋江书记亲自给蒋希文打电话,通知蒋希文上午八点半,他在政府招待所一号楼三〇一房间等候蒋希文。蒋希文准时到达杨秋江书记指定的房间。杨秋江书记只是与蒋希文寒暄两句,就眼里闪烁出不快,抛出对蒋希文的不满:“蒋董事长,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向法院告你?”蒋希文装傻充愣:“哪一个告我?” 杨秋江书记对蒋希文更加不满,他精明的两只眼睛面对着蒋希文,闪射出难以遏制的怒火:搭在沙发扶手上的白白净净的两只手不停的颤动。他道一句“我简直不认识你蒋董事长是哪一个了!”再说,“蒋董事长,我对你十足的相信,相信你会把凤凰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干好,为金光县革命老区增添光彩,为你也为我争得荣誉。因此,我千方百计的对你支持!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对蒋希文不可重看,不必过分支持,要对他多加小心为好,我对人不加理睬。哪儿知道,人家把你看得千真万确!我杨秋江太无知!你同人签订施工合同,结果成了一张废纸。人催你履行合同,你花言巧语,拒不执行。你随意克扣朝凤凰岭打工工人们的工资,人去向你讨要欠款,你竟然变成了你哥哥蒋希武,说你蒋希文自杀身亡,随便的捉弄人家,我杨秋江怎么也想不到你的骗术如此不凡!你克扣了人的工资,建宾馆,盖别墅,养情妇,找三陪,肆意挥霍。” 杨秋江书记喘息,蒋希文接话:“是一个姓白叫冰冰的告了我?”
“不错,是槐树坡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白冰冰找我来反映了你目无党纪国法,严重损害党的声誉。”杨秋江书记的口气越来越严厉。
蒋希文不在乎,跷起二郎腿,背依沙发,掏出纸烟点着,慢慢悠悠的抽纸烟。
杨秋江书记怒气冲冲地斜蒋希文两眼,轻微地冷笑一声,忽然眼皮微合,抿着薄薄的嘴唇沉默片刻,让他的怒火沉到心底,面皮松松展展,语气平平和和:“希文,我告诉你,你切不要小看白冰冰这个庄稼汉子!” 杨秋江书记饮一口茶,将白冰冰与糊糊司令的关系详尽的讲给蒋希文,再严肃认真的说,“白冰冰已经向我申明,找见我再告不倒你,他就进京求见糊糊司令。糊糊司令绝不会不接见他!糊糊司令绝不会不为他说话!糊糊司令虽然早已离职,但他说句话可还顶句话哩!每到春节,中央领导同志都往他家里去看望他。” 杨秋江书记喘一口气,“我告诉你说,我已经得到消息,接替陈书记的正是从北京派下来的糊糊司令的老二。糊糊司令只要为白冰冰张一张口,你蒋希文就难不身败名裂,我杨秋江也难脱干系!”
蒋希文嘴唇抿成一条线,目珠凝滞,不言不语。
杨秋江书记压在心底的怒火猛然间爆发,他举手拍响桌面,大发雷霆:“姓蒋的,请你听着,我只警告你一句,你必须尽快去向白冰冰道歉,归还白冰冰的欠款,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姓蒋的负责!”
只是转眼之间,能装善变的蒋希文即变为另一副面孔:满脸披笑,急忙诚恳而又谦敬地发誓:“杨书记,请你息怒,我尽快去向白支书诚恳地道歉,如数归还对白支书的欠款。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到做到,你只管放心。”
只有鬼才知道蒋希文与杨秋江书记的发誓是虚是实。他驾车即将驶进槐树坡村口的时候,心里还朝白冰冰骂了一声他妈的!蒋希文在槐树坡村委会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白冰冰,如在杨秋江书记办公室里向杨秋江书记书记发誓那样,满脸披笑,诚恳而又谦敬:
“白支书,我今儿个找您来是向您道歉的,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跟您去凤凰岭打工的哥儿们兄弟,没有按时交还您百万工钱。更严重的,更不可宽恕的是,我还对您不择手段的欺骗,我败坏了革命老区金光县的声誉,损害了我们党的威信。归根结底,或者说是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我受到拜金主义的严重影响,对三个代表学习的不透,领会的不深。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心胸宽广、忠厚老实的您,一定会不记小人之过,原谅我的失误。我向您发誓:今后,我一定学透吃透‘三个代表’的实质,完全彻底的改正我的错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绝对心口如一,说到做到!”
未道过一句假,未道一句空,对骗深恶痛绝的白冰冰,对蒋希文流畅的谈吐全神贯注,一字一句都不流失在耳外。
“白支书,请您允许我再同您解释两句。”蒋希文的语气愈加诚恳,神情越发显得真诚,“您听到的我克扣大家的工资,建宾馆,盖别墅,养情妇,找三陪什么的,全是对我的诬陷!这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地痞,去找我敲诈勒索,我没有使他得逞,他就四处对我栽赃陷害!你想想,我的失误再严重,我也还是个为革命教育基地做出了贡献的共产党员,我岂能如贪官污吏那样的无耻。”
蒋希文利索地刹住自己流利的谈吐,喘一口气,掏出手绢擦净两滴委屈的泪水,从提包里取出大捆钱票,推向白冰冰面前:“白支书,这是我给您送来的百万欠款,请您收下。”
白冰冰注意到蒋希文带来的提包,他却没有想到提包里装的欠他的百万欠款。他想蒋希文之“流畅”之“诚恳”,不过是耍一耍嘴皮子罢了。习惯见甜则乐的白冰冰,看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实实在在的百万人民币——他与杨大年、韩美凤等困难户们的千辛万苦,难免不乐,而他的眉目中未透星星点点的笑意。他只是说:“谢谢你给我送来了欠款。”再搭一句:“中午,我请你喝盅红枣老酒。”一直对白冰冰目不转睛、诡计多端的蒋希文已经看出,白冰冰对他不会宽恕,白冰冰留他喝盅红枣老酒,只不过是和他客套。而他却瞎子牵驴——不松手: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