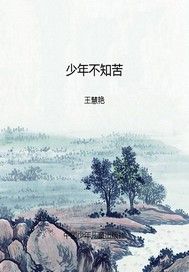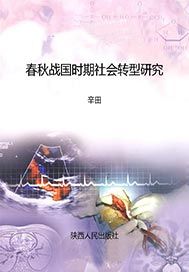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十七章 惊心动魄的日子
1
今天是槐树坡诞生新村长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诞生新村长、新支书的日子。候选人只要当选村长,按照乡里村长、支书合二而一的要求,他只要是党员,也必定当选为支书。
这一日子,是与槐树坡每家每户都休戚相关的重要日子,从选举结果看,这一日子也是惊心动魄的日子。
看来,选举后要热热烈烈的祝贺一番。不知哪一位检验炮仗的效果,使一个大两响砰的一声窜向高空,升向蓝天,啪了一声,爆出一团青烟,裂出无数红红黄黄的纸片,如彩蝶一般朝四下飘落,引逗得不少男娃女娃雀跃着叫好。
实验炮仗的是拿得张金锁千元喊过张金锁“村长”的张二九。男娃女娃们雀跃着喊好,张二九仰望着蓝天里的“彩蝶”眉飞色舞,把长长的舌头吐出口外。他的细细的两条长腿也异常轻快,他在戏楼下的广场上眉飞色舞完毕,转眼之间,他又在张金锁家东厢房屋里落脚。
张金锁正在吃早饭,吃得脸面红润似火,煞是好看。张二九当然的又先喊一声“村长”。张金锁未批评张二九:“不要瞎叫,八字还没有一撇!”张二九接着说:“村长,你怎么才吃早饭?” 张金锁吃下一大口面条,痛快的说他的早饭不迟,说着扔给张二九一根纸烟。张二九顾不得抽纸烟,把纸烟放在耳夹里,积极地向张金锁提出建议:“金锁哥,不,村长,你怎么还是原身衣裳,土里土气的,今儿个你上马,必须得改换行头,穿身时髦的适合你身价的衣裳,不能给大家丢脸。” 张金锁吃尽面条,推开饭碗,嘿嘿嘿地笑笑,脸面越发红里透红,感谢张二九的建议,说换一身跟潮的衣服,不给大家丢脸。张二九让张金锁笑得更响,面色越发好看。“金锁哥,我起得很早,我饭也没顾得吃一口,就去找见武术会上执挥旗的老李,与老李协商妥当,选举结束之后,请耍武术的人们人人出场,实加实地祝贺祝贺,要红火得比正月十五还要红火。他要求不高,只要三条太行牌纸烟即可。我把三条烟拿给他以后,我们俩又把锣鼓家伙擦拭了擦拭。” 张金锁不看先扔出的一根纸烟还在张二九耳朵夹里,又扔给张二九一根纸烟,再喜呵呵的朝张二九伸出两根拇指。张二九还要朝张金锁汇报什么,一光头汉子拿着一套理发用具,撂开门帘即站到张二九脸前:
“金锁叔,我给你净一净头脸。”
张金锁答应张二九改换改换行头,换身跟潮的衣服,只是嘴上痛快痛快,未想要包装一下自己,更没有净一净头脸,他了解乡亲们习惯朴实,他担心遭人笑话他轻浮,丢失选票。尽管他认定他抛出去五十万已把村里的两块印章拿稳。他与光头汉子笑笑说:
“球的,老大不小的啦,还净什么头脸儿?甭费你的工夫啦。”
日子紧巴的光头汉子从张金锁手里接住的钱票,比张二九多着五百,对张金锁的感激、对张金锁的殷勤,绝不能不超过张二九:
“金锁叔,正是你老大不小的了,我才扔下家里的营生,来让你年轻年轻。你要接任村长、支书,成为槐树坡的领导,咋能不跟上形势?咋能不与时俱进?现在,从中央到基层干部一律年轻化。你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老气横秋,哪一个还下你的票哩?即便大家下了你的票,乡里的头头脑脑也不会看起你来。快快快,别让我磨牙费嘴啦。”光头汉子说着把凳子摆好,将罩布抖开。
“金锁哥,你今儿个必须得听我们的!”张二九说着把张金锁拉得在椅子上坐下来,再劝说张金锁,“你村长、支书当定了,就不是一般人了。常说,当狼像狼,当虎像虎,当了村官儿,必须得有村官的样子。你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乡官的行头、乡官的样子,就得村官很不一产。县里的官员又和乡官的行头、乡官的样子大不一样。县官和乡官一样了,就失了县官的身份。乡官和村官的行头、样子一样了,就失了乡官的身价。村官和百姓的行头、样子一样了,就失了村官的身份。我听一个乡长说,身价就是地位,关系着老百姓眼里的威望,重要得很哩!”
光头汉子细心地为张金锁推剪着头上的一寸余长的黑发接话:“张二九文化不高,口才不错,有两下子,句句说到点子上。金锁叔,你朝镜子看一看你的头,推一推、剪一剪,和不推不剪大不一样了吧?显得精神了吧?显得年轻了吧?我再把你的脸上的汗毛、胡子一扫而光,那就更精神、更年轻了。”光头汉子紧喘一口气,不等又想朝张金锁送痛快的张二九接话,“金锁叔,你的体面,也是我的体面,也是张二九的体面,也是下你票的人们的体面……”
张金锁无声的笑得一双眼睛没有过的光亮,鼻孔里没有过的畅快。他的五十万人民币在他头脑里一闪而过。他垂着的一只手慢慢拿起放在胸前,他的内心不寻常的滋润,他遍身都感到舒适。他意识到他在光头汉子、张二九眼里已不同往常,他在他人的眼里他会有变;变得地位高了,威望高了。他的装束也应该略微变一变了,不能再老一套,土里土气。
“光头侄子来让我年轻年轻、美观美观,完全应该。”
说话间,光头汉子已为张金锁的寸发剪齐,又将张金锁的脸面刮光。
“金锁叔,你在镜子里再照一照,看一看满意不满意?”
“哈哈哈,相当满意,相当满意!”张金锁的说话腔调也不由自主的有变,“回头我买两个猪肘子,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两杯。”他把喝字拉得很长,把杯子说得很脆很实,与村官身份十分协调。
“陪客的自然是我张石头和张二九了。”张石头贸然走进屋里,他一手拿着半根纸烟,一手拿着写满钢笔字的两张白纸。他的嘴唇透着饥渴,眉眼中连着疲倦。他将张二九揪得站下,他与张金锁面对面的坐到沙发上,伸一伸懒腰,得意而又不失谦和的表白他的来意:
“金锁……”
“石头哥,你说,你说。”
“昨天晚上,我开了多半宿夜车,终于把你的竞选发言稿和选举后的登台亮相讲话稿,勾划出了个大概,我拿来请你抓紧时间过过目,有不妥之处,你就把它改正。”说着把张金锁的竞选发言稿和选举后张金锁的登台亮相讲话稿递给张金锁。
张金锁从茶几小抽屉里拿出花镜戴到眼上,精心的过目发言稿与亮相稿,反来复去的过目,脸上一会儿流露出喜悦,一会庄重地点一点头,喜悦过多次、点过头多次之后说道:
“总的讲很好!你不场子比我高明,头脑里点数真多,让我金锁心服口服。不过……”
“不过什么,你直截了当。”张石头不瞒张金锁停顿。
张金锁说:“竞选发言稿中间有两句不够谦虚,我的意见,在父老乡亲面前,不能有一句不够谦虚,一句不够谦虚都可能丢票。”
张石头接话:“把那句不够谦虚的句子改了。我赞成你的谨慎,越是有了成功的把握,越是不能粗心大意。我家去吃早饭了。乡干部大概很快就到了,我吃过早饭,就在大喇叭里吆喝集合。”张石头不等张金锁点头就扬长而去。
“我也走了。”张二九与光头汉子同时开腔,同样兴高采烈。“单等祝贺你上台,点响炮仗,敲响锣鼓,喝你一杯喜酒!拜拜。”
张金锁也不说再见,也说英语。他得意的说着心里闪过炮仗与锣鼓的响声,泰然地将张二九与光头汉子送出院门。
2
选举村长的会场安排在戏楼下的打麦场里。打麦场里清扫得洁净如洗,做为主席台的戏台上摆满桌凳。天上无云,地上无风,阳光明媚,已入冬的天气暖暖和和。这时,有人把武术会上的锣鼓抬来,又把长枪短刀抱来。挂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里也传出响亮的吆喝声:
“父老乡亲注意啦,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就要隆重举行,请有被选权和选举权的男女公民,赶快朝戏楼下集合。这次选举其意义非常重大,请大家不要迟到早退;不要带孩子,不要带针线营生。我再广播一遍,好好听着……”声音宏亮,底气很足。男女村民路路续续地朝戏楼下走来,大家结伴,三三两两,有的提小板凳,有的拿草铺团。走过老槐树下的一男一女嫌弃大喇叭里的声音刺耳,忙把耳朵捂掩。一会儿,他们放下手来,女村民问男村民,谁在大喇叭里吆喝?男村民回答,像是张石头。男村民没有回答错,确确实实是张石头。昨天,村民们集合起来,产生了村委会的正副村长、委员候选人,张金锁与白冰冰当选为村长候选人,张石头、杨大年当选副村长候选人。张石头与杨大年还当选为选举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主持换届选举。张石头的积极性飞跃般的高涨起来。从大喇叭里也可感到他不寻常的积极性。
朝戏楼下走来的男女村民越来越多。看来,不管是白发、不管是刚到有选举权的村民,人人满意自己当家作主,直选自己当家人——村委会的干部。谁也不像当社员的时候,听见队长吆喝上工,干一样的活儿,分一样的粮食,无所用心。谁也不可能间而单之,不用一番心思掂对过来又掂对过去。想想眼前,再想想长远。谁心里也不可能还没有底数。而谁也不肯露底。一红脸汉子边走边问一矮个后生:锉子,今儿个下哪位票啊?矮个后生说:“还不知道哪儿炕凉哪儿炕热哩。”大都随随便便的寒暄:“吃过啦?”“吃过啦。”“今儿个天气不赖。”“不赖,快小雪了,还这么暖和。”也有人嗓门挺高的亮出底牌:“今儿个,我们一家子全投张金锁的票。”亮出底牌的还不是一位两位。
老支书刘福福忽然从打麦场东南角露头,不声不响的同瞎子老人等坐在一起。他脸色不大好看。他东躲西藏,张石头始终未能见到他,张石头却扔给了他老伴五百块钱。这让他为难到家:给张石头送回,得罪了张石头,又得罪了张金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实在拉不下脸来;若投张金锁一票,又深感亏心,他已知张金锁在村里掌权的目的——个人暴富。他对张金锁的目的极为反感。五百块钱如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上,他不安的一夜没有合眼,到吃早饭的时候,一棵心还上上下下的颤抖。到了张石头在大喇叭里吆喝起来,他才朝自己碎了一口唾液,扇了自己一掌,痛骂了自己一声“窝囊”,咬紧牙齿定一定心,硬着头皮慢慢朝戏楼台下走来。
瞎子老人问田福福,张金锁露面没有哩?低着头的田福福抬头朝四下暸一暸,告诉瞎子老人张金锁还没到。瞎子老人再问田福福,杨大年、韩美凤露面没露面?田福福朝西北角上瞅一眼,告诉瞎子老人杨大年、韩美凤到啦。
杨大年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四、五个壮年汉子坐在一起。韩美凤坐在中年妇女堆里。二人都显得文雅安详,而心里并不娴静,他们都在担心,他们并不能如愿,张金锁会当选为村长。
瞎子老人再与田福福嘀咕:“田福福,白冰冰到没到?”田福福小声说:“看不见他在哪儿。”田福福,你估计估计今儿的戏……“田福福打断瞎子老人:别问啦,乡里领导干部和张金锁、张石头来啦。”
乡里两位干部与张金锁并驾齐驱从老槐树下朝会场走来。两位乡干部穿戴跟潮,白白净净的,气宇不凡,与张金锁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张金锁走在中间,张石头跟在张金锁身后。张金锁西服一身,皮鞋锃亮,脚步不快不慢,与两位干部走在一起,毫不逊色。坐在戏台西南角的十多位乡亲,见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走来,齐刷刷的站立起来,向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呈现热情,表示恭敬——笑呵呵地紧给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让路。一矮个子后生还满脸披笑地与张金锁握一握手。
白冰冰随后走来,他之穿扮神态与素常无别,原有衣裳,土气而不俗气。
选举进度甚快,主持选举的张石头请两位乡干部作了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后,就请两位竞选村长的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
“现在,我们首先请张金锁发表竞选演说。”张石头如在大喇叭里吆喝一样用力。吆喝毕,把张金锁推到台前。
“父老乡亲们,”张金锁成竹在胸,面目似笑非笑,神态谦和而又庄肃,语气平和而又激昂。“首先我实实在在地感谢父老乡亲们推选我做村长候选人。我当选不了村长,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父老乡亲们看得起我,给我面子。”他看一眼坐在主席台上的两位干部,“我要能得到大家信任,当选了村长,要听从乡里的领导,用毛主席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武装头脑。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绝不能让乡亲们老在温饱线上止步不前,争取在一两年之内,让槐树坡的面貌焕然一新:家家不再缺零花钱;住老房子的盖上新房;应该结婚的光棍娶上新娘;考上高中、大学的能交起学费。我请父老乡亲监督,我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父老乡亲们服务。我就说这么两句吧。不对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又是掌声又是笑声,相当的热烈。
“现在,我们再请白冰冰发表竞选演说。”张石头依然如在大喇叭里那样用力,他还特意的加一句。“请大家拍手欢迎。”
掌声没有张金锁的掌声热烈。
白冰冰慢步走上戏台。他面目平静,脚步轻松,无事人似的。而他的心里却挂着沉重。他不把当选不当选村长放在心上,他晓得当今钱的作用,他认为村里的两块印章定然落在张金锁手里。让他沉重的是:一,村里的两块印章落在张金锁手里以后,如何使张金锁独占南山的打算变为白日做梦;让张金锁的打算落空,并不是轻而易举。二,如何向蒋希文讨要百万欠款,摆脱欠朋友七十五万元的负担;向蒋希文讨要到百万欠款,撕破蒋希文政治骗子的假面具,更不容易。
张石头催促白冰冰发表竞选演说。
白冰冰心里并未装着现成的演说词儿。而他既然走上戏台上,立到了众乡亲们面前,就不能不随意的应酬两句:
“乡亲们:我朝戏台下来的时候,有人问我,白冰冰,今儿个你要登一登台,怎么也不包装包装?实话实说,我这黑脸儿,包装包装,也好看不了多少。”
台下有人哈哈大笑。
白冰冰继续应酬:“乡亲们:又有人问我白冰冰,你不包装包装,是不是不乐意当官儿?我实话实说,我没意当官儿。不是当初,当初,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我看自个儿亲了,怕落下不是,让人骂娘。”
白冰冰咳嗽两声,郑重其事:“乡亲们:如果大家还要我拉套,我就还拉。怎么拉哩?有人发现南山里储存着铁矿,我的主要精力就放铁矿开发上。怎么开发哩?简单明了:向华西、南街、刘庄学习,集体开发,共同富裕。绝不能让南山归了一家一户,富了一家一户。有人说,开采矿山,必须得有靠山:一要依靠当官儿的,得让当官儿的和黑社会头目入股,二要依靠黑社会,我说这是瞎子架电线——胡扯!我只想依靠槐树坡的乡亲们。绝不允许当官儿的和黑社会头目白白的入股,占乡亲们一分钱的便宜!我不再罗嗦了,就瞎说这么两句。”
掌声稀稀拉拉。也听不到一声笑声。只见瞎子老人与田福福嘀咕:“冰冰咋不多说两句哩……”
选举很快出现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不少人支棱起耳朵朝前探头探脑;一些人站立起向前注目;有人自言自语地说怪;坐在戏台上的两位乡干部交头接耳;坐在戏台上的张石头瞪大两眼张开大口;同张石头坐在一个长凳上的张金锁,面色变得让人再认不出是他。
唱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中年妇女许是做姑娘的时候进过剧团,嗓音极为动听,吐字十分清楚,无一人说她把候选人的名字唱错。朝黑板上书写票数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认真负责,无一人怪他把票写错。开始,张金锁的票数高于白冰冰,而五十票之后,二人的票数开始相平,一百票之后张金锁落后于白冰冰。很快,张金锁的名字下不再增添一个“正”字,白冰冰的票数已达到三百零五票,超过了半数。
忽然间,台上台下,不管是乡里干部,不管是男女村民,人人惊心动魄:有的喊天!有的喊呀!有的伸头探脑。
坐在戏台上一条长凳上的张金锁,原本聚精会神的闻听唱票人唱出他的名字,全神贯注的注视他的每一张选票;选票,分明是他的财富,也是他的名誉、地位;他每多一张选票,他的目中多一分光芒,脸上即多一分亮色。他的票数与白冰冰票数相等之后,脸上少了亮色。白冰冰的票数增多到三百零五票,他的眼睛顿时白多黑少,翻了两翻,嘴唇颤栗,上身前后左右的摇晃摇晃,一下瘫倒在地下再站不起来。让人想不到是否还有一口气。
今天是槐树坡诞生新村长的日子,也可以说是诞生新村长、新支书的日子。候选人只要当选村长,按照乡里村长、支书合二而一的要求,他只要是党员,也必定当选为支书。
这一日子,是与槐树坡每家每户都休戚相关的重要日子,从选举结果看,这一日子也是惊心动魄的日子。
看来,选举后要热热烈烈的祝贺一番。不知哪一位检验炮仗的效果,使一个大两响砰的一声窜向高空,升向蓝天,啪了一声,爆出一团青烟,裂出无数红红黄黄的纸片,如彩蝶一般朝四下飘落,引逗得不少男娃女娃雀跃着叫好。
实验炮仗的是拿得张金锁千元喊过张金锁“村长”的张二九。男娃女娃们雀跃着喊好,张二九仰望着蓝天里的“彩蝶”眉飞色舞,把长长的舌头吐出口外。他的细细的两条长腿也异常轻快,他在戏楼下的广场上眉飞色舞完毕,转眼之间,他又在张金锁家东厢房屋里落脚。
张金锁正在吃早饭,吃得脸面红润似火,煞是好看。张二九当然的又先喊一声“村长”。张金锁未批评张二九:“不要瞎叫,八字还没有一撇!”张二九接着说:“村长,你怎么才吃早饭?” 张金锁吃下一大口面条,痛快的说他的早饭不迟,说着扔给张二九一根纸烟。张二九顾不得抽纸烟,把纸烟放在耳夹里,积极地向张金锁提出建议:“金锁哥,不,村长,你怎么还是原身衣裳,土里土气的,今儿个你上马,必须得改换行头,穿身时髦的适合你身价的衣裳,不能给大家丢脸。” 张金锁吃尽面条,推开饭碗,嘿嘿嘿地笑笑,脸面越发红里透红,感谢张二九的建议,说换一身跟潮的衣服,不给大家丢脸。张二九让张金锁笑得更响,面色越发好看。“金锁哥,我起得很早,我饭也没顾得吃一口,就去找见武术会上执挥旗的老李,与老李协商妥当,选举结束之后,请耍武术的人们人人出场,实加实地祝贺祝贺,要红火得比正月十五还要红火。他要求不高,只要三条太行牌纸烟即可。我把三条烟拿给他以后,我们俩又把锣鼓家伙擦拭了擦拭。” 张金锁不看先扔出的一根纸烟还在张二九耳朵夹里,又扔给张二九一根纸烟,再喜呵呵的朝张二九伸出两根拇指。张二九还要朝张金锁汇报什么,一光头汉子拿着一套理发用具,撂开门帘即站到张二九脸前:
“金锁叔,我给你净一净头脸。”
张金锁答应张二九改换改换行头,换身跟潮的衣服,只是嘴上痛快痛快,未想要包装一下自己,更没有净一净头脸,他了解乡亲们习惯朴实,他担心遭人笑话他轻浮,丢失选票。尽管他认定他抛出去五十万已把村里的两块印章拿稳。他与光头汉子笑笑说:
“球的,老大不小的啦,还净什么头脸儿?甭费你的工夫啦。”
日子紧巴的光头汉子从张金锁手里接住的钱票,比张二九多着五百,对张金锁的感激、对张金锁的殷勤,绝不能不超过张二九:
“金锁叔,正是你老大不小的了,我才扔下家里的营生,来让你年轻年轻。你要接任村长、支书,成为槐树坡的领导,咋能不跟上形势?咋能不与时俱进?现在,从中央到基层干部一律年轻化。你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老气横秋,哪一个还下你的票哩?即便大家下了你的票,乡里的头头脑脑也不会看起你来。快快快,别让我磨牙费嘴啦。”光头汉子说着把凳子摆好,将罩布抖开。
“金锁哥,你今儿个必须得听我们的!”张二九说着把张金锁拉得在椅子上坐下来,再劝说张金锁,“你村长、支书当定了,就不是一般人了。常说,当狼像狼,当虎像虎,当了村官儿,必须得有村官的样子。你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乡官的行头、乡官的样子,就得村官很不一产。县里的官员又和乡官的行头、乡官的样子大不一样。县官和乡官一样了,就失了县官的身份。乡官和村官的行头、样子一样了,就失了乡官的身价。村官和百姓的行头、样子一样了,就失了村官的身份。我听一个乡长说,身价就是地位,关系着老百姓眼里的威望,重要得很哩!”
光头汉子细心地为张金锁推剪着头上的一寸余长的黑发接话:“张二九文化不高,口才不错,有两下子,句句说到点子上。金锁叔,你朝镜子看一看你的头,推一推、剪一剪,和不推不剪大不一样了吧?显得精神了吧?显得年轻了吧?我再把你的脸上的汗毛、胡子一扫而光,那就更精神、更年轻了。”光头汉子紧喘一口气,不等又想朝张金锁送痛快的张二九接话,“金锁叔,你的体面,也是我的体面,也是张二九的体面,也是下你票的人们的体面……”
张金锁无声的笑得一双眼睛没有过的光亮,鼻孔里没有过的畅快。他的五十万人民币在他头脑里一闪而过。他垂着的一只手慢慢拿起放在胸前,他的内心不寻常的滋润,他遍身都感到舒适。他意识到他在光头汉子、张二九眼里已不同往常,他在他人的眼里他会有变;变得地位高了,威望高了。他的装束也应该略微变一变了,不能再老一套,土里土气。
“光头侄子来让我年轻年轻、美观美观,完全应该。”
说话间,光头汉子已为张金锁的寸发剪齐,又将张金锁的脸面刮光。
“金锁叔,你在镜子里再照一照,看一看满意不满意?”
“哈哈哈,相当满意,相当满意!”张金锁的说话腔调也不由自主的有变,“回头我买两个猪肘子,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两杯。”他把喝字拉得很长,把杯子说得很脆很实,与村官身份十分协调。
“陪客的自然是我张石头和张二九了。”张石头贸然走进屋里,他一手拿着半根纸烟,一手拿着写满钢笔字的两张白纸。他的嘴唇透着饥渴,眉眼中连着疲倦。他将张二九揪得站下,他与张金锁面对面的坐到沙发上,伸一伸懒腰,得意而又不失谦和的表白他的来意:
“金锁……”
“石头哥,你说,你说。”
“昨天晚上,我开了多半宿夜车,终于把你的竞选发言稿和选举后的登台亮相讲话稿,勾划出了个大概,我拿来请你抓紧时间过过目,有不妥之处,你就把它改正。”说着把张金锁的竞选发言稿和选举后张金锁的登台亮相讲话稿递给张金锁。
张金锁从茶几小抽屉里拿出花镜戴到眼上,精心的过目发言稿与亮相稿,反来复去的过目,脸上一会儿流露出喜悦,一会庄重地点一点头,喜悦过多次、点过头多次之后说道:
“总的讲很好!你不场子比我高明,头脑里点数真多,让我金锁心服口服。不过……”
“不过什么,你直截了当。”张石头不瞒张金锁停顿。
张金锁说:“竞选发言稿中间有两句不够谦虚,我的意见,在父老乡亲面前,不能有一句不够谦虚,一句不够谦虚都可能丢票。”
张石头接话:“把那句不够谦虚的句子改了。我赞成你的谨慎,越是有了成功的把握,越是不能粗心大意。我家去吃早饭了。乡干部大概很快就到了,我吃过早饭,就在大喇叭里吆喝集合。”张石头不等张金锁点头就扬长而去。
“我也走了。”张二九与光头汉子同时开腔,同样兴高采烈。“单等祝贺你上台,点响炮仗,敲响锣鼓,喝你一杯喜酒!拜拜。”
张金锁也不说再见,也说英语。他得意的说着心里闪过炮仗与锣鼓的响声,泰然地将张二九与光头汉子送出院门。
2
选举村长的会场安排在戏楼下的打麦场里。打麦场里清扫得洁净如洗,做为主席台的戏台上摆满桌凳。天上无云,地上无风,阳光明媚,已入冬的天气暖暖和和。这时,有人把武术会上的锣鼓抬来,又把长枪短刀抱来。挂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里也传出响亮的吆喝声:
“父老乡亲注意啦,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就要隆重举行,请有被选权和选举权的男女公民,赶快朝戏楼下集合。这次选举其意义非常重大,请大家不要迟到早退;不要带孩子,不要带针线营生。我再广播一遍,好好听着……”声音宏亮,底气很足。男女村民路路续续地朝戏楼下走来,大家结伴,三三两两,有的提小板凳,有的拿草铺团。走过老槐树下的一男一女嫌弃大喇叭里的声音刺耳,忙把耳朵捂掩。一会儿,他们放下手来,女村民问男村民,谁在大喇叭里吆喝?男村民回答,像是张石头。男村民没有回答错,确确实实是张石头。昨天,村民们集合起来,产生了村委会的正副村长、委员候选人,张金锁与白冰冰当选为村长候选人,张石头、杨大年当选副村长候选人。张石头与杨大年还当选为选举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主持换届选举。张石头的积极性飞跃般的高涨起来。从大喇叭里也可感到他不寻常的积极性。
朝戏楼下走来的男女村民越来越多。看来,不管是白发、不管是刚到有选举权的村民,人人满意自己当家作主,直选自己当家人——村委会的干部。谁也不像当社员的时候,听见队长吆喝上工,干一样的活儿,分一样的粮食,无所用心。谁也不可能间而单之,不用一番心思掂对过来又掂对过去。想想眼前,再想想长远。谁心里也不可能还没有底数。而谁也不肯露底。一红脸汉子边走边问一矮个后生:锉子,今儿个下哪位票啊?矮个后生说:“还不知道哪儿炕凉哪儿炕热哩。”大都随随便便的寒暄:“吃过啦?”“吃过啦。”“今儿个天气不赖。”“不赖,快小雪了,还这么暖和。”也有人嗓门挺高的亮出底牌:“今儿个,我们一家子全投张金锁的票。”亮出底牌的还不是一位两位。
老支书刘福福忽然从打麦场东南角露头,不声不响的同瞎子老人等坐在一起。他脸色不大好看。他东躲西藏,张石头始终未能见到他,张石头却扔给了他老伴五百块钱。这让他为难到家:给张石头送回,得罪了张石头,又得罪了张金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实在拉不下脸来;若投张金锁一票,又深感亏心,他已知张金锁在村里掌权的目的——个人暴富。他对张金锁的目的极为反感。五百块钱如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上,他不安的一夜没有合眼,到吃早饭的时候,一棵心还上上下下的颤抖。到了张石头在大喇叭里吆喝起来,他才朝自己碎了一口唾液,扇了自己一掌,痛骂了自己一声“窝囊”,咬紧牙齿定一定心,硬着头皮慢慢朝戏楼台下走来。
瞎子老人问田福福,张金锁露面没有哩?低着头的田福福抬头朝四下暸一暸,告诉瞎子老人张金锁还没到。瞎子老人再问田福福,杨大年、韩美凤露面没露面?田福福朝西北角上瞅一眼,告诉瞎子老人杨大年、韩美凤到啦。
杨大年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四、五个壮年汉子坐在一起。韩美凤坐在中年妇女堆里。二人都显得文雅安详,而心里并不娴静,他们都在担心,他们并不能如愿,张金锁会当选为村长。
瞎子老人再与田福福嘀咕:“田福福,白冰冰到没到?”田福福小声说:“看不见他在哪儿。”田福福,你估计估计今儿的戏……“田福福打断瞎子老人:别问啦,乡里领导干部和张金锁、张石头来啦。”
乡里两位干部与张金锁并驾齐驱从老槐树下朝会场走来。两位乡干部穿戴跟潮,白白净净的,气宇不凡,与张金锁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张金锁走在中间,张石头跟在张金锁身后。张金锁西服一身,皮鞋锃亮,脚步不快不慢,与两位干部走在一起,毫不逊色。坐在戏台西南角的十多位乡亲,见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走来,齐刷刷的站立起来,向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呈现热情,表示恭敬——笑呵呵地紧给张金锁与两位乡干部让路。一矮个子后生还满脸披笑地与张金锁握一握手。
白冰冰随后走来,他之穿扮神态与素常无别,原有衣裳,土气而不俗气。
选举进度甚快,主持选举的张石头请两位乡干部作了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后,就请两位竞选村长的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
“现在,我们首先请张金锁发表竞选演说。”张石头如在大喇叭里吆喝一样用力。吆喝毕,把张金锁推到台前。
“父老乡亲们,”张金锁成竹在胸,面目似笑非笑,神态谦和而又庄肃,语气平和而又激昂。“首先我实实在在地感谢父老乡亲们推选我做村长候选人。我当选不了村长,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父老乡亲们看得起我,给我面子。”他看一眼坐在主席台上的两位干部,“我要能得到大家信任,当选了村长,要听从乡里的领导,用毛主席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武装头脑。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绝不能让乡亲们老在温饱线上止步不前,争取在一两年之内,让槐树坡的面貌焕然一新:家家不再缺零花钱;住老房子的盖上新房;应该结婚的光棍娶上新娘;考上高中、大学的能交起学费。我请父老乡亲监督,我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父老乡亲们服务。我就说这么两句吧。不对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又是掌声又是笑声,相当的热烈。
“现在,我们再请白冰冰发表竞选演说。”张石头依然如在大喇叭里那样用力,他还特意的加一句。“请大家拍手欢迎。”
掌声没有张金锁的掌声热烈。
白冰冰慢步走上戏台。他面目平静,脚步轻松,无事人似的。而他的心里却挂着沉重。他不把当选不当选村长放在心上,他晓得当今钱的作用,他认为村里的两块印章定然落在张金锁手里。让他沉重的是:一,村里的两块印章落在张金锁手里以后,如何使张金锁独占南山的打算变为白日做梦;让张金锁的打算落空,并不是轻而易举。二,如何向蒋希文讨要百万欠款,摆脱欠朋友七十五万元的负担;向蒋希文讨要到百万欠款,撕破蒋希文政治骗子的假面具,更不容易。
张石头催促白冰冰发表竞选演说。
白冰冰心里并未装着现成的演说词儿。而他既然走上戏台上,立到了众乡亲们面前,就不能不随意的应酬两句:
“乡亲们:我朝戏台下来的时候,有人问我,白冰冰,今儿个你要登一登台,怎么也不包装包装?实话实说,我这黑脸儿,包装包装,也好看不了多少。”
台下有人哈哈大笑。
白冰冰继续应酬:“乡亲们:又有人问我白冰冰,你不包装包装,是不是不乐意当官儿?我实话实说,我没意当官儿。不是当初,当初,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我看自个儿亲了,怕落下不是,让人骂娘。”
白冰冰咳嗽两声,郑重其事:“乡亲们:如果大家还要我拉套,我就还拉。怎么拉哩?有人发现南山里储存着铁矿,我的主要精力就放铁矿开发上。怎么开发哩?简单明了:向华西、南街、刘庄学习,集体开发,共同富裕。绝不能让南山归了一家一户,富了一家一户。有人说,开采矿山,必须得有靠山:一要依靠当官儿的,得让当官儿的和黑社会头目入股,二要依靠黑社会,我说这是瞎子架电线——胡扯!我只想依靠槐树坡的乡亲们。绝不允许当官儿的和黑社会头目白白的入股,占乡亲们一分钱的便宜!我不再罗嗦了,就瞎说这么两句。”
掌声稀稀拉拉。也听不到一声笑声。只见瞎子老人与田福福嘀咕:“冰冰咋不多说两句哩……”
选举很快出现令人料想不到的情况:不少人支棱起耳朵朝前探头探脑;一些人站立起向前注目;有人自言自语地说怪;坐在戏台上的两位乡干部交头接耳;坐在戏台上的张石头瞪大两眼张开大口;同张石头坐在一个长凳上的张金锁,面色变得让人再认不出是他。
唱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中年妇女许是做姑娘的时候进过剧团,嗓音极为动听,吐字十分清楚,无一人说她把候选人的名字唱错。朝黑板上书写票数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认真负责,无一人怪他把票写错。开始,张金锁的票数高于白冰冰,而五十票之后,二人的票数开始相平,一百票之后张金锁落后于白冰冰。很快,张金锁的名字下不再增添一个“正”字,白冰冰的票数已达到三百零五票,超过了半数。
忽然间,台上台下,不管是乡里干部,不管是男女村民,人人惊心动魄:有的喊天!有的喊呀!有的伸头探脑。
坐在戏台上一条长凳上的张金锁,原本聚精会神的闻听唱票人唱出他的名字,全神贯注的注视他的每一张选票;选票,分明是他的财富,也是他的名誉、地位;他每多一张选票,他的目中多一分光芒,脸上即多一分亮色。他的票数与白冰冰票数相等之后,脸上少了亮色。白冰冰的票数增多到三百零五票,他的眼睛顿时白多黑少,翻了两翻,嘴唇颤栗,上身前后左右的摇晃摇晃,一下瘫倒在地下再站不起来。让人想不到是否还有一口气。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