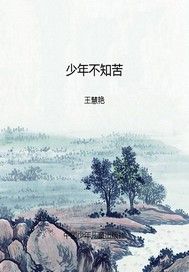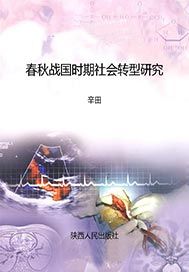第十三章 夫妻俩短兵相接
1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世间难有平静。
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阶级斗争天天抓月月抓,抓的人心慌以期、提心吊胆,谁都害怕高帽落在自己头上,自己敲打着锣鼓游街示众,被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家家难有平静,人人难有心安。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下马,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报纸上不见踪影,在人们的口上不再提起之后,流行的是开放搞活,致富不再为耻,发财成为光荣,人心飞腾,人人驱赶“穷鬼”,人人争取“光荣”,千方百计致富,不遗余力的竞争,无业无止,一天比一天激烈,很快市场上物资丰富,多数人家告别了难以告别的贫穷,吃饱穿暖。然而,不平静依旧存在。
槐树坡村最不平静最不和睦的是张金锁之家。张金锁心比天高,一心争取“光荣”,想拿村里两块印章,独揽村里党政大权,登上梦想的天堂。偏偏张金锁的妻子史梅梅就害怕张金锁心比天高,反对张金锁心中的“天堂”。原本夫妇俩先恋爱后结婚,情投意合:饭少了,史梅梅让张金锁吃足;衣服不足,史梅梅让张金锁穿暖。晚上,张金锁只要想夫妇之间床上的事情,不用言语,投给史梅梅一个眼神,或是朝史梅梅含情的微微一笑,史梅梅就要全力配合,让张金锁心满意足。近几天,夫妇俩争斗不是一次,一次比一次气高火旺,气高火旺的不再同屋同床,只差不吃一锅饭了。
张金锁的儿子拴虎已分家另过,二儿子拴猫跟姑姑生活在一起,张金锁的老院只是张金锁与妻子史梅梅居住。张金锁住在东厢房屋里,史梅梅住在老公公、老婆婆原居住的上房东屋。太阳已经落进西山,槐树坡村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出炊烟,呆在上房东屋里的史梅梅还没心思往厨房里点火。她坐在炕沿上,两只脚踩着地炉,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卡在腰里,黄乎乎的脸上冷冰冰的,薄薄的两片嘴唇干巴巴的圆圆的一对眼睛阴森森的。炕上的被褥枕头散散乱乱,屋地下左一片鸡毛右一片蒜皮。
“拴虎妈,天黑啦,该做饭啦!”张金锁又吆喝,并带出几分火气。
史梅梅心里说,你等着吧。她坐的稳实得如庙里的泥胎。
要说,史梅梅也算是个怪人,当今,只贪安然,只图自在,不想让丈夫贪官发财的少见,史梅梅可以算是羊群里的骆驼,史梅梅偏不认“骆驼”为奇,不怕人谈论她怪。
史梅梅之怪,就怪在她的娘家哥哥身上。史梅梅的娘家距县城很近。史梅梅的哥哥史海峰肚里有墨水,不是普通人物。史海峰原在县政府资料组里拿笑声,月薪六百多元,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恩恩爱爱,小日子美满而又幸福。社会上流行跑官卖官之后,史梅梅的哥哥史海峰不再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将与妻子的积蓄拿出,又向好友借得五万元,一锅抛出,到一个乡里接任了副乡长一职。他接着再攒钱,再去借,再抛出,一年半之后他升为乡长。而后他顺水推舟、轻车熟路,不休不止,两年之后,就在县里一个油水很大的局里坐了第一把交椅。农民春种秋收,史海峰也开始“秋收”。一贯谨小慎微的史梅梅苦口婆心的劝说哥哥,要谨慎小心,要脚步周正,要两袖清风,别胆大妄为,随意胡来,倒了跟头后悔就晚了。史海峰官大权力大之后,在恭维声中官气越来越足,不由自主的与父母的关系有了距离,妹子史梅梅在他眼里也就的藐小,不把史梅梅放在眼里,冷着脸硬邦邦的顶撞史梅梅:“不用为我担心,我心里底限清楚我会守住我的底限。”史梅梅心里的底限是四不:张手不收多,大吃不大喝,不忘常请客,跳舞不乱摸。“张手不收多”是一次只收五千元,县纪委有规定,受贿不过五千不立案查办。史海峰开始的确牢牢地盯着底限、守护着底限,张手不收多,大吃不大喝,不忘常请客,跳舞不乱摸。而不过一春一夏,他看到一位局长的住房已经增到七处,超过他四他,还被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他的底限就断然崩溃:来者不拒,七千八千也张手,一万两万也敢要;进酒家听歌跳舞,不仅乱摸,还要上床。他玩“三陪”还不满足,又养起一个号称“水仙花”的情妇。情妇胃口甚大,还公开张扬和他玩乐很体面。他害怕栽跟头身败名裂,与“水仙花”谈判断绝往来,水仙花提出要二十万现款和三室一厅住房。他说水仙花胃口太大,求水仙花降低要价,水仙花不干,与他大吵大闹。他失去冷静,扇水仙花一下耳光,水仙花就撕破脸皮,跑到县纪委揭发了他。县纪委负责人找到他谈话之后,他回到单位再看不到奉承的笑脸,听不到讨好的恭维,回家路上到一小酒馆里喝下半斤白酒,越过金光河大桥,一头扎下河里淹死。
史梅梅得到过哥哥史海峰特殊的关爱,与哥哥史海峰的感情极深。史海峰跳河一命呜乎时,史梅梅正巧来给父母上坟烧纸。她看到史海峰被人从河里捞出,疯跑到史海峰尸体前边,一声声地喊叫哥哥,哭得死去活来,差一点神经失常。
史梅梅哭着跟随灵车送哥哥往火葬场火化之后,与哥哥的情感难分难别,常常为哥哥叹息,为哥哥落泪,又不断念叨:人不能不知足,爬的高摔得重,老老实实在资料组里写材料,和嫂嫂过自己的小日子,吃的饱穿的暖,安安然然,自自在在,是多么地舒心,非要买官,非要贪权,官大了权大了,就要有人巴结,就要有人送红包。家家门前过,谁也躲不开,谁也难不伸手,伸了手,钱多了,就要进宾馆跑舞厅,养情妇玩三陪,自个儿把自个儿玩倒了……史梅梅看到丈夫张金锁一心想拿得村里两块印章当村官,就更为她哥哥叹息,更为她哥哥掉泪,更加念叨她的念不完的伤心经。
2
独自躲在东厢房屋里的张金锁,神色也不受看,胖乎乎的一张脸灰不溜溜的,平时亮晶晶的一双眼睛暗沉沉的,素常红润润的两片嘴唇干瘪瘪的,脑袋耷拉在胸前,稳坐在长沙发上动也不动。他朝史梅梅吆喝过天不早了,该做饭啦,听不到史梅梅回音,瞅不见史梅梅从上房屋里出来往小院厨房里点火,心里骂一声不是省油的灯,脸色越发难看。
张金锁本来心里不大宽松,出气儿不大畅顺。他遵着他的“高参”张石头“有钱买得鬼推磨”的高见,以钱为他的“心中的天堂”开路,信心下足地与张石头分头走访韩美凤与杨大年,他想用不了三言两语,只要把钱拿给韩美凤与杨大年,解决了二人的困难,他就会达到目的。他万万没有料到,韩美凤偏偏不做“鬼”,杨大年偏偏不“推磨”。他看到张石头不快的不畏人喊独眼龙,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歪着脖子“呸呸呸”地碎唾沫。他从韩美凤屋里碰了软钉子返回家,心里烦躁的深深浅浅地琢磨:他也许时运不佳,命里注定拿不到‘心中的天堂’,由命不由人,就服时运不佳,就认命里没有‘心中的天堂’,就不再一味地谋权求财。
大前天,张金锁往县城出售柿子,很快出手,而且卖得高价,五百斤柿子多得百元,心里畅快,将自行车存好,随意在城里转悠。他打听到县城新开业的绅士俱乐部是个吃喝玩乐的她去处,吃得、喝得、玩得、乐得为全县之首,无处可比。他拿定主意,豁出多破费几张钱票,进一进绅士俱乐部,开一开眼界,美滋滋地吃一口,痛痛快快得喝一杯。
他大摇大摆地走向异常豪华的绅士俱乐部,离人不用推拉就可进入的门外还有两三丈远,一个保安就冲到他脸前,伸开双臂威严地问他:“老憨,你干什么?”
他进城忘记穿套逛服,一身老式的退色衣服,一双老式的张口布鞋,使他土里土气,山民样儿十足。他就是穿身他认为可抬高身价的逛服,他也难让城里人不看他土气。时下,宾馆饭店的门口大都有保安守门,他见过不少保安,他不把保安看得多么高大,他与保安辩驳:
“你说话文明一点,本人有名有姓,不叫老憨。我想往绅士俱乐部里开开眼。”
“往山疙瘩上开眼去!”保安依旧把他看成老憨,“绅士俱乐部是你开眼的地方?”
他说:“我给钱。”
“给钱也不许你进去!走走走,快走!”一个怪模怪样的三陪小姐从出租车里走出,朝保安飞眼儿、大摇大摆地走过张金锁地脸前,保安急忙低头弯腰地送三陪小姐进入绅士俱乐部。
张金锁不再也保安斗气,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绅士俱乐部。一位离休干部告诉张金锁说,绅士俱乐部是掌权的官儿和有钱的款儿玩乐的地方,不是老百姓的去处。
张金锁继续在县城看红火瞧热闹,将要走到大众广场一角时,一只狮子形状的名犬突然扑到张金锁的面前,朝着张金锁就要咬,张金锁随手将烟尾抛在名犬脸上,烫的名犬一声声的哀叫。张金锁刚要走开,一个穿戴不凡的半大小子从一个胡同里窜出,气势汹汹地将张金锁拦住,愤怒地盯着张金锁,嚷道:“我的贝贝惹你啦?你用烟P股烫它?” 张金锁说:“它差点儿就咬着我,许你的狗随便咬人?”半大小子说:“你胡说八道,我就没看见我的贝贝咬你。” 张金锁想,和半大小子说不出高低,转身要走,半大小子又将张金锁拦住:“你不能白白的欺负我的贝贝,你得给它磕一个头才能走开。”七八个男女围观,无一人批评半大小子无礼。一位中年汉子迈着与众不同的脚步走来。他衣冠楚楚、大腹便便、整个人看上去颇有气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张金锁怎么和狗斗气?抱起贝贝将半大小子拉走。张金锁很快看出,抱走贝贝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必定是可进出绅士俱乐部的头面人物。他朝地下碎两口唾液,暗暗骂道:“他妈的,这可真是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没钱的爷爷是孙子了”气哼哼地走开。
张金锁气呼呼的返家,一路嘴不干净,骂了保安,又骂抱去狗的中年汉子。他回到家里,依旧咽不下在绅士俱乐部门前受的窝囊气,吞不下半大小子要他给狗叩头的侮辱,饭不想吃茶不想喝,“啪啪”地拍着茶几做出决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妻子怎样阻拦,也不能仍开谋权求财。
呆在东厢房屋里的张金锁脸上的不悦慢慢地有些收缩,目光也不再那么暗淡,头也渐渐抬高。他想没有必要和妻子史梅梅半斤八两,针尖对麦芒,吵吵闹闹,他要和史梅梅平心静气谈一谈,让史梅梅不再做他的绊脚石。他摇一摇手臂,抬一抬脚,松弛松弛,笑眯眯地走向上房东屋,与史梅梅和和气气:“拴虎妈,别寒眉冷眼的了,做饭去吧,吃过饭咱们和风细雨商量商量,谁对咱就听谁的。成不成?”
史梅梅也不乐意老和张金锁这么别扭,她见张金锁脸不阴沉、口气平和,跳动着的心立刻平稳:“我说拴虎爹,别急着吃饭,咱俩说出个上下,论出个高低,我再去点火。我和你说不到三句话,就和你敲鼓打锣,咚咚当当,让你心里说我是牛皮鼓、大铜鼓。我脾气不好,你甭和我一般见识……”
“拴虎妈,”张金锁打断史梅梅,“算你上我下你高我低,成不成?”
“话儿再好听,也不能吃不能喝,你甭拿话儿对付我,你说我上你下我高你低也不是你的心里话。”史梅梅不火不恼,离开炕沿,放到张金锁P股下一个凳子,再坐回到炕沿上,等张金锁坐下来,又和风细雨。“我没生拴虎那几年,咱们不盼别的,只盼顿顿吃细(粮),现在咱们天天三顿细(粮),夏天不缺单的,冬天不少棉的,银行里有了存款,可是说是我们都盼到了,拴虎和他媳妇儿又孝顺,又不叫爹娘着急,谁不说咱两口子凳子好有福,谁不眼热咱们的好日子。你还一个心眼儿的谋算着当村里的头头干什么?眼前,不是行批斗行戴高帽的时候,当头头的吆喝甚就是甚,谁也不说三道四冒凉腔。现时,你拉选票,叫他选你当头儿,你得满足他的利益。是不是?”张金锁刚要插话,“你先别插话,狗吃不了日头,我说完了你再说。”史梅梅忙喘一口气,再咽一口唾沫。润一润嗓子。“我说到哪儿啦?噢,我说到你能满足他的利益吗?他说他要违背计划生育,要让他老婆生三个生四个,你能满足吗?还有人要求你卖了他的责任田进城做买卖,你能满足他吗?有人胡作非为犯了法,要你当保护伞,你能满足他吗?多啦!多啦!你满足不了他,就把他得罪啦,翻过脸来报复你:也许把你的树砍了;也许把你的菜毁了;也许往你的猪槽里扔包耗子药;也许到了大年初一早晨,朝你的门外倒桶尿,往你的门上刷满屎。自己过得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快快活活的,找那不自在干什么?”史梅梅的未句说得包火又包气,如木柴断折一样脆生。
张金锁够沉得住气,坐得稳稳当当。一会儿,他跷起二郎腿,眯缝着的两只眼睛睁开,做出笑脸,提起凳子再挨近史梅梅一步,语气温和的赛过春风:“拴虎妈,我和你说了不是一回,我想在村里掌权的目的是:我在村南荒沟野洼里发现了大量的铁矿石,把大师的铁矿石开挖出来,我们的存款可就不是千儿八百万了。可是,只有当了村支书,当了村长,拿到了村里的两块印章,握死了村里的党政大权,自己说一不二,把集体的荒沟野洼买到自己手里,铁矿石才能全部归了自己。”
“咱们发那么大的财干什么?花得了吗?”
“你……你小寡妇讨饭——太死心眼!”张金锁脑袋歪在一个肩膀上,看着史梅梅,“你头脑里只有钱票没有政治,现在是允许个人发财,鼓励个人发财,发的财越大,地位就越高,脸面就越大。咱们只要把咱村的铁矿石搂到手里,咱政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了。哈哈哈,咱就抖起来了……”
“瞧你越说越美得不是你啦!”史梅梅的脸上早已漏气,她气呼呼的白张金锁一眼,“我死也不赞成你一步登天抖起来。人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一模一样;地位一高就牛气,钱财一多脸就变。你拴虎爹心里也不是没有我哥哥,我哥哥在县政府资料组当一般干部的时候,可老百姓啦,村里人们都夸他老百姓。他见人跑官买官,他也不再安分守已,买得官大了,受贿钱多了,就不老百姓了,就花天酒地,就找三陪、养情妇,落个身败名裂跳河淹死,惨也不惨?……”
“我不是你哥哥!”张金锁与史梅梅短兵相接。
“你也不是不吃腥的猫,你要不要把你的歪心收拾到篮篮儿里,你也许比我哥哥落得还惨!”史梅梅寸步不让,火气越来越盛,劲头儿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粗,声音越来越高。“你一口把集体的铁矿石独吞了,你富得花天酒地,村里老百姓年老的有病没钱进不了医院,考上高中、大学的孩子没钱念不了书,人们能和你善罢甘休?”
“国家宪法为私营经济开窗户、靠梯子、放绿灯,个人发多大的财别人红眼也白红眼。何况现在讲团结、讲稳定,谁不善罢甘休,谁就是屎壳郎掉进尿缸里——自找倒霉!” 张金锁狠喘一口气,耐心失尽,对史梅梅下最后通谍。“我和你把话说绝,你要老不开窍和我死巴巴的咬着狗屎橛子当香蕉,我和你就只有一条道走!”
“一条什么道?”
“孟良摔葫芦——散伙!”
“嗬嗬,你甭拿孟良吓唬我,我是钟楼上的雀——耐惊耐吓。”史梅梅冷冷地笑笑。“拴虎妈是个铁葫芦,不是你想摔就能摔的!……”
“噢呦呦,你们快把屋顶吵塌了,吃饱撑的!”张石头睁着一双大眼突然闯进屋里来,伸手拉起张金锁,“走走走,我那儿有人等着你回话。”硬把张金锁拉走。
3
张石头家里只有张石头在家,张石头一口气把张金锁拉到他的屋里,让张金锁在挨着桌子的坐柜上坐下来,埋怨张金锁:“你能和她争论出高低上下,把她搁在一边,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张石头递给张金锁一杯白开水再张口:“我告诉你说,白冰冰回来了。”张金锁习惯眯缝着的两只眼睛紧睁开,忙问张石头:“他找到没找到大眼儿?”张石头说:“没见到他,我是听别人说他回村来了。他许是找到大眼。我拉你来,重要问题不是他找到找不到大眼,是个奇闻!” 张金锁问张石头什么奇闻?张石头神秘的笑笑叫张金锁猜一猜。张金锁眯缝着眼睛停一停说猜不着。张石头嗬嗬嗬地笑笑,才脑袋伸到张金锁面前,字字清楚的说:
“莫说你猜不着,你这哥要得不到准确信息,你这哥也猜不着。白冰冰并没有拿到凤凰岭教育基地的百万欠款……”
“他付给大家的欠款是哪儿来的?”张金锁奇怪的瞪着俩眼插话。
“他拿出了他的二十五万积蓄,又向他的一个朋友借了七十五万。”张石头得意的笑笑,“金锁,你说他白冰冰拿出自个儿的积蓄,又找别人借款,付给打工户们工钱是为了甚?”
“我不如你高明,你说说看。”张金锁谦虚的说。
“首先说,”张石头自豪的挽一挽衣袖,我当初说他白冰冰往凤凰岭去要帐会白跑,我不是放空炮。白冰冰动自己的积蓄,找旁人借款,付给打工户们欠款,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怕在乡亲们面前栽面儿,为的是给自己涂脂抹粉。他自认他自己高明,让大家夸他有人缘,实际上他走的是一步臭棋——欠人的七十五万拴住了他的手脚;他就是有意和你竞争当选支书、村长,他也无能为力了。
张金锁不哼不哈,一对灵活的目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转一转才问张石头:“石头哥,你说冰冰姐夫拿出了他的积蓄,又找人借了七十五万,付给了打工户们是真的?”
“你觉着奇是不是?”张石头睁着一只眼睛问张金锁。
“奇!”
“谁也不会说不奇。可你石头哥的嘴不是乌鸦嘴——瞎呱呱。五里坡镇信用社主任亲口同我说白冰冰取走了他的积蓄。我往县城卖花生,碰上了白冰冰的好友武不强,我和武不强也有交往。武不强与我聊起他和白冰冰的友谊,聊着聊着就把白冰冰朝他借去七十五万说给了我。白冰冰成了咱村最大的欠债户,可以说是铁板上钉钉。你想他扛上七十五万欠款还不把他扛垮了?……”
“你石头哥不愧比我高明,你说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回头我要去和冰冰姐夫坐一坐,聊一聊。”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世间难有平静。
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阶级斗争天天抓月月抓,抓的人心慌以期、提心吊胆,谁都害怕高帽落在自己头上,自己敲打着锣鼓游街示众,被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家家难有平静,人人难有心安。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下马,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报纸上不见踪影,在人们的口上不再提起之后,流行的是开放搞活,致富不再为耻,发财成为光荣,人心飞腾,人人驱赶“穷鬼”,人人争取“光荣”,千方百计致富,不遗余力的竞争,无业无止,一天比一天激烈,很快市场上物资丰富,多数人家告别了难以告别的贫穷,吃饱穿暖。然而,不平静依旧存在。
槐树坡村最不平静最不和睦的是张金锁之家。张金锁心比天高,一心争取“光荣”,想拿村里两块印章,独揽村里党政大权,登上梦想的天堂。偏偏张金锁的妻子史梅梅就害怕张金锁心比天高,反对张金锁心中的“天堂”。原本夫妇俩先恋爱后结婚,情投意合:饭少了,史梅梅让张金锁吃足;衣服不足,史梅梅让张金锁穿暖。晚上,张金锁只要想夫妇之间床上的事情,不用言语,投给史梅梅一个眼神,或是朝史梅梅含情的微微一笑,史梅梅就要全力配合,让张金锁心满意足。近几天,夫妇俩争斗不是一次,一次比一次气高火旺,气高火旺的不再同屋同床,只差不吃一锅饭了。
张金锁的儿子拴虎已分家另过,二儿子拴猫跟姑姑生活在一起,张金锁的老院只是张金锁与妻子史梅梅居住。张金锁住在东厢房屋里,史梅梅住在老公公、老婆婆原居住的上房东屋。太阳已经落进西山,槐树坡村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出炊烟,呆在上房东屋里的史梅梅还没心思往厨房里点火。她坐在炕沿上,两只脚踩着地炉,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卡在腰里,黄乎乎的脸上冷冰冰的,薄薄的两片嘴唇干巴巴的圆圆的一对眼睛阴森森的。炕上的被褥枕头散散乱乱,屋地下左一片鸡毛右一片蒜皮。
“拴虎妈,天黑啦,该做饭啦!”张金锁又吆喝,并带出几分火气。
史梅梅心里说,你等着吧。她坐的稳实得如庙里的泥胎。
要说,史梅梅也算是个怪人,当今,只贪安然,只图自在,不想让丈夫贪官发财的少见,史梅梅可以算是羊群里的骆驼,史梅梅偏不认“骆驼”为奇,不怕人谈论她怪。
史梅梅之怪,就怪在她的娘家哥哥身上。史梅梅的娘家距县城很近。史梅梅的哥哥史海峰肚里有墨水,不是普通人物。史海峰原在县政府资料组里拿笑声,月薪六百多元,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恩恩爱爱,小日子美满而又幸福。社会上流行跑官卖官之后,史梅梅的哥哥史海峰不再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将与妻子的积蓄拿出,又向好友借得五万元,一锅抛出,到一个乡里接任了副乡长一职。他接着再攒钱,再去借,再抛出,一年半之后他升为乡长。而后他顺水推舟、轻车熟路,不休不止,两年之后,就在县里一个油水很大的局里坐了第一把交椅。农民春种秋收,史海峰也开始“秋收”。一贯谨小慎微的史梅梅苦口婆心的劝说哥哥,要谨慎小心,要脚步周正,要两袖清风,别胆大妄为,随意胡来,倒了跟头后悔就晚了。史海峰官大权力大之后,在恭维声中官气越来越足,不由自主的与父母的关系有了距离,妹子史梅梅在他眼里也就的藐小,不把史梅梅放在眼里,冷着脸硬邦邦的顶撞史梅梅:“不用为我担心,我心里底限清楚我会守住我的底限。”史梅梅心里的底限是四不:张手不收多,大吃不大喝,不忘常请客,跳舞不乱摸。“张手不收多”是一次只收五千元,县纪委有规定,受贿不过五千不立案查办。史海峰开始的确牢牢地盯着底限、守护着底限,张手不收多,大吃不大喝,不忘常请客,跳舞不乱摸。而不过一春一夏,他看到一位局长的住房已经增到七处,超过他四他,还被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他的底限就断然崩溃:来者不拒,七千八千也张手,一万两万也敢要;进酒家听歌跳舞,不仅乱摸,还要上床。他玩“三陪”还不满足,又养起一个号称“水仙花”的情妇。情妇胃口甚大,还公开张扬和他玩乐很体面。他害怕栽跟头身败名裂,与“水仙花”谈判断绝往来,水仙花提出要二十万现款和三室一厅住房。他说水仙花胃口太大,求水仙花降低要价,水仙花不干,与他大吵大闹。他失去冷静,扇水仙花一下耳光,水仙花就撕破脸皮,跑到县纪委揭发了他。县纪委负责人找到他谈话之后,他回到单位再看不到奉承的笑脸,听不到讨好的恭维,回家路上到一小酒馆里喝下半斤白酒,越过金光河大桥,一头扎下河里淹死。
史梅梅得到过哥哥史海峰特殊的关爱,与哥哥史海峰的感情极深。史海峰跳河一命呜乎时,史梅梅正巧来给父母上坟烧纸。她看到史海峰被人从河里捞出,疯跑到史海峰尸体前边,一声声地喊叫哥哥,哭得死去活来,差一点神经失常。
史梅梅哭着跟随灵车送哥哥往火葬场火化之后,与哥哥的情感难分难别,常常为哥哥叹息,为哥哥落泪,又不断念叨:人不能不知足,爬的高摔得重,老老实实在资料组里写材料,和嫂嫂过自己的小日子,吃的饱穿的暖,安安然然,自自在在,是多么地舒心,非要买官,非要贪权,官大了权大了,就要有人巴结,就要有人送红包。家家门前过,谁也躲不开,谁也难不伸手,伸了手,钱多了,就要进宾馆跑舞厅,养情妇玩三陪,自个儿把自个儿玩倒了……史梅梅看到丈夫张金锁一心想拿得村里两块印章当村官,就更为她哥哥叹息,更为她哥哥掉泪,更加念叨她的念不完的伤心经。
2
独自躲在东厢房屋里的张金锁,神色也不受看,胖乎乎的一张脸灰不溜溜的,平时亮晶晶的一双眼睛暗沉沉的,素常红润润的两片嘴唇干瘪瘪的,脑袋耷拉在胸前,稳坐在长沙发上动也不动。他朝史梅梅吆喝过天不早了,该做饭啦,听不到史梅梅回音,瞅不见史梅梅从上房屋里出来往小院厨房里点火,心里骂一声不是省油的灯,脸色越发难看。
张金锁本来心里不大宽松,出气儿不大畅顺。他遵着他的“高参”张石头“有钱买得鬼推磨”的高见,以钱为他的“心中的天堂”开路,信心下足地与张石头分头走访韩美凤与杨大年,他想用不了三言两语,只要把钱拿给韩美凤与杨大年,解决了二人的困难,他就会达到目的。他万万没有料到,韩美凤偏偏不做“鬼”,杨大年偏偏不“推磨”。他看到张石头不快的不畏人喊独眼龙,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歪着脖子“呸呸呸”地碎唾沫。他从韩美凤屋里碰了软钉子返回家,心里烦躁的深深浅浅地琢磨:他也许时运不佳,命里注定拿不到‘心中的天堂’,由命不由人,就服时运不佳,就认命里没有‘心中的天堂’,就不再一味地谋权求财。
大前天,张金锁往县城出售柿子,很快出手,而且卖得高价,五百斤柿子多得百元,心里畅快,将自行车存好,随意在城里转悠。他打听到县城新开业的绅士俱乐部是个吃喝玩乐的她去处,吃得、喝得、玩得、乐得为全县之首,无处可比。他拿定主意,豁出多破费几张钱票,进一进绅士俱乐部,开一开眼界,美滋滋地吃一口,痛痛快快得喝一杯。
他大摇大摆地走向异常豪华的绅士俱乐部,离人不用推拉就可进入的门外还有两三丈远,一个保安就冲到他脸前,伸开双臂威严地问他:“老憨,你干什么?”
他进城忘记穿套逛服,一身老式的退色衣服,一双老式的张口布鞋,使他土里土气,山民样儿十足。他就是穿身他认为可抬高身价的逛服,他也难让城里人不看他土气。时下,宾馆饭店的门口大都有保安守门,他见过不少保安,他不把保安看得多么高大,他与保安辩驳:
“你说话文明一点,本人有名有姓,不叫老憨。我想往绅士俱乐部里开开眼。”
“往山疙瘩上开眼去!”保安依旧把他看成老憨,“绅士俱乐部是你开眼的地方?”
他说:“我给钱。”
“给钱也不许你进去!走走走,快走!”一个怪模怪样的三陪小姐从出租车里走出,朝保安飞眼儿、大摇大摆地走过张金锁地脸前,保安急忙低头弯腰地送三陪小姐进入绅士俱乐部。
张金锁不再也保安斗气,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绅士俱乐部。一位离休干部告诉张金锁说,绅士俱乐部是掌权的官儿和有钱的款儿玩乐的地方,不是老百姓的去处。
张金锁继续在县城看红火瞧热闹,将要走到大众广场一角时,一只狮子形状的名犬突然扑到张金锁的面前,朝着张金锁就要咬,张金锁随手将烟尾抛在名犬脸上,烫的名犬一声声的哀叫。张金锁刚要走开,一个穿戴不凡的半大小子从一个胡同里窜出,气势汹汹地将张金锁拦住,愤怒地盯着张金锁,嚷道:“我的贝贝惹你啦?你用烟P股烫它?” 张金锁说:“它差点儿就咬着我,许你的狗随便咬人?”半大小子说:“你胡说八道,我就没看见我的贝贝咬你。” 张金锁想,和半大小子说不出高低,转身要走,半大小子又将张金锁拦住:“你不能白白的欺负我的贝贝,你得给它磕一个头才能走开。”七八个男女围观,无一人批评半大小子无礼。一位中年汉子迈着与众不同的脚步走来。他衣冠楚楚、大腹便便、整个人看上去颇有气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张金锁怎么和狗斗气?抱起贝贝将半大小子拉走。张金锁很快看出,抱走贝贝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必定是可进出绅士俱乐部的头面人物。他朝地下碎两口唾液,暗暗骂道:“他妈的,这可真是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没钱的爷爷是孙子了”气哼哼地走开。
张金锁气呼呼的返家,一路嘴不干净,骂了保安,又骂抱去狗的中年汉子。他回到家里,依旧咽不下在绅士俱乐部门前受的窝囊气,吞不下半大小子要他给狗叩头的侮辱,饭不想吃茶不想喝,“啪啪”地拍着茶几做出决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妻子怎样阻拦,也不能仍开谋权求财。
呆在东厢房屋里的张金锁脸上的不悦慢慢地有些收缩,目光也不再那么暗淡,头也渐渐抬高。他想没有必要和妻子史梅梅半斤八两,针尖对麦芒,吵吵闹闹,他要和史梅梅平心静气谈一谈,让史梅梅不再做他的绊脚石。他摇一摇手臂,抬一抬脚,松弛松弛,笑眯眯地走向上房东屋,与史梅梅和和气气:“拴虎妈,别寒眉冷眼的了,做饭去吧,吃过饭咱们和风细雨商量商量,谁对咱就听谁的。成不成?”
史梅梅也不乐意老和张金锁这么别扭,她见张金锁脸不阴沉、口气平和,跳动着的心立刻平稳:“我说拴虎爹,别急着吃饭,咱俩说出个上下,论出个高低,我再去点火。我和你说不到三句话,就和你敲鼓打锣,咚咚当当,让你心里说我是牛皮鼓、大铜鼓。我脾气不好,你甭和我一般见识……”
“拴虎妈,”张金锁打断史梅梅,“算你上我下你高我低,成不成?”
“话儿再好听,也不能吃不能喝,你甭拿话儿对付我,你说我上你下我高你低也不是你的心里话。”史梅梅不火不恼,离开炕沿,放到张金锁P股下一个凳子,再坐回到炕沿上,等张金锁坐下来,又和风细雨。“我没生拴虎那几年,咱们不盼别的,只盼顿顿吃细(粮),现在咱们天天三顿细(粮),夏天不缺单的,冬天不少棉的,银行里有了存款,可是说是我们都盼到了,拴虎和他媳妇儿又孝顺,又不叫爹娘着急,谁不说咱两口子凳子好有福,谁不眼热咱们的好日子。你还一个心眼儿的谋算着当村里的头头干什么?眼前,不是行批斗行戴高帽的时候,当头头的吆喝甚就是甚,谁也不说三道四冒凉腔。现时,你拉选票,叫他选你当头儿,你得满足他的利益。是不是?”张金锁刚要插话,“你先别插话,狗吃不了日头,我说完了你再说。”史梅梅忙喘一口气,再咽一口唾沫。润一润嗓子。“我说到哪儿啦?噢,我说到你能满足他的利益吗?他说他要违背计划生育,要让他老婆生三个生四个,你能满足吗?还有人要求你卖了他的责任田进城做买卖,你能满足他吗?有人胡作非为犯了法,要你当保护伞,你能满足他吗?多啦!多啦!你满足不了他,就把他得罪啦,翻过脸来报复你:也许把你的树砍了;也许把你的菜毁了;也许往你的猪槽里扔包耗子药;也许到了大年初一早晨,朝你的门外倒桶尿,往你的门上刷满屎。自己过得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快快活活的,找那不自在干什么?”史梅梅的未句说得包火又包气,如木柴断折一样脆生。
张金锁够沉得住气,坐得稳稳当当。一会儿,他跷起二郎腿,眯缝着的两只眼睛睁开,做出笑脸,提起凳子再挨近史梅梅一步,语气温和的赛过春风:“拴虎妈,我和你说了不是一回,我想在村里掌权的目的是:我在村南荒沟野洼里发现了大量的铁矿石,把大师的铁矿石开挖出来,我们的存款可就不是千儿八百万了。可是,只有当了村支书,当了村长,拿到了村里的两块印章,握死了村里的党政大权,自己说一不二,把集体的荒沟野洼买到自己手里,铁矿石才能全部归了自己。”
“咱们发那么大的财干什么?花得了吗?”
“你……你小寡妇讨饭——太死心眼!”张金锁脑袋歪在一个肩膀上,看着史梅梅,“你头脑里只有钱票没有政治,现在是允许个人发财,鼓励个人发财,发的财越大,地位就越高,脸面就越大。咱们只要把咱村的铁矿石搂到手里,咱政治上就算是一步登天了。哈哈哈,咱就抖起来了……”
“瞧你越说越美得不是你啦!”史梅梅的脸上早已漏气,她气呼呼的白张金锁一眼,“我死也不赞成你一步登天抖起来。人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一模一样;地位一高就牛气,钱财一多脸就变。你拴虎爹心里也不是没有我哥哥,我哥哥在县政府资料组当一般干部的时候,可老百姓啦,村里人们都夸他老百姓。他见人跑官买官,他也不再安分守已,买得官大了,受贿钱多了,就不老百姓了,就花天酒地,就找三陪、养情妇,落个身败名裂跳河淹死,惨也不惨?……”
“我不是你哥哥!”张金锁与史梅梅短兵相接。
“你也不是不吃腥的猫,你要不要把你的歪心收拾到篮篮儿里,你也许比我哥哥落得还惨!”史梅梅寸步不让,火气越来越盛,劲头儿越来越大,嗓门越来越粗,声音越来越高。“你一口把集体的铁矿石独吞了,你富得花天酒地,村里老百姓年老的有病没钱进不了医院,考上高中、大学的孩子没钱念不了书,人们能和你善罢甘休?”
“国家宪法为私营经济开窗户、靠梯子、放绿灯,个人发多大的财别人红眼也白红眼。何况现在讲团结、讲稳定,谁不善罢甘休,谁就是屎壳郎掉进尿缸里——自找倒霉!” 张金锁狠喘一口气,耐心失尽,对史梅梅下最后通谍。“我和你把话说绝,你要老不开窍和我死巴巴的咬着狗屎橛子当香蕉,我和你就只有一条道走!”
“一条什么道?”
“孟良摔葫芦——散伙!”
“嗬嗬,你甭拿孟良吓唬我,我是钟楼上的雀——耐惊耐吓。”史梅梅冷冷地笑笑。“拴虎妈是个铁葫芦,不是你想摔就能摔的!……”
“噢呦呦,你们快把屋顶吵塌了,吃饱撑的!”张石头睁着一双大眼突然闯进屋里来,伸手拉起张金锁,“走走走,我那儿有人等着你回话。”硬把张金锁拉走。
3
张石头家里只有张石头在家,张石头一口气把张金锁拉到他的屋里,让张金锁在挨着桌子的坐柜上坐下来,埋怨张金锁:“你能和她争论出高低上下,把她搁在一边,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张石头递给张金锁一杯白开水再张口:“我告诉你说,白冰冰回来了。”张金锁习惯眯缝着的两只眼睛紧睁开,忙问张石头:“他找到没找到大眼儿?”张石头说:“没见到他,我是听别人说他回村来了。他许是找到大眼。我拉你来,重要问题不是他找到找不到大眼,是个奇闻!” 张金锁问张石头什么奇闻?张石头神秘的笑笑叫张金锁猜一猜。张金锁眯缝着眼睛停一停说猜不着。张石头嗬嗬嗬地笑笑,才脑袋伸到张金锁面前,字字清楚的说:
“莫说你猜不着,你这哥要得不到准确信息,你这哥也猜不着。白冰冰并没有拿到凤凰岭教育基地的百万欠款……”
“他付给大家的欠款是哪儿来的?”张金锁奇怪的瞪着俩眼插话。
“他拿出了他的二十五万积蓄,又向他的一个朋友借了七十五万。”张石头得意的笑笑,“金锁,你说他白冰冰拿出自个儿的积蓄,又找别人借款,付给打工户们工钱是为了甚?”
“我不如你高明,你说说看。”张金锁谦虚的说。
“首先说,”张石头自豪的挽一挽衣袖,我当初说他白冰冰往凤凰岭去要帐会白跑,我不是放空炮。白冰冰动自己的积蓄,找旁人借款,付给打工户们欠款,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怕在乡亲们面前栽面儿,为的是给自己涂脂抹粉。他自认他自己高明,让大家夸他有人缘,实际上他走的是一步臭棋——欠人的七十五万拴住了他的手脚;他就是有意和你竞争当选支书、村长,他也无能为力了。
张金锁不哼不哈,一对灵活的目珠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转一转才问张石头:“石头哥,你说冰冰姐夫拿出了他的积蓄,又找人借了七十五万,付给了打工户们是真的?”
“你觉着奇是不是?”张石头睁着一只眼睛问张金锁。
“奇!”
“谁也不会说不奇。可你石头哥的嘴不是乌鸦嘴——瞎呱呱。五里坡镇信用社主任亲口同我说白冰冰取走了他的积蓄。我往县城卖花生,碰上了白冰冰的好友武不强,我和武不强也有交往。武不强与我聊起他和白冰冰的友谊,聊着聊着就把白冰冰朝他借去七十五万说给了我。白冰冰成了咱村最大的欠债户,可以说是铁板上钉钉。你想他扛上七十五万欠款还不把他扛垮了?……”
“你石头哥不愧比我高明,你说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回头我要去和冰冰姐夫坐一坐,聊一聊。”
-
更多
编辑推荐
- 1一分钟心理控制术
- 2赢利型股民、基民必备全书
- 3人人都爱心理学:最妙...
- 4看图炒股
- 5一看就懂的股市赚钱图形
- 6基金投资最常遇到的1...
- 7买基金、炒股票就这几招
- 8明明白白买基金、炒股票
- 9新手上路 实战股市
- 10少年不知愁
看过本书的人还看过